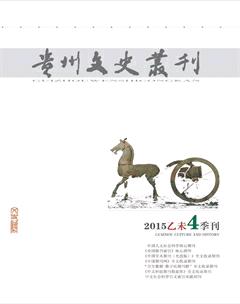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
羅夕 史義銀
摘 要:西方的中國形象伴隨著中西關系的變化而不斷發生改變,“他者的意象”往往難免“在他自己的心靈中重新思想它們”的思想史痕跡,對中國的“美化”和“丑化”既有其客觀觀感,也有其主觀臆測。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無疑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重要構成部分,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群體進行研究是區別于傳統個案研究的新路徑和新嘗試。晚清西方來華女性不同的社會身份、政治背景、個人經歷及其教育程度等,使得她們的對華觀感異彩紛呈。通過探究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不僅可以厘清西方晚清來華男女關于中國觀感的差異、歸納出西方來華女性群體中觀感的差異,而且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并豐富了西方的中國形象,對西方外交政策的執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而在近代中外關系史上譜寫了獨特的篇章,對今天正確認識和處理中西關系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晚清 中西關系 西方的中國形象 西方來華女性 外交官夫人
中圖分類號:K825.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5)04-87-92
晚清,中國在經歷“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過程中被動地融入當時的世界體系,伴隨著列強的“堅船利炮”而來的還有日益“東漸”的“西學”,這些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來華西人主要由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員等組成,他們打量這塊古老而陌生的國度,撰寫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文字著述。在晚清來華西人中,西方來華女性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不僅在其中占較大的比例,而且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個性,使得她們的對華觀感既有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共性特征,又有區別于整個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個性特征。
當時,晚清來華的外交官夫人曾自行形成一個團體。又因這些外交官夫人在晚清來華婦女中處于較高等的地位,相對于漂洋過海且社會地位不高的西方商人妻子、女旅行家來說,晚清來華外交官以及其夫人在中國享受到了中國上層官僚極好的待遇,此外,外交官夫人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水平及交際圈多優于其他來華婦女,所以外交官夫人的著作也自有其特點,值得將其單獨研究。應該看到,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以其女性獨特的視角以及社會地位捕捉晚清社會的方方面面,故它們不僅成為西方的中國形象的重要組成部份,而且也是晚清“大變局”的歷史見證。
對晚清西方來華女性特別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進行研究,學界鮮有涉及,偶有涉獵者也多就某個具體的西方來華女性或其著述進行一般性的介紹與評述,未將其從總體上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來進行研究,因而,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1〕根據這些晚清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信札、游記、回憶錄等著述,對這樣一個特殊群體的中國觀感進行初步的探討,分析其中國觀感的特征,厘清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和西方的中國形象之關系,并試圖揭示其中國觀感對西方以及中國的影響,相應的,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視到西方國家對晚清的外交政策執行情況。
一、晚清西方外交官夫人的來華開端
清代初、中期,清政府為減少西方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曾制定一系列法規,嚴厲禁止西方商人攜女眷來華。隨著中西力量對比西方力量逐漸顯示優勢之時,清政府對這些條例的執行逐漸松動。《南京條約》談判期間,英方談判代表璞鼎查曾將此作為重要問題與清政府進行交涉,條約第二款明確規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2〕使原先的禁令難以持續。此后《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亦作出類似規定,但后兩個條約中準許他們在通商口岸建造“禮拜堂”的規定,將此前《南京條約》中的“家眷”范圍進行了擴展和延伸,使西方的女傳教士和修女們也可以來中國。之后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的沿海和內陸城市越來越多,西方來華女性日益增多,她們大批進至中國的城市生活和居住,個別女性還進入城市周邊的鄉村并開始與中國人進行接觸,西方婦女大規模來華的狀況已成事實。〔3〕
外交官夫人相比晚清來華婦女中的女傳教士等群體來華稍遲一些。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公使以“開戰入京”的條件威脅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其中規定:“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大清、大英兩國京師。”明確規定英國公使及其眷屬可在京城長期居住或隨時往來。隨后的《北京條約》肯定了《天津條約》的內容,西方國家的公使開始陸續來到北京。在簽訂《天津條約》以前,雖有西方使節來訪,但是由于無法在中國常駐,所以這些早期出使的使者們基本上都沒有攜帶家眷。是產生于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天津條約》使得西方更易執行其外交政策,開始派出職業外交官并允許攜帶家眷常駐。
各國外交官家眷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的妻子薩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德國駐華公使海靖的妻子伊麗莎白·馮·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英國公使休·福冉瑟的妻子瑪麗·福冉瑟(Mary Crawford Fraser)、英國駐喀什噶爾總領事喬治·馬嘎特尼的妻子凱瑟琳·馬嘎特尼(Lady Macartney),奧地利公使訥色恩夫人(Paula von Rosthorn)。其中,1898-1904年,康格夫人隨丈夫出使中國,在北京生活了七年,親自經歷了“庚子之變”中的使館被圍。她與美國國內親友書信后被輯為《北京信札——特別是關于慈禧太后和中國婦女》,其收錄了康格夫人寫給親朋好友的八十封書信,她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記錄下來的北京風貌,往往是同時代來華者所看不到和無法記錄的。而尤其難得的是,康格夫人較其他駐華公使來講,始終抱有非一般的同情與理解。海靖夫人出生于普魯士王國的一個貴族家庭,其丈夫埃德勒曾是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二人感情破裂后她和埃德勒的學友海靖男爵一見鐘情,欲與海德勒離婚遭拒,海德勒自殺后,她不顧家庭和世俗的偏見堅決和海靖結合,此后和海靖一起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駐外生活。1896年到達中國,1899年離開中國,其所著《德國公使夫人日記》中記述了海靖夫婦在中國的見聞和作為。
瑪麗·福冉瑟于1851年出生在意大利,曾在塞維爾姐妹開辦的女子寄宿學校中接受教育。她與休.福冉瑟于1874年結婚并隨著她的外交官丈夫出訪了北京、越南、羅馬、圣地亞哥與東京。她的丈夫死于1894年。她曾將自己的經歷寫成多本著作,其中《外交官夫人出訪記》記載了她到北京的所見所感。
凱瑟琳·馬嘎特尼(1877-1949),出生于蘇格蘭,是第一任英國駐喀什噶爾總領事喬治·馬嘎特尼的妻子,二十一歲時隨其丈夫到達中國新疆喀什噶爾,居住在英國駐當地領事館中。她在喀什噶爾生活了十七年,耳聞目睹了喀什噶爾的紛繁變遷和各種人事,是那個地方和那段歷史的見證人。她所著《一個外交官夫人對喀什噶爾的回憶》,當系研究西域探險史的寶貴資料。
訥色恩夫人于1873年生,出生在維也納的一個醫生家庭,也是訥色恩的遠方親戚。兩人于1895年結婚。后與丈夫來到北京,居住在“玫瑰別墅”中。她的丈夫訥色恩于1895年成為奧匈帝國駐華臨時代辦,為公使館的實際領導人。訥色恩于1917年回國后,撰寫了大量的關于中國的著作,如《中國人的社會》《中國歷史》《中國的考古學研究》等。
二.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外交官夫人來華的高峰期,許多外交官夫人曾親歷了諸如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等晚清中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她們把對中華文明的驚嘆與好奇、對晚清人民的憐憫與悲哀、對家鄉的眷戀與牽掛、對中國社會的偏見與傲慢、對本國政府對華外交的配合與支持等情感揉合在一起,形成了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最先觀察的是中國的景色、風俗人情,然后逐步深入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并開始思考這一切發生的原因,她們對中國的觀感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中國自然風光與城市環境建設的最初印象與反映
晚清來華外交官夫人的著作中大都贊美了中國的自然風光。即使是始終對中國懷有較強敵意的海靖夫人也陶醉于長江兩岸的風景,她從長江下游上溯游歷的第一天,就用她的畫筆留下了江陰“異常秀美”的景色。〔4〕她對漢口的印象遠超想象,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中國”〔5〕。除此之外,她們也好奇打量著這個古老國家的城市環境及城市所折射的歷史文化。康格夫人把北京城比喻成“藍袍之城”〔6〕,因為她在街上幾乎很少看到中國女性。康格夫人對長城以及中國遍布各地的城墻所體現的文化象征意義和民族心理分析得比較透徹,她認為“中國似乎不僅防備著本國民眾,對外面的世界也處處設防。〔7〕
當晚清西方來華的外交官夫人欣賞完中國的山河與城市建筑后,再細細打量這個古老國家的公共衛生時,每位外交官夫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難以忍受。凱瑟琳·馬嘎特尼感覺,“喀什噶爾回城的街道狹窄,骯臟不堪。”〔8〕海靖夫人和丈夫抵達北京前必須經過通州,她對通州的感覺是“令人驚詫”,“城里的巷子十分狹窄”,“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垃圾和臟物隨意堆放在大街上,里面間或翻滾著覓食的黑豬,空氣里蒸騰著種種熏人的臭氣。”〔9〕經過“特別臟臭的”馬路進入北京城后,海靖夫人感覺特別糟糕,以至于后來她自嘲“我對北京街道的物理反應如同讓我親吻一個對我來說十分事業心的人”。〔10〕
(二)對中國人生活狀態與自身品質的關注與憐憫
常駐在京的公使夫人們交往的多為宮廷權貴,而遠駐在喀什噶爾的凱瑟琳·馬嘎特尼則更多接觸廣大的社會中下層,她目睹了當時中國下層人民的苦難困境,因看到嬰兒因為較差的衛生醫療導致“渾身臟的一塌糊涂,在夏季烈日下,身上滿是瘡”,〔11〕還曾伸出援助之手,盡可能幫助這些得疾病的孩子們。
晚清西方來華的外交官夫人對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品德雖不吝贊揚和肯定,但也指出了中國人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有些還涉及到對中國的國民性的觀察和思考。如凱瑟琳·馬嘎特尼認為“喀什噶爾的老百姓性情平和溫順。”〔12〕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則通過若干事例說明中國人的勤勞能干及他們身上表現出誠實、冷靜的品質等特點。1905年4月28日,康格夫人在返回美國的“西伯利亞”號輪船上寫信給她的妹妹,信中談及自己在中國七年對中國人的觀感,對中國人的品質大加贊賞,她認為“中國人心地善良、熱心大方”、“中國人很謹慎,他們總是三思而后行”、“中國人具有不可超越的重要品質”。
當然,康格夫人也通過觀察一些生活瑣事,指出中國人存在的一些不足,如公使館內中國仆人燒飯、洗衣、買煤愛貪小便宜、組成小團體、愛使小心眼等。康格夫人的關于中國人的“面子”問題的看法在其他晚清來華婦女諸如立德夫人、伯德夫人筆下也有所記錄。康格夫人甚至認為清政府也存在“面子外交”的問題,如外國公使覲見清朝皇帝都是從一個邊門或某個后門進入,在一間專為此種場合而安排的簡陋裝飾的殿堂受到接見,從而使清朝君臣能獲得天朝上國曾經接受萬邦來朝的心理上的自我陶醉。
(三)熱心中國局勢與近代化發展的反思與行動
中國秀美的自然風光、悠久的歷史文化、優秀的傳統美德和晚清嚴酷的刑法、愚昧的裹腳陋習等在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眼中形成鮮明的對比。她們也在思考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她們認為,中國近代的落后和衰敗的原因,并不僅僅是由于政治專制、經濟落后和外交滯后,更主要的是文化保守和思想僵化導致了天朝夢破。康格夫人比較同情當時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中國,她認為中國人只要把自身的優秀品質“糅合起來”,就會“顯示出一個遲早會躋身于大國之列的強大民族是如何形成這種鮮明的性格的”,她大膽預言“他們會爆發出我們無法想象的力量,這將震驚全世界。”〔13〕此外,對中國懷抱深切同情的康格夫人還積極行動起來,她在覲見慈禧太后時,向慈禧太后談起自己參觀的一所學堂,并試探性地向慈禧太后提出派遣青少年到國外留學的建議,慈禧太后欣然同意。〔14〕
訥色恩夫人則在所著之書中詳細地描述了義和團運動與聯軍入侵的場景,并對入侵的罪行表示厭惡,“所有的東西都毫不留情地被摧毀,所有貴重的東西都被搶走,然后放火燒掉房子,同樣的事情在天津、通州和北京發生過多次,這損害了歐洲人的形象。看來戰爭會讓人變得野蠻,使你我的正誤概念完全混淆了。”〔15〕
上述幾個方面是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的主要部分。此外,晚清西方來華的外交官夫人還表現出對晚清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社會生活方面的濃厚興趣,留下了許多詳細的描述,較為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中的民俗民情。從客觀上來說,西方外交官夫人來華前的出生背景、家庭環境、教育程度、交往范圍等許多因素影響其來華的中國觀感的形成。此外,個人情感例如對中國人民的偏見或憐憫、對中國文化的蔑視或熱愛等復雜的情感相夾雜,都對她們中國觀感的形成造成影響,女性特有的細膩情感也會在不同環境和心境下發生變化,從而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她們的中國觀感。
少數晚清西方來華的外交官夫人還因受了西方殖民主義心態的影響,表現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輕視或歧視,還多有中國表現極富侵略性的言論,這與她們長期奉行的歐洲中心主義觀、狹隘的民族偏見與文化偏見不無關系,她們下意識地以其所持有的文化價值標準與某些先入為主的偏見作為評判標準。海靖夫人是其中的典型,她記述初進北京城的感覺是特別糟糕,“北京的第一景象實在是太丑陋了,讓人幾乎把眼前的一切當做高燒后的幻象,或是宛如做了一場噩夢”。她公然叫囂“我們必須在巨大的中國寶盆里搶占一席之地”。〔16〕因此,她和海靖“夫唱婦隨”,竭力鼓吹并積極推動德國在山東強租租借地,充當了列強瓜分中國狂潮中的急先鋒。海靖夫人對中國赤裸裸的侵略要求,既是西方殖民主義的體現,也是十九世紀末德國急于對外擴張心態的真實寫照。
但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中亦有能暫時拋開外國人身份,對列強侵略中國表示憤憤不平,對中國受到的凌辱和痛苦感同身受,設身處地為中國出謀劃策者,如康格夫人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代表。康格夫人在回國后仍然關注中國,反對西方過多地插手中國事務,她堅信“如果外國人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繼續下去,中國遲早會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她希望中國能夠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保護自己的國家。〔17〕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康格夫人對中國的同情和好感固然主要是由于她的個人修養和良好品質,當然也要看到當時正是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美國在華利益有“親華”的需求,因而,康格夫人對中國的“好感”和“善意”也正是她個人品行與國家利益的有機統一的結果。
三.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與西方中國形象的關系
當代理論家哈伯馬斯提出,“互為主觀”是突破封閉體系,發展前進的前提。對于今天我們重構自己的文化傳統,參與世界文化的總體對話來說,認清“中國形象”在國外的發展變化,顯然具有重要意義。外交官夫人所記述的關于中國觀感的著作,其出發點往往是作為一種與自我相對立的“他”而存在的。其所渴求、所遐想以及在現實中生活無法滿足的,都會幻化成一種“他性”投射于對方,這種投射大部分屬于作者的主觀,并不能真實反映客體,但是從中仍可以獲得某種信息。〔18〕同樣的,有學者也指出所謂的“西方的中國形象”,即“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種關于文化他者的幻想,是西方文化自我審視、自我反思、自我想象與自我書寫的方式,表現了西方文化潛意識的欲望與恐怖〔19〕;并認為它主要包含三個層次的內涵:中國現實的反映,中西關系的意識,西方自身文化心態的表現與折射;〔20〕故其形成得益于兩種坐標的參考,一是西方中國形象的自身演變,另外一種是中國自身的現實,兩種缺一不可。〔21〕“西方的中國形象”在清代出現了大轉折,即由“文明”開始轉向“野蠻”,表面上看,西方想象中國的態度變了,即從原來美妙虛幻的中華帝國到衰敗落后的東亞病夫的形象觀感,但是這也可以實際反映中國國力的衰弱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之間一種微妙的關系,西方人大量來華并深入了解中國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與西方的中國形象起著一種相互影響的作用。她們的日記、書信、回憶錄等著述在歐、美很暢銷,因此對塑造和培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她們對中國古老文明的推崇更加吸引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向往,她們的見證和良知也有力地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及其文化的偏見,而她們對中國的某些偏見自然使沒有機會來中國的西方人對中國形成錯誤的印象。如當時多數西方人認為晚清中國女性依然普遍處于一種封建保守的思想狀態,但通過康格夫人給親友的書信,美國民眾了解到晚清中國家庭婦女的生活和地位已經逐漸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如北京城內的17所女子學校均有女性資助和管理,女性也比以前渴望得到更多的教育。由于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著述的主要讀者多為外國人,確切地說是那些不曾到過中國但對中國卻感興趣的外國人,這些著述進一步刺激了她們對中國的興趣,一定程度上改變或扭轉了她們既有的中國形象,對晚清融入國際舞臺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西方的中國形象也反作用于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對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形成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1750年前后,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大轉折時期,原先“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帝國”的形象類型逐漸演變成“停滯的中華帝國”“專制的中華帝國”“野蠻的中華帝國”,西方開始“從美化中國到丑化中國,從愛慕中國到憎惡中國”,“美化”和“愛慕”中國是西方思想變革中試圖“用中國形象表現他們對西方社會的不滿與改革的期望”,而“丑化”和“憎惡”中國則是西方“以西方現實為尺度衡量并貶低中國,確證現存的西方現代性的合法性”。〔22〕因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來到晚清的西方女性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中國形象的影響,從而在她們的中國觀感中往往體現出對中國“愛慕”和“憎惡”的兩種極端或兩者兼而有之的矛盾統一。她們對中國的“美化”進一步刺激了西方對古老而又神奇的中華帝國的向往,她們對中國的“丑化”也使西方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對中國的厭惡和防范。
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對塑造并形成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產生了重要影響,是西方中國形象總體構成中的一個特殊部分。對中國古老文明心懷敬仰,對中國落后現實充滿感慨,對中國民眾生活艱難滿懷同情,對本國對華政策保持清醒,這些是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中國觀感的主體。
回顧晚清西方來華外交官夫人的中國觀感,對正確定位當前中西關系以及中西之間如何相處仍有借鑒意義。雖然海靖夫人鼓吹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她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有偏激和片面的問題,但她的某些評價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如1897年2月20日,她寫信給德國駐丹麥公使馮·基德倫說“中國給我的第一印象實在是太糟糕了”,并認為“這個國家屬于典型的閉關自守,它的國民們極其愚昧地生活在自我封閉的狹小空間里。……但他們固執地拒絕與外界交往;盡管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認知極為匱乏,卻盲目自大地認為自己依靠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仇視一切外國人和改革……”〔23〕在改革開放日益深化的今天,重溫海靖夫人的這一番話,對我們避免重走“固守僵化”的老路也有很大的警示意義。此外,我們也可以從中窺察出當時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執行情況,對我們研究晚清的外交也大有裨益。
在當代語境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他者”存在的重要性,認識到只有在與”他者”的互識、互補、互證中才能更好地認識自我,因而不再把異國形象看成是單純的對異國現實的復制,而是放在“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互動關系中進行研究。而這些著述恰恰為我們國人了解那個時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攬他人之鏡以自照,這必將有助于我們民族的自我認識,也有助于我們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因此,不管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如何演變,我們必須不因贊譽而自傲,不因批評而自卑,不斷加強民族自省,樹立民族自信,實現民族自立、自強,才能最終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西方的中國形象包含了晚清西方來華女性的中國觀感,相關資料目前國內主要有黃興濤、楊念群主編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的“西方的中國形象”譯叢十種。廈門大學周寧教授長期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先后著有《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上、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異想天開——西洋鏡里看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世界之中國——域外中國形象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其研究成果使筆者獲益甚多。但在已有的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中,多未將西方來華女性特別是外交官夫人視為一個單獨的群體進行研究,此亦筆者撰寫此文主要動機。
〔2〕蔣世弟、吳振棣.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91.
〔3〕李占才.清朝禁止西方女性來華導致的沖突〔J〕.文史天地, 2010(8).
〔4〕〔5〕〔9〕〔10〕〔16〕〔23〕(德)海靖夫人.德國公使夫人日記〔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第92頁、第94頁、第12頁、第38頁、第44-45頁、第42-43頁。
〔6〕 〔7〕〔13〕〔14〕〔17〕(美)薩拉·康格.北京信札——特別是關于慈禧太后和中國婦女〔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第264頁、第1頁、第299頁、第208-209頁、第307-308頁。
〔8〕〔11〕〔12〕(英)凱瑟琳·馬嘎特尼. 一位外交官夫人對喀什噶爾的回憶〔M〕. 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第62頁、第106頁、第64頁
〔15〕 paula von Rosthorn Peking 1900,Erinnerungen an den Boxeraufstand in Peking,Marz bis August 1900 轉摘于(德)艾林波 巴蘭德等 王維江等輯譯《德語文獻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358
〔18〕〔19〕〔20〕〔21〕〔22〕(美)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第6頁、第3頁、第331頁、第396頁、第7頁。
Perception of the western diplomatists wiv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uo Xi Shi YiYin
Abstract:The western image of China has constantly changed associated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myth and demonizing that behind the images not only have unintended misunderstandings,but also have intentional attacks. The perception of Western diplomatistswives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 part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West.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gard them as an independent group to study. Because of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identity,background,experience,education and so on and so forth of the Western women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perception may look splendor. Exploring the perception of Western diplomatistswives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e can als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broa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but also summed up the differences among women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erception of the western diplomatistswiv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riches th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west and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foreig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t wrote a unique chapte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 foreign relations,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oday also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of the reference.
Key word:late Qing Dynas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the western image of China, western female abroad , diplomatistswives
責任編輯: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