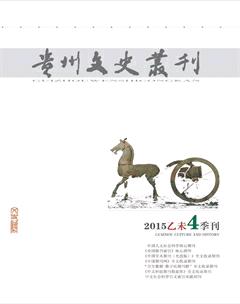鼎盛與危機:明清東亞宗藩體系嬗變
崔思朋
摘 要:東亞地區宗藩關系自西周時期發軔至明朝發展至鼎盛時期,明清易代也是宗藩關系由盛轉衰的重要歷史階段。清朝雖采取多種手段對宗藩關系加以維護,但在清中后期西方殖民體系的介入下,終究未能挽救宗藩體系的瓦解。宗藩體系秩序之下的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地位等級明確、權利義務分明,雙方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至清朝建立,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居于宗主國地位是不符合傳統儒家君臣道義的正統思想,受到了朝鮮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藩屬國的一致排斥。加上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都沖擊了清朝主導下的宗藩體系,但清朝未能適時而動,融入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固守傳統宗藩體系,最終導致宗藩體系的瓦解與清朝后期落后與被侵略。
關鍵詞:東亞地區 宗藩關系 明清易代 鼎盛 危機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5)04-67-75
特定時期內相互聯系的各政治行為體之間會維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空間結構,即“地緣政治格局”。〔1〕在東亞地區,這種地緣政治格局表現為宗藩秩序。布羅代爾就此問題指出:“如果不談奴隸與附庸性經濟,歐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樣,如果不談其國內的未開化民族和國外的藩屬,中國也是不可理解的”。〔2〕(P.117)可見,宗藩體系對于中國、東亞的歷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紀是東亞宗藩關系由盛轉衰的重要時期,明朝將宗藩關系推至鼎盛,清朝面對宗藩體系的內憂外患也采取了一些補救手段,但終究未能挽救危機的擴大及在十九世紀的瓦解。危機的出現是多方因素促成的,清朝的補救措施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十七至十八世紀宗藩秩序,但其所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卻大大縮減。清朝時宗藩關系由盛轉衰也與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密切相關,明清之際西方勢力開始向東亞滲透,日本也企圖沖破傳統中國影響下的宗藩體系,加上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受到朝鮮等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藩屬國的反對等都是促成危機的因素。十九世紀末的中法戰爭中國對越南宗主國權力的喪失,預示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傳統關系發生了變化,近代西方殖民體系開始介入。至中朝之間宗藩關系的解體則預示著中國主導下宗藩體系的徹底終結。
一、東亞及東亞宗藩體系
宗藩體系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天下觀的基礎上,源于西周宗法制度,即天子在京畿外,由內而外漸次分封天子和諸侯,雙方有一定的制度性禮儀往來。〔3〕也經歷了秦漢、隋唐、宋元至明清的發展、成熟、穩定、鼎盛、滅亡等階段。明朝是宗藩體系的鼎盛時期、由明入清也是宗藩體系由盛轉衰的階段。
對于東亞宗藩體系的研究離不開對其地域范圍的界定,東亞范圍的劃分說法不一,楊軍提出“古代東亞包括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區”的說法。〔4〕費正清也提出了東亞是由中國、朝鮮、越南、日本及小島琉球地區組成,這些地區是由古代中國分衍出來,并且是在中國文化區域內發展起來的。〔5〕(P.1)西方人眼中的東亞一般包括:“東部西伯利亞、中國、蒙古、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6〕(P.1~11)此外,也有學者結合了當時受中國文化影響,與中國在地理位置、文化交流、朝貢貿易等方面來往較為緊密的國家,即從中國文化影響的角度劃分東亞。本文綜合上述各觀點,將當時受中國影響下今日地理范圍上的東亞、東南亞等地的藩屬國均列入東亞范圍內。
傳統宗藩關系是“華夷”秩序下,受中國影響的國家政治模式,是古代東方世界所遵循的國際制度安排,且是最主要的制度。加之中原王朝的先進性,華夷觀念也隨之而生。隨著中國版圖的擴大以及同朝鮮半島、琉球群島等地區聯系的出現,此華夷觀的應用也逐步擴大到藩屬國。當時中國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高度發展,并領先于其所影響地區的藩屬國,受此吸引,各藩屬國以宗藩朝貢關系為紐帶,與中原王朝之間確立了一個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向四周呈現輻射狀的華夷秩序。其不可動搖的原則便是上下有別、尊卑有序,并將此原則制度化。宗藩關系的內容包括“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民間貿易、領土及領海的爭端、僑民問題等”。宗藩關系是古代社會中國世界秩序存在和維系的核心,“華夷秩序”也是宗藩關系的主要內容,更是中國社會文化的產物。具體而言,宗藩關系實際上是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等級有序的關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節義”理念對外關系中的延伸,這便要求藩屬國對中國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7〕宗藩體系的建立是中原王朝憑借自身極強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實力,對藩屬國產生的威懾和吸引,并附之以武力鎮壓,故而當時的宗藩體系是建立在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不平等關系基礎上。相比于西方殖民體系,宗藩關系能夠長期存在也是有其原因的。這也離不開中國基本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態度,不干預朝貢國的內部事務,同時為其提供一定的保護,以確保其延續。〔8〕(P.529)
實現對藩屬國的吸引也源于中國優越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韓愈曾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9〕(P.1863)隨著時代的發展,對于中原正統王朝的區分也不再以血緣為標準。如北魏鮮卑族、李唐王朝、蒙元王朝、朱明朝、大清帝國等,其統治階層都是出身蠻夷或者貧民。因此,“區分古代社會中原華夏族與蠻夷的標準是文化的發達程度,而不是自身出身血統的高低”。〔10〕(P.107)基于此,宗主國不斷更迭也就有其合理性。宗藩體系下,“藩屬國需向中國稱臣納貢,而中國則通過對其‘冊封和‘保護履行宗主國的責任”。〔11〕“宗藩關系下的中國統治者是‘君天下,除對自身統治外,也統治中國之外的地區。因而中國與屬于‘四海的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是同一政權內部各地區的關系”。〔12〕宗藩關系的中心為中國,其模式是以中國為中心并向四周呈輻射狀,或者說是眾星捧月般的存在。中國高高在上及各藩屬國臣服納貢的地位不可逾越。這樣的宗藩體系自古有之,延續上千年,直到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紀,在中外多方因素的影響下,才出現了新的變化,然而清朝不能做到隨時而動,想方設法的固守這一體系,謀求的是中原王朝高高在上的那種傳統天朝國威與不可逾越的尊嚴。endprint
論及宗藩體系的維護則離不開朝貢制度及其影響,張勇進也曾將朝貢體系作為一種制度來解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13〕(P.51~58)。朝貢制度對于東亞地區宗藩關系的維護和運行至關重要,所謂朝貢,是指“朝鮮、琉球、越南、緬甸等在歷史上受到中國影響的東亞地區國家,堅持以中國為中心,以中華理念為根本而形成的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國派遣貢使,并向中國皇帝表示恭順之意”。〔14〕中國這樣朝貢外交及其觀念的出現與長期中國的華夏中心論與中國天下之主的觀念是分不開的,也是此種思想長期積淀的結果。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納貢關系是中國人唯一承認的處理國際關系的一種形式”。〔15〕(P.76)朝貢制度是宗藩關系得以維系的基礎,明朝統治者的對于其與藩屬國之間朝貢關系的重視也為東亞地區宗藩關系的發展及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礎。以明朝時確立的朝貢制度為例,明朝與各藩屬國之間的朝貢遵循“古者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的原則。〔16〕朝貢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業貿易行為進行的活動,也就是說因朝貢關系而使得以朝貢貿易關系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得以形成。〔17〕(P.38~39)中國與各藩屬國之間的宗藩關系,在政治上有冊封制度確定的臣屬關系,外交上有遣使和貢賜制度,經濟上有官方通商往來。這一關系的維持需要有朝貢制度的支撐。值得注意的一點,這種宗藩關系也是維系古代東亞地區國家關系的基礎,也是古代東亞文化圈得以形成和鞏固的政治保障。〔18〕可見,朝貢制度對于宗藩關系運用的重要作用。
二、明朝宗藩體系的鼎盛時期
明朝是宗藩體系發展至鼎盛的時期,其鼎盛也主要體現在朝貢國數量的增加與朝貢活動的繁榮等方面。就其朝貢國而言,終明之世,其朝貢國數量多達一百五十余國,這與其統治者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明成祖時期,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歷經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足跡踏遍亞非三十七個國家和地區。所經之國紛紛派遣使者來大明帝國。明朝則按“厚往薄來”的原則厚贈來使,導致來朝貢的國家多達一百四十八個,可謂盛況空前。〔19〕萬明也指出:鄭和的船隊帶著深受各國喜愛的紗羅、彩帛、藥材、銅鐵器物等,這對于所經地區國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鄭和下西洋的活動使中國與各海外國家間的貿易關系發展到全新階段,這也促成了朝貢貿易的空前發展,〔20〕(P.176)促成了明朝出現盛況空前的朝貢局面。《明史》也載:“東起遼海,西至嘉嶺,南至瓊、崖,北抵云、朔,東西萬余里,南北萬里。其聲所訖,歲時納贄,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屬者,不在此數”。〔21〕(卷41,地理一,P.882)由此不難看出,明朝宗藩體系的鼎盛。其次,就其朝貢活動而言,明代朝貢活動往來也極為頻繁。明朝成立之初,為了修復元末戰亂破壞下的東亞地區秩序,明朝統治者對藩屬國采取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終明之世也多是參照此準則對待藩屬國。明初朱元璋曾親自遣使前往高麗、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等國,尋求建立宗藩朝貢關系。〔22〕(P.749~775)不僅如此,明朝統治者也通過在高麗、安南、占城等地頒科舉、祭祀山川等活動對各藩屬國加以拉攏。〔22〕(P.954~1021)以安南為例,僅明一朝,中國前往安南的使團有三十余次,安南遣使來中國則有一百多次。〔23〕(P.134)以致出現“四方賓服,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的盛況。〔21〕(卷7,成祖本紀,P.105)
宗藩體系發展至鼎盛也有其原因。首先,離不開統治者對于宗藩朝貢關系的高度重視,明朝統治者的重視為宗藩體系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明朝統治者對發展宗藩關系指出:“凡外夷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既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互市”。〔24〕宗藩體系的維護也離不開朝貢制度的存在。可以說朝貢制度是宗藩關系維持的重要手段,通過朝貢關系使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確立不平等地位、禮儀上的制度、經濟上的往來等,朝貢制度也是體現宗藩關系的重要形式。東亞秩序的形成與朝貢制度是有著直接聯系的。因此,統治者對于朝貢活動的支持也是促成宗藩體系發展至鼎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東亞地區的宗藩關系維系上千年是與朝貢制度分不開的,朝貢制度之下宗主國與藩屬國之間各取所需,積極維持著這一秩序的存在。陳尚勝也指出:明朝建立之后,雖采取過海禁政策,但是洪武十六年辦法勘合之后,海外貿易與交往逐漸增多,也將朝貢定為海外貿易的唯一途徑。〔25〕其次,對于藩屬國的保護、幫扶及貿易利益,是吸引藩屬國來朝并指出宗藩體系運行的重要手段。朝鮮貢于明,明朝則負有保護朝鮮的職責。日本曾入侵朝鮮,明朝則承擔起宗主國職責。史載:“二十年四月,遣其將請正、行長、義智、僧玄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馬島渡海陷釜山……朝鮮望風潰,請正等遂逼王京。朝鮮王李昖棄城奔平壤,又奔義州,遣使絡繹告急……中朝仍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都督李如松為提督,統兵討之”。〔21〕(卷322,外國三·日本,P.8358)皇太極發兵征討朝鮮時,朝鮮便向明朝求援。史載:“十年正月(即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責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域悉潰。朝鮮告急,命總兵陳洪范調各鎮舟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數月,山東巡撫顏繼祖奏屬國失守……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故朝貢絡繹,賜賚使藩,殆不勝書”。〔21〕(卷320,外國一·朝鮮,P.8306~8307)各藩屬國進貢時,在正貢之外,也會附帶一些進物及來華的交易物資,即“附至番貨”,這些貨物是海外國家帶至中國進行貿易的,換取本國所需物資與獲得利益。再次,海上貿易的發展為宗藩體系的鼎盛起到了促進功能。中國的出海貿易可追溯至西漢時期的廣州東南地區的港口,西漢時期便在這些地區形成了從事“珠璣、象犀、玳瑁”的貿易。〔26〕(P.754)至宋、齊時,至者十余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于前代矣”。〔27〕(P.783)通過海外貿易而取得與藩屬國的往來,這也是擴大宗藩體系影響的手段。最后,就東亞地區而言,十五世紀初期,東亞地區相繼出現了一些新國家,這些國家獲得生存、發展與獲得中國的承認也選擇了與中國間進行朝貢關系。〔28〕(P.51~60)鑒于以上各因素的影響,東亞宗藩體系在明朝發展到了鼎盛時期。endprint
三、清朝宗藩體系的危機
清朝時,其朝貢國的數量相比于明朝時的近一百五十個朝貢國的盛況明顯減少。康熙皇帝也說過:“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29〕(P.751~752)可見清初時宗藩體系發展的衰落。清朝作為北方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成為宗主國,這是與傳統宗藩體系所不相符的,受到了朝鮮等屬國的排斥,加之當時國際環境的變化,都對宗藩體系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危機也主要體現在藩屬國對宗主國的反抗方面。
(一)宗主國的過分干預,引起了藩屬國的抵觸
政治上,清朝對藩屬國的管治引起了藩屬國的不滿:明清戰爭爆發后,明朝限制對其貿易。后金及初建的清朝便不得不采取同東亞各國的貿易獲得所需物資。然而屬國并不重視與清之間貿易,抵觸情緒高漲。丁卯之役后,清朝取得了對朝鮮軍事上的勝利,皇太極也與朝鮮國王修書指出“今兩國既成一國,中江大開關市,竊思東邊之民,原在會寧做市矣,今見此處開市,皆欲往會寧貿易,料無王命,會寧官豈敢擅專。故具悉預報,如允當,速令會寧官遵行”。〔30〕然朝方卻以“會寧空虛之地,以何人物得成市貿也”的理由加以拒絕。〔30〕清立國后,“朝方更加深了對清的憎恨,甚至清朝使團出使朝方也受到監視和舉國抵觸”。〔31〕朝鮮對清也積極備戰,朝鮮國王令諭:“我國卒致丁卯之變,不得已權許羈縻,而溪壑無厭,恐嚇日甚,此誠我國家前所未有之羞恥也……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從征,期于共濟艱難,以報國恩”。〔32〕(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P.412)朝鮮方面的抵抗持續十余年,隨著清朝統治地位的確立,便不得不認同清的宗主國地位。就朝鮮履行助宗主國出兵助討義務時極不情愿,但在清高壓政策下,不得已出兵助清攻皮島。《朝鮮仁祖大王實錄》載:“乃命信川郡守李崇元,寧邊府使李浚,領黃海道戰舡赴之”。朝鮮不忍心助清討明,攻皮島時甚至向明透露情報,可見傳統儒家君臣思想的根深蒂固。
司法上,當時的屬國沒有獨立司法權,主要是在大明律與大清律的基礎上制定,要遵循中國之法。以朝鮮為例,清朝和朝鮮兩國禁止其民越境,遇越境案,“清帝或令兩國官員至鳳凰城會審,遇到重要案件則朝鮮應將人犯押解到沈陽,由盛京刑部擬審,國王擬罪奏報,必經三法司核議具奏,經清帝裁定后方由禮部咨知朝鮮遵旨執行”。〔33〕當時的宗主國權力凌駕于藩屬國司法權之上。清初,朝鮮未重視清朝,派兵討時延誤了時期,在清朝威脅下,朝鮮國王深感恐懼,只得尋找替罪羔羊向清廷請罪。據載:“朝鮮國王李倧,以違誤軍期,遣崔鳴吉赍咨到部請罪。咨云:戚遵敕諭催督進兵,前后申嚴,不止再三,而事乃大謬,竟致愆期。私心憂懼,坐不安席……除席藁伏地恭俟嚴遣外,特遣陪臣領議政崔鳴吉赍咨馳進,口陳本國事情,煩乞貴部備將前因轉奏天聽,俾蒙皇上特垂諒察,不勝幸甚”。〔32〕(卷44,崇德三年十月至十二月,P.579)
外交上,屬國沒有獨立的外交權,與別國之間的往來需獲清政府的批準。就朝鮮而言,“1637年至1881年的近一個半世紀之間,朝鮮先后共有十一次遣使日本,每次出使都必須將出使的原因、出使時隨從人員姓名、官職、出使時間等向清朝奏報,審批后方能出使”。〔34〕(P.210)此種控制,在清朝前期表現的格外突出。然而隨著平定三藩、收復臺灣與平定蒙古準格爾叛亂的成功,對藩屬國外交的控制有所削弱。我想這與國家政權穩定、社會秩序恢復正常是密切相關的。直至西方國家進入后,中國對于藩屬國外交的控制又有所加強。清朝對于當時藩屬國外交的限制也出于對明朝的孤立,及清朝自身實力不足以對抗明朝與眾多屬國的聯合。清帝又對朝鮮國王下令限制其于明朝之間有所往來,并以軍事武力加以威脅。向朝鮮國王敕令,嚴厲指責朝鮮國王與明朝來往的罪狀。指出“種種罪狀難以悉數。又聞私與明國往來,凡事巧言抵飾,詭言欺罔,負恩滅理,天寧不爾鑒乎?〔32〕(卷53,崇德五年十月至十二月,P.706)清朝對屬國外交的限制,其最主要的目的不外乎是建立政權與鞏固其統治。
(二)藩屬國對宗主國的抵觸,也導致了宗藩體系發展的衰退
文化上,藩屬國中,尤以朝鮮、日本等國為代表,認為清朝是北方蠻夷,并非正統,并不認同其宗主國地位。這也源于當時受到儒家君臣思想的影響,東亞宗藩體系主要依據儒家傳統倫理而確立的政治權力學說,此學說運用到中原王朝與其他國家直接的關系上,是三綱中封建君臣關系在對外關系中的延伸。〔35〕就朝鮮而言,作為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屬國,其儒家夷狄大防和忠君事大思想根深蒂固,清朝在武力上使朝鮮臣服,但要使其思想領域中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的“事大事業”的思想得到改變是很難一時做到的,要求其棄明朝而臣服于“落后”的女真族是難以接受的。〔36〕當時屬國間存在的一個普遍的觀點就是對清排斥,認為清朝是“蠻胡之群”,在思想文化等領域遠不足其他屬國。朝鮮認為自己是“小中華”,在東亞地區地位僅次于明。成宗曰:“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37〕因此,對待立國之初的清朝,藩屬國都是持以蔑視的態度。弘光二年(公元1645年)八月,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派人向越南求助。次年二月,越南派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綿、陳概等同天朝督使林參駕海往福建,賀隆武帝即位并求封爵。〔38〕以及后來的永歷王朱由榔登基即位,越南都遣使祝賀并求冊封。與朝鮮等國對待清朝態度不同的是,日本持有其稱霸東亞的目的。但不可否認,在日本統治者看來:“清朝是北方蠻夷,蠻夷身份取代中華正統地位,這與儒家義理的正統思想是嚴重相悖的。所以,東亞地區國家秩序的構建需要排除清朝,確立日本為東亞中心的東方國際新秩序”。〔39〕清立國初,日本在以清為蠻夷身份拒不承認其宗主地位的原因中帶有自我稱霸的色彩,然而清朝帝國的崛起和強大,又阻礙了日本稱霸東亞的步伐,懾于清朝強盛國力的威脅,又不得不屈服于清,但這也為以后日本的崛起和入侵中國埋下了伏筆。endprint
雙方遣使及朝貢,藩屬國對清朝多是敷衍。清立國初,東亞各國并不認同其宗主地位,尤其是明清對峙時期,各藩屬國仍以明朝馬首是瞻,明未覆滅時以明朝為主,不愿改投清朝,明滅后仍舊對清朝機不中式,尊崇南明小朝廷,企圖明朝光復。清未建國時,為抗明及不知是否能勝過朝鮮的情況下,選擇與朝鮮約為兄弟之國,于天聰元年確立了兄弟關系。然懾于明朝影響,朝鮮與后金的交往也是隱瞞于明朝而私下進行。在此情形下“朝鮮若遇明代官員來臨,便取消與后金的來往,雙方來使交往的時間上的推遲和耽誤是時有發生的”。〔31〕如天聰八年時,“朝鮮方面準備派遣大臣李時英前往后金為其主皇太極慶祝元旦,但當時的明朝駐皮島副總兵程龍前往朝鮮訪問,朝方便等到正月二十六日明皮島副總兵程龍離開才派遣使臣前往后金慶賀,這位專門為皇太極慶賀元旦的使臣于二月十八日才到達后金,近兩個月”。〔32〕(卷17,天聰八年正月至二月,P.225)對于后金的抵觸,一方面是怵于明朝的威懾,另一方面則是其自身所持有的對后金蠻夷落后非正統觀點的認知。從雙方朝貢物品方面來看,東亞各國尤其是以朝鮮為代表,認為自己在文化、思想等方面高于清朝。因此,以朝鮮為代表的藩屬國不愿承認清朝的宗主國地位,明存時以明為主,明滅后也不對清朝給予一定重視,在所貢物品及納貢時間上對明有所側重和對清的不重視。十七世紀初期,明朝影響力仍舊存在的情況下,后金對朝鮮在“丁卯之役”時有保全性命的恩情,認為朝鮮向后金納貢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朝方卻認為丁卯年“雖有城下之恥,姑紓目前之急,第無厭之欲,難從之請”。〔40〕因此,朝鮮對于當時后金的朝貢及不能按時納貢,質量上也有差別。據載:“天聰五年正月,朝鮮派使臣樸蘭英前往后金貢春季方物。后金以額數漸減,悉卻之”。〔32〕(卷8,天聰五年正月至三月,P.110)因此,朝鮮不但不能按時,所贈禮物也時多時少,不論從數量還是從貨色上,比送給明朝的要差得多。〔31〕
藩屬國內反清意識的高漲,“明清易代后,藩屬國受到華夷觀念及國內政局的影響,朝鮮對明朝感恩不已,對清朝則大加排斥。也即孟森所提出的“當清全盛時,無日不望其速亡”。〔41〕(P.190)清朝入關顛覆明朝政權之后,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全國統一尚未實現,國內外反清勢力高漲。北方有明朝時退居漠北的蒙古軍隊虎視眈眈,西南的三藩漢王勢力,臺灣則是鄭氏割島自立,清朝表面上是大一統,然實際卻是內外矛盾重重。因此,朝鮮寄希望于各方勢力,對于反清給予厚望。臺灣多次遣使日本請求聯合伐清,朝鮮也希望如此,任由鄭、日兩方的船只自由航行于濟州海域,甚至還建議其“假道朝鮮,出送援兵”。〔42〕“朝鮮留戀于南明小朝廷,雖在清朝的逼迫下確立了宗藩關系;但仍通過清鮮往來的使臣、來往朝鮮的漢商和漢人等打探明朝及中國情況,對明朝仍抱有幻想。至仁祖時期,國王仍舊在宮中設立牌位,向西中原哭拜明朝。朝鮮孝宗也主張反對清朝,銘記丙子之亂的仇恨,提出了北伐論等反清的策略”。〔43〕即使是在清朝確立在東亞的統治之后,藩屬國仍舊留戀于明朝。三藩之亂時,朝鮮在履行助宗主國出兵戰爭時的推脫,在參戰時記述的戰爭情況和參戰人員歸國后匯報的情況帶有濃重主觀色彩,及傳達情報時體現的反清態度。“朝鮮在史書中對清朝大加貶低,對康熙皇帝的勤政和勵精圖治不曾提及,對康熙皇帝和一些官員的執政能力也不做出客觀的評價,其所言帶有濃重的主觀色彩。當三藩之亂爆發,他們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也為其固有的偏見找到了更多的素材,認為清朝會因此敗沒的幸災樂禍之情也就自然的出現在了朝鮮使臣歸國的匯報中”。〔44〕
四、清朝宗藩體系危機成因
清朝是東亞地區宗藩關系出現危機的重要歷史時期,危機的出現是受到內外雙重因素影響下而出現的。就其外部因素而言,清朝是東西方之間出現了發展差異,西方殖民體系的介入沖擊了傳統的宗藩關系,清朝出于國家安全角度出發,其所主導下的宗藩關系帶有濃厚的國防安全目的;就其內部而言,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缺乏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正統性,加之東亞地區日本發展后對傳統宗藩關系的沖擊等都是造成清朝時宗藩關系危機出現的原因。
外來因素對宗藩體系變化的影響:十七世紀是中國對外了解加深的時期,這與明朝時期遣使出海也是密不可分的,更是新航路開辟后大發現時代的產物,是中國同世界取得了聯系,雖在此后清朝閉關企圖切斷與外界的來往,但卻也難以阻礙歷史的發展。楊巖指出:“清政府為防止外來侵略,消除隱患,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然而清朝剛入主中原,在黑龍江流域便受到了沙俄殖民者的入侵。在南方口岸,英、葡、荷等國陸續叩關等”。〔45〕各國外勢力的介入,加上清朝定鼎中原的統治尚未鞏固,建國初,宗藩體系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是較多的。不僅沙俄對中原王朝的統治產生了影響,東亞的日本也對明清之際的宗藩關系也產生了影響。日本與明朝的朝貢關系,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是為實現與明朝之間在朝貢關系之下的貿易活動。明廷在“招撫遠夷”目的影響下,推行“厚往薄來”的朝貢制度,當時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為對自己已獲政權加以鞏固,及政權的合理性的增強,毅然接受了明朝的冊封,稱之為“日本國王”。當時的日本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掌握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權,這一職務的擔任是實現明朝與日本之間貿易加強與經濟交流頻繁的有利幫助。然而后繼的統治者認為“日本屈服于中國而求得的朝貢貿易對日本而言是莫大的恥辱,于是日本當局在1411年至1432年決定脫離與明朝的朝貢體系”。〔14〕室町幕府的第六任將軍足利義教(1394—1441)掌握了實權以后,為改善幕府因與中國斷絕朝貢關系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發展停滯和危機,日本政府決定出兵朝鮮以轉移危機。當時“日本改國王所居山城為大閣,廣筑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婿必誅,以故所向無敵。乃改元文祿,并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21〕(卷322,外國三·日本,P.8357)日本對朝鮮的入侵,損害了明朝宗主國的地位及其利益,出于共同利益基礎上,明朝與朝鮮之間進行了合作,共同對抗日本侵略,當然明朝出兵干涉,對付日本,也是宗主國對藩屬國保護職責的體現。在明朝與朝鮮強大軍事武力的威脅之下,日本也不得不做出讓步,以豐臣秀吉為首的日本代表團與明朝進行會談,共同提出了休戰的七大條件,“之一便是要恢復日本與明朝的朝貢貿易關系”。〔14〕可見,明朝之后,東亞地區的宗藩關系便受到了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屬國的沖擊。清朝建立后,日本也不愿承認清朝的宗主國地位,為擺脫朝貢關系,曾一度侵占朝鮮,或扮演海盜的角色,侵擾中國東部及東南沿海。清朝則選擇關閉東南沿海的門戶,斷絕與外界往來的方式加以防范。此外,清朝也采取朝貢貿易之下,對貿易限制的方式阻隔與外界往來。因此,在此外來因素的影響下,明清易代時期,清朝的宗藩朝貢體系逐漸縮小,政治性的目的也更為明顯。endprint
清朝自身因素對宗藩關系變化的影響: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其所采取的治邊思想的核心是“守中治邊與守在四夷”的思想。所謂的邊即包括邊疆少數民族,也有中國周邊的藩屬國。而這種秩序在中國得以存在上千年之久,也有其維系的紐帶和核心,費正清將“朝貢制度”認定為維系這種東亞各國秩序的核心。正是因為朝貢制度使得宗主國與藩屬國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之間等級分明,關系明確。然而沙俄的介入,卻使得這一觀念難以實行。無論是疆域、實力上,沙俄都可以同清朝相媲美。沙俄雖是當時介入東亞的國家之一,然而其出現及與清朝之間的對抗,卻使得中國古代沿襲了上千年的宗藩朝貢關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有論者指出:“清朝所主導的宗藩體系最初,也就是清朝入主中原之時的目的在于其對自身政權的鞏固及對邊疆安全的維護。清朝龍興東北之時,便武力征服朝鮮,解除朝鮮與明之間的宗藩關系,迫使其向自己稱臣納貢,確立雙方宗藩關系。定都北京后,又迫使安南、琉球等國斷絕與明殘存勢力的來往,并收回明朝時的封誥印敕。這也體現了清朝通過重新確立與明朝的各藩屬國間的朝貢關系而徹底的消滅明朝。對于自身而言,也是企圖通過宗藩關系而維護自身的統治,及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清朝這樣的統治思想,便產生了施政方針中固守邊土的政策,采取了守中治邊,通過限制屬國與外界的往來、限制宗藩朝貢關系等方式切斷與外界來往的方法,固守其在東亞的統治地位。其意圖不過是通過與周邊國家確立宗藩朝貢關系,將周邊的諸國變成自己的藩籬和外界進入中國的屏障。順治皇帝對于安南與清朝的關系的目的在于讓其永作清朝“屏藩”的要求。乾隆皇帝也要求中亞各部王公“約束所部,永守邊界,不生事端”。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下,當清朝的實力難以維持固有的宗藩秩序時,便不得不犧牲藩屬國而換取暫時的和平,繼續維護暫存的宗藩關系。以清末時中、日、琉球之間關系為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勢力主張放棄,指出:“琉球以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于中國而近日本,中國受其朝貢本本無大利,若受其貢而不能保護其國,固為諸國所輕”。〔46〕(P.4~6)李鴻章采取犧牲琉球國而滿足日本的侵略需求,換取暫時的和平與維護宗藩關系,最終在1881年中國承認日本對琉球的宗主權。琉球的喪失是屬國一個個相繼被割去的序幕,清政府的軟弱的做法也給其他屬國心理上投下了宗主 國無力保護的陰影,也導致了清后期藩屬國的離去,至宗藩關系的瓦解。〔47〕(P.301~320)可見,清朝自身思想的保守性對于其宗藩朝貢制度的推行是影響最深切的。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而傳統的天下觀念指導下,少數民族是邊疆蠻夷,是宗藩關系中的藩屬地位,也是朝貢制度下的貢方。因此,清朝為實現其統治的合理性,抽去了大一統理論中華夷之辨的內容,改造為‘四海之內共尊一君的君主專制的‘大一統觀念。這也是十七世紀東亞宗藩關系出現變化的一個方面的體現。十七世紀,由明入清的改朝換代,朝貢制度作為宗藩關系的基礎,隨著朝貢制度的變化,宗藩關系作為朝貢關系的實質性所在,其變化也同朝貢關系是一致的。其自身因素作為主因的變化,是導致明清易代的十七世紀宗藩朝貢關系變化的主要因素。
結 語
清朝“通過在武力征服及繼承明代宗藩關系基礎上建立了由宗主國清朝和七個藩邦所組成的東亞華夷秩序;另一種是殖民體系,十九世紀中葉,由于資本主義列強的瘋狂擴張,亞洲多數國家先后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列強在亞洲建立起殖民體系”。〔48〕近代以來,尤其是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體系逐漸介入東亞地區,雖在此之前東亞也有部分地區的宗藩體系被殖民體系所取代,但是作為宗主國的中國在殖民體系的沖擊下,對于東亞宗藩關系的影響才是最為嚴重的。鴉片戰爭對于宗藩關系被破壞只是開端,宗藩體系真正意義上解體的標志是中國失去對朝鮮的宗主權。“1894年甲午戰敗,中國喪失對朝鮮的宗主權,是宗藩政治徹底瓦解的標志。從西方列強武力入侵,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清政府腐朽等論說了宗藩體系瓦解的影響”。〔49〕
參考文獻:
〔1〕伍玉西.地緣政治與明朝對外政策〔J〕,求索,2009,(3).
〔2〕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M〕,顧良等譯,上海:三聯書店, 1992.
〔3〕王元崇.中規中矩:明清以來的中朝宗藩關系〔N〕,東方早報,2014年7月22日.
〔4〕楊軍.中國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2).
〔5〕(美)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M〕,杜繼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6〕(美)馬士,密亨利.遠東國際關系史〔M〕,姚曾廙等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7〕戴可來.略論古代中國和越南之間的宗藩關系〔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2).
〔8〕李少軍主編.國際戰略報告:理論體系、現實挑戰與中國的選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9〕韓愈.原道〔A〕,李沄.文苑英華〔C〕,北京:中華書局,1966.
〔10〕林沄.戎狄非胡論〔A〕,呂紹綱.金景芳九五誕辰紀念文集〔C〕,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11〕孫建黨.清代中越關系史研究的新成果——讀孫宏年博士著《清代中越宗藩關系研究》〔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1).
〔12〕楊軍.中國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2).
〔13〕Yongjin Zhang,System: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Michael Cox,Tim Dunne and Ken Booth,eds.Empire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endprint
〔14〕謝好.從東亞朝貢體系看日本的對外政策〔J〕,科技風,2009,(15).
〔15〕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6〕明太祖實錄〔M〕,卷七十六,洪武五年十月.
〔17〕(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貿易圈〔M〕,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8〕汪高鑫.古代東亞文化圈的基本特征(一)〔J〕,巢湖學院學報,2008,(2).〔19〕李寶俊,劉波.“朝貢—冊封”秩序論析〔J〕,外交評論,2011,(2).
〔20〕萬明.15世紀中國與東亞貿易關系的構建〔A〕,明史研究第八輯〔C〕,2003.
〔21〕張廷玉.明史〔M〕,卷四十一,地理一,志第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
〔22〕明太祖實錄〔M〕,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23〕于建勝等.落日的挽歌——19世紀晚清對外關系簡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4〕王圻.續文獻通考〔M〕,卷三十一,市糴考·市舶互市,北京:現代出版社,1986.
〔25〕陳尚勝.東亞貿易體系形成與封貢體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為中心〔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
〔26〕司馬遷.史記〔M〕,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
〔27〕姚思廉.梁書〔M〕,卷五十四,海南諸國傳,北京:中華書局,2003.
〔28〕D.R SarDesai.southeast Aisa:Past & PrentSent,Westview Press,Fouth Edition,1997.
〔29〕清圣祖實錄〔M〕,卷一百六十,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30〕李朝仁祖實錄〔M〕,卷十八.
〔31〕刁書仁.論清朝與朝鮮宗藩關系的形成于確立〔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32〕清太宗實錄〔M〕,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
〔33〕同文匯考·原編〔M〕,卷三。另,趙興元得編纂《同文匯考·中朝史料》(長白叢書)〔M〕,四卷本中三冊中也有體現,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4〕(韓)全海宗.中韓關系史論集(中譯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35〕謝俊美.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對遠東國際關系的影響〔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5).
〔36〕柳岳武.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關系下的司法運作之研究〔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
〔37〕朝鮮成宗實錄〔M〕,卷二十,成宗三年七月十日.
〔38〕轉引自陳文源博士論文《明朝與安南關系研究》〔D〕一文中所引《大越史記全書》(下冊)卷十八,第980頁,廣州:暨南大學,2005年.
〔39〕周愛萍.明末清初東亞政治經濟形勢變動與日本近世貨幣制度的建立〔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
〔40〕李朝仁祖實錄〔M〕,卷十五
〔41〕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2〕崔景日.明末清初朝鮮與明、后金及清的關系〔D〕,延邊:延邊大學碩士論文,2002.
〔43〕孫紅英.清朝前期朝鮮的對華觀——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中心〔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
〔44〕龔捷.論朝鮮對清朝“三藩之亂”的反應〔D〕,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2.
〔45〕楊巖.清代前期外交研究〔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5.
〔46〕吳汝綸輯.李文忠公全集〔A〕,譯署函稿〔C〕,第八卷,光緒刻本.
〔4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M〕,第二卷,上海:三聯書店,1958.
〔48〕吳蓓.十九世紀亞洲的宗藩體系與殖民體系〔J〕,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8,(1).
〔49〕謝俊美.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對遠東國際關系的影響〔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5).
Prosperity and Crisis: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in the great change of Zoning system in Ming and Ding dynasties
Chi Sip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angsha District, 102488)
Abstract: Zoning relation in East Asia, which began with Western Chou dynasty and prospered in Ming dynasty. While, i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period for Zoning relation , coming from superlative to downfall during Ming to Ding dynasties. With the colneocolonialism getting involved , Qing dynasty failed to maintaining Zongfan system, though she had already done her best. The position and grad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uzerain and dependency were so specific that they would never be surpassed or confused. Qing governors was rejected by some dependencies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like Korea , because it wasnt eligible for the orthodox and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monarch and morality for Qing to be the master of Central China as a minority. Whats more, the international also gave them a shock. Qing dynasty hadnt made some alternativ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new society, but insisted old Zongfan system,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llapse of it and the backward 、aggression in the later stage of Qing dynasty.
Keyword: Eastern Asia;Zongfan relation;the period of Ming to Qing dynasties;prosperity;crisis;
責任編輯:林建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