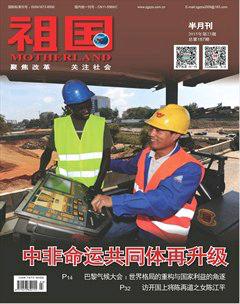巴黎氣候大會:世界格局的重構與國家利益的角逐
楊晨
張天平,國防大學軍事戰略學博士,軍事戰略學副教授。央視特約軍事評論員。曾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曾長期擔負國家軍事戰略研究、軍隊高級軍官的戰略教學和為軍委提供戰略咨詢的工作,提出了“信息和知識制勝”的戰略觀和創立了中國戰略信息戰的理論體系,著有《戰略信息戰研究》《戰略回顧與展望》《恐怖與反恐怖》(合著)等軍事著作;退役后,創立和構建了中國市場戰爭學的理論和戰法體系,著有《市場戰爭學》《市場信息戰》《市場謀略戰》和《市場攻防戰》等經濟類著作。參加過國家“863”計劃課題、國家“九五”重點課題、軍隊和國防大學重點課題,獲得過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國防大學科研成果一等獎等;在海內外發表戰略論文和評論數百篇;現為北京生態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長。
恐怖襲擊后,巴黎再一次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不久前結束的巴黎氣候大會迎來了1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大會并發表講話闡述中國對于全球氣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張。在發言中,習近平引用了法國作家雨果的話:“最大決心產生最高智慧。”只要各方展現誠意、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巴黎大會一定能夠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
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亟待解決“魚與熊掌同時兼得”問題:一方面要保持經濟穩步快速增長,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一方面又要控制污染,加強環境治理。此外,中國在積極參與國際氣候對話,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時,也要始終將國家和民族利益擺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并考慮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訴求,從戰略的角度出發,結合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通盤考慮我國接下來在相關領域的原則、立場。
日前,我國著名戰略專家,原國防大學軍事戰略博士、副教授,北京生態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長張天平博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談到:“國際氣候變化大會形成的最終協議將會影響未來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和走向。”
張天平認為,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國際經濟進入石油-美元體系時代,隨著全球對石油的需求大幅降低甚至停滯,且油價滑落,全球對于石油以及石油能源的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另一方面,隨著頁巖氣革命帶來的石油產量井噴式增長,導致了石油產量大幅升高;虛擬經濟繁榮、實體經濟萎縮的現實則又進一步導致全球對石油的需求疲軟,這些都嚴重威脅石油-美元體系地位。
美國自然不愿放棄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發現石油-美元體系來日無多,自然要尋求新的美元對價物,并與之建立起新的主宰世界經濟的美元對價物體系。而這種對價物,就是多年來國際氣候大會所討論問題當中的核心要素——碳。也就是說,石油-美元時代終結后,隨即導入碳-美元時代,這正是美國要打的如意算盤。
不僅如此,美國等西方世界為了拖住第三世界或新興經濟體發展的后腿,定然會大打“碳排放”的牌。眾所周知,第三世界和新興經濟體近年來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傳統工業和能源消耗型行業,這些都是碳排放較高的產業領域。一旦被要求大大降低碳排放量,其增長速度必然大大放緩;如果還要讓這一類經濟體系保持運轉,并保持碳排放“達標”,還必須從擁有環保產品技術優勢的西方國家進口環保設備。高額的環保投入,將大大增加傳統工業生產成本,而西方國家還能通過環保技術產品“打劫”傳統工業領域的“血汗錢”,從而導致對廣大第三世界和新興經濟體發展不利的局面。
相反,西方國家早已越過了傳統工業時代,并大肆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帶有嚴重污染的各種工業生產企業,其國內經濟主要依托于低碳行業或無須碳排放的經濟領域(如知識產權經濟和服務業),降低碳排放,對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什么影響。
我們說,為協調全球環境治理,共建人類美好家園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如果以降低碳排放為核心議題的氣候大會被少數西方國家操縱,成為擺布占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第三世界和新興經濟體、維系霸權國家地位的工具,那么這樣的“氣候治理”則會變味兒,最終也會由于多數國家的反對,無法達到全球協作減排的目的。
作為世界負責任大國、第三世界和新興經濟體發展中的“領頭羊”,中國直面國際氣候變化問題,近年來積極參與氣候變化相關國際事務,但同時,一些細節也充分體現出中國的原則立場:
2014年11月12日在北京達成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就明確提出:“(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要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考慮到各國不同國情”。
2015巴黎氣候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就以國際氣候治理為基點,對未來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嶄新的展望。他說,長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為發達國家所主導,被霸權主義、單邊行動、南北分歧所困擾,應對氣候變化舉步維艱。中國在國際氣候治理的架構過程中,率先推動合作共贏、公平正義、包容互鑒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強調應對氣候變化與經濟發展可以共贏,強調向綠色低碳發展轉型才是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出路,強調互惠共贏、共同發展這一國際治理的新模式。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氣候治理新體系的積極構建者,更將以此為契機擴大全球對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的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對目前的全球治理模式進行修正和重構”。因此習主席強調“巴黎協議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巴黎協議不僅是國際氣候治理的新起點,更是以合作、公平、包容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新起點。
此外,中國還將進一步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發揮更大影響力,宣布了中國推動氣候變化領域南南合作的新舉措,在今年9月宣布設立200億人民幣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基礎上,習主席宣布中國將在2016年啟動在發展中國家開展10個低碳示范區、10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及1000個應對氣候變化培訓名額的項目。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機制創造條件。
張天平說:“通過長期研究表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將環境、氣候、碳排放等話題早已列為遏制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層面加以考量,且其前后策略連貫性、體系性都很強。比如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主導下的世界銀行和西方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貸款援助時,就將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指標作為抵押物,那時第三世界國家對于碳排放根本沒有多少認識,又急需發展資金,就將碳排放指標‘廉價賣給了西方世界。使自己的碳排放權利降低,而西方卻因此得到了更多的碳排放權。而當西方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企業后,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突然高了上去,且又不能輕易把GDP的增長降下來,這時發展中國家發現自己的碳排放指標不夠了,于是只好向西方購買碳排放指標。這一時期,西方經濟轉型完畢,已經沒有多少污染企業,碳排放量本身就很低,卻把持大量碳排放指標,不僅通過向第三世界傾銷碳排放權大發橫財,還由此牢牢控制著世界經濟的主導權、話語權。此外,氣候大會將對未來世界的經濟產生深遠影響,通過碳排放制定未來世界經濟的規則。”
因此,中國絕不能在應對國際氣候變化的活動中缺少話語權地位,應當主動參與相關規則的制定,最大程度地使之契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并考慮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
“另一個方面還要重點談到網絡安全,我們說‘網絡安全將決定未來國與國之間的主權利益,以及企業及民間經貿往來的權利、義務。而未來的碳經濟,以及與碳對應的貨幣很大程度上將衍生為電子或數字表現形式,經濟活動的主體也將在網絡上進行。我們看到,不管是習近平此前訪美期間,中美在網絡安全議題上達成共識,以及雙方再次發表關于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還是在最近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之后,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郭聲琨訪美與美國司法部部長林奇、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遜共同主持首次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這些看似巧合的‘氣候變化-網絡安全新聞事件背后,似乎呈現著一種特殊的微妙關聯。”張天平說。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碳排放規則和網絡安全規則將決定未來世界的規則與走向。而中美這兩個與碳排放關系最為密切的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網絡產業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世界的未來。通過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變化大會和國際氣候治理行動,我們也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共同建設人類美好家園的信念與對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貫堅守,必然是我國參與包括國際氣候治理在內的一切國際活動與國際規則制定的原則和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