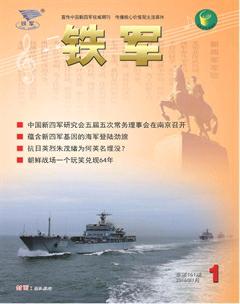云嶺的石柱
章熙建

皖南云嶺,時光把一段腥風血雨濃縮進了9根石柱。佇立圣潔石柱前,我在聆聽一組異曲同工的絕唱。軍人父親在槍炮聲中雕琢世界,山農父親則在敲鑿聲中演繹生命——那是一曲貫穿生命阡陌的美麗交響。
時光回溯到1941年1月初。寒風凜冽的皖南云嶺村,面對桌上的5塊銀元,默默吸著旱煙的云嶺村石匠詹順子,將目光投向妻子和她懷抱的女娃。兩年前的這個時節,山民生下才7天的女娃罹患蕁麻疹夭折。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女戰士張茜和軍法處楊干事找上門,商請他們幫一對新四軍夫婦奶孩子,孩子的母親因戰事顛沛擠不出一滴奶水。純樸的山民夫婦當時不假思索就應承下來。
而此時,新四軍軍部即將撤離云嶺北上抗日。山雨欲來,將士們都在做開拔前的應急處置。朔風呼嘯的黑夜,一雙軍人敲開詹家茅舍,昏暗的油燈亮到天明,兩個軍人裹著寒風悲壯離去,一個凄婉故事留了下來。
山民不知道,一場驚天浩劫正悄然向云嶺逼近。兩天后的凌晨,恬靜美麗的山坳驟然淪為刀光血影的煉獄。1941年1月6日晨,從皖南涇縣云嶺開拔北上抗日的新四軍部隊9000人,突遭國民黨軍7個師8萬重兵包圍襲擊,僅2000人突圍。
石匠帶家人藏進山后開采石料時發現的巖洞,每天趁黑潛回茅屋取些食物。數天后,刀戟相擊的詭譎喧囂漸漸散去,逃難避險的鄉親才陸續回返山村。但劫后的云嶺仍兇險四伏,探知尚有新四軍傷員藏匿密林,還有些新四軍后代寄養百姓家中,窮兇極惡的蔣軍展開篦子式搜捕,并頒發敕令:凡有窩藏者殺無赦,且株連家族。
風聲鶴唳的時刻,新四軍首長的囑托不時在詹順子耳畔回響:新四軍后代是紅色種子,必須哺育成人教育成材。目不識丁的山民深知,接納這個孩子對遭遇喪子之痛的妻子是短暫慰藉,帶給家庭的則是禍福難測。但縱然有險厄,又怎能跟新四軍拋家棄兒打鬼子相比!石匠和妻子連夜奔走數十里山路,將叫做萬牛的新四軍孩子送到山中遠親家中寄養,返回時未入家門就在村口被敵軍截住。他們翻箱倒柜搜查后將石匠帶走吊打到半夜,山民一口咬定自己孩子早已夭折。那個寒夜,詹妻頂著如刃寒風奔走于崎嶇山道,跌跌撞撞地敲開一家家茅舍跪求鄉鄰。終于,山民們舍命聯保才把遍體鱗傷的石匠抬回家。
夜夜驚心的日子里,山農惶惶然如履薄冰。那個黃昏,石匠打柴歸來路過村口老楓樹下,一個穿長衫戴墨鏡的陌生人攔住他,打聽是否知道有個老鄉家寄養新四軍女娃。雖然為小萬牛找到身生父母是縈繞心頭的期盼,可敵軍瘋狂搜捕的恐怖如寒夜夢魘般浮現,石匠漠然敷衍幾句便匆忙離去。
終于熬到鬼子投降,石匠憂郁的臉龐泛起了紅潤,小萬牛出落得聰穎可愛。山民時常獨自靜坐村口老楓樹下,眼神怔怔地投向山嶺盡頭的豁口,那是進出山村的門戶,他巴望那個濃眉大眼的新四軍如風飄臨。他甚至7次賣糧籌款,擱下農活外出找部隊,然而日升日落又一年,石匠始終沒有碰到奇跡出現。
1946年寒冬的子夜,石匠突然起床抽起悶煙,天剛亮就擔著兩筐新打的稻谷出了門。晌午返回踏進茅屋就把小萬牛緊摟懷里,對妻子說要送娃兒上學堂念書!
皖南群山綿延,自然資源豐饒。但日軍侵略帶來的兵燹之災,徹底打破了古老山村悠然自足的寧靜。春寒料峭時節,梳起羊角辮、穿上花格衣的詹家小囡,肩挎書包披著姐妹們羨慕的眼神走進學堂,而身后本已拮據的詹家從此更加度日維艱。許是出生時斷過奶水留下的禍根,小萬牛體質一直很孱弱,憨實的石匠巴望小豆芽能長得茁壯些。家中老少13口以粗糧甚至糠菜果腹度日,甚至將14歲的長女送往鄰村當童養媳,卻讓小萬牛獨享僅有的一點細糧。心生怨氣的姐妹們不知道父親心底藏掖一份痛楚,直到小萬牛13歲那年突然被部隊接走,石匠才向家人道出深藏心底7載的秘密。
那個寒風怒號的黑夜,熟睡中的石匠突被一陣剜心刺痛驚醒,四周靜寂如魅,而夢中的一幕卻沉沉壓在心頭:那個戴玳瑁眼鏡的斯文軍人,在那場山高水惡的激戰中愴然倒下,烈士手按噴涌鮮血的胸口,眼神殷殷地直瞅著石匠,似在訴說心頭無法割舍的一縷牽掛。
任職蕪湖軍分區之前,我曾多次拜謁云嶺石柱雕塑。而此刻,一段塵封的史實漸漸揭去面紗,無異于讓我陡然觸摸不朽石柱的靈動魂魄。純樸甚至有些愚鈍的山民,因勞累而過早佝僂的身子,竟在那一刻突然挺直了腰板。我甚至激情難抑地遐想,雖然紀念館尚未竣工山民即溘然辭世,但他無疑屬于圣殿建造者中最杰出的工匠,因那叢殘斷石柱上烙印著不屈生命的鮮亮鑿痕。準確說他遠在圣殿誕生前就已嘔心瀝血完成作品,即濃縮原本式微的生命薪火,淬煉了烈士遺孤特別的脊骨與內質。
時光再次回溯64年前。1952年初冬清晨,小萬牛陡然察覺到茅屋里外氣氛異常。母親早起給她備好干凈衣裳,灶臺上剛煨好的雞湯散發濃香,早餐是雞湯面加荷包蛋。父母端坐桌前似乎愁腸百結地愣瞅著,待萬牛碗中湯面見底,母親臉上淚珠霎時連成了線。
太陽剛升上東山坳,村口老楓樹下來了輛軍用吉普。懵懂而又興奮的小萬牛被送上軍車,父母只說是部隊首長接她去城里念書。幾天后輾轉進入坐落南京衛崗的華東軍區干部子弟學校,13歲的詹萬牛被插班小學二年級。可姑娘驀然發現一切都顯得陌生怪異,班上同學大多是沒爹娘的烈士遺孤,自己名字也突然被改成孟烈。倔強的山里姑娘找到老師,生來頭一次流下委屈的淚水:我有爸媽,我要回云嶺回自己的家!
于此,我查閱資料梳理出一縷脈絡:1952年深秋,中央老區訪問團到云嶺,除正常工作外還擔負一項特殊使命,即受陳毅夫人張茜大姐托請尋訪一個烈士遺孤。許是戎馬倥傯十多年,張茜依稀記得女孩父親姓孟,母親叫李辛。因線索尚不夠連貫完整,訪問團同志與蕪湖軍分區領導頗費一番周折,最后鎖定云嶺村的詹萬牛。
然而,托孤父母都是攜筆從戎的軍中翹楚,緣何給孩子起名萬牛呢?軍分區領導推斷這不合情理中定存蹊蹺,如不能還烈士遺孤一個清晰完整的身世謎底,尋訪任務或屬于未竟甚至失敗。于此他們寫信給中央訪問團,請他們聯系張茜大姐進一步補充核對線索。數月后收到北京來信,這時改名孟烈的詹萬牛狀態漸趨穩定。軍分區領導反復斟酌后決定暫時將信壓下,以免讓經受命運顛沛的姑娘因此再一次心生波瀾。
轉眼到孟烈初中畢業,軍分區領導借出差特地將姑娘接回云嶺。一別8年,詹家茅屋東側新砌了敞亮瓦房,而曾經的山村黑丫頭則變成了城里俏姑娘。依舊是當年那盞油燈前,軍分區領導掏出8年前那封北京來信,將姑娘身世的來龍去脈細捋了一遍。
姑娘生身父母叫孟星野和李辛,當年都是新四軍軍部干部。戰爭倥傯,皖南事變爆發前兩天的告別,隱隱中已蘊含托孤之意。戰友們商量臨別得給只有乳名楠楠的孩子取個大名,戰地服務團才女張茜一錘定音:征戰此去無歸期,孩子是新四軍留在皖南的紅色種子,就叫“皖留”吧!
至于何以陰差陽錯被叫作“萬牛”,蕪湖軍分區領導推測,或歸于不通文墨而聽音隨俗的緣故,抑或為隱瞞真情而化繁就簡所致。而于托夢之說亦經查證得知,李辛在皖南事變突圍中與戰友失散,而孟星野確于1946年冬在山東前線犧牲。
那個恍如隔世的夏夜,暗自啜泣的姑娘徹夜未眠。清晨旭日東升,姑娘掀開的生命冊頁落下濃重心跡,她告訴父母改回本名孟皖留。暑假的兩個月里,姑娘白天隨母耕作田間,夜晚茅屋服伺慈父,那份勤勞孝悌讓整個云嶺山坳都為之羨嘆。暑期結束后孟皖留返校升讀高中,然而,一道無法抗拒的扯拽時時讓她心馳神往。
那是回返山村跨進家門的一刻,石匠父親因腰傷正側臥在茅屋竹躺椅上。青磚瓦房落成3年,可倔犟的石匠仍貓在老茅屋堅守一抹殘留的溫馨。姑娘疾奔向前緊緊抓住那雙幾近枯槁的手,淚水霎時如小河決堤般流下來。淚眼朦朧間,竹躺椅側面一尊半身石刻像倏然閃入眼簾,那依稀就是自己8年前離家時的青澀模樣。
紅繩綰扎的長辮斜掛胸前,瞳仁綻射稚氣與憧憬,那是一株生命力蓬勃的戰火嫩苗。3000個日夜呵,篤實情重的父親就把對女兒的思念,傾注于一錘一釬的雕鑿中!還有那只楓樹根雕基座,修長虬勁的根蔓似乎要扎透地面,那是否在訴說一種根對于土壤的渴望,讓遠方的游子感應血脈的呼喚?
或許原本就屬于沸騰的血液就在那一刻被激活的。文靜寡語的孟皖留突然著迷于學校圖書館,她默默而艱辛地跋涉于皖南典故和新四軍史料,恰似給心頭點燃的夢想篝火添薪打底。終于,高中畢業那年,姑娘悄然辭別寄存瑰麗夢想的南京,一如父母當年開拔征戰般回返云嶺,她無法回絕山村茅屋那尊石像魂牽夢縈的呼喚。
再次凝目聳立天地間的圣潔石柱,那真正是一束不能釋懷的雷霆閃電,一道時代不能遺忘的斑斕背影呵!
兩根完整石柱背襯藍天傲然挺立,猶如2000突圍將士正翱翔蒼穹追逐夢想;7根殘斷石柱身枕青山凜然如磐,仿佛7000犧牲失散將士正熔鑄音符揮筆史詩。矚目的一瞬,驀然感覺碑身在晃動,呵!那絕非云動抑或地搖,而是心在那一刻臨風飄舉,飛向無垠天際。蒼穹深處仿佛回響《戰爭與和平》中的經典,那是娜塔莎對歷經劫難的皮埃爾說:“你就像這古老建筑,飽經滄桑,但屹立不倒!”
我突然詩意地遐想,孟皖留或許只是無數寄養百姓家的英雄兒女中的一個,但烽火洗禮賦予英雄女兒許多生命奇緣,更有一種執著讓她把生命鑄成了傳奇。遠離戰火的歲月里,英雄女兒定然時常佇立肅穆圣園,平靜而深情的目光長久凝注于石柱,就像透過時光煙云追尋遠行的英雄父輩。
心念瞬間貫通,是追尋!這個字眼讓我豁然理喻一個烈士女兒的超常之舉,因為血液傳承一個信念:“英雄”二字雖寥寥數筆,卻是不朽生命凝鑄的精神坐標,值得這個民族用永恒的意志去丈量與追尋! (責任編輯 王浩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