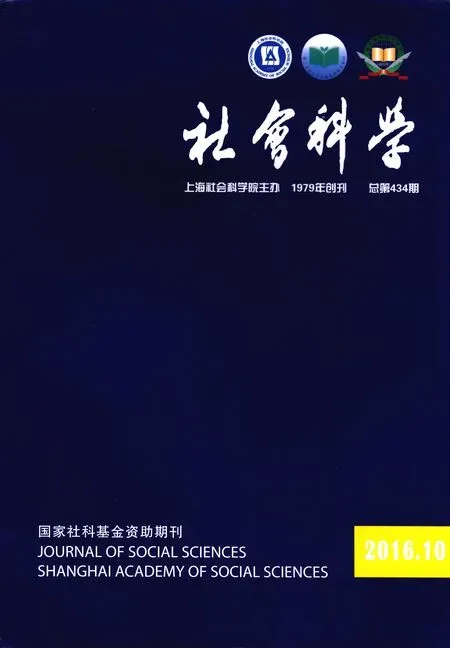歐洲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再探
劉林海
?
歐洲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再探
劉林海
貧困是困擾16世紀歐洲的一大社會問題,也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內容。濟貧改革超越了基督教的教派界限,具有普遍性。它打破了傳統的理論和實踐模式,確立了新的規范,為近代歐洲福利制度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學術界對濟貧改革的斷裂、連續和后現代政治理論等模式的解讀,有助于不斷深化認識,但也存在一些誤區,如將宗教因素排除在外,割裂具體的歷史環境等。宗教動機與濟貧改革相始終,這也是它區別于西方后來福利改革的關鍵。在對濟貧改革的解讀中,作為主角之一的宗教應該始終在場。
宗教改革;濟貧問題;宗教與濟貧改革
16世紀前后,隨著歐洲經濟等變化,貧困問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普遍關注。隨著宗教改革的推進,濟貧改革也如火如荼展開。與以往相比,宗教改革時期的社會濟貧改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為現代歐洲福利制度的發展奠定了有利條件。19世紀后半期以來,隨著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也逐漸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被作為認識16世紀歐洲社會變革的重要切入點。20世紀中期以來,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激增,也出現了幾種代表性的研究模式,從而不斷深化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國內學術界對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研究起步較晚,成果較少,多集中在英格蘭都鐸王朝。本文在簡略勾勒這個時期的貧困問題的基礎上,對幾種代表性的認識模式進行分析,同時對宗教因素在16世紀濟貧改革中的作用做進一步的思考。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討論這個時期濟貧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的具體情況*相關內容可參閱拙文《從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時期基督教濟貧觀念的變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一、 貧困問題及濟貧改革
貧困問題是16世紀前后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圍繞貧困問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社會改革之一。學術界一般認為,盡管歐洲的貧困問題并非產生于這個世紀,但它真正引起社會各界的嚴重關注,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難題,卻是在這個時候。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導致貧困成為社會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戰爭、疾疫、自然災害、貨幣貶值、物價上漲、人口增加、失業等。對于16世紀的歐洲人而言,這些現象都是司空見慣的,而上述任何一種災難都足以使大批人陷于貧困*E. M. Leonar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Relie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00, pp.14-17.。當然,也有深層的經濟結構變化的因素。16世紀前后,西歐的封建制開始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興起。越來越多的農奴獲得人身自由,農業人口逐漸減少。在英國,圈地運動的發展將越來越多的農民趕離土地,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土地,同時又找不到工作。這些人涌入城市,或者乞討或者流浪*Thomas A. Brady ed., Handbooks of European History 1400-1600, Vol.1, Brill, Leidon, 1994, pp.1-50, pp.113-146。于特(Robert Jütte)分析了造成貧困的偶然因素、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4, pp.21-44.。
此外,宗教觀念也與貧困問題關系密切。古代基督教對貧困及乞討的態度與傳統希臘羅馬有所不同,整體上肯定其在宗教生活中的積極作用。隨著基督教地位的變化及在歐洲的普及,教會逐漸形成一種觀念,使貧困及與之相關聯的乞討行為在宗教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使之成為人救贖的重要砝碼。按照這種理論,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美德,窮人比富人更受神的青睞,在未來的救贖中占據有利位置。與此相反,富人及財富則被視為救贖的障礙。富人要想獲得神的青睞,需要通過付出財物等方式贖罪,而對窮人等的施舍被視為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富人在物質上幫助窮人,以此積累救贖的資本;作為精神上的富有者,窮人則通過祈禱祝福等幫助富人,雙方形成一種互惠的交換關系。4世紀的米蘭主教安布羅斯曾聲稱“施舍可以贖罪”*B. Ramsey, Almsgiving in the Latin Church: The Late Fourth and Early Fifth Century, Theological Studies, 43, 2, 1982, p.242.,9世紀的朗斯主教辛克馬則說,“神本可以使所有的人都富有,但他愿意世界上有窮人存在,以便富人有一個贖罪的機會”*Carter Lindberg, Beyond Charity: Reformation Initiatives for the Poor, Augsburg Fortress, Minneapolis, 1993, pp.32-33.。這種理念的形成和流行具有顯著的社會效果。一方面,它強化了教會等宗教機構的社會救濟職能,從理論中演化出一套復雜的實踐體系;另一方面,還催生了眾多的貧困者,為貧困及其衍生的乞討行為提供了積極的理論支持。12世紀末以來,隨著社會上以效法基督過赤貧生活觀念的流行,很多人尤其是新興的各種托缽修會自愿貧困,把以乞討為生的赤貧生活作為侍奉神的方式。方濟各會的章程規定,修士們要“在貧困和謙卑中侍奉神,讓他們自信地去祈求施舍,他們不應該為此感到羞恥,因為主為了我們使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窮困。……這是最崇高的貧困的頂峰,它使你們成為天國的繼承者和王:在財物上貧困,但在美德上超群”*P. Robinson trans., The Writings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The Dolphin Press, Philadelphia,1906, p.69.。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進一步擴大了乞討的群體,致使魚龍混雜,增加了社會的負擔,也加重了社會的貧困。德國1523年的《陳情書》第八條對于托缽會的乞討造成的社會危害有深刻的描繪:“在托缽修會的乞討制度下,城鎮或鄉村的每個地方沒有不被他們侵擾的。他們因游蕩范圍受到限定而被稱為有條件乞討者(Terminaries)。他們違反了會章的規定到處巡回,這并非為生計所迫,而是受無法滿足的貪欲的驅使,是毒瘤。因為有時在一個人口并不多、面積也很狹小的村子里,就會發現兩三個甚至更多的這些家伙們的聚會所,里面堆積著搜刮來的各種施舍。與此同時,那些攜妻帶子的市民或居民們,他們誠實自立,付出辛勤勞動和汗水,卻被疾病和年老耗盡并陷于窮困,因饑餓和缺少食物而死亡。”*Charles Hastings Collette ed., One Hundred Grievances, S. W. Partridge & Co., London, 1869, p.195.
貧困問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乞討行為劇增,乞丐泛濫,變成突出的社會問題。從歐洲大陸到英倫三島,乞丐的泛濫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1525年,弗蘭德爾的伊普雷市(Ypres)濟貧法令序言說:“這么一大批窮人和生活窘迫的人(他們遍布每條街道和每個教堂,以及每家門前,實際上遍布這個王國境內的每個地方,無所事事,淫邪放蕩,他們生活貧困,習慣于像流浪漢那樣到處游蕩)需要救濟、援助和幫助。”*The Ypres Scheme of Poor Relief, in F. R. Salter, Some Early Tracts on Poor Relief, Methuen, London, 1926, p.33.幾十年后英格蘭的哈里森則說“現在的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共和國沒有一支龐大的窮人隊伍,以及那些急需富有者救濟的人,否則他們就將餓死并陷于完全的混亂”*Lothrop Withington ed., Elizabethan England: From “A Description of England”, By William Harrison (in “Holinshed Chronicles”), Walter Scott, London, 1876, pp.122-129.。
乞丐的泛濫及規模可以從當時遺留下來的相關資料中窺見一斑。一方面,乞丐及其造成的危害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素材,是伊拉斯謨、莫爾、莎士比亞等人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主題,甚至形成了乞丐文學。另一方面,乞丐的行業化程度不斷加深。社會上不但存在眾多的兄弟會性質的乞丐組織甚至行會,而且出現了許多關于乞丐的專題文獻甚至手冊指南,這一點在乞丐問題最突出的英格蘭尤甚。1514年,德國出現了一個匿名的小冊子——《乞丐手冊》(LiberVagatorum), 里面詳細描繪了各種各樣的乞丐、乞討術,并附了很多實例。該小冊子的第一部分記載了28種乞丐,而在作者看來,這些人并非真正的乞丐,而是打著行乞的口號干各種不道德甚至違法亂紀的勾當*Martin Luther ed., The Book of Vagabonds and Beggars, with a Vocabulary of Their Language, edited by Martin Luther in the year 1528, John Camden Hotten trans., John Camden Hotten, Piccaadilly, London, 1860, pp.7-42.。在英格蘭,1561年,奧德利(John Awdeley)出版了《乞丐兄弟會》(FraternityeofVacabondes)。1566年,英格蘭的托馬斯·哈爾曼(Thomas Harman)撰寫的《當心乞丐》一書出版。這些著作對乞丐及其騙術等做了分類敘述,其中前者羅列了20多種乞丐及騙術,后者則更加詳細地對乞丐行業做了描述*John Awdeley, The Fraternity of Vagabonds,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Extra Series, IX, London, 1869, pp.1-16; Thomas Harman, A Caveat or Warning for Common Cursetors, Vulgarly Called Vagabonds, London, 1814.。1577年,哈里森在《英格蘭風物志》中則列出了14種男乞丐和9種女乞丐*Lothrop Withington ed., Elizabethan England: From “A Description of England”, By William Harrison, p.128.。這些著作不但對于乞丐種類和行乞騙術有詳細記載,而且還匯集了乞丐的行話。乞丐隊伍的規模從中可見一斑,乞丐已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
乞丐的泛濫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危害。龐大的寄生階層尤其是乞討隊伍耗費了大量的資源,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馬丁·路德曾經估算過,除去繳給教會和世俗政府的稅之外,如果把各種托缽修會和形形色色的乞丐加起來,“一個城鎮加起來每年就要被勒索60次”*Martin Luther,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II, A J. Holman Company, Philadelphia, 1916, p.135.。英國新教徒西蒙·費什(Simon Fish)在《為乞丐祈愿》(1529)中也曾做過測算。當時英格蘭有52000座堂區教堂,按照每座教堂有10戶人家計算,共有520000萬戶。每戶人家每季度給5個乞討的托缽修會修士各一便士,一年就是20便士。全國加起來,每年就是43333磅6先令8便士*Simon Fish, A Supplication for the Beggars,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Extra Series, XIII, London, 1871, pp.2-3.。此外,乞丐泛濫還造成社會的勞動力缺乏,影響了正常的經濟生活。而當時歐洲社會因戰爭、疾病、災荒等急需勞動力。不僅如此,他們還擾亂了社會的正常運轉。這些人并沒有固定的居所,他們涌入城市,在街道、教堂等公共場所擾鬧喧嘩,騷擾市民,許多人欺詐、偷盜、搶劫,甚至組成了兄弟會*Carter Lindberg, Beyond Charity: Reformation Initiatives for the Poor, p.44.,成為犯罪的淵藪,成為城市社會治安的隱患。乞丐們大都衣著邋遢,不講衛生。大量的流動人口給城市的健康衛生帶來挑戰,他們也被視為瘟疫等各種傳染疾病的重要傳播源*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C. Matheeussen, C. Fantazzi, eds., Brill, Leiden, 2002, II. i.3.,而16世紀前后歐洲各地正是傳染病頻發的時期。
乞丐的泛濫還造成嚴重的社會道德問題。在龐大的貧困隊伍中,有很多的假冒者。這些人身體健康又不愿意勞動,他們假冒貧困,專門靠救濟生活,有些人甚至同時在多個機構領取救濟*Brian Pullan,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 State, to 1620,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71, pp.197-286;Thomas Max Safley ed.,The Reformation of Charity: The Secular and Religious in Early Modern Poor Relief, Brill, Boston, 2003, p.78.。更多的假冒者則加入乞討隊伍,把乞討變為一種發財致富的職業。他們用各種欺騙的手段騙取施舍*Carter Lindberg, European Reformations: Source Book,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2000, p.70.,甚至武力搶劫。有些乞丐為了發財,不僅自殘肢體,而且殘害自己或別人孩子的肢體,甚至用“病弱或綁架的兒童,以博得施舍者更多的同情”,“這些人很富有,但他們卻乞求施舍”*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 v.4.。他們拒絕任何改變其處境的幫助,有些家長甚至寧愿讓孩子去乞討,也不愿意去勞動,因為乞討更能賺錢。而那些自愿貧困的人,尤其是托缽修會的修士,雖然他們標榜個人的貧困,但在整體上卻是最富有的群體,囤積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教會里面腐敗盛行,教士們無所事事,甚至把本應該用作救濟的財物挪作他用,致使真正需要得到救助的得不到救濟,背離了濟貧的初衷*Martin Luther, On Trade and Usury, William I. Brandt ed., Luther’s Works, Vol.45, Muhlenberg Press, Philadelphia, 1962, p.284.。
乞丐的泛濫只是歐洲貧困問題的一個方面,它并非單一的國家或局部現象,而是整個歐洲面臨的共同難題,因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
首先是新教改革家。作為宗教改革的旗手,馬丁·路德非常關注貧困問題,并先后在《致德意志貴族公開書》、《論貿易與高利貸》等著作中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提出批判,呼吁濟貧改革*Martin Luther, On Trade and Usury, pp.286-287.。1520年,他曾經為維登貝格市起草濟貧改革法令,并建議設立濟貧公共基金,他的相關思想和主張集中體現在1523年萊斯尼希市頒布的濟貧法令中。路德不但為該法令撰寫了序言,全力支持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希望它成為其他城市改革的范本*Martin Luther, Preface to Ordinance of A Common Chest, Suggestion on How to Deal with Ecclesiastical Property, William I. Brandt ed., Luther’s Works, Vol.45, pp.169-176.。為了讓人們認清乞丐的真面目,馬丁·路德在1528年還專門編輯出版了《乞丐手冊》一書,并撰寫了前言,匯集了乞丐的行話,供人們閱讀,以辯真假*Martin Luther ed., The Book of Vagabonds and Beggars, Luther’s preface.。路德對乞討的批判及其對濟貧改革的設想在德國新教內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黑森的菲利普選帝侯在1524年進行改革。路德的社會濟貧思想后來經約翰·伯根哈根的努力,在各地推廣*Walter M. Ruccius, John Begenhagen Pomeranus, A Biographical Sketch, the United Lutheran Publication House, Philadelphia, 1924.。后來轉向激進派的卡爾施塔特也曾撰文討論乞丐問題,呼吁禁止乞討*E.J. Furcha ed. and trans., The Essential Carlstadt: Fifteen Tracts by Andreas Bodenstein(Carlstadt) from Karlstadt, Herald Press, Waterloo, 1995, pp.120-128.。著名的改革家馬丁·布克爾曾經專門撰文討論濟貧改革問題,他不但在斯特拉斯堡等地推行改革,還向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六世建議,實行包括濟貧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Martin Bucer, De Regno Christi, in Wilhelm Pauck ed., Melanchthon and Bucer, The Westminster Press, Philadelphia, 1969, pp.256-259, pp.306-315; A Treatise, How by the Worde of God, Christian Mens Almose to be Distributed, 1557(?).。加爾文在著作中有專門的論述,濟貧改革也是他在日內瓦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Robert M. Kingdon, “Social Welfare in Calvin’s Genev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1, Vol.76, 1971, pp.50-69;“Draft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 in Calvin :Theological Treatises, The Westminster Press, Philadelphia, 1978, pp.64-66.。
其次,貧困問題也引起了包括人文主義者在內的公教徒的關心。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在自己的著作中有相關的論述*From Carter Lindberg, Beyond Charity: Reformation Initiatives for the Poor, pp.186-189.。1526年,旅居布魯日(Bruges)的西班牙著名人文主義者維威斯(Juan Luis Vives)發表了《論對窮人的支持》一書,針對該城的狀況,系統提出了濟貧改革的設想。維威斯的建議雖然沒有被采納,但其詳備的討論和周全設想卻成為這個時期最著名的濟貧專論。他的規劃也成為其他許多地區改革的樣本,對尼德蘭、神圣羅馬帝國、法蘭西、西班牙乃至英格蘭等地的濟貧改革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529年,里昂的人文主義者沃策勒(Jean de Vauzelle)呼吁市政府改革。1535年,耶穌會的創始人羅耀拉在自己的家鄉西班牙的阿斯佩蒂亞(Azpeitia) 幫助市政府實施濟貧改革。1545年,多明我會修士德索托(Domingo de Soto)和本篤會修士墨迪那(Juan de Medina)還就濟貧問題展開了爭論*關于這個時期濟貧專論目錄,參見Robert Jütte,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ppendix。爭論的主要內容見:Michele L. Clouse, “Medicine, Government, and Public Health”, in Philip II’s Spain: Shared Interests, Competing Authorities, Ashgate, VT: Burlington,2011, pp.153-156.。
在學者們進行理論思考的同時,歐洲的世俗政權紛紛開始了立法活動,從而開啟了新一輪的社會濟貧改革。世俗政權的濟貧改革分為以城市為中心的市政府改革和國家范圍的改革。按照時間的先后,改革的城市主要有:威尼斯(1495)、奧格斯堡(1522)、紐倫堡(1522)、萊斯尼希(1523)、黑森(1524)*William J. Wright, “Reforma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Policy in Hess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9, 2,1977, pp.1145-1179.、蘇黎世*F. R. Salter, Some Early Tracts on Poor Relief; Lee Palmer Wandel, Always Among Us: Images of the Poor in Zwingli’s Zuri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3, appendix A,B.(1525)、伊普爾(1525)、巴黎(1529-1530)、里昂(1531)*Natalie Zemon Davis, “Poor Relief, Humanism, and Heresy”,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65, pp.17-64.、魯昂(Rouen)(1534)*F. R. Salter, Some Early Tracts on Poor Relief, pp.104-119.、圖盧茲(Toulouse)*Beckerman Davis, Barbara, “Reconstructing the Poor in Early Sixteenth-Century Toulouse”, French History, 7, 3, 1993, pp.249-278.(1534)、布魯塞爾(1534)等。1535年,羅耀拉幫助自己的家鄉實行濟貧改革*改革全文見Henry Dwight Sedgwick, Ignatius Loyola: An attempt at an Impartial Biograph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3, pp.153-155。。此外,日內瓦*Robert M. Kingdon, “Social Welfare in Calvin’s Genev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1, 1971, pp.50-69.、荷蘭*Charles C. Parker,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Social Welfare and Calvinist Charity in Holland, 1572-16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8;Timothy C. Fehler, Poor Relief and Protestantism: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Sixteenth-Century Emden, Ashgate, VT: Burlington, 1999.、西班牙*Linda Martz, Poverty and Welfare in Habsburg Sp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3(2009).等地的一些城市也先后采取了改革措施。在這些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普爾市。該市從1525年實施改革,到1529年,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F. R. Salter, Some Early Tracts on Poor Relief, pp.66-72.。伊普爾的改革還成為其他城市或國家改革的范本,與維威斯的濟貧計劃一起,成為宗教改革時期歐洲濟貧改革理論和實踐的典范。
改革也在國家層面展開。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1531年10月頒布了在帝國境內禁止乞討的法令。1536年,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下令每個堂區要對自己的窮人進行登記造冊,對沒有能力的窮人實行救濟,資金來源于個人自愿捐助,由教士負責管理。每個堂區設立一個貧困捐獻箱,供信徒每次禮拜時捐獻。此外,原來流傳下來的固定的私人濟貧基金也作為一個來源。身體健全的乞丐必須勞動,否則受到懲罰。1540年,西班牙的卡斯蒂爾頒布《貧困法》(Poor Law)。總體而言,到16世紀中期,包括新教和公教政權在內,歐洲大陸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先后立法或采取措施,進行濟貧改革。
濟貧改革同樣在英格蘭進行。與歐洲大陸相比,英國的濟貧改革無論是在規模和深度上都是比較突出的。由于其經濟發展較快,經濟結構轉型較早,造成大量的人員離開土地,引發乞討及流民問題。此外,16世紀英格蘭人口增長快,通貨膨脹加劇,因此,其貧困問題也就尤其突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的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局面*傳統認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切斷了大量的濟貧資源,眾多濟貧機構的消失使很多窮人得不到救濟。不過,這種觀點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有人認為修道院的解散整體上影響不大。最近的研究表明,傳統的觀點在整體上是成立的,但其影響更多在于把大量相關人員推向勞動力市場,從而加劇了本已嚴重的貧困問題。。英格蘭的改革也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的,一個是地方改革,尤其是城市的改革,一是國家層面的改革。相對而言,城市層面的時間較早,并在改革的前半期發揮主導作用。如倫敦從1514年起就試圖采取立法措施改革濟貧工作。國家層面的改革始于1530年代,并逐漸發揮了主導作用。1530年,亨利八世發布聲明,指出“無所事事是萬惡之源”,下令鞭笞乞討者。1531年,《流浪漢法案》獲批,取代了1495年亨利七世頒布的《流浪漢與乞丐法案》。該法案區分了對乞討的真假貧困,在懲罰假貧困者的同時,對真正貧困的人實行乞討資格證制度。1536年,英格蘭再次立法,確立了以下幾條原則:為失業者提供工作機會;乞討是錯誤行為,社區對無助者負有義務;堂區作為救助機構,必須對此實行監督。此后,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期間,分別在1547年、1549年、1551—1552年頒布了相關法令,對濟貧、乞討、資金募集等做了規定。伊利莎白一世時期,英格蘭的濟貧改革繼續推進,相繼在1563年、1569年、1572年、1594年、1597年和1601年頒布法令。1601年法令的頒布與實施,最終確立了全國性的救助體制和強制性救濟稅制度,奠定了英國現代救濟制度的一般原則*E. M. Leonar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Relie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00; Paul A. Fidelex, Societas, “Civitas and Early Elizabethan Poverty Relief”, in Charles Carlton, A. J. Slavin eds., State, Sovereigns &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ssays in Honour of A. J. Slavin, St. Martin Press, New York, 1998, pp.59-69.。
二、 現代學術視野中的濟貧改革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研究,西方學術界對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也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就實踐層面而言,主要有:原先分散的濟貧資源得到整合與集中,公共基金體制建立;私人的直接濟貧(施舍)被禁止,機構化的運作成為主體;濟貧的運作集中化,出現了專職的機構及管理人員;普遍設立資格審查制度,以區分真假貧困,規范乞討行為(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禁止乞討,有些地方為符合條件的發放乞討證);消極的救助轉變為積極的幫助,為貧困者提供教育、職業培訓等,以便擺脫貧困。從觀念層面來說,最主要的就是中世紀盛行的互惠救贖觀念被打破,貧困及乞討與救贖的關系被否定,濟貧的宗教意義由互利轉向展示基督教的仁愛精神,濟貧自愿色彩減弱,強制色彩增加。
學術界雖然對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有不少共識,但在總體定位上還存在較大差異。從對該問題研究的整體影響而言,以下幾種模式值得注意。
第一種認識模式是宗派式的,主要強調新教在改革乃至現代西方福利國家的創造性貢獻,是斷裂式的。19世紀后期以來,學術界對于新教改革的評價很高,將它與現代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等聯系在一起,充分肯定新教與現代西方社會的內在關聯。宗教改革時期的一些措施也被視為歐洲世俗化的開端。與此相反,公教會卻被視為落后保守的同義語。這種判斷在著名的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的著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韋伯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聯系在一起,提出宗教觀念對歐洲現代資本主義成長的重要作用*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Capitalism, Talcott Parsons tra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0.。他認為,作為一種獨特的倫理體系,新教尤其是清教倫理雖然在無意中孕育了后者,但其帶來的經濟后果卻對這個時期的濟貧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摧毀了傳統的慈善形式,為清教打破傳統濟貧觀念及體制的革命奠定了基礎*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 s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8, pp.588-589.。特勒爾奇則認為加爾文派的理論是適合現代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其社會理論是一種革命,拋棄了中世紀教會乃至路德派的觀念,對于新的制度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Christian Churches, Vol.II,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Kentucky, 1992, p.577.。英國學者R. H. 托尼(R. H. Tawney)則積極評價了清教濟貧改革的新舉措*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apitalism, Gloucester, MA: P. Smith, 1962, pp.253-273.。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新教也被視為這場濟貧改革的推動者和領導者,新教的宗教觀念則從理論上提供了支持,對于歐洲近現代濟貧制度乃至福利制度的形成意義重大。
第二種模式則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入手,試圖超越狹隘宗派觀念,探討引發改革的深層社會經濟原因。在這方面,美國史學家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英國史學家普蘭(Brian Pullan)是其中的代表。他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關于濟貧問題的傳統觀點。
首先是濟貧變革的動因。在他們看來,嚴峻的現實問題,如戰爭、瘟疫、自然災害,以及經濟問題,如失業、貧困人口增加、勞動力缺乏等,是各種改革措施出臺的直接動因。這些問題危及到社會的正常秩序,迫使各界采取措施,改革與宗教觀念沒有關系。戴維斯認為,近代早期濟貧改革的動力在于“城市危機,是由較為古老的貧困問題和人口增長及經濟擴張結合而致的”*Natalie Zemon Davis, “Poor Relief, Humanism, and Heresy”,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aasys, p.59.;普蘭也認為,變革的動力在于“更為巨大的經濟需求,而非思想觀念的激進改變”*Brian Pullan,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 State, to 1620, p.189.。其次是改革的群體。在他們看來,濟貧改革并非新教的專利,公教會同樣是改革的積極實踐者。濟貧改革是這個時期歐洲的普遍現象,與宗派無關。戴維斯指出,這個時期的濟貧改革實際超越了宗派乃至階層的界限,新教、公教會、人文主義者不約而同地采取相同的措施,甚至“協同努力”*Natalie Zemon Davis, “Poor Relief, Humanism, and Heresy”,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aasys, p.35.,推進改革的進程,確立新的集中化的救濟體制。再次是改革起源問題。普蘭指出,在濟貧改革方面,真正的先驅是公教而非新教。16世紀二三十年代實施的改革措施,實際在14和15世紀就已經出臺了。對于流浪人員的立法限制、建立集中化的救助醫院體制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經在英格蘭和北意大利出現了,甚至12世紀的教會法學家也曾經提出不要不加分別地施舍。中世紀晚期公教會的許多改革措施已經為未來的活動奠定了基礎,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濟貧制度。它所表現出的特征與新教沒有分別,甚至在有些地方(如募集資金給窮人提供低息貸款等措施)要遠優于新教。最后是改革的定性。在經濟社會史家看來,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整體上并沒有新奇之處,只不過是15世紀的延續。普蘭認為,“很有可能是,16世紀在慈善和社會立法方面的變化是程度而非性質的變化,是量變而非質變,是由巨大的經濟需要而非思想態度的劇變促成的”*Brian Pullan,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 State, to 1620, p.189.;“無區別的、教會主導的‘中世紀’慈善與有區別的世俗控制的‘早期近代’社會政策之間實際上并沒有鮮明對比”,“在16世紀威尼斯的公教政府里面,威尼斯政府與公教會內部新興修會對貧困問題的態度沒有明顯分歧”*Brian Pullan,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 State, to 1620, p.198.。
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中世紀史家蒂爾尼(Brian Tierney)就曾指出,中世紀教會法里的濟貧體制與近現代西方濟貧體制之間有內在連續性。“現在流行的觀點似乎是,通過立法規范濟貧制度并由公共權威操作的貧困法,主要是16世紀的一個發展……實際上,中世紀世俗立法的零星片段表明,只要是意在濟貧而非抑制流浪乞討,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不過是重現了教會法學家著作中的原則,后者包含了該領域內中世紀法律的主體。”*Brian Tierney, Medieval Poor Law: A Sketch of Canonical Law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pp.5-6.就英國的情況而言,“事實當然是,教會法的濟貧制度在英格蘭從來沒有‘中斷’(break down)過。盡管它的不完善之處日益增加,它仍然延續到16世紀,為都鐸王朝的世俗貧困法奠定了基礎”*Brian Tierney, Medieval Poor Law: A Sketch of Canonical Law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and, p.128.。雖然他研究的側重點仍在政治(他認為中世紀的教會就是一個世俗政權),但他也強調社會及經濟環境的巨變使原先的機制失去效率,強調發展的連續性*Brian Tierney, Medieval Poor Law: A Sketch of Canonical Law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and, p.110ff.。因此,他無疑是這方面的先行者。
第三種模式以近代國家及公共權力的形成為出發點,將這個時期的濟貧改革視為政府和貴族對社會弱勢群體,尤其是對窮人的社會規訓和懲罰過程(social discipline)。德國史學家奧斯特里奇(Gerhard Oestreich)及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是主要奠基者。
20世紀60年代末,奧斯特里奇在研究歐洲絕對君主制的形成問題時提出,當時歐洲對包括貧困問題在內的應對措施,是一種社會規訓。奧斯特里奇的“社會規訓”概念與20世紀50年代最早由德國史學家澤登(Ernst Walter Zeeden)提出的“認信化”(Confessionalization)理論有相同之處,雙方關心的大主題與絕對君主制有關,后者也將社會控制視為“認信化”的一個主要特征。1970年代末以來異軍突起的“認信化”研究模式就是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Robert van Krieken, “Social Discipline and State Formation: Weber and Oestreich on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Subjectivity”, Amsterdams Sociologisch Tijdschrift 17, 1, 1990; Susan R. Boettcher, Confessionalization: Reformation, Religion, Absolutism, and Modernity, History Compass, 2, 2004.,是濟貧改革研究的新理論來源之一。福柯在研究癲狂及監獄等問題的過程中提出了“大囚禁”(great confinement)理論。他認為,歐洲16、17世紀進行的各種社會濟貧改革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17世紀巴黎的以總醫院(HpitalGénéral)為中心的濟貧改革措施,實際上是對社會群體中的一部分人的隔離與囚禁。這項措施將各種救助機構合并,并賦予機構負責人行政、司法等權力,以對巴黎的所有窮人進行管理。這個對窮人的救助機構并非一個醫療機構,而是“一種半司法結構,是一個行政單位,與已經設立的權力一起,在法庭外行使決定、判決和執行權”*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London, 2006, p.49;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4, p.125.(二者英文翻譯稍異。)。這是政府為了應對經濟危機采取的控制措施,是經濟和道德控制的工具。這個具有絕對權力的壓制性機構不僅限于巴黎,而是遍及整個法國和歐洲。這種對窮人的囚禁觀念從16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在這方面,新教和公教是殊途同歸*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London, 2006, pp.57-58.。它具有雙重的作用,在危機時期通過控制囚禁無業者,確保勞動力價格穩定和社會安定;在非危機時期則通過給予被囚禁者工作,作為充分就業和高工資狀態下廉價的勞動力,為社會的繁榮做貢獻*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London, 2006, p.66; pp.68-69.。囚禁不但具有壓制性的懲罰特征,還具有積極的改正(校正)功能,它還是市民階層(布爾喬亞)重新塑造和推行倫理和道德觀念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被重新劃分,一些原先被視為正常的行為被列入非理性領域并遭到禁止。集體、家庭乃至個人行為等規范被重新調整,并通過對被囚禁者的強制性改造,使他們接受了這一價值規范,從而使社會的價值觀念趨同*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Madness, Routledge, London, 2006, pp.101-108.。在福柯看來,這種囚禁與監獄一樣是一種政治策略、技術和手段,是對人身體的一種控制。
雖然從權力話語和社會控制角度的解讀在學術界引發了爭論,但其對宗教改革時期濟貧改革研究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都是循著這個思路進行的*R. Po-chia Hsia, Social Discipline in the Reformation: Central Europe 1550-1750, Routledge, London, 1989; H. C. M. Michielse, Policing the Poor: J. L. Vives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rvice Review, 64, 1, 1990, pp.1-21; Philip S. Gorski, 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3.,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國社會史學家羅伯特·于特(Robert Jütte)。根據他的總結,勞動、監督、控制、檢查、教育、懲罰*Robert Jütte, “Poor Relief and Social Discipline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11, pp.25-52;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94.是這個時期濟貧的主要特點。世俗和教會政府通過立法活動建立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對秩序的需求使得戒律成為普遍的做法,這實際上超越了宗教派別的界限,新教和公教都如此。社會控制機制在規訓部分人的同時懲罰另一些人(游手好閑者、非居住民、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乞丐)。社會福利政策是讓窮人適應資產階級價值觀念的文化適應。
毫無疑問,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是近代早期歐洲的濟貧活動變革的主要動因,改革者希望通過整合傳統的濟貧資源,以更加合理有效的管理,解決日益增長的貧困問題。各種政策變化正是這個體現。同樣,在這個過程中,針對被救助者采取資格審查、登記及懲罰措施,也確實使得這個時期的濟貧活動帶有與以往不同的強制色彩。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史和社會史角度的研究對于深化對歐洲近代早期的濟貧改革無疑貢獻巨大,對于認識濟貧改革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是必要的。此外,不同的理論相互補充,也有助于研究的不斷深入。如經濟社會史的研究糾正了韋伯主導的宗派價值觀念理論的偏頗,指出了經濟及社會原因對于改革的重要性;福柯的解讀則表明,從長時段來看,改革還是現代國家控制建立的工具。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者明顯的不足。第一,這些研究基本是社會科學而非歷史學角度的,借助的是社會學等理論,是一種共時性而非歷時性研究,在操作上脫離了基本的歷史環境,在認識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偏差。從韋伯的新教倫理到經濟社會史研究,再到福柯的權力話語,都是如此。第二,這些研究大都矯枉過正,陷于以偏代全、非此即彼的誤區。經濟社會史學派糾正韋伯過于強調宗教倫理的弊端,但又把經濟社會原因視為唯一的動因;社會規訓理論則用后果代替了具體過程,完全忽略了當事者的主觀動機,屏蔽了其對窮人幫助和支持的一面。第三,這些研究都將宗教因素排除在外,完全誤讀了歷史,也是不可取的。
三、 宗教與濟貧改革
在這些新視角下,宗教因素逐漸淡出研究視野,甚至被否定。這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這個時期的濟貧活動完全是經濟或政治行為,與宗教無關了,至少是不再重要了。此其一。其二,由于這次大規模的社會濟貧改革并非始于新教改革家,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改革家在濟貧方面的努力也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其三,在這個時期濟貧改革表現出一些相同之處的情況下,教派之間的差異似乎也不存在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史學界的許多學者已經對這種偏頗的認識提出了批評,反對割裂當時的具體環境,強調宗教在改革中的不可或缺性*Harold. J. Grimm, “Luther’s contributions to sixteenth-century organization of poor relief”,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61, 1970, pp.222-234; Carter Lindberg, “There Should Be No Beggars Among Christians”: Karlstadt, Luther, and the Origins of Protestant Poor Relief, Church History, 46, 3, 1977, pp.313-334; Lee Palmer Wandel, Always among Us: Images of the Poor in Zwingli’s Zuri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Ole Peter Grell, “The Religious Duty of Care and the Social Nedd for Contro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 1, 1996, pp.257-263; Ole Peter Grell, “The Protestant imperative of Christian care and Neighbourly Love”, in Ole Peter Grell, Andrew Cunningham eds.,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Protestant Europe 1500-1700,Routledge, London, 1997; Joel F. Harrington, “Escape from the Great Confinement: The Genealogy of a German Workhous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1, 2, 1999, pp.308-345.。實際上,就連一些經濟社會史學派的實踐者,也清醒意識到把宗教因素排除在外的缺陷。如普蘭就指出,雖然不能把宗教因素作為這個時期濟貧改革的主導(全部),但也不能置之于不顧,因為“在沉溺于近代早期歐洲的經濟危機和法律與秩序問題的當代時尚中,它有不合適的被遮蔽的危險”*Brian Pullan, “Catholics and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Vol.26, 1976, p.33.。
在經濟社會史理論和以規訓懲罰為主要指標的現代國家形成理論的影響下,包括濟貧改革在內的宗教改革研究曾經顯赫一時。但是,繁榮并不能掩蓋存在的問題。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過分理論化的認識模式不但難以調和各方,而且存在不斷異化甚至失去宗教改革的危險。可以說,人為將主角之一的宗教逐出濟貧改革研究的舞臺正是問題的寫照。面對這種困境,業內學者也在反思,并試圖找到新的突破口,超越原有理論的局限,宗教在濟貧改革研究中的回歸就是一種努力。當然,更多的學者則試圖從宏觀的宗教改革研究出發尋求突破,如有學者提出用“宗教改革的文化史”取代以往的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涵蓋具體歷史*Bruce Gordon Et.al., “Forum: Religious History beyond Confessionalization”, German History, 32, 4, Dec., 2014.。
宗教改革雖然肇始于宗教領域,但作為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它事關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不能簡單化處理。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說,這是作為上層建筑的宗教觀念與深層次的經濟基礎矛盾的體現,改革本質上也是使二者相適應的努力。作為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少了宗教,當然不能全面理解這個時期的濟貧改革。在這個意義上,宗教的回歸是毋庸置疑的,值得肯定。不過,從相關研究來看,回歸后的宗教似乎仍沒有擺脫傳統的優劣判斷邏輯,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重復。雖然在細節研究上有所深入,但整體意義不大,不少重要的問題仍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在筆者看來,這些認識存在一些誤區,不利于正確理解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
第一個誤區是,將濟貧改革觀念及方式的改變等同于宗教因素的消失,將連續發展的歷史斷裂化,遮蔽了復雜的歷史發展過程。
在西方主流話語里面,宗教改革被視為現代化的重要開端,后者又大都被理解為世俗化,也就是不斷擺脫宗教的過程,世俗化的表現則是宗教信仰的衰落。這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確實,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活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但這些特征是否必然與宗教內涵的剝離為前提,世俗化和現代化是否一定意味著宗教信仰的衰落和消失?歷史學、宗教學和社會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問題并不那么簡單。隨著學術界對宗教認識由本質向功能的轉變,宗教作為人的一種基本需求的一面逐漸受到重視。作為一種需求,在不同的時期可能有形式的變化,但需求本身不會改變。從這個角度看,傳統的宗教與世俗二元對立的觀點顯然偏頗了些。有學者指出,現代化和世俗化與宗教活力之間并不一定是對立關系*Philip S. Gorski, “Historicizing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Church,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 1300-17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1, 2000, p.162.,宗教改革雖然帶來了基督教信仰的多元化,但與改革前相比,它并沒有改變宗教性的程度,而只是改變了宗教的特征,雙方的不同主要在于宗教的表現形式上*Philip S. Gorski, “Historicizing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Church,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 1300-1700”, p.148.。世俗與神圣之間雖然成為改革家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但實際上,誠如一些學者所言,世俗與神圣的二元對立在近代早期并不明顯。“世俗與神圣在近代早期的濟貧結構和功能中是無法分開的”*Thomas Max Safley ed., The Reformation of Charity: The Secular and Religious in Early Modern Poor Relief, p.196.,宗教改革實際是世俗與神圣之間的分別(differentiation)和去分別(de-differentiation)并存的過程*Philip S. Gorski, “Historicizing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Church,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 1300-1700”, p.150.。這種認識對于全面認識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活動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濟貧改革的合理化和世俗化并非意味著宗教因素的消失或不重要,而只是以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由施舍過程中的互利行為轉變為對神的愛,也就是通過基督徒之間的愛以達到榮耀神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層面的內涵不是縮小了,而是加大了。
此外,在近代早期的歐洲世界里,教會和社會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體的,這就決定了宗教因素是無法超越的。一方面,基督教對社會的認識理論仍然沒有改變,傳統的機體論仍是主體。根據這種理論,整個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社會和教會之間沒有分別,都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實現共同的目標,個人要從屬于整體,維系整體的是對神之愛和由此體現出來的兄弟之愛*Abel Athouguia Alves, “The Christian Social Organism and Social Welfare: The Case of Vives, Calvin and Loyola”,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0, 1, 1989, pp.3-22.。教會、社會、世俗政權在這個時期雖然有職責的區分,但在本質上都服務于至高的神,為的是人的最終救贖。另一方面,教會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的改革,二者也無法分開。從路德的《致德意志貴族公開書》和加爾文的《日內瓦教會法令草案》可以看出,改革既包括教會的信條、禮儀和組織,又包括婚姻家庭及個人的道德規范,還包括教育,濟貧改革只是龐大改革計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重建基督徒共和國的重要內容。雖然這個計劃不乏懲罰性的內容,但懲罰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個關懷的網絡*Robert M. Kingdon, “Geneva Consistory in the time of Calvin”, in Andrew Pettegree, Alastair Duke, Gillian Lewis eds., Calvinism in Europe, 1540-16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這個關懷網絡的前提和基礎是基督徒的兄弟之愛,在這個網絡里面,所有的人都應該得到應有的關懷和照顧,對窮人的救濟則是最好的體現之一。物質上的救濟是必要的,但更主要的是通過積極的手段改善貧困者的處境,提升其道德水平,以便使他徹底脫離貧困。要實現這個目標,無論新教還是公教神學家,都認為教育和勞動是關鍵。教育可以使貧困兒童掌握正確的信仰知識,養成高尚的品德,獲得謀生的技能,以便徹底擺脫貧困。勞動則是醫治乞討的良藥,不但使人自食其力,而且可以去除壞念頭,以免無所事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維威斯提出,不但身體健全者要勞動,就連老弱病殘和孤兒也應該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 iii. 9-10.。各種措施本質上也都在于實現基督徒共和國的理想,對貧困的救助是手段而非目的。
應該指出的是,從宗教的角度來說,這個時期的濟貧觀念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達方式的變化,而非消除其宗教內涵。其普遍的特征是消除或弱化集體或個人濟貧的等價交換作用,由原來強調的互利轉向了基督徒之間的兄弟之愛,強調作為基督徒的責任與義務。但對貧困及其根源的認識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與以往相比,沒有本質不同。在這一點上,新教和公教基本一致。維威斯認為,貧窮的根源在于人的驕傲與墮落,在于原罪。貧窮的具體原因有兩種,一是部分人因為自然的原因使然,如殘疾、疾病、自然災害喪失財富等;另外一種原因則在于神的不為人所知的安排,神賦予一些人財富,同時使另一些人失去財富*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ii.7.。窮人應首先明白“他們的貧困是神以最公正最秘密的設計送給他們的……因此不但要以順從之心容忍貧困,而且要以喜悅之心作為神的禮物予以接納”*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vi.1.。加爾文也認為,許多人的貧困并非偶然,而是有著確定的原因,窮人的存在是為了給人實踐仁愛的機會,這是神的旨意*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Matthew, Mark, Luke, Vol.3, Ages Software, OR: Albany, 1997, pp.145-146.。
不但對貧困的認識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濟貧的行為同樣如此。濟貧并非目的,而是一種手段,最終還是指向救贖問題。對于信徒而言,這種行為不是單純的經濟行為或憐憫之情,而是為救贖積累資本,只不過是由原來的直接的等價交換變成了間接投資。維威斯說,憐憫幫助窮人的原因在于神*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xi.7.;施舍的功用并非在于求好和作善事,而是為了神*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xi.13.;因為“我們從人那里希望得到的越少,我們從神那里收到的就越多”*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xi.16.。加爾文則更加清楚地闡明了這一點。他認為,人生的最終目的還是在于天國,應該將財富轉移到那里。而轉移財富的最好的方式在于“為窮人提供所需的東西,給予他們的一切,主都算作給予他自己的(《馬太福音》25:40);由此才有了那句著名的允諾:‘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箴言》19:17)。同樣,‘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哥林多后書》9:6)。因為出于愛的義務奉獻給我們的弟兄的就是儲存在主的手里。他是一位可信的保管,有一天會以豐厚的利潤回報”*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F. L. Battles trans., The Westminster Press, Louisville, 1960, III. xviii.6.。
濟貧所具有的濃厚的宗教內涵在公教會官方的價值中甚至沒有動搖。在特倫特宗教會議上,除了廢除了專門發行贖罪券的專員外,贖罪券及購買贖罪券等傳統行為仍然被視為信徒為救贖積累資本的重要手段,也得到教會的支持和鼓勵。在經過改革的公教地區,也是如此。普蘭就指出,雖然這個時期的貧困是由經濟原因引起的,但從濟貧實踐的角度來說,并非是純世俗的,宗教在其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從威尼斯來看,“至少在這些團體的人眼里,濟貧的目的從來不是正式的‘世俗的’。他們的工作從來不是官方設計的以追求人類社會的善為目的本身。最高頌揚的目的是精神性的,濟貧既是一種禁欲主義形式,也是通過服務神的子民表達的神之愛。他們的部分考慮是自我成圣(self-sanctification),但也關注他人的靈魂。……精神性的目的和道德判斷統攝了所有慈善行為,甚至滲透到醫生和病人的關系中”*Brian Pullan,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 State, to 1620, p.280.。因此,在承認濟貧改革是為了直接應對經濟危機及社會現實問題的同時,也不能否認其宗教方面的內涵。對這個時期的公教徒而言,“其最高理想在于通過英雄般的個人對窮人的服務而實現的自我成圣,而非在于通過隨意或非個人的施舍而獲得的善功,其中心目標在于藉有組織的慈善征服靈魂,其中作為恩典的渠道和救贖的方式的圣禮,尤其是圣餐禮和懺悔禮,起到了重要作用”*Brian Pulla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Medical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p.25.。
對這個時期的基督徒來說,濟貧實踐固有的宗教內涵是不可或缺的,所不同的是雙方表達的方式。對新教徒來言,或者是體現自己是真信徒的方式,或者是信仰得救路上的一個證明。對于公教徒而言,則延續了原來的觀念,是為未來救贖的投資,會得到更大的收益*Brian S. Pullan, “Catholics and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ifth Series) 26, 1976, pp.15-34; “Catholics, Protestants, and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5(3), 2005, pp.441-456.。
第二個誤區是,在強調前宗教改革相關制度及其延續性的同時,否定了新教對于濟貧改革的作用意義,陷入了以偏概全、非此即彼的錯誤。
論者如普蘭認為,新教的濟貧實踐在本質上與以往沒有不同。這種觀點已經遭到許多學者的批判。如格雷爾(Grell)就提出,宗教改革對16世紀濟貧改革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沒有新教改革家及其對宗教方面改革的呼吁,濟貧改革的速度和廣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急需對它進行新的修正解釋*Ole Peter Grell, “The religious duty of care and the social need for contro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 1, 1996, p.263.。一方面,新教雖非濟貧的開創者,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對于實踐沒有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公教與新教雖然在實踐上表現出了一定的共同特征,但也不意味著新教在對實踐的理解和認識上沒有改變。無論從理論和實踐上來看,新教對于這場濟貧改革運動的推動作用都是非常明顯的。
從理論上說,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觀念的變化是基督教神學理論變化的邏輯必然。傳統基督教以互惠救贖為特點的濟貧觀念是以善功等理論為基礎的,這個理論的重要特點是神對人的救贖是與個人的努力分不開的,并以此為前提。這種觀點認為,神雖然藉耶穌基督赦免了人的罪,但并不意味著個人的救贖已經實現;相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要想最終得救,要首先付出,為未來的救贖準備條件,也就是行各種各樣的善功,施舍則是最為重要的善功之一。神根據人的善功決定個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得救是神對人的善功的一種回報或獎賞,是“善功稱義”。不過,在拉丁基督教會看來,神對人的命運的決定不是直接實現的,而是通過神在人間的代言人——教士實現的。在實際的操作中,教會則利用特權,把善功量化,變成了一種經濟活動,從而成為教士階層牟利的工具,造成嚴重的腐敗。
新教神學尤其是馬丁·路德的“唯信稱義”(sola fide)理論,徹底否定了公教的“善功稱義”理論。路德認為,使人成為義人的不是善功,而是靠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且唯有信仰才能使人成為義人。人首先在信仰里成為義人,然后才能有所謂的善功。從本質上來說,信仰不是靠人的努力或善功得到的,而是神的一種仁慈的恩典,是先于任何善功的無條件的贈與。對人而言,信仰耶穌基督就是最大最主要的善功,是其他所有善功的前提。唯信稱義理論不但否定了善功賴以存在的基礎,而且極大改變了對人與神關系、職業等方面的觀點。既然人可以藉信仰在耶穌基督里面成為義人,建立與神的直接的關系,每個人也就成為自己的教士,教士階層的存在就沒有必要了,教會宣揚的教俗、等級、職業之間的差別就不再有說服力了。路德指出,“在信仰里,所有的工作都成為同等的,彼此相同,工作之間的差別消失了”*Martin Luther, “On Good Works”,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1, p.190.,屬靈與屬世之間并不存在高低之分,銅匠、鐵匠、農民與主教一樣,只是職責不同。神賦予每個人一個天職(calling),使之有一個職位和功能*Martin Luther,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2, p.69.,人正是在這些不同的職位上在勞動中榮耀神的。但是,神的這些天職中并不包括乞討,一方面,神并不要人無所事事,更不能容忍不勞而獲*Martin Luther,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2, p.100.;另一方面,乞討不符合基督徒的愛的精神,“神的子民中不應該有貧困或乞討”*J. Pelikan ed., Luther’s Works, Vol.9,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Saint Loius, 1960, p.147.。同樣,施舍與做生意、吃飯、睡覺、祈禱、禁食等活動一樣,也沒有價值上的區別,都是人侍奉神的方式,是稱義的結果,是真基督徒身份的表現。
如果說“唯信稱義”為濟貧觀念的變化奠定了基礎,圣經權威的確立則為新教提供了新的濟貧理念的原型。新教圣經權威的確立與人文主義運動關系密切。以伊拉斯謨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非常注重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提倡用回到源頭(ad fontes)的方法研究《圣經》。雖然新教與人文主義者在自由意志等神學問題上存在分歧,這種方法卻被新教神學家普遍繼承下來,成為與羅馬教會斗爭的重要工具。他們通過希伯來文《舊約》和希臘文《新約》原文,不但發現了通俗拉丁文本的錯誤,而且發現教會信仰中的很多東西都在《圣經》中找不到依據。在新教神學家看來,《圣經》作為神對人的啟示,是基督教信仰的依據,并且是唯一的依據。只有回歸《圣經》,才能徹底消除長期盛行的謬誤,才能恢復教會本來的面目。對新教神學家來說,無論善功、煉獄、圣徒的代禱,還是贖罪券,都在《圣經》中找不到依據,自然應該拋棄。《圣經》中雖然有許多關于窮人與濟貧的論斷,但其中的愛的精神和原則,在羅馬教會以功利為目的的濟貧觀中則蕩然無存。所以,要正本清源,回到源頭,恢復以神之愛和兄弟之愛為根本的濟貧觀,也就是榮耀神的愛(charity)。
新教普遍接受了馬丁·路德的理論,一致反對善功,這也就在理論上否定了公教會所宣揚的濟貧的理論支撐,并在實踐上否定了與此有關的機構和行為,如修道院、乞討、直接施舍等。這些都直接體現在新教的改革措施中。此外,新教改革家無一例外地積極宣傳和推進濟貧改革,并且將它作為重塑基督教、實現理想的重要手段之一。這種變化可以從1528年路德編輯出版的《乞丐手冊》及幾十年后奧德利等人關于乞丐的著述中發現端倪。在路德列舉的28種乞丐中,大部分與宗教有關,而在奧德利等人所列的23種乞丐中,則鮮有與宗教關聯者。這表明,宗教觀念的變化與新教濟貧改革有著內在關系。
第三個誤區是,仍然拘泥于新教與公教濟貧體制優劣的思路,對宗教在雙方不同濟貧制度形成中的作用關注不夠,而這一點應該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簡單的優劣二元模式的破除無疑是一大進步。如普蘭認為,不能用簡單的優劣來判別這些改革措施,新教的不一定好,同樣公教的不一定就差或者不好*Brian Pullan, “The Counter-Reformation, Medical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Counter-Reformation Europe, pp.18-39.。對歷史學研究而言,探討新教與公教不同的濟貧體制及形成原因,遠比簡單的優劣判定更為重要。近一段時間的相關研究表明,新教和公教政權改革后形成的濟貧體制有較大差異,這種差異既表現在不同的新教派別之間,也存在于公教陣營內部不同的國家。除了具體環境及傳統等因素外,宗教觀念是造成這些差異的重要原因*Sigrun Kahl, “The Religious Roots of Modern Poverty Policy: Catholic, Lutheran, and Reformed Protestant Traditions Compared”, Arch. europ. sociol., XLVI, 1, 2005.。
一般說來,新教由于拋棄了濟貧與善功之間的內在神學聯系,因而在濟貧機構的設置、具體操作等方面與以往都有較大的不同。各種宗教濟貧機構或者被撤銷、或者被合并,其承擔的濟貧職能大大削弱。乞討行為普遍遭到禁止,而個人的直接施舍也同時被禁止。在管理方面,則是世俗權逐漸占據了主導。當然,在這方面,不同的教派有所區別。在路德派盛行的地區,濟貧事務完全掌握在世俗政府手里,因為路德認為這些都是外在的東西,與個人的靈魂救贖沒有直接的關系,理應由政府負責。而在加爾文教派盛行的地區,則是由教會的執事負責,世俗政權雖然參與這項事務,但基本是從屬性的。這種局面的形成自然與加爾文的觀點密不可分。在他看來,濟貧是教會最本質的工作之一,執事則是教會法定人員中的一種,負責接收和向窮人發放濟貧的錢物,也負責照看窮人。教會的濟貧職能與絕罰權一樣是教會權力的體現和象征。在日內瓦,雖然濟貧的資源和機構實現了集中化,也有世俗的參與,但教會的主導權實沒有改變。不僅如此,教會還非常反對世俗政權的干預。在尼德蘭的濟貧改革中,則出現了教會與世俗政府斗爭的局面,前者為了捍衛自己的濟貧主導權而與后者發生沖突。英格蘭的教會則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體制,堂區的濟貧執事和監督由地方治安法官任命并監督,后者在濟貧資源的配置和實施方面有著較大的權力。
與此相對的是公教。它在保留傳統觀念和實踐的同時,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一,從特倫特公會議(1546—1563)發布的決議來看,支撐原來的互惠救贖濟貧理念的一些重要信條如善功、煉獄、圣徒的代禱、贖罪券等,都被保留下來了。個人的施舍、自愿貧困等仍然得到教會的鼓勵,教會也繼續按捐贈者的意愿為煉獄里的靈魂做彌撒,但為的是“死者靈魂的福祉”*James Waterworth,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C. Dolman, London, 1848, p.258.,已不再強調贖罪的功能,相互幫助的兄弟之情和責任逐漸成為重點。而對于像維威斯之類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來說,濟貧的動機和目的除了在于神,是“為了神的緣故愛神和他的兄弟”*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 xi. 1.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涵——即不求任何回報的美德*J. L. Vives, De subvent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nis necessitatibus, I.viii.2.。第二,公教會雖然在濟貧資金和機構方面也實現了整合,但并沒有建立一個排他性的體系。原先的一些宗教機構仍然存在,與新的集中化的體系一起發揮著濟貧職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出現了許多由兄弟會主辦的濟貧機構,這種現象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蘭西比較突出。與此同時,各公教世俗政權興辦濟貧事業的力度也不斷加大,形成二元并存的局面。這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濟貧的效率,以至于我們看到后來一些國家不斷采取整合措施,以提高效率。第三,在管理權上,則是教會或者兄弟會占據了主宰,世俗政權基本上是從屬性的*James Waterworth,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p.262-264.。在這一點上,公教會與加爾文派的觀點是一致的,把它視為自己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權力。此外,特倫特宗教會議上,濟貧的主導權也完全交給了主教。在巨大的經濟和地方利益支撐下,教會的主教們更不愿意放棄這項權力。當然,為了應對新教的挑戰,解決教會內部嚴重的腐敗問題,保證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公教會也加強了對乞討、貧困、濟貧事務等的管理,以減少弊端,如立法禁止托缽修士乞討,嚴禁他們接受任何形式的錢物等*J. C. Olin,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Savonarola to Ignatius Loyola,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2, p.130, pp.162-163.。
(責任編輯:陳煒祺)
The Poor Relief Reform in the Reformation Reconsidered
Liu Linhai
Poverty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at endangered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Reformation, the poor relief reform which transcends the denominational boundaries of Christianity is universal. It not only broke down the tradi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but also set up new systems, providing positiv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uropean welfare system. Although indispensable to the broadening of understanding the poor relief reform, academic interpretations such as discontinuity, continuity and post-modern political theory are not free from misunderstandings, among others, dispelling religion from the poor relief reform and isolating it from the history. Religious motivation, though not exclusively, always entangles with the poor relief reform, distinguishing itself from the later Western welfare reforms. As one of the leading roles, religion should always be present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or relief reform is concerned.
Religion Reformation; Poor Relief; Religion and Poor Relief Reform
2016-03-29
B979; K503
A
0257-5833(2016)10-0152-14
劉林海,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