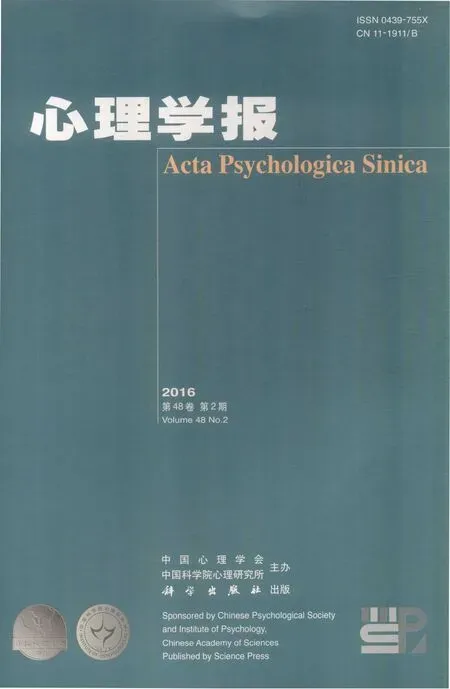聽障和聽力正常人群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的交互作用*
王愛君 沈 路 遲瑩瑩 劉曉樂 陳 騏 張 明
(1蘇州大學心理學系, 蘇州 215123) (2東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長春 130024)
(3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廣州 510631)
1 引言
視覺信息的皮層加工至少存在兩條分離性的神經通路:一條是從初級視覺皮層出發沿著背側方向到達頂葉的“枕頂通路”, 即背側通路; 另一條也是從初級視覺皮層出發沿著腹側方向到達顳葉的“枕顳通路”, 即腹側通路(Ungerleider & Mishkin,1982)。腹側通路主要負責對客體屬性的知覺, 將視覺輸入轉換為知覺表征, 包括客體的固有特征以及它們的空間關系。而背側通路主要負責對客體的空間位置進行加工以及對客體施以行為動作, 如夠取和抓握(Griffiths, Marslen-Wilson, Stamatakis, & Tyler,2013; Kim, 2014; Vossel, Weidner, Driver, Friston, &Fink, 2012)。
知覺/反應模型的觀點認為, 對手臂范圍內(近處空間)和手臂范圍外(遠處空間)的注意是基于不同的大腦信息加工通路(Berti & Frassinetti, 2000;Christiansen, Christensen, Grünbaum, & Kyllingsb?k,2014; Gilet, Diard, & Bessiere, 2011; Haazebroek,van Dantzig, & Hommel, 2011; Mennemeier, Wertman,& Heilman, 1992; Vuilleumier, Valenza, Mayer,Reverdin, & Landis, 1998)。因為個體可以對近處空間的客體直接地施以行為動作, 因此, 背側通路負責近處空間的加工。相反, 出現在遠處空間的客體,個體無法直接地對其施以行為動作, 因此, 腹側通路負責對出現在遠處空間的客體進行知覺表征。知覺/反應模型的提出是基于對一個枕顳皮層中雙側腹側通路損傷患者的研究。盡管該病人患有高強度的視覺失認證, 也就是患者既不能正確地識別視覺客體也不能正確地辨認視覺客體, 但是該患者能夠正確地對同樣的視覺客體施以行為動作(Goodale &Milner, 1992; Goodale, Milner, Jakobson, & Carey,1991)。然而, 有研究表明, 無論是知覺任務還是反應任務, 只要其出現在近處空間就由背側通路負責加工, 而出現在遠處空間就由腹側通路負責加工(Weiss, Marshall, Zilles, & Fink, 2003)。這些結果表明了, 背側通路和腹側通路在近處和遠處空間表現出的不同激活模式本質上并不是依賴于任務需求(如, 知覺或者反應) (Pitzalis, Di Russo, Spinelli, &Zoccolotti, 2001), 而是依賴于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即背側通路與腹側通路的功能分離是與選擇了合適的空間參照框架相關(Bruno, 2001)。在大腦中,一個客體既可以以自我參照框架的形式呈現(如,相對于觀察者的身體效應器), 也可以以環境參照框架的形式呈現(如, 相對于另一個客體或者與觀察者無關的周圍事物) (Jiang & Swallow, 2013; Viarouge,Hubbard, & Dehaene, 2014; Vogeley & Fink, 2003)。自我表征通常是由背側通路將其轉化為相應的感覺運動表征(Andersen & Buneo, 2002; Andersen,Snyder, Bradley, & Xing, 1997; Cohen & Andersen,2002; Ma, Hu, & Wilson, 2012), 而環境表征則通常是由腹側通路將其轉化為相應的知覺表征(James,Culham, Humphrey, Milner, & Goodale, 2003; James,Humphrey, Gati, Menon, & Goodale, 2002)。在以往神經心理學的研究中, 要求先前提到的視覺失認證患者在基于自我參照和環境參照的條件下同時完成知覺任務和運動任務(Schenk, 2006)。結果發現,視覺失認證患者在基于自我參照框架條件下兩種任務的成績并未受到影響。相反, 在基于環境參照框架條件下兩種任務的成績受到了影響。實驗表明,影響視覺失認證患者完成任務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可能是空間參照框架的選取(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而不是任務需求(知覺vs.反應)。
以往研究表明, 背側通路和腹側通路在解剖上的差異導致了兩者分別主要負責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的加工以及環境參照框架和自我參照框架的加工, 且以往研究較多的是分別關注空間主導性(近處空間 vs.遠處空間)和空間參照框架(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但關于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這兩個維度的交互作用則關注較少。近期一項研究采用聽力正常群體為研究對象, 考察了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之間交互作用的神經機制。結果發現, 當腹側通路負責的知覺表征與背側通路負責的感覺運動表征存在交互作用時, 頂枕聯合區(parietal-occipital junction, POJ)產生了更高的激活。研究認為, 頂枕聯合區參與了背側通路與腹側通路交互作用的神經表征(Chen, Weidner, Marshall, &Fink, 2012)。這個問題之所以關鍵是因為, 其能夠有效地處理三維環境中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的客體信息與日常生活的空間判斷能力(不同參照框架)相結合的任務。來自神經心理學的研究也表明, 空間主導性可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自我參照判斷或者環境參照判斷。如, 單側視覺空間忽視癥患者(即自我參照框架受損的患者)在近處空間或者遠處空間完成二分任務時可以選擇性地影響其基于環境參照的表征(Berti & Frassinetti, 2000; Berti, Smania,& Allport, 2001; Vuilleumier et al., 1998)。
本研究選取聽障被試為主要研究對象, 將空間主導性與空間參照框架相結合, 目的在于考察聽障人群中這兩種維度之間潛在的交互作用。此外, 我們選用聽力正常人群作為實驗被試, 將聽障人群與聽力正常人群兩組被試的成績進行比較, 有利于考察空間主導性與空間參照框架的交互作用是否在聽力喪失之后會發生改變。以往研究發現, 當要求聽障人群完成視知覺任務時, 先天聽障被試對運動刺激在外周視野的活動得到了增強。如, 當目標的時間或空間屬性不確定時, 相對于聽力正常被試,聽障被試對外周視野呈現的運動刺激反應更快且更準確(Stevens & Neville, 2006)。但是對于中央視野呈現的刺激, 聽力正常被試與聽障被試的表現不存在顯著差異(Bavelier, Dye, & Hauser, 2006)。此外,聽障被試背側通路的視覺運動區(middle temporal/medial superior temporal, MT/MST)對于外周視野出現的刺激表現出更高的激活, 而聽力正常被試背側通路的視覺運動區對中央視野出現的刺激有著更高的激活(Bavelier et al., 2001)。神經層面的證據也表明, 視覺運動刺激的加工(Beauchamp, Cox, &DeYoe, 1997; O’Craven, Rosen, Kwong, Treisman, &Savoy, 1997)和外周視野刺激的加工(Clavagnier, Prado,Kennedy, & Perenin, 2007; Prado et al., 2005)均由背側通路負責。因此, 聽障人群背側通路的視覺功能更易受影響而具有可塑性的變化(Bavelier et al.,2001; Lomber, Meredith, & Kral, 2010)。此外, 有研究認為, 先天性的耳聾會引起前庭蝸神經的部分損傷, 不僅包括耳蝸功能, 還包括前庭傳入。而前庭傳入纖維的破壞是引起平衡缺陷的原因之一(Siegel,Marchetti, & Tecklin, 1991), 所以, 聽障人群的本體平衡感會表現出比正常人差(Angelaki, Klier, &Snyder, 2009)
綜上所述, 聽障被試是因為背側通路改變可能導致自我參照框架的變化, 進而導致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的交互作用模式發生了變化, 還是因為其本體平衡感本身存在缺陷導致自我參照框架的變化, 進而導致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的交互作用模式發生了變化?為了驗證上述觀點, 我們進行了本研究。實驗1操縱了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客體自我參照下的位置和環境參照下的位置(圖 1),要求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分別在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針對相同的物理刺激(實驗中的叉子)做出自我參照框架和環境參照框架的判斷。通過這樣的實驗設計, 主要考察空間主導性與空間參照框架之間潛在的交互作用是否在聽力喪失之后會發生改變。但由于聽障被試前庭蝸神經的部分損傷, 會導致聽障被試的主觀平衡感可能受到了影響(Siegel et al.,1991), 為了排除聽障被試和聽力正常被試在以自我參照判斷任務中的差異是由基本的本體平衡能力上的差異造成的。實驗2采用open loop實驗考察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的空間判斷能力差異是否是由于主觀平衡感的差異所引起。如果有差異, 則實驗1的結果必須考慮這種差異對實驗結果造成的影響。如果沒有差異, 則可以推斷實驗的效應主要是由于聽障被試背側通路發生了改變所引起的。
2 實驗 1:聽障和聽力正常人群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的交互作用
2.1 方法
2.1.1 被試
聽障被試為 17名來自長春市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生(男生 7名, 女生 10名, 平均年齡為 17.5歲),聽力喪失的年齡均為3周歲之前, 雙耳聽力損失大于 90 dB, 他們均熟練掌握了手語, 并且出生后就將其作為其第一語言。聽力正常被試為 17名來自東北師范大學大學一年級學生(男生8名, 女生9名,平均年齡為 18.5歲)。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且視力或者矯正視力正常。實驗所選取的聽障被試為特殊師范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學生, 與所選取的聽力正常被試年齡接近, 且本實驗的任務為空間參照框架判斷, 所以兩組被試受教育水平上的略微差異并不是一個影響實驗結果的主要因素。所有被試在實驗之前具有知情同意權, 且在完成實驗后給予相應的報酬或禮品。
2.1.2 實驗儀器和刺激
整個實驗在一個微暗的實驗室內進行, 聽障被試在完成實驗過程中由主試和手語老師共同對其進行實驗的指導。遠處空間的刺激通過筆記本電腦投影到大屏幕上呈現, 被試眼鏡距離屏幕中央的距離為226 cm。近處空間的刺激通過14英寸IBM筆記本電腦呈現, 被試眼鏡距離屏幕中央的距離為50 cm。遠處空間刺激與近處空間刺激的視角保持一致。實驗的刺激材料為一個盤子和盤子上的一個叉子。盤子的直徑為 15°視角, 叉子近端尾部的視角為2.5°。以自我為參照條件下(相對于身體的中矢面)叉子的位置和以環境為參照條件下(相對于盤子的中矢面)叉子的位置成正交變化。叉子相對于被試身體的中矢面有不同的4種位置, 形成了4種以自我參照條件下叉子的位置:?5°、?3.5°、3.5°和 5°。叉子相對于盤子的中矢面有4種不同的位置, 形成了 4種以環境為參照條件下叉子的位置:?2.4°、?1.7°、1.7°和 2.4° (如圖 1)。

圖1 實驗刺激材料(引自Zhang et al., 2014)
2.1.3 實驗設計和實驗程序
實驗為2 (空間主導:近處空間vs.遠處空間) ×2 (任務類型: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的被試內設計。聽障被試與聽力正常被試分成兩組, 分別要求其針對同樣的刺激在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完成空間參照框架判斷任務。在做自我參照判斷的任務中, 要求被試判斷叉子位于自己身體中線的左側還是右側。在做環境參照判斷的任務中, 要求被試判斷叉子位于盤子的左側還是右側。無論在近處空間還是遠處空間做參照框架判斷任務, 都要求一半的被試針對左側的刺激用右手的食指按鼠標左鍵, 而對右側的刺激用右手的中指按鼠標的右鍵。
實驗中, 兩種任務類型以組塊的方式呈現給被試, 即自我參照判斷和環境參照判斷組塊交替呈現。本研究中的實驗并未采用中央注視點去引導被試的注意, 因為實驗中若出現“+”, 被試在完成自我參照判斷的任務時更加傾向將注視點作為參照物來判斷叉子的位置。實驗中, 每個組塊呈現之前,以指導語的方式(3 s)告訴被試即將完成的任務類型。組塊中每個試次呈現的時間共1650 ms (其中,目標刺激呈現時間為 150 ms, 被試反應時間為1500 ms), 10個試次為一組, 兩種任務類型在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各 8組, 即每個被試需要完成320個試次。正式實驗為11 min左右。實驗中聽障被試在進行正式實驗之前需要進行5 min左右的練習來熟悉實驗任務, 以確保實驗的正確率。聽力正常被試在進行正式實驗之前需要進行3 min左右的練習來熟悉實驗任務。
2.2 結果與分析
2.2.1 聽障被試
剔除反應錯誤的試次; 剔除反應時小于 100 ms和大于1500 ms的試次; 剔除正負3個標準差以外的試次; 總剔除的試次占總試次的18.6%。表1顯示了各條件下被試的平均反應時、錯誤率。將錯誤率進行2 (空間主導:近處空間vs.遠處空間) × 2 (任務類型: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被試內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 空間主導性和任務類型的主效應顯著均不顯著,Fs < 1。兩者的交互作用也不顯著,F(1,16) = 2.40,p> 0.05。

表1 聽障被試各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ms)和錯誤率(%)
將正確試次下的反應時進行 2 (空間主導:近處空間vs.遠處空間) × 2 (任務類型: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被試內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空間主導性的主效應顯著,F(1,16) = 9.22,p< 0.01,η2= 0.36, 被試對遠處空間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47 ms)顯著慢于近處空間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27 ms)。任務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16) = 9.44,p< 0.01, η2=0.37,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16 ms)顯著快于自我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59 ms)。此外, 空間主導性與任務類型的交互作用顯著,F(1,16) = 4.33,p =0.05, η2= 0.21 (圖 2)。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 當目標出現在遠空間時,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30 ms)顯著快于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564 ms),t(16) = 2.13,p< 0.05,d= 0.75; 當目標出現在近空間時,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01 ms)顯著快于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553 ms),t(16) = 3.93,p =0.001,d=1.38。

圖2 聽障被試各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誤(ms)
2.2.2 聽力正常被試
剔除反應錯誤的試次; 剔除反應時小于 100 ms和大于1500 ms的試次; 剔除正負3個標準差以外的試次; 總剔除的試次占總試次的8.4%。表2顯示了各條件下被試的平均反應時、錯誤率。將錯誤率進行2 (空間主導:近處空間vs.遠處空間) × 2 (任務類型: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被試內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 僅任務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17) = 8.21,p< 0.05, η2= 0.34, 環境參照條件下錯誤率(5%)顯著少于自我參照條件下錯誤率(7.5%)。其他主效應和交互作用均不顯著,Fs <1。

表2 聽力正常被試各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ms)和錯誤率(%)
將正確試次下的反應時進行 2 (空間主導:近處空間vs.遠處空間) × 2 (任務類型:自我參照vs.環境參照)被試內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空間主導性的主效應不顯著,F<1。任務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16) = 13.31,p< 0.005, η2= 0.45,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14 ms)顯著慢于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491 ms)。此外, 空間主導性與任務類型的交互作用顯著,F(1,16) = 5.40,p<0.05, η2= 0.25 (圖 3)。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分析, 當目標出現在遠處空間時,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17 ms)顯著慢于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481 ms),t(16) = 3.64,p< 0.005,d= 0.64; 當目標出現在近處空間時,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511 ms)與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501 ms)無顯著差異,t(16) = 1.55,p >0.05。
通過聽障被試和聽力正常被試的數據可以看出, 聽障被試的結果表現為環境參照框架下的反應(516 ms)快于自我參照框架下的反應(559 ms), 但是聽力正常被試卻表現出相反的模式, 即環境參照框架下的反應(514 ms)慢于自我參照框架下的反應(491 ms)。而且, 將兩組被試的結果進行對比可以看出, 聽障(516 ms)和聽力正常(514 ms)被試在環境參照框架條件下的反應時之間并無顯著差異,t<1。但自我參照框架條件下的反應時之間存在顯著差異,t(16) = 2.21,p =0.05,d= 0.78, 表現為, 聽障被試在自我參照條件下的反應(559 ms)慢于聽力正常被試自我參照框架下的反應(491 ms)。

圖3 聽力正常被試各條件下的平均反應時和標準誤(ms)
同時我們也可通過兩組被試的數據看出, 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的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具有不同的交互作用模式。聽障被試在近空間與遠空間做環境參照框架判斷的反應時存在差異, 表現為遠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長于近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但是, 聽障人群在近空間與遠空間做自我參照框架判斷的反應時不存在差異。而聽力正常被試卻表現出相反的模式, 近處空間與遠處空間做環境參照框架判斷的反應時不存在差異, 但在近處空間與遠處空間做自我參照框架判斷的反應時存在差異,表現為遠處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短于近處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
3 實驗 2:聽障和聽力正常人群本體平衡感的差異
為了排除實驗效應的出現是由于聽障人群的本體平衡感比正常人差, 進而表現出對以自我參照框架下位置的感覺能力存在缺陷。我們采用 open loop實驗來考察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的空間判斷能力差異是否由于主觀平衡感的差異所引起。有研究在猴子的背側通路中與夠取和抓握反應相關的區域發現了編碼手的位置反饋信息的神經元(Galletti,Kutz, Gamberini, Breveglieri, & Fattori, 2003; Galletti,Gamberini, Kutz, Baldinotti, & Fattori, 2005; Pitzalis et al., 2013)。因此, 在夠取和抓握行為中, 對手的位置進行實時的視覺加工可能依賴于背側通路。采用fMRI技術通過比較close loop條件下(伸手時能看到自己的手)和 open loop條件下(看不到自己手的位置)的夠取和抓握行為, 可以考察人類是否也存在類似的夠取和抓握區域來調節對手的視覺反饋, 并且發現, 視覺運動區(middle temporal cortex,MT)和上枕皮層(superior occipital cortex, SO)參與對手的運動的視覺反饋, 而這些區域都位于背側通路(Thaler & Goodale, 2011)。實驗過程中確保被試不能看到自己的手(實驗裝置如圖 4), 由于參與對手的運動視覺反饋的腦區都位于背側通路, 實驗中看不到手的運動就實現不了對手運動的視覺反饋。此外, 背側通路既是視覺反饋的通路, 也是觸覺/本體感覺反饋的通路(Milner, 2012; Whitwell &Buckingham, 2013)。實驗過程中被試即使看不到視覺客體, 只要有觸覺反饋, 也能夠促進抓握行為(Bruno& Franz, 2009; Franz, Hesse, & Kollath, 2009)。但在本實驗中并未給予被試包含位置信息的觸覺反饋,在這過程中被試也不能根據觸碰的位置調整判斷,因為被試在完成“點”追隨任務后也不知道是否準確。因此, 是沒有所謂觸覺反饋的位置信息對任務判斷造成的影響。所以, 即使聽障和聽力正常人群的觸覺反饋存在差異, 但在本任務中, 觸覺并未對任務判斷產生作用。所以, 通過open loop實驗的設計和裝置使得被試在完成實驗任務時既沒有視覺反饋也沒有觸覺反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背側通路的使用), 而完全依賴于本體的主觀感覺。
3.1 方法
3.1.1 被試
實驗1所有被試均參與本實驗。
3.1.2 實驗儀器和設備
實驗刺激為出現在屏幕不同位置上的紅色小方框(3 mm × 3 mm)。刺激通過一個22吋的LCD顯示器垂直投射在一面鏡子上(550 mm × 350 mm)。該鏡子安裝在一個 600 mm (長) × 400 mm (寬) ×300 mm (高)的去除了底面的紙箱子上, 箱子則置于700 mm高的桌子上。LCD顯示器到鏡子的距離與鏡子到桌面的距離相等, 均為 300 mm, 這樣的設置可以使得從鏡子里看到的刺激到鏡子的距離與鏡子到桌面的距離一致, 因此, 讓被試可以感覺目標刺激好似呈現在桌面上(圖 4)。目標刺激可能出現在屏幕中矢面的左側或者右側, 每次都有 10種不同的位置, 距離屏幕中矢線的距離分別為23 mm、37 mm、51 mm、65 mm、79 mm、93 mm、106 mm、120 mm、134 mm和148 mm。每種位置在左右兩側均重復5次, 共計目標出現在左側50次, 出現在右側50次。被試用手指出目標的位置通過一張鋪在桌面上的白紙(550 mm × 350 mm)記錄, 整個手指追隨目標的過程通過外置攝像頭進行實時記錄(圖4)。

圖4 Open loop實驗設備。目標點呈現在平面P上, 沿著圖中的實線方向呈現, 并被投射到鏡子(Q平面)中。被試直立坐在桌子前, 保持頭部固定, 眼睛看向鏡子中的目標, 確保不能看到自己的手, 手指在白紙上(平面R)指出鏡中點的位置。一個攝像頭位于被試的左側以記錄被試的整個反應過程(引用并修改自Prablanc, Echallier, Komilis, & Jeannerod,1979)。
3.1.3 實驗設計
實驗過程中要求被試正直地坐在桌子前, 身體中線對著鏡子中的中線, 眼睛看向鏡子里的目標,并確保被試不能看到自己的手。將被試用來指出目標位置的手指綁上棉簽, 其中左側目標對應左手,蘸上黑墨水。右側目標對應右手, 蘸上紅墨水。一半被試先用左手追隨左側目標, 后用右手追隨右側目標, 另一半被試則反過來, 達到被試間平衡。實驗中要求被試盡可能準確地指出目標的位置, 確定目標的位置后就用手上的棉簽點在紙上相應的位置, 時間上不做限制。因此, 手的移動主要是依賴于目標相對于被試以自我參照進行判斷的位置上。
實驗為2 (被試類型:聽障人群vs.聽力正常人群) × 2 (反應手:左手vs.右手)的混合設計。因變量為屏幕中目標點距離鏡子中線的實際距離與記錄在紙上的相應點到中線的距離之差的絕對值。
3.2 結果與分析
將手指追蹤的目標位置與實際位置的偏差進行2 (被試類型:聽障人群vs.聽力正常人群) × 2 (反應手:左手vs.右手)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 只有反應手的主效應顯著,F(1,32) = 7.07,p<0.05, η2= 0.23。表明了左手的偏差(37 mm)大于右手的偏差(28 mm)。被試類型的主效應和交互作用均不顯著,F值均小于1 (如圖5)。

圖5 open-loop實驗各條件下手追蹤的目標位置與目標實際位置的偏差
實驗可以看出被試類型的差異并不顯著, 而只存在左右手間的顯著差異。由于實驗中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因而, 無論聽障被試還是聽力正常被試,右手的表現都比左手好。盡管在open loop任務中要判斷的位置也是以自我參照判斷下的坐標, 但由于沒有身體運動的視覺反饋, 實驗中也沒有提供位置信息的觸覺反饋, 因而在完成“點”追隨反應的任務中被試主要依靠自身的本體平衡感。實驗表明了,聽障被試和聽力正常被試在基本的本體平衡能力上沒有差異, 因而可以證實, 兩類被試在以自我參照判斷任務中的差異可以排除這個影響, 即聽障被試是因為背側通路改變而導致了自我參照框架的變化, 進而導致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的交互作用模式發生了變化。
4 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于考察聽障人群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之間潛在的交互作用, 并且通過將聽障人群與聽力正常人群兩組被試進行比較, 考察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之間的交互作用是否在聽力喪失之后會發生改變。實驗1要求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分別在近處空間和遠處空間內完成不同空間參照框架的判斷。結果發現, 對于聽障被試來說, 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之間存在交互作用。無論目標出現在遠處空間還是近處空間,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均顯著快于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但在近處空間條件下, 兩者的差異更大一些,t(16) = 2.20,p< 0.05,d= 0.77 (圖2)。對于聽力正常被試來說, 雖然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之間也存在交互作用, 但與聽障被試的模式不同。當目標出現在遠處空間時,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顯著慢于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 當目標出現在近處空間時, 被試對環境參照條件下目標的反應與自我參照條件目標的反應無差異(圖 3)。實驗 2要求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分別完成open loop實驗中。結果發現, 兩類被試在本體平衡感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從而證明了并不是由于聽障被試在主體平衡感上存在缺陷對實驗效應造成的影響, 而是由于聽障被試因背側通路發生了改變而導致其在完成自我參照框架判斷時產生的變化。
我們的實驗結果發現, 聽力正常被試在環境參照判斷條件下的反應時短于自我參照框架條件, 這與以往研究的結果較為一致(Chen et al., 2012)。通過聽障和聽力正常被試進行對比可以看出, 聽障被試在完成環境參照判斷中的表現與聽力正常被試的表現相當, 而在完成自我參照框架判斷的反應時長于聽力正常被試。因此可以說明, 聽障被試空間參照框架中的環境參照框架判斷的能力正常, 而自我參照框架判斷的能力受到的一定的損害, 而自我參照框架判斷是由背側通路負責的(Andersen &Buneo, 2002; Cohen & Andersen, 2002; Andersen et al.,1997), 因此, 可以說聽障被試自我判斷能力的受損是由背側通路的變化所引起的, 而這又導致了聽障被試在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之間的交互模式與聽力正常被試不同。
聽障被試在不同參照框架的表現不同是他們自身長期生活過程中逐漸累積的。由于自我參照框架的表征是依賴于身體效應器(指向行為目標的部位)的坐標信息。而環境參照框架的表征則依賴于外部世界客體位置的坐標信息。比如, 在日常生活中, 當我們走在馬路上的時候, 身后不遠的地方一輛呼嘯而來的汽車正向我們駛來, 這時我們需要將視線立刻轉移到這輛車上。在這過程中了解車輛鳴笛的空間方位信息, 對于我們判斷我們與車輛之間的位置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 自我參照框架的判斷中, 來自其他感覺通道的信息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如聲音。而聽障人群由于長期缺少聽覺信息的傳入, 進而會影響他們對自我參照框架的表征,導致他們在對自我參照框架的判斷不如聽力正常的被試。此外, 由于聽障被試長久以來使用手語進行日常的溝通和交流, 為了更好的與人溝通和交流, 他們必須注意到對方手的姿勢、位置以及兩只手的位置關系與身體之間的位置關系(Heracleous, Beautemps,& Aboutabit, 2010), 而這些訊息均屬于環境參照框架的范疇。因此, 聽障被試在環境參照框架的判斷表現完好, 自我參照框架的判斷較差。
有研究認為, 聽障人群的本體感覺存在著缺陷,而本體平衡感對于身體傾斜的感知以及空間朝向則較為重要(Angelaki et al., 2009)。因此, 這會導致聽障被試對相對于自身空間位置的判斷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我們的實驗中為了控制這一問題造成的影響, 通過 open loop實驗來對此問題進行說明。實驗結果說明了, 聽障被試和聽力正常被試并不存在著這一問題造成的差異, 因此排除了聽障被試自我參照框架表征的損傷是由本體感覺的缺失所引起。
遠處空間刺激的加工依賴于腹側通路, 腹側通路同樣也參與空間參照框架中環境參照框架的表征。而近處空間刺激的加工依賴于背側通路, 背側通路同樣也參與空間參照框架中自我參照框架的表征。由于聽障被試背側通路受損, 而腹側通路完好, 因此, 他們的結果表現為, 無論是在近處空間還是在遠處空間進行自我參照框架的判斷都表現出較長的反應時, 且兩者并不存在顯著差異。而在進行環境參照框架的判斷時, 遠處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顯著長于近處空間條件, 這一結果與我們的假設有些不符合。我們認為, 遠處空間的表征和環境參照的表征均由腹側通路負責, 因此, 遠處空間條件下環境參照的表征較易得到表征, 而近處空間條件下環境參照的表征存在背側與腹側通路之間的沖突, 因此, 這種條件下大腦中需要有一個將來自背側通路的信息與來自腹側通路的信息進行交換的場所, 根據以往研究發現, 頂枕聯合區(Parietal-Occipital Junction, POJ)則在這過程中起到了這樣的關鍵作用(Chen et al., 2012)。并且, 在進行環境參照框架的判斷時, 相對于遠處空間刺激的表征, 頂枕聯合區更偏向于對近處空間刺激進行表征(Chen et al., 2012; Quinlan & Culham, 2007; Weiss et al.,2003)。因此, 聽障被試的結果表現出, 即使在進行環境參照框架的判斷, 近處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仍然短于遠處空間。聽力正常被試的結果正好相反,無論在近處空間還是在遠處空間進行環境參照框架判斷的反應時均較長, 且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而在進行自我參照框架的判斷時, 近處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顯著長于遠處空間條件。相對于近處空間刺激的表征, 頂枕聯合區更偏向于對遠處空間刺激進行表征(Chen et al., 2012; Quinlan &Culham, 2007; Weiss et al., 2003)。因此, 聽力正常被試的結果表現出, 即使在進行自我參照框架的判斷, 遠處空間條件下的反應時仍然短于近處空間。
5 結論
(1)聽障被試由于背側通路發生了改變, 進而導致了自我參照框架判斷的能力受損;
(2)聽障被試與聽力正常被試在空間主導性和空間參照框架中的交互作用模式不同。
致謝:感謝長春市特殊教育學校段老師和王老師對實驗順利開展提供的幫助與支持。
Andersen, R. A., & Buneo, C. A. (2002). Intentional maps in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5, 189–220.
Andersen, R. A., Snyder, L. H., Bradley, D. C., & Xing, J.(1997).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in the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and its use in planning movements.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0, 303–330.
Angelaki, D. E., Klier, E. M., & Snyder, L. H. (2009). A vestibular sensation: Probabilistic approaches to spatial perception.Neuron, 64(4), 448–461.
Bavelier, D., Brozinsky, C., Tomann, A., Mitchell, T., Neville,H., & Liu, G. (2001). Impact of early deafness and early exposure to sign language on the cerebral organization for motion process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1, 8931–8942.
Bavelier, D., Dye, M. W. G., & Hauser, P. C. (2006). Do deaf individuals see better?.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0,512–518.
Beauchamp, M. S., Cox, R. W., & DeYoe, E. A. (1997).Graded effects of spatial and featural attention on human area MT and associated motion processing areas.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78, 516–520.
Berti, A., & Frassinetti, F. (2000). When far becomes near:Remapping of space by tool use.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2(3), 415–420.
Berti, A., Smania, N., & Allport, A. (2001). Coding of far and near space in neglect patients.NeuroImage, 14, S98–S102.
Bruno, N. (2001). When does action resist visual illusions?.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5, 379–382.
Bruno, N., & Franz, V. H. (2009). When is grasping affected by the Müllerr-Lyer illusion? A quantitative review.Neuropsychologia, 47, 1421–1433.
Chen, Q., Weidner, R., Weiss, P. H., Marshall, J. C., & Fink, G.R. (2012). Ne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spatial domain and spatial reference frame in parietal-occipital junction.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4(11), 2223–2236.
Christiansen, J. H., Christensen, J., Grünbaum, T., & Kyllingsb?k,S. (2014). A common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features drives action and perception: Grasping and judging object features within trials.PLoS One, 9(5), e94744.
Clavagnier, S., Prado, J., Kennedy, H., & Perenin, M. T.(2007). How humans reach: Distinct cortical systems for central and peripheral vision.Neuroscientist, 13, 22–27.
Cohen, Y. E., & Andersen, R. A. (2002). A common reference frame for movement plans in the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3, 553–562.
Franz, V. H., Hesse, C., & Kollath, S. (2009). Visual illusions,delayed grasping, and memory: No shift from dorsal to ventral control.Neuropsychologia, 47, 1518–1531.
Galletti, C., Gamberini, M., Kutz, D. F., Baldinotti, I., &Fattori, P. (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6 and PO in macaque extrastriate cortex.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1, 959–970.
Galletti, C., Kutz, D. F., Gamberini, M., Breveglieri, R., &Fattori, P. (2003). Role of the medial parieto-occipital cortex in the control of reaching and grasping movements.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53, 158–170.
Gilet, E., Diard, J., & Bessiere, P. (2011). Bayesian action–perception computational model: Interac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ursive letters.PLoS One,6(6), e20387.
Goodale, M. A., & Milner, A. D. (1992). Separate visual pathways for perception and action.Trends in Neurosciences, 15(1),20–25.
Goodale, M. A., Milner, A. D., Jakobson, L. S., & Carey, D. P.(1991). A neurological di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ing objects and grasping them.Nature, 349, 154–156.
Griffiths, J. D., Marslen-Wilson, W. D., Stamatakis, E. A., &Tyler, L. K. (2013).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neural language system: Dorsal and ventral pathways are critical for syntax.Cerebral Cortex, 23(1), 139–147.
Haazebroek, P., van Dantzig, S., & Hommel, B. (2011).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perception and action for cognitive robotics.Cognitive Processing, 12, 355–365.
Heracleous, P., Beautemps, D., & Aboutabit, N. (2010). Cued Speech automatic recognition in normal-hearing and deaf subjects.Speech Communication, 52, 504–512.
James, T. W., Culham, J., Humphrey, G. K., Milner, A. D., &Goodale, M. A. (2003). Ventral occipital lesions impair object recognition but not object-directed grasping: An fMRI study.Brain, 126, 2463–2475.
James, T. W., Humphrey, G. K., Gati, J. S., Menon, R. S., &Goodale, M. A. (2002).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viewpoint on object-driven activation in dorsal and ventral streams.Neuron, 35, 793–801.
Jiang, Y. V., & Swallow, K. M. (2013). Spatial reference frame of incidentally learned attention.Cognition, 126(3), 378–390.
Kim, H. (2014). Involvement of the dorsal and ventral attention networks in oddball stimulus processing: A meta-analysis.Human Brain Mapping, 35(5), 2265–2284.
Lomber, S. G., Meredith, M. A., & Kral, A. (2010). Cross-modal plasticity in specific auditory cortices underlies visual compensations in the deaf.Nature Neuroscience, 13,1421–1427.
Ma, Y. Y., Hu, X. T., & Wilson, F. A. (2012). The egocentric spatial reference frame used in dorsal–lateral prefrontal working memory in primates.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6(1), 26–33.
Mennemeier, M., Wertman, E., & Heilman, K. M. (1992). Neglect of near peripersonal space: Evidence for multidirectional attentional systems in humans.Brain, 115(1), 37–50.
Milner, A. D. (2012). Is visual processing in the dorsal stream accessible to consciousnes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279, 2289–2298.
O’Craven, K. M., Rosen, B. R., Kwong, K. K., Treisman, A.,& Savoy, R. L. (1997). Voluntary attention modulates fMRI activity in human MT-MST.Neuron, 18, 591–598.
Pitzalis, S., Di Russo, F., Spinelli, D., & Zoccolotti, P. (2001).Influence of the radi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on lateral neglect.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36, 281–294.
Pitzalis, S., Sereno, M. I., Committeri, G., Fattori, P., Galati, G.,Tosoni, A., & Galletti, C. (2013). The human homologue of macaque area V6A.NeuroImage, 82, 517–530.
Prablanc, C., Echallier, J. F., Komilis, E. K., & Jeannerod, M.(1979). Optimal response of eye and hand motor systems in pointing at a visual target.Biological Cybernetics, 35,113–124.
Prado, J., Clavagnier, S., Otzenberger, H., Scheiber, C., Kennedy,H., & Perenin, M. T. (2005). Two cortical systems for reaching i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vision.Neuron, 48,849–858
Quinlan, D. J., & Culham, J. C. (2007). fMRI reveals a preference for near viewing in the human parieto-occipital cortex.NeuroImage, 36,167–187.
Schenk, T. (2006). An allocentric rather than perceptual deficit in patient D.F.Nature Neuroscience, 9, 1369–1370.
Siegel, J. C., Marchetti, M., & Tecklin, J. S. (1991).Age-related balance changes in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Physical Therapy, 71, 183–189.
Stevens, C., & Neville, H. (2006). Neuroplasticity as a doubleedged sword: Deaf enhancements and dyslexic deficits in motion processing.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8,701–714.
Thaler, L., & Goodale, M. A. (2011). Neural substrates of visual spatial coding and visual feedback control for hand movements in allocentric and target-directed tasks.Frontiersin Human Neuroscience, 5, 92.
Ungerleider, L. G., & Mishkin, M. (1982). Two cortical visual systems. In : D. J. Ingle, M. A. Goodale, & R. J. W.Mansfield (Eds.),Analysis of visual behavior(pp. 549–586).Cambridge, MA: MIT Press.
Viarouge, A., Hubbard, E. M., & Dehaene, S. (2014). The organization of spatial reference frames involved in the SNARC effec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7(8), 1484–1499.
Vogeley, K., & Fink, G. R. (2003).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first-person-perspective.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1),38–42.
Vossel, S., Weidner, R., Driver, J., Friston, K. J., & Fink, G. R.(2012). Deconstructing the architecture of dorsal and ventral attention systems with dynamic causal model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31), 10637–10648.
Vuilleumier, P., Valenza, N., Mayer, E., Reverdin, A., &Landis, T. (1998). Near and far visual space in unilateral neglect.Annals of Neurology, 43, 406–410.
Weiss, P. H., Marshall, J. C., Zilles, K., & Fink, G. R. (2003).Are action and perception in near and far space additive or interactive factors?.NeuroImage, 18, 837–846.
Whitwell, R. L., & Buckingham, G. (2013). Reframing the action and perception dissociation in DF: Haptics matters,but how?.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09, 621–624.
Zhang, M., Tan, X. Y., Shen, L., Wang, A. J., Geng, S., & Chen,Q. (2014). Interaction between allocentric and egocentric reference frames in deaf and hearing populations.Neuropsychologia, 54, 6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