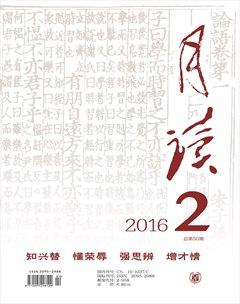醫理與治道
對于病人而言,宜“不治已病治未病”;對于國家而言,當“不治已亂治未亂”,治國和治病原理相通。治早治小、固本培元、綜合辨證、預防為主……中醫的許多核心理念都值得今人借鑒。
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病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爭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從事焉。”
《扁鵲見蔡桓公》是中國古典散文中的名篇,出自《韓非子·喻老》。《史記·老子申韓列傳》指出申子(即申不害)、韓子(即韓非子)深受老子影響,《喻老》即是通篇運用寓言故事來解釋老子《道德經》。這篇短文將中醫望、聞、問、切之“望診”展示得神乎其神,讓人嘆為觀止;它用醫學的小故事,講老子的大道理:有形之類,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細也。故曰:“圖難于其易也,為大于其細也。”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小病不治,卒成大病。小禍不除,終成大災。古人說防微杜漸,就是要把問題解決在萌芽階段。扁鵲很早就看到病癥,并提出治療意見,如能早治,并非大事難事,但這一先見之明被剛愎自用的蔡桓公拒絕,最終蔡桓公因小病轉重而不治身亡。
扁鵲的故事不止于此。《鹖冠子·世賢》還有一則:
(魏文王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镵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于諸侯。”
扁鵲兄弟三人都是名醫,長兄醫術最高,但治病于病情微末未發之際,所以聲名不出于家;二哥治病在病情初顯之時,所以名聲不出鄉里;扁鵲則往往施治于大病已成、性命垂危之際,故天下皆知。然而,若論境界,扁鵲兄長遠在扁鵲之上。
見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這是中國古代對醫者的基本要求。作為我國中醫理論的總綱,《黃帝內經》是醫經之首,既是一本醫書,又蘊含著豐富的哲理。書中講道:“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兵,不亦晚乎!”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病而求醫,就像口渴了才去鑿井,開戰時才鑄造兵器一樣。然而也有人就像蔡桓公一樣諱疾忌醫,只有在大病發作時,才猛然醒悟,卻往往重病難治,悔之晚矣。重養生、重預防,“不治已病治未病”,這一準則被歷代醫學大家奉為圭臬。當代名醫陸廣莘先生說:“上醫治未病之病,謂之養生;中醫治欲病之病,謂之保健;下醫治已病之病,謂之醫療。”扁鵲的兄長就是所謂的上醫。
對于病人而言,“不治已病治未病”;對于國家而言,是“不治已亂治未亂”,治國和治病原理相通。“藥王”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診候》說:“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在孫思邈看來,最一流的醫生治理國家,第二流的醫生治理人心,第三流的醫生才去治病。治國事關天下人的福祉,善莫大焉。“醫圣”張仲景辭去長沙太守之職,回鄉行醫時就曾感嘆:“進則救世,退則救民;不能為良相,亦當為良醫。”
那么,中醫之理和治政之道有哪些共通之處呢?
概括來講,中醫講求整體和辨證。首先,人生存于天地之間,應遵循“天人相應”和“天人合一”,人和天地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其次,每個人的身體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系統,身體的各部分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共同實現身體的整體功能;第三,每一個病癥都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因此中醫會出現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情形。真正的中醫大師是通天地、通人心、通病癥的。中醫的整體觀和辨證觀,是一種綜合而辯證的思維方式,體現了中國人獨特的世界觀。
國家和人一樣,每個人的體質不同,每個國家的基礎也不同,對癥下藥時自然不能千篇一律。西方自由派經濟學家給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開出了“休克療法”的藥方,根據“華盛頓共識”,同時推進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過程。這一做法使俄羅斯陷入了經濟和社會的長期衰退,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視了蘇聯時期俄羅斯原有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妄圖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廢墟上直接建立自由市場的大廈。相反,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倡導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既保持了政治、社會的穩定,又保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就如同治病,一個人能夠承受的手術強度是有限的,如果不顧體質情況,強行手術,不僅不能使病人盡快康復,反而會造成身體的巨大損傷。中醫的重要支脈“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主張“脾胃內傷,百病由生”,十分強調脾胃的重要作用,主張通過脾胃的調和濡養,協調解決各種病癥。脾胃是“后天之本”,有受納食物,消化和運輸水谷,化出五味營養以養全身和統攝血液等功能。人出生后,有賴于脾胃功能的健全,攝入的營養才能消化、吸收,輸送到全身,才能保證機體的正常發育和能量的需要。因此,脾胃功能的強弱,直接關系到人體生命的盛衰。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不損傷“脾胃”下推進的“增量改革”,原有的經濟活動繼續滋養,通過“調理”,新的經濟(如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集體經濟成分)異軍突起,國家元氣充沛,各項改革才能逐步開展。
又如,中醫的辨證療法講求“八綱”,八綱即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是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之一。八綱辨證,是將“望、聞、問、切”四診得來的資料,根據人體正氣的盛衰、病邪的性質,將病癥歸納為八類證候,陰陽協調是治病的根本宗旨。陰虛與陽虛是人體臟腑陰陽虧損病變產生的證候。在正常生理狀態下,人體陰陽要維持相對的平衡,即“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素問·生氣通天論》),一旦陰陽失去這種相對平衡,就會發生陰陽盛衰的變化,從而產生疾病。經濟活動也是如此,通貨膨脹是指紙幣的發行量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數量,從而引起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經濟現象,也就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通貨緊縮是與通貨膨脹相反的一種經濟現象,是指在經濟相對萎縮時期,物價總水平較長時間內持續下降,貨幣不斷升值的經濟現象,也就是社會總需求持續小于社會總供給。一個健康的經濟狀態應該是“陰陽協調”,總供給和總需求相匹配,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也是如此。
再如,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需要有合理的經濟結構,當經濟發展出現低迷時,通過大規模投資進行刺激,盡管在短時期內有成效,但從長期來看,對于經濟發展很可能弊大于利。以房地產為例,瘋狂發展可能帶動關聯產業和土地稅收的一時飛漲,但是資源浪費、環境破壞、過度建設對于經濟整體的負面作用遲早會凸顯出來。這就如同一個人身體不適,如果不分虛實,一味進補,有可能適得其反,破壞身體平衡,引發更多的病癥。僅以人參為例,它能大補元氣,生津安神,但多食反而會引起體內功能紊亂,出現口腔潰瘍、鼻出血、胸悶心煩、胃部脹悶、食欲減退、大便秘結等癥狀,甚至導致腹瀉、失眠,引起更為嚴重的惡果。
醫理和治道之間相通相和的地方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治早治小、固本培元、綜合辨證、預防為主,這些中醫的核心理念尤其值得今人借鑒。平時多讀一點經典的中醫理論著作,不僅有利于養成良好的個人生活習慣,而且會極大地有助于開拓思路,訓練思維,更好地治國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