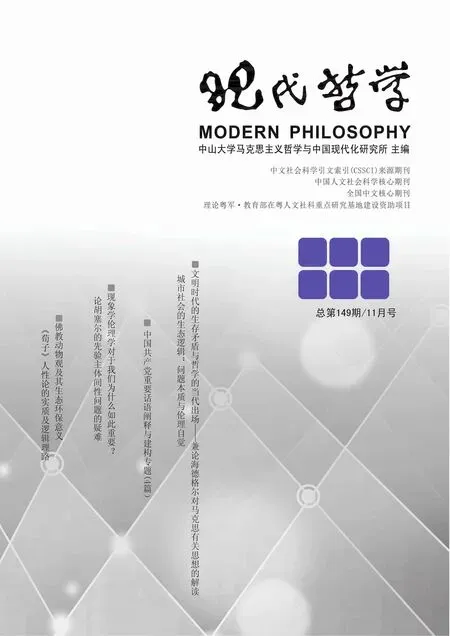論胡塞爾的先驗主體間性問題的疑難*
李云飛
?
論胡塞爾的先驗主體間性問題的疑難*
李云飛**
胡塞爾的先驗主體間性問題不僅是其先驗現象學的試金石,而且聚焦了其思想發展的最深層次的問題和疑難。文章借阿爾弗雷德·舒茨與歐根·芬克的論爭引出胡塞爾解決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原自我”方案,表明胡塞爾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所給出的“復多性主體”方案的素樸性。通過對丹·扎哈維關于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討論的分析,展顯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層次結構。最后,通過對原自我的個體化問題的論述,揭示更深維度的問題和疑難。
胡塞爾;主體間性;復多性主體;原自我;個體化
現象學從一開始就要求成為先驗哲學,要求解決客觀認識的可能性問題。但進行還原的先驗自我本身似乎從一開始就限制了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因為“當我這個沉思著的自我,通過現象學懸擱,把自己還原為我的絕對的先驗自我時,我不就成為那個唯一的我(solus ipse)了嗎?”①[德]胡塞爾:《笛卡爾沉思與巴黎演講》,張憲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頁。現象學似乎已陷入了先驗的唯我論。因此,現象學的主體間性問題(Intersubjektiviaet)源于其理論的自身要求,即“先驗現象學要求成為先驗哲學,要求能以一種在被先驗地還原了的自我的范圍內活動的構造的問題性和理論的形式去解決客觀世界的先驗問題”。②同上,第126頁。(譯文參照德文原版有所修正)誠如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言:“胡塞爾哲學中的他人問題是先驗現象學的試金石……他人問題在胡塞爾那里扮演的角色與上帝的誠實在笛卡爾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一樣,因為它奠定了每一種真理和實在的基礎。”③Paul Ricoeur,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Volume IV, The Web of Meaning: Language, Noema and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Routledge, 2005, p.318.
眾所周知,胡塞爾關于主體間性問題的最詳盡和系統的探討是在第五《笛卡爾式的沉思》(以下簡稱《沉思》)中進行的。然而,胡塞爾的批評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他在第五《沉思》中關于主體間性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失敗的,并且他最終也未能提供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在諸多的批評者中既有胡塞爾的親炙弟子,例如歐根·芬克(Eugen Fink)、路德維希·蘭德格雷貝(Ludwig Landgrebe)和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等,也有后繼著名的現象學研究者。他們依據相關的文本——胡塞爾生前發表的著作或未出版的遺稿——各自從不同角度對胡塞爾關于主體間性問題的論述進行系統的闡明和批評,并且都或多或少試圖從胡塞爾的文本中探尋可能的解決方案。本文從舒茨與芬克的論爭談起,旨在揭示胡塞爾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層次結構和核心疑難。
一、舒茨與芬克的論爭
1957年在盧瓦蒙特(Royavmont)召開的“胡塞爾學術研討會”上,舒茨作了題為《胡塞爾的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舒茨依據第五《沉思》對胡塞爾關于主體間性問題的論述提出了系統的辯駁。他認為第五《沉思》的解決方案中的每一個步驟都伴有異乎尋常的困難,這些困難使人們懷疑“胡塞爾發展一門先驗的他人經驗理論(同感)——作為一門先驗的客觀世界理論的基礎——的努力是成功的”,而且使人們懷疑“這樣一種努力無論如何都能在先驗領域獲得成功”。*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Volume I, Circumscriptions: Classic Essays o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Routledge, 2005, p.93.舒茨的辯駁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學術影響。具體來說,舒茨依據第五《沉思》的論述線索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其系統的辯駁:1)原真還原的疑難;2)他人身體的構造的疑難;3)他人構造的疑難;4)高級共同體的構造的疑難。舒茨認為,原真還原的疑難主要在于,如何能夠確認本己性領域和非本己性領域的范圍;*Ibid., pp.95-96.他人身體的構造的疑難在于,“相似性統覺”如何可能;*Ibid., pp.99-100.他人構造的疑難在于,共現和同感如何可能;高級共同體的構造的疑難則在于,個體主體如何能不是作為共同體的成員而具有意義。*Ibid., pp.106-108.鑒于本文的主旨,我們這里主要討論與后兩個疑難相關的問題。
他人構造的問題是第五《沉思》的第三個步驟。按照胡塞爾的觀點,隨著他人身體的共現,任何屬于另一個我的具體化的東西,首先作為他的原真世界,然后作為充分具體的單子,通過同感被共現。在高層次的統覺中,我共現作為一個“在那里”與我共存的自我的他人。由于經驗到他人,與他人一同被共現的世界被添加到我的原真地被構造起來的世界上,這個共現的層次被經驗為與我的原真地被構造起來的世界處于綜合的統一性中。因此,客觀世界就作為自我與他人之主體間共同體的相關項被構造起來。舒茨認為,胡塞爾試圖從主體間性導出世界的客觀性的做法是一個方法上的錯誤,而事實上可能恰恰相反,客觀世界是主體間性的前提,因為一切交往的過程都已經以作為支撐物或媒介的客觀事物為前提了。因此,在他看來,世界的客觀性優先于主體間性。
就個體主體如何可能不是作為共同體的成員而具有意義的問題,舒茨指出,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以下簡稱《危機》)中,胡塞爾涉及“從‘自我’……向‘他我’,向‘我們大家’(由許多個‘我’構成的‘我們’,在其中我只是‘一個’我)的意義轉變”,涉及“從自我出發,甚至‘在’自我‘之中’構成作為這個‘我們大家’的主體間性問題”。*[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21頁。(譯文參照原文有所調整)但問題是,這些自我,這個“我們大家”,在實行了先驗還原后不是變成了單純的現象嗎?難道情況不是:實行懸擱的哲學家既不將自己也不將他人作為人來對待,而是作為先驗回問的自我極來對待嗎?因此,在舒茨看來,問題是,談論復多性的先驗自我是可想象的和有意義的嗎?先驗自我的概念不是只有在唯一性中才是可想象的嗎?它也能被變格為復數性的嗎?*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Volume I, Circumscriptions: Classic Essays o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Routledge, 2005, p.109.
在《在當代批評中的埃德蒙德·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中,芬克就先驗自我的復多性問題指出:
對意向性的探詢……導致對一種具有獨特結構的復多的先驗自我的存在關聯的先驗證明,這些先驗自我只能借單子這一“形而上學的”標題被標示,而不能被標明。因此,一種大量的復多性絕不是被搬進先驗的領域,同樣,先驗自我也不能在世間的單個性的觀念下被思考。“諸單子”的蘊含是重大的問題的標題,它標識著單子復多性的非廣延的存在,單子復多性只是標識著在先驗領域內一種非個體化的交織的可能方式。*Eugen Fink, Studien zur Ph?nomenologie, 1930-1939, Martinus Nijhoff, 1966, S. 136-137.
胡塞爾在《危機》中說:
懸擱不僅在個別心靈內部進行的個別還原中是不適合的,而且它作為從心靈到心靈的個別還原也是不適合的。全部心靈構成一個處于諸個別主體的生活流的相互關聯之中的意向性的唯一的統一,這種統一可以由現象學系統地闡明;在樸素的實在性或客觀性中是相互外在的關系,如果從內部來看,就是意向上彼此內在的關系。*[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第307頁。(譯文參照原文有所調整)
對此,舒茨指出,芬克和胡塞爾的上述觀點是極其悖謬的,因為完全不清楚的是,“意向上彼此內在”如何能說明那種屬于單個主體、甚至全部心靈的生活流的交互蘊含呢?*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Volume I, Circumscriptions: Classic Essays o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Routledge, 2005, p.110.最終,舒茨得出結論說,胡塞爾根據先驗自我的意識操作來說明先驗主體間性的構造的企圖是失敗的。他認為,主體間性不是一個能在先驗領域內解決的構造問題,而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種被給予性,一個既定事實。它是人之在世存在的基本的存在論范疇。自我對自身進行反思的可能性,發現自我的可能性,實行懸擱的能力,以及一切交往的可能性和建立一個交往的周圍世界的可能性,這一切都奠基于對我們-關系的原初經驗中。因此,在他看來,只有生活世界的存在論,而不是先驗的構造分析,才能澄清主體間性的本質關系。*Ibid., pp.113-114.
在盧瓦蒙特會議上,芬克對舒茨所提出的辯駁作了回應。
首先,關于客觀世界與主體間性何者優先的問題,芬克指出客觀性與主體間性之間不可能存在優先與否的問題,毋寧說,客觀性與主體間性可能是共同原本的。
其次,關于個體主體如何可能不是作為共同體的成員而具有意義的問題,芬克說:
在其寫于《笛卡爾式的沉思》后的晚期手稿中,胡塞爾……認識到將內世間的復多性主體簡單地轉移進先驗領域所包含的困難……而且,在某些手稿中,他達成了奇特的原-自我、原-主體性的觀念,這種原自我、原主體性先于原真的主體性與其他單子的先驗主體性之間的區分而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他似乎想把復多性從先驗領域內撤回……根據胡塞爾在這些很晚的手稿中的觀點,存在一種原始生活,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事實性的,也不是本質性的;而是所有這些區分的終極基礎:一種先驗的原始生活,它將自身轉變成一種復多性,并且在自身中產生分化,即分化成事實與本質。*Alfred Schütz, Collected Papers III, Studies in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Martinus Nijhoff, 1970, p.86.
這段論述的核心涉及到原自我與先驗自我的復多性的關系問題,“原自我(Vor-Ich)”、“原主體性”和“原始生活”這類表述蘊含著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層次結構,這實際上指明了解決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一個可能方案。在芬克看來,如果考慮這些后期手稿的文本,那么胡塞爾在《沉思》中的論述所伴有的各種疑難就會在一種十分不同的光亮中顯現出來。
二、圍繞“原自我”方案的論爭
在《胡塞爾在弗萊堡時期的晚期哲學》一文中,芬克更為具體地提出了與前述相同的觀點:
在胡塞爾晚年的研究手稿中產生了奇特的思想,最原初的意識生活深處不再有本質與實存的區分,毋寧說,它是原始-基礎(Ur-Grund),事實與本質、現實性與可能性、樣本與種屬、一與多之間的分叉首先發源于它。與這種奇特的思想動機相關聯的還有一種同樣奇特的改變,即胡塞爾最晚期的主體概念的改變。《笛卡爾式的沉思》第五沉思極堅定地論述了復數的先驗主體的命題——世界和一切世間存在者的客觀性都回溯到一種單子大全的主體間性。這種立場雖然后來沒有被胡塞爾放棄,在手稿中卻出現了原自我的思想,這種原自我先于自我與其他自我的區分,它首先使復數從自身中突現。時間建基于一個創造時間的當下中,這個創造時間的當下不在時間中;一切存在者的分裂(本質-實存)都建基于一個原始-統一性中,這個原始-統一性既不是“事實性的”,也不是“可能性的”,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一個范例,也不是一個屬;主體的復多性建基于一個生活深處,這個生活深處先于任何一個自身性的個體化(Inviduation)……胡塞爾試圖用感覺靈敏的現象學分析工具把握逃逸可言說性的東西。胡塞爾想要回思無定形的基礎,各種構形就產生于這種無定形的基礎中……但卻不是以一種神秘地沉入黑夜的方式,像黑格爾所嘲笑的那樣,“其牛皆黑”;他想要將其理解(把握)為沖破生命基礎的原始-裂縫(Ur-Sprung),理解為裂口,理解為最原始的存在中的否定性……胡塞爾雖然使用了“絕對形而上學”的詞匯,但他實際上遠離它。他獲得這類令人可疑的概念……不是通過思辨的思想……他在某種程度上試圖“當場”捕獲先驗意識的生活實行(Lebensvollzug)。*Eugen Fink, N?he und Distanz, Ph?nomenologische Vortr?ge und Aufs?tze, Verlag Karl Alber GmbH Freiburg/München, 1976, S. 223-225.
這段著名的論述清楚地表明了胡塞爾在解決現象學的主體間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探問方向。首先,“最原初的意識生活深處”、“原始-基礎”、“原自我”和“原始-統一性”這些幾乎同義的表述,本質上是從不同的角度點明了先驗還原的方向和先驗的主體間性的問題層次;其次,先于個體化自我的原自我的復數化問題指明了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關節點,它既是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問題解決的方向和途徑;再次,“沖破生命基礎的原始-裂縫”的觀念揭示了先驗的主體間性之“同一-差異”的結構特征;最后,“當場捕獲先驗意識的生活實行”的說法表明了一種拒絕思辨的形而上學的先驗現象學立場。因此,盡管芬克在這段論述中沒有具體展開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討論,但仍為我們指明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既“原自我”方案。
這一方案引發了后繼研究者的持久討論,我們在此以扎哈維(Dan Zahavi)的系統探討為切入點來凸顯胡塞爾的先驗主體間性問題上所聚焦的核心難題。
與“原自我”方案將先于一切個體化的原始生活作為最終的構造基礎的觀點相對,扎哈維堅持先驗的主體間性是最終的構造基礎的立場。他認為存在兩條探討主體間性問題的進路:一條是展顯視域意向性的進路,它揭示的是“開放的主體間性”,這種“開放的主體間性”在一切具體經驗中發揮“構造性的”作用,它是我們的世界經驗本身的一個形式的結構要素;*Dan 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 by Elizabeth A. Behnk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9-52.另一條是本欲意向性的進路,它通過對各種本欲和情感的分析從現象學上說明“共在”或“為他人存在”。*Ibid., pp.74-75.
按照芬克的觀點,最終的構造基礎是原自我或原始生活,它先于任何個體化,因此也先于自我的復多性。扎哈維認為,這不僅是對“原自我”概念的一種“形而上學”解釋,而且明顯與胡塞爾始終強調先驗主體的復數性和差異性的觀點相矛盾。如果先驗主體的復數性在一個先于一切個體化的絕對自我之自身復數化中有其基礎的話,那么先驗主體之間的差異性就不可能被保持。但問題是,在芬克的論述中已經明確考慮到胡塞爾的這一立場,“《笛卡爾式的沉思》第五沉思極堅定地論述了復數的先驗主體的命題”,并且強調“這種立場后來沒有被胡塞爾放棄”。顯然,芬克并不認為《沉思》中“復數的先驗主體的命題”與晚期手稿中的“原自我”概念存在原則性的沖突。因此,扎哈維與其指責芬克對“原自我”概念的“形而上學”解釋,倒不如問:芬克的論述如何自洽?換句話說,胡塞爾的“復數的先驗主體的命題”與他的“原自我”概念如何才能達成一致呢?
在扎哈維看來,盡管胡塞爾本人的確有關于“自我的自身復數化”的說法,但也只是“偶爾論及”。*Ibid., p.67.例如,我們在《危機》中可以讀到:
因此,我,自我,擁有源于某種成就的世界,通過這種成就,我一方面構造我和我的他者視域,并與此同時構造同質的我們-共同體,而且這種構造并非世界構造,而是可以被稱作自我的單子化的成就——作為人格的單子化的成就,單子的復數化的成就。在自我中,在它的成就中,自我被構造起來,它擁有其他的自我,每一個自我都是唯一的,每一個自我都自在自為地是絕對的功能主體,對于一切構造成就而言是唯一的,每一個自我都被單子化,并構造起它的單子性的“我們-全體”,其中的每一個自我都蘊含著作為他我的每一個他我,蘊含著作為我們的它的我們,而且在它的我們中,又蘊含著所有的我們,并將所有的我們同質化,等等。*[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第498頁。(譯文參照原文有所調整)
對此,扎哈維也覺得這似乎直接支持了芬克的觀點,但他認為胡塞爾在這里顯然將單子化理解為由同等狀態和本質相同的單子構成的單子大全的構造,因此,只不過是對“自身異化”的一種新描述。*Dan 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 by Elizabeth A. Behnk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7.然而,切近的分析表明,胡塞爾這里的論述涉及一個不同尋常的“前自我”概念,即“在自我中,在它的成就中,自我被構造起來”中的“自我”,而且這個“自我”構造“我的他者視域”和“同質的我們-共同體”。胡塞爾強調,“這種構造”可以被稱為“自我的單子化的成就”、“單子的復數化的成就”。顯然,扎哈維的關注點在于“同質化”的自我,而沒有對這個不同尋常的“前自我”概念給予應有的注意。
事實上,扎哈維對于這個不同尋常的“前自我”概念持明確否定的立場。為此,他需要對胡塞爾關于“前自我”概念的一段明確論述做出合理的解釋。在一份出自1933年的手稿中,胡塞爾說:“對原始的當下(佇立的活的流動)的結構分析將我們引向自我結構(Ichstruktur)和為自我結構奠基的固定的底層的無自我的流動,這通過對那種使積淀的活動得以可能的東西和積淀的活動以之為前提的東西的堅持不懈的回問而回引到徹底的前-自我之物(Vor-Ichliche)。”*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598.顯然,胡塞爾在這里明確肯定了“前自我”概念,而且將“前自我”規定為一種“為自我結構奠基的固定的底層的無自我的流動”。但扎哈維卻認為,胡塞爾關于無自我的談論只是一種抽象的說法,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原始的原本的自我-極——它甚至在匿名的意識過程中也起支配作用——的話,則在其原始的原本性中的意識流是不可想象的。在他看來,胡塞爾同時提到意識的無自我性和自我性表明了概念上的歧義性。當胡塞爾談論“無自我的流動”時,“無自我的”這一表述指的并非自我的缺乏,而是指流動的原始的被動性,它處于自我的影響之外。而當他談論一個前自我的層次時,這決不是指一個絕對的前個體化的基礎,而是在談論一個先于作為反思的論題對象的自我的構造層次。對此,扎哈維強調,作為進行構造的自我,作為一切進行構造的觸發和行為的接受-發射中心,作為已時間化的和正在進行時間化的東西,自我始終是自身覺察的。但是,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對自身的“覺察”,也就是說,自我不是一個自然意義上的意向對象。因此,在反思之前有一個非論題性的和非對象性的意識,自我的存在是一個持續通過絕對的自身顯現的自為存在,而反思的對象化以此前反思的自身覺察為前提。*Dan 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 by Elizabeth A. Behnk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1-72.顯然,扎哈維的解釋是成問題的。首先,“無自我的流動”既然是指流動的原始被動性,即“處于自我的影響之外”,為什么它“并非自我的缺乏”呢?其次,扎哈維試圖以自身覺察與自身覺察的對象、前反思與反思之間的區分來消解“前自我”概念的做法也是站不住腳的,當他說“作為進行構造的自我,作為一切進行構造的觸發和行為的接受-發射中心,作為已時間化的和正在進行時間化的東西,自我始終是自身覺察的”時,他已經將“前自我”排除在外了。按照胡塞爾的觀點,扎哈維所說的“作為進行構造的自我,作為一切進行構造的觸發和行為的接受-發射中心,作為已時間化的和正在進行時間化的東西”恰恰是由“前自我”奠基的。因此,關節點仍然在于“復數的先驗主體的命題”與“前自我”(亦即“原自我”)之間的關系問題。
為了堅持其基本立場,即在胡塞爾那里不存在從前個體化的絕對意識向復數的先驗主體的個體化的維度,先驗的主體間性是最終的構造基礎,扎哈維又探討了本欲意向性(Triebintentionalit?t)問題。在本欲意向性的標題下,胡塞爾論及在被動的流動內被喚起的各種本能,無自我的時間化。在那里,主體間性的關聯純粹產生于原初的被動的意向性,亦即產生于各種朦朧的主體間性的本能。只有當它們通過被充實而得到揭示時,這些本能才能顯示它們的意義。對此,胡塞爾在《現象學的心理學》中說:“被動性、本能的本欲生活已經產生了主體間的關聯。例如,在最底層上,一種性關系已經由性本能的生活產生,盡管只有通過充實才可能揭示其本質的主體間性。”*Husserliana IX, Martinus Nijhoff, 1968, S. 514.盡管胡塞爾未能系統闡明本欲意向性領域內的主體間性問題,但他已指明在性欲本身中已存在與他人的關聯性。*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593-594.而且他注意到,由于個體單子與其他單子在本能上的關涉,它從自身內部產生一個超出自身的指向,以至于個體單子本身是不自足的。*Husserliana XI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257.在此語境下,胡塞爾甚至談論一個通過相互滲透的本欲充實被建立起來的復多的原真性的統一性,*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594.并且將先驗自我的復多性標識為一種以相互滲透的共存的方式的共在。*a.a.O., S. 367-368.因此,我們在單子共同體內發現的東西是一種意向的蘊含,一種先驗的共存,自我的生活和活動的一種單子間的相互滲透。*a.a.O., S. 370.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特拉塞爾(Stephan Strasser)斷言,必須放棄各個意識流的嚴格分離,這與本欲意向性的概念不協調。因為本欲意向導致一種相互滲透的充實,以至于各個單子的內在之間的嚴格分離被取消了。因此,胡塞爾會說,“原始地佇立的流動”先于各別的個體單子的流動。*Stephan Strasser, “Grundgedanken der Sozialontologie Edmund Husserl”,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29(1975), S. 16-17.然而,扎哈維堅持認為,主體間的統一性始終是一個源于復多性的統一性,意向上的相互滲透絕不意味著自我間的融合,而是以它們之間的差異為前提。在他看來,主體的復多性和差異性恰恰是任何共同性的可能性條件,而融合和同一則意味著主體間性的消解。顯然,扎哈維關于本欲意向性領域主體間性問題的解釋也是成問題的。一方面,他試圖借助本欲意向性領域內意向的超越指向和主體間的關涉性論證主體間性是最終的構造基礎,這必然導致在本欲意向的層次上不存在主體間的差異性和復多性;另一方面,他卻堅持相反的結論,即“意向上的相互滲透絕不意味著主體間的融合,而是以它們之間的差異為前提”。因此,這種解釋的悖論性質是顯而易見的。
在《危機》中,胡塞爾論及原自我與先驗的主體間性的關系:“原-自我——通過一種它所特有的特殊的基本成就——將自己變成對于自己本身來說是先驗的可以變格的東西;因此它從自己出發,并且在自己本身之中,構造先驗的主體間性,在這種情況下,它將自己作為具有特權的一員,即作為先驗的他者當中的‘我’,也歸屬這種主體間性。”*[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第224頁。(譯文參照原文有所調整)顯然,這種明確將原自我作為先驗的主體間性的構造基礎的觀點對扎哈維的立場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但扎哈維認為,胡塞爾“偶爾”關于原自我是最終構造層次的主張與主體間性理論并不矛盾;毋寧說,原自我概念恰恰是其主體間性理論的前提。在他看來,胡塞爾所說的主體間性指的是自我與他人之間的一種關系,而對于主體間性的闡明必然以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為出發點。因此,只有通過徹底展顯自我的經驗結構,才能闡明主體間性。主體間性不僅意味著主體間的自我性,而且同時意味著自我的主體間性的結構化。因此,“只有從個體自我的立場出發,才能從現象學上展示主體間性和構造中心的復多性”。*Dan Zahavi,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 by Elizabeth A. Behnk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9-80.顯然,扎哈維在此的策略是,既堅持先驗的主體間性是最終的構造層次,又以闡明先驗主體間性的名義保留原自我。但問題是,扎哈維對此是將原自我直接等同于“個體的自我”了,這顯然有違胡塞爾對此的明確主張。
為了強化其先驗的主體間性作為最終的構造基礎的立場,扎哈維一再援引胡塞爾的觀點:“主體性只有在主體間性中才是其所是:構造性地起作用的自我。”*[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第208頁。(譯文參照原文有所調整)然而,問題是,胡塞爾同時堅持這樣的觀點:“絕對自我,它在決不可打破的永久性中先于一切存在者,包含一切存在者,在其‘具體化’中先于一切具體化,它包含一切可想象的的存在者,它是還原所獲得的最初的‘自我’——一個自我,這樣稱呼是錯誤的,因為對它來說,一個他我沒有意義。”*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586.按此觀點,絕對自我不是仍具有變格性的“你”、“我們”的自我,它是獨一無二的,而只能借助一種歧義性才能被稱作“自我”。顯然,這里的疑難在于,一方面是先驗的主體間性的不可還原性,另一方面則是原自我的絕對的唯一性,二者之間如何調解呢?
對此,扎哈維給出的回答是,這種矛盾是表面性的。因為在他看來,所謂“原自我的不可變格性”指的是“我”的指示性特征,而不是指實體性的唯一性。就“我”的指示性特征而言,他人也具有唯一性,例如當他人經驗其自身時、當他說“我在”時。而就充分和具體的自我而言,先驗主體性則是先驗的主體間性。在先驗的主體間性內預先有一種向自我——作為擁有我們-意識的自我——的必然的中心化,但這絕不意味著,必須有某種主體間性先于個體化的自我而存在,然后經歷了一種中心化;毋寧說,先驗的主體間性作為其展開的場所在自身內包含先驗主體性。最終,扎哈維得出結論說,徹底的還原不僅導致先驗主體性,而且導致先驗的主體間性,二者不可能孤立地被思考。顯然,扎哈維在此的論述是站不住腳的。首先,當胡塞爾說“主體性只有在主體間性中才是其所是:構造性地起作用的自我”時,所說的“主體性”并非原自我,而是指已個體化了的自我,已“同質化”的自我。因此,這里的問題涉及的是自我的層次的劃分,而不是援引“我”的指示性特征能夠消解的。其次,扎哈維關于“先驗主體間性向自我的中心化”說法也是令人費解的。一方面,先驗的主體間性預先有一種向自我的必然的中心化;另一方面,則否認有某種主體間性先于個體化的自我而存在,然后經歷了一種中心化。這二者之間的張力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問題的癥結恰恰在于,扎哈維始終拒絕原自我與個體化自我之間的層次區分。
三、“原自我”方案及其疑難
扎哈維的論述所伴有的疑難表明,胡塞爾的先驗主體間性問題主要聚焦于這樣幾個方面:1.構造的最終基礎是個體的先驗主體還是先驗的主體間性的問題;2.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層次秩序,即先驗自我的復多性問題與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之間的關系問題;3.原自我與先驗自我的復多性的關系問題。
在蘭德格雷貝看來,“胡塞爾在第五《笛卡爾式的沉思》中對其主體間性理論所做的第一次詳盡的展示是失敗的,因為他想要靜態地闡明這一理論”。他認為胡塞爾后期超越了靜態分析的框架,試圖“通過共現的相似性統覺將主體間性的構造回溯到其在一種聯想地創立的共現中的被動的前構造(Vorkonstitution)”。但這仍然未能解決問題,因為“就這種聯想的相似化而言,單子與你、與我們、與一般的他人的自身區別已經被作為前提了”。*Ludwig Landgrebe, “Die Ph?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al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in Edmund Husserl,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edited by 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Volume IV, The Web of Meaning: Language, Noema and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Routledge, 2005, S. 178.顯然,蘭德格雷貝在此提出的是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層次秩序,即先驗自我的復多性問題與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之間的關系問題。事實上,在《沉思》中,盡管有向原真領域還原的方法論步驟,但先驗自我的意義已發生了某種變化:這個自我已然是“一個”自我,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單數性的自我,它站在其他自我的旁邊,它與其他自我具有同等的有效性。這是先驗還原的素樸性造成的。因此,蘭德格雷貝認為,在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上,我們首先應面對的不是如何從復多性的主體性構造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而是“被作為前提的”復多性的主體之間的區分和同質化問題。就像胡塞爾所提出的那樣:“并非首先存在若干心靈,然后問題是,在何種條件下它們彼此‘和諧地’實存;毋寧說,問題在于,當我確信一個心靈并且沉浸于它的本己本質之中(在自身給予的直觀中),我如何能得知,它只是‘一個’心靈而且只能是‘一個’心靈,以至于它在這個本質中必然指向其他的心靈?我如何能得知,這個心靈雖然自在自為,但它卻只有在一種基于其自身、從它自身中展開的復多性中才具有意義?”*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341.(斜體部分是筆者所作的強調)因此,與芬克的立場一致,蘭德格雷貝對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解決也訴諸于原自我或原始生活。
事實上,在胡塞爾后期關于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思考中,面對唯我論的指責,一個根本的動機在他那里產生了。這個根本的動機是將主體的個體性看作本身被構造起來的。因此,它是使先驗還原超出這種個體性的動機,它所要達到的是一個“前自我”的層次,胡塞爾也稱為“原自我”。在這個“原初的層次”上,構造不再是個體自我綜合和聯結其經驗的行為,而是最初產生自我的東西。在此方向上,先驗還原超出個體性的層次,最終達到個體性和時間性的基礎。因此,芬克完全有理由確認胡塞爾后期手稿的立場:“時間建基于一個創造時間的當下中,這個創造時間的當下不在時間中;一切存在者的分裂(本質-實存)都建基于一個原始-統一性中,這個原始-統一性既不是‘事實性的’也不是‘可能性的’,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一個范例,也不是一個屬;主體的復多性建基于一個生活深處,這個生活深處先于任何一個自身性的個體化。”*Eugen Fink, “Die Sp?tphilosphie Husserls in der Freiburger Zeit”, in N?he und Distanz, Ph?nomenologische Vortr?ge und Aufs?tze, Verlag Karl Alber GmbH Freiburg/München, 1976, S. 223-224.先驗還原揭示了一個原初的構造層次,這個原初的構造層次是原始的時間化層次,即時間構造的非時間的起源層次。對于胡塞爾來說,這也是一個我們能直接通達他人的層次:“對于每一個個體來說,時間構造的原初的起源點都是對其當下的原初經驗,同樣也是每一個個體經驗他人的權能……也就是說,在其本己的活的當下內,每一個個體以原初的方式經驗他人的權能,因此,經驗其本己的存在與他人的存在之間原初的相合的權能。”*Edmund Husserl, Ms.C 17 I, S.4-5, 1931.轉引自James Richard Mens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 p.20.(本文對胡塞爾“原自我”方案的論述部分參照了門施的觀點。)在他看來,回溯時間構造的起源點就是還原到先于復多性主體的生活深處,將他人經驗為另一個主體必然要求這樣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我與他人具有一種原初的同一性。
然而,將他人經驗為另一個主體不僅要求“我與他人具有一種原初的同一性”,而且要求“我與他人存在一種原初的差異性”。如果缺乏我與他人存在的原初差異性,則不僅會導致唯我論,而且直接消解了主體間性問題。胡塞爾應對這兩種要求的舉措是,在不同的層次上分別滿足這兩種要求:在奠基的層次上滿足同一性要求,而在被奠基的層次上滿足差異性要求。據此解決方案,將他人經驗為另一個主體在于,他人不是被經驗為我的構造物,而是被經驗為一個本己的構造中心,即在其經驗的現時性中起作用的構造中心。因此,對差異性的經驗揭示了他人在一個原初的同一性層次上的奠基。但問題是,胡塞爾將如何通過先驗還原達到這個先于差異性經驗的“原初的同一性層次”呢?
在《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以下簡稱《觀念I》)中,為了突出純粹意識的絕對性,胡塞爾做了一個著名而又極具爭議的思想實驗:
設想一下每種超越物本質中包含的非存在的可能性:因為顯然,意識的存在,即每一個體驗流一般的存在,由于物的世界的毀滅而必然變樣了,但其自身的存在并未受到影響。當然是變樣了。因為世界的毀滅相應地只意味著,在每一個體驗流中……某些有序的經驗聯結,以及因此與那些經驗聯結相關的理論化理性的聯結,都被排除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它體驗和體驗聯結也被排除了。因此實在的存在,在顯現中對意識呈現和顯示的存在,對于意識本身(在最廣泛的體驗流意義上)的存在不是必不可少的。*[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33頁。(譯文依德文原版有所調整)
這表明世界的毀滅與意識流的消解一體相關,但最終還剩下“純粹的”或“絕對的”體驗,只不過這些體驗已喪失了任何秩序性,而變成了一團混沌。胡塞爾在《觀念I》中仍然將這種混沌的體驗流稱為“意識”,然而,它已變成一個無自我的“意識”流了。“意識”雖然還存在,但只剩下無秩序性聯結的體驗成分了。這表明絕對存在的是“意識”流本身,無論其中的體驗成分的聯結發生什么變化,它都存在。客觀存在的顯現依賴于“意識”流中體驗成分的聯結,因此,自我和世界二者都依賴于這種聯結。
按照胡塞爾的觀點,問題不在于“現時的經驗只能在這類聯結形式中進行”,這類聯結的消解“并不意味著,其它體驗和體驗聯結也被排除了”。*同上,第133頁。(譯文依德文原版有所調整)毋寧說,任何類型的聯結都是可能的,因此不存在先天的經驗的聯結形式。對此,胡塞爾說:“可以想象,在我們的經驗中擁塞著不只是對我們來說、而且在其自身上都不可調和的沖突,如經驗可能突然顯示出對繼續協調地維持物的設定這一要求的抗拒;如經驗聯結會失去由側顯、統握、顯現等作用構成的固定的規則秩序;又如不再存在有任何世界。”*同上,第133頁。(譯文依德文原版有所調整)因此,一旦我們否定任何先天的聯結形式和聯結規則的實存,而肯定最終的事實性,那么就會產生兩個結果:首先,我們可以設想抽離出任何聯結形式的經驗,可以設想抽離出由這類聯結形式所構造起來的世界的經驗;其次,可以設想,還原所達到的絕對意識是一個“純粹的”體驗流,這個體驗流獨立于任何被給予的世界。它沒有被預先規定,它不遵守任何先天規則。
鑒于對絕對“意識”流的這種理解,先驗自我的個體化問題凸顯出來。首先,自我依賴于它的周圍世界,這種依賴實際上是自我和世界對意識的有序聯結的共同依賴,最終是對無自我的“意識”流的共同依賴。其次,一同被構造起來的統一性都是偶然的,因為所有被構造起來的統一性的最終基礎是無任何聯結形式的事實性的體驗要素。對于被構造起來的世界整體來說,這些事實性的體驗要素顯示了一種絕對的被給予性。這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層次的構造具有先天必然性,因此,一切構造過程的結果都是偶然的。作為最終基礎的絕對“意識”流是一切客觀存在的構造性基礎。胡塞爾有時也徑直將“最終基礎”、“絕對意識”稱為“絕對”。如果我們把絕對看作“意識”流,那么由于個體性的自我本身是被構造起來的,因此,世界從“意識”流中的構造無需一個外在于這個“意識”流中的個體性的自我。個體性的自我及其周圍世界都是由這個絕對“意識”流被動地構造起來的。二者對于“意識”流之事實性的依賴性涉及它們作為個體的、聯結在一起的統一體的存在。因此,這種依賴性同樣適用于復多性的個體自我,亦即適用于由復多的個體性主體所構成的主體間性。對此,胡塞爾說:“如果我們在系統的進展中從下面搭建預先被給予的世界的先驗構造的話,那么應當注意:在每次做出的對本質形式的‘澄清’中,在流動的佇立中的現實內涵的事實(Faktum)當然被作為前提。這顯然也同樣適用于‘絕對’,適用于先驗的主體間性一般。我們所揭示的絕對是絕對的‘事實’(Tatsache)。”*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1973, S. 403.從詞義上講,“Tatsache”就是“做事”,但在這里沒有“行為者”(T?ter)。*a.a.O., S. 669.它先于意向行為或我思活動。因此,這種事實不是偶然的事實,不是一種個體的自我論的事實,而是“永久地奠基自我結構的、無自我的河流的基層”,是“那個使被積淀的活動成為可能和被積淀的活動以之為前提的東西”,是“徹底的前自我性的東西”。對此,胡塞爾進一步規定說:“原始的河流和原始地被構造起來的非自我是原素的宇宙(現實的經驗內容的宇宙),它本身是構造性的,而且它已經不斷地被構造起來;它是一個時間化著的-時間性的原始發生著的事件(Urgeschehen),這個原始發生著的事件不是產生于自我論的起源;因此,它產生而沒有自我的參與。”*Edmund Husserl, Ms. C 10, S. 25, 1931.轉引自James Richard Mens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 p.150.在他看來,絕對領域的要素可以被看作一個由各種純粹體驗構成的字母表,這些純粹體驗按照確定的時間位置被秩序化而形成經驗的聯結,由此產生一個特殊的經驗視角,一個具有某種特定秩序的構造中心。經驗視域的視角性的結構構成世界的個體經驗者之實存可能性的基礎,正是經驗的視角性的秩序化使得這些個體經驗者在空間和時間中有一個確定的零點,這個確定的零點就是被理解為一個主觀的經驗中心的純粹自我。于是,絕對的“意識”流個體化為一個本己的意識流。以此方式,胡塞爾就通過絕對的個體化確立了兩個不同的自我層次:1.前自我的絕對或原自我;2.個體性的復多性主體。
按照胡塞爾的觀點,正是絕對“意識”流中純粹體驗的聯結構造起不斷進行中的我思,因而構造起行為的人格自我。絕對在其中客體化自身的個體主體表現出特殊的視角,它們束縛于界定它們的有限的周圍世界。個體主體作為一個純粹的和人格的自我的自身保持系于其周圍世界的自身保持,而絕對則在其客觀的“樣式”中保持自身。絕對的客觀“樣式”指的是個體主體的構造著的生活。對此,胡塞爾說:“絕對普遍地自身保持在其持續不斷的構造中,在每一個個體人格中作為自身構造的不變項重復自身。”*Edmund Husserl, Ms. C 17 V, S. 22-23.轉引自James Richard Mens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 p.153.在他看來,絕對不只是在一個個體主體中保持自身,而是在每一個個體主體中保持自身。世界的視角性特征,亦即其視域的無限的可延伸性,使得世界超越我的本己的經驗和綜合的有限權能。因此,如果我的自我統一性在與這個超越的世界統一性的關聯中被給予,那么它必然在與其他主體的關聯中被給予。其他主體能補充我自己的有限權能,它們是我的經驗世界的共同的有效性載體。
每一個具體的主體性都被看作絕對的一個自身客體化,絕對的“自身表現”產生經驗的視域結構,產生世界和每一個具體的主體性。一方面,我的世界視域是我的經驗具有特定視角性的有序聯結,正是這種特定視角性的有序聯結給予我的具體的主體性以作為一個時空世界中的一個有限性的意義。另一方面,在我之中客體化自身的絕對不可能在我的有限性中窮盡自身,它必然超越我的有限性。據此,他人能以一種新的方式被看作蘊含在我之中。我設定他人是基于我對世界的有限通達,而經驗的秩序化是導致這種有限的通達的東西,因而導致我自身理解為有限的。這種秩序化是我設定他人的基礎。經驗的視角性的秩序化為個體的經驗者所要求;而這種秩序化也給予個體的經驗者一種意義,即他依賴于他人去展顯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此,我的有限的主體性和他人的有限的主體性二者都相關于視域性的、視角性地被秩序化的經驗結構。這意味著,作為蘊含在我之中的他人的觀念最終指向的不是作為客觀的人的我的有限性,而是指向我的無限性的基礎,即絕對。最終被表明的東西是不受限制的或無限的絕對,它不可能將自身具體化在一個個體的經驗者中而沒有超越它。這種超越意味著,作為絕對的具體化的他人也是有限的客體化。因此,自我與他人通過他們的超越性基礎而相互蘊含。
作為一切經驗視域的基礎,絕對是無限的,而個體主體作為一個確定的世界的經驗中心,只能體現一個可能的視域,因此,絕對在其有限性中的顯示是一種自我限制。就絕對本身而言,它不僅能構成個體的周圍世界的基礎,而且能構成每一個可能的世界視域結構的基礎。因此,最終的世界視域不是復多性主體的成就,而是絕對的成就。絕對存在于一切可能性的基礎中,它是構成一切可能性之基礎的可能性。從絕對的層次看來,他人對我的呈現是作為超越的世界視域性的相關項,因此,超越的世界視域性不是他人的構造成就,他人不應被看作世界的有效性載體,而應被看作與其視域性的世界一同“出生”。正如耿寧所正確指出的那樣:“世界構造或擁有世界的自我(‘先驗統覺的自我’)在先驗主體性自身中不存在基礎。”*Iso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um, Martinus Nijhoff, 1964, S. 297.因此,我將他人看作蘊含在我之中,是因為我們共同存在于一個被奠基的超越的視域性中,是因為我的最終基礎的超越的無限性。作為最終基礎的絕對總是超越我的有限性,因而總是蘊含著他人。
最終,我不再將我和他人看作我們的共同世界的基礎,而是將我們理解為視角性地展開的、視域性地被建構起來的經驗世界的意義相關項。如果世界和復多性主體是一同被奠基的,那么他人在我之中的蘊含性——在這個新的層次上——就變成了我們在我們的共同的基礎中的蘊含性了。在最終的構造層次上,主體間處于一種本質性的相合中。這種本質性的相合不應被理解為各構造系統之間的一種簡單的融合。在個體主體間的差異性中,一個奠基性的同一性的保持絕不意味著,每一個主體都重復同類主體的構造過程。主體的復多性不僅顯示了各構造系統的同一性,而且顯示了它們之間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源于個體主體的偶然性及其經驗視域的視角性。
我們至此的論述已從作為最終基礎的絕對“意識”流的個體化的角度粗略地勾勒出胡塞爾的先驗主體間性問題的“原自我”方案的進路。無疑,與《沉思》的方案相較,“原自我”方案揭示了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更深維度。從中所展顯的問題域的層次和關聯似乎表明,問題只能循此路徑推進,并且這可能也是胡塞爾在這一問題上的最終立場。但是,如果我們對前述的“原自我”方案做更切近的分析,就會發現這一思考進路上面臨的疑難和有待解決的問題。首先,就像芬克指出的那樣,胡塞爾在進路上使用了諸多“‘絕對形而上學’的詞匯”,例如“前自我”、“原自我”、“原存在”(Ursein)、“無自我的流動”、“絕對的流動”、“絕對”等等。正因為這樣,后繼的研究者之所以批評芬克的解釋和拒絕胡塞爾的“原自我”的方案,盡管芬克在不同的場合都曾反復強調,胡塞爾實際上遠離“絕對形而上學”,他的這類令人可疑的概念不是通過思辨的思想獲得的,而是其徹底實行先驗還原的必然結果。但問題是,胡塞爾關于“原自我”方案的論述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現象學的探討,盡管這種探討在發生現象學的框架下進行,訴諸于一種“發生性的解釋”,而不是“靜態的描述分析”?其次,胡塞爾關于本欲意向性的論述似乎將最終的構造基礎錨定在先驗的主體間性上,因此,一方面是先驗的主體間性維度上的本欲意向性,另一方面則是先于任何個體化——因而先于復多性的先驗主體——的原自我或前自我。二者之間如何協調呢?盡管芬克強調,胡塞爾不是像黑格爾那樣“以一種神秘地沉入黑夜的方式”“回思無定形的基礎”,而是“將其理解為沖破生命基礎的原始-裂縫,理解為裂口,理解為最原始的存在中的否定性”,但問題是應當如何規定這種“原始-裂縫”或“最原始的存在中的否定性”呢?第三,如果本欲意向性與原自我能夠協調一致,那么《沉思》中關于同感——它在那里的先驗的主體間性的構造中占有核心地位——的論述還繼續有效嗎?畢竟,在“原自我”方案涉及的那些晚年手稿中,同感問題仍是胡塞爾聚焦的核心問題。第四,“原自我”方案的核心無疑是“絕對的流動”的個體化問題。這種“絕對的流動”的個體化,胡塞爾有時又稱“原時間化”(Urzeitigung),在這個意義上,他晚年常援引活的當下的脫當下擁有(Ent-gegenw?rtigung)與原自我的自身異化(Selbstentfremdung)之間的類似性藉以說明個體化問題。然而,問題是,這種類比性的說明在何種意義上能夠充分闡明原自我的自身異化呢?換句話說,胡塞爾如何能在原始的時間性維度具體闡明原自我的個體化問題呢?最后,在原自我經受個體化而達到同質化的復多的個體主體的層次上,是否還有一個先驗的主體間性的構造問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樣一種先驗的主體間性構造與本欲意向性之間如何協調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原自我在個體化的過程中是如何完成先驗的主體間性的構造呢?
因此,誠如芬克所言,如果考慮胡塞爾晚年手稿的文本,則先驗的主體間性問題的各種疑難就會在一種十分不同的光亮中顯現出來,“然而,在此情況下只會增加各種實質性的困難”。*Alfred Schütz, Collected Papers III, Studies in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Martinus Nijhoff, 1970, p.86.
(責任編輯 任 之)
*本文系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2FZX026)、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2&ZD124)的階段性成果。
B516.52
A
1000-7660(2016)06-0069-11
**作者簡介:李云飛,哲學博士,(廣州 510006)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