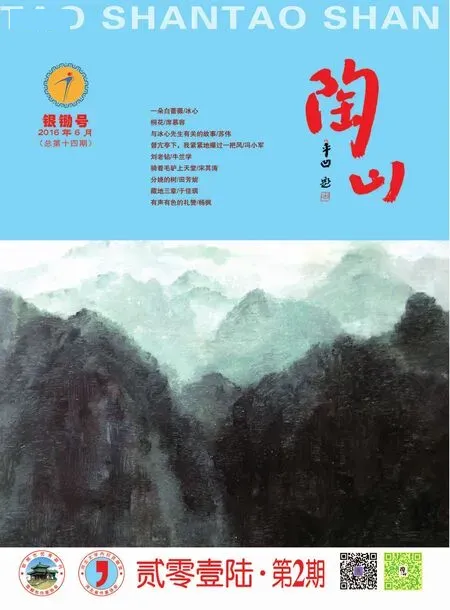草木鄉村
◎戴永瑞
草木鄉村
◎戴永瑞
院子里散發著草木的清香,月光傾瀉而下,一把一把齊頭的稻草,白天里陽光下顯出的硬朗幾乎消失,柔軟的黃色里面依稀能分辨出絲絲的青色。它們站在院子里,每把稻草的頭部被束住,底部呈弧形散落開來,也有點好像支持不住要傾倒的可笑樣子。滿滿當當,調皮、坦然、散淡,它們緊貼著大地的身體,傾聽著村莊的呼吸,它們的身心是松弛的,歲月靜好,一切安然。
關于剛收割好的稻草的記憶,讓我永遠覺得溫暖。陽光鉆進它的身體,又讓它的每一根纖維蓬松起來。我們常常在草垛跟前轉悠,尋找最理想的位置,扯著咬的很緊的稻草,然后埋進自己的身體,身體的四周全是稻草的清香。稻草也包裹著我們小小的身體,那個時候覺得自己是最安全和愜意的,就像回到了出生前母親的肚子里,新鮮好奇。稻草蠕動著,跳躍著,碰著自己的面孔,酥癢的感覺無法形容。或者,我們會躺倒在草垛頂上,看村莊里高高低低的房子,房頂上我們平時想看的任何東西,或者就隨意看著天上的白云,白云下面飛過的鳥兒,看村莊里升起的炊煙,嗅著草木被焚燒后的另一種味道,想象著它在空中升騰、跌宕,變幻出另一種奇妙的形態。
父親在月光下一下一下地磨著短鐮,小心地用手指試著鋒刃,秋天的風送來田野的稻香。可以想象,站立在田野里的稻子迫不及待地等待著被放倒的那一刻了。烈日下,母親在田頭看著父親,光著被汗水濕透的脊梁,一下下地割著稻子。當短鐮碰到稻稈的那一瞬間,父親聽到了稻草快活輕松的叫喊。“擦擦擦”,那一刻,只有父親才能感應到稻草的內心——被分離的快感。稻草隨即暈眩,伏于大地,身心釋然。清香在空中彌撒著,父親此刻血液順暢,進入生命從未有過的飽滿狀態。
母親和我們姐弟幾個,蹲著身子忙著捆稻草。夕陽下,父親用木杈挑著捆好的稻草,搬運到船上,整齊的稻草碼放在船上,田地里只剩下短茬的光溜溜的稻田。空曠,靜寂,像回到了時光的盡頭。接著是很繁重的勞動,脫粒,先前是用石碾子壓,牛拖著石碾子被吆喝著打圈。反復的碾壓才會顯出功效來。后來,有了脫粒機,夜晚拉上電燈,塵土飛揚的夜晚,卻分不清人的面孔,只聽到人的叫喊聲。稻草終于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亂頭的就堆起了草垛,齊頭的等曬干了再碼好。疲憊和欣喜交織著,父親終日忙得不見人影。偶爾見到他,雖然灰頭灰臉,但總是很有精神。
就這樣稻草完全交給了我們。晚上我們姐弟就用稻草搓繩,月亮被我們扣住一回又一回。用榔頭捶熟了的稻草很服帖,稻草和我們的手掌相親以后,徹底地融為一體了。大人們則用稻草編織草簾,編織草簾工序更單調,放草,擺動筋絡(用細塑料繩代替),收緊,累了就趴在稻草上打個盹。鄉村的生活就這樣簡單樸實,草繩和草簾賣了可以換回一些生活用品,運氣好,還可以賺一些費用。有時候,我們累得不行了,就躲在草窩里睡著了。睡夢中,會摸到稻草上的一顆稻粒,它與稻草滑爽的感覺有別,有點硌手,我會不由自主地放到口中仔細地咀嚼,草木的香氣全集中在它的上面,那些夢,會甜美幸福得要死。
冬天來了,母親會忘不了在我們的床上鋪上厚厚的稻草。那清香抬高了我們的好夢,溫暖,快樂,自足,鄉村的日子也隨著這些草木變得厚實起來。而牲口們在冬天里的食物,主要是靠著它們來維持。牛們直接吞食著選好的上等草料,它們的反復咀嚼讓所有的日子變得更有意義。豬的飼料需要將這些草木碾碎,然后才能進入它們的胃里。其實,草木懂得大地才是它們真正的歸宿,牲口們的糞便融進泥土,讓草木的前世今生有了銜接,燃燒后化為炊煙和虛無的,終究要和雨水混為一體,塵埃落定,最后尋找它們的今生緣分。
在鄉村里,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當成大地上的草木,活出精神,死得從容。我的鄉民們離開村莊,到另一個世界忙碌,追尋他的先輩們,必須要在自己的身下鋪上一層厚厚的稻草,只有這樣,他才覺得自己的靈魂安妥。或許,身邊的草木,就是他至死難舍難棄的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