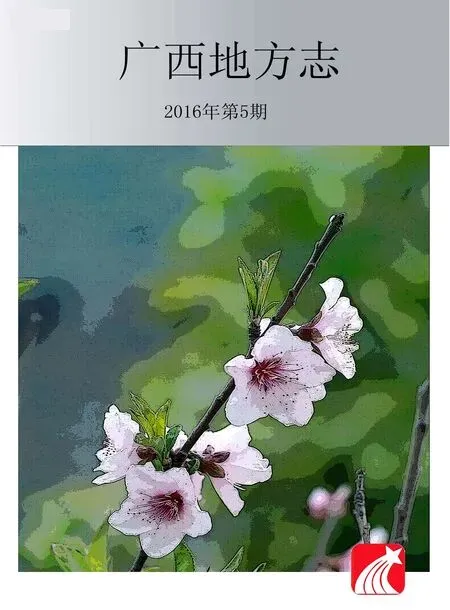關(guān)于當(dāng)代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的思考
沈松平
(寧波大學(xué)人文與傳媒學(xué)院,浙江寧波,315211)
關(guān)于當(dāng)代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的思考
沈松平
(寧波大學(xué)人文與傳媒學(xué)院,浙江寧波,315211)
鄉(xiāng)鎮(zhèn)志在今天仍有其編修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完全在于它具有省、市、縣志所不可替代的保存史料的功能,即記述鄉(xiāng)鎮(zhèn)的內(nèi)容比較微觀(guān)而具體,可彌補(bǔ)省、市、縣志記載的不足,因此在編修中應(yīng)遵循不照搬市、縣志體例,以微觀(guān)記述為主,突出地方特色等原則。而2014年底啟動(dòng)的《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既秉承了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的本意,同時(shí)在形式上有所創(chuàng)新,是拓展讀志用志、服務(wù)社會(huì)途徑,探索地方志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形式的一大創(chuàng)舉。
鄉(xiāng)鎮(zhèn)志;《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編修方法
鄉(xiāng)鎮(zhèn)志是以一鄉(xiāng)、一鎮(zhèn)為記述范圍或相當(dāng)于鄉(xiāng)、鎮(zhèn)一級(jí)的縣以下某區(qū)域的志書(shū),是方志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員。據(jù)大多數(shù)人的看法,鄉(xiāng)鎮(zhèn)志始于宋代,常棠所撰的浙江省海鹽縣《澉水志》應(yīng)是我國(guó)最早的鄉(xiāng)鎮(zhèn)志。宋代所修的鄉(xiāng)鎮(zhèn)志共有4部,即常棠的《澉水志》、梅堯臣的《青龍雜志》、沈平的《烏青記》和張即之的《桃源志》,元代所修鄉(xiāng)鎮(zhèn)志僅有豐灼的《三茅山志》(三茅山,此處代指鄉(xiāng)名,在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qū)),而這5部鄉(xiāng)鎮(zhèn)志中,除《澉水志》外,余皆亡佚。至明、清兩代,鄉(xiāng)鎮(zhèn)志漸多,尤以清代為盛,朱士嘉在《中國(guó)地方志綜錄》“序”中說(shuō):“至清則自省府廳州縣外,并鄉(xiāng)鎮(zhèn)亦多有志,開(kāi)歷代未有之記錄”[1]朱士嘉.中國(guó)地方志綜錄[M].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1935.。據(jù)統(tǒng)計(jì),明代編纂的鄉(xiāng)鎮(zhèn)志有53種,今存16種;清代纂修的鄉(xiāng)鎮(zhèn)志有318種,今存208種[2]黃葦,等.方志學(xué)[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3:736.。民國(guó)時(shí)期編修的鄉(xiāng)鎮(zhèn)志現(xiàn)存計(jì)54種[3]黃燕生.中國(guó)歷代方志概述[M]//來(lái)新夏.中國(guó)地方志綜錄(1949-1987).合肥:黃山書(shū)社,1988:436.。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鄉(xiāng)鎮(zhèn)成為我國(guó)行政區(qū)劃中的一級(jí)政區(qū),也是最基層的一級(jí)政權(quán)組織。雖然國(guó)家僅規(guī)定省(直轄市、自治區(qū))、市(地區(qū)、自治州、盟)、縣(市、自治縣、旗、區(qū))三級(jí)修志,但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修也很普遍,特別是在經(jīng)濟(jì)比較發(fā)達(dá)的沿海地區(qū),撰修了不少的鄉(xiāng)鎮(zhèn)志,據(jù)中國(guó)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辦公室的統(tǒng)計(jì),截至2013年12月,全國(guó)共編修鄉(xiāng)鎮(zhèn)村志、街道社區(qū)志4090部,[4]中國(guó)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辦公室.2013年度全國(guó)地方志系統(tǒng)工作進(jìn)展情況統(tǒng)計(jì)[J].中國(guó)方志通訊,2014(19):9.這樣的發(fā)展速度是清代和民國(guó)時(shí)期望塵莫及的。毋庸置疑,鄉(xiāng)鎮(zhèn)志的興修與地域經(jīng)濟(jì)的繁榮息息相關(guān)。明清時(shí)期,我國(guó)鄉(xiāng)鎮(zhèn)志數(shù)量大增,且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區(qū),這一現(xiàn)象與南宋以來(lái)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促進(jìn)村鎮(zhèn)勃興有關(guān)。清乾嘉時(shí)期的學(xué)者洪亮吉在論及黎里鎮(zhèn)修鎮(zhèn)志時(shí)說(shuō):“黎里為吳江縣一鎮(zhèn),今其土壤之富庶,民居之稠密,于西北可比大縣,于東南則中、下縣或有不及焉。民居戶(hù)籍既繁,則風(fēng)氣亦日開(kāi),文采亦日盛,人物軒冕亦遂擅于東南,推之而園亭、祠宇、藝文、金石皆可各立一門(mén),此而不及今條記之,則后此者將何所考焉?”[1][清]徐達(dá)源.黎里志[M]//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zhuān)輯: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111.同樣道理,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guó)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進(jìn)入高峰期,導(dǎo)源于80年代中期以來(lái)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異軍突起和90年代我國(guó)城市化的迅猛發(fā)展。但是,在如何編修鄉(xiāng)鎮(zhèn)志的問(wèn)題上,還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看法,本文擬對(duì)我國(guó)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作一歷史思考,進(jìn)而探討當(dāng)代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修方法,誠(chéng)望行家斧正賜教。
一、歷史上鄉(xiāng)鎮(zhèn)志的體例
舊鄉(xiāng)鎮(zhèn)志有不平衡性、區(qū)劃性不明顯、私纂性、資料性的特點(diǎn),所以編纂體例相對(duì)比較自由,不拘一格,并無(wú)定型體例,大致可以分為3類(lèi):一是套用州、縣志的體例,如清《黎里續(xù)志》提出:“里志與縣志、府志體例悉同,僅異詳略”[2][清]蔡丙圻.黎里續(xù)志[M]//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zhuān)輯: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315.。民國(guó)年間修的《黃埭志》也認(rèn)為:“以鄉(xiāng)為縣治分區(qū),體例當(dāng)從縣志”[3]朱福熙,等修.程錦熙纂.黃埭志[M]//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zhuān)輯: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555.。二是仿圖經(jīng)的體例,以記述地理方面內(nèi)容為主,如清咸豐年間黃醇的《甘棠小志》。三是主張鄉(xiāng)鎮(zhèn)志無(wú)定例,由編者自定,編纂體例不必同于府、縣志,如清嘉慶年間焦循編撰的《北里小志》,有敘六、記十、傳二十一、書(shū)事八、家述二,共47篇,別具一格,其中“家述”還記載了作者焦循的家譜。清《南翔鎮(zhèn)志》僅分疆里、營(yíng)建、小學(xué)、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雜志等類(lèi),其《凡例》聲稱(chēng):“賦役、戶(hù)口、保甲、鄉(xiāng)約,概不載,恐等于邑志也”[4][清]張承先.南翔鎮(zhèn)志[M].程攸熙訂正.//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zhuān)輯: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454,457.,又卷一稱(chēng):“鎮(zhèn),非州縣比也,不得稱(chēng)疆域”[5][清]張承先.南翔鎮(zhèn)志[M].程攸熙訂正.//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zhuān)輯: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454,457.。
新編鄉(xiāng)鎮(zhèn)志較舊鄉(xiāng)鎮(zhèn)志,其非區(qū)劃性、私纂性的特點(diǎn)已不復(fù)存在,與省、市、縣(區(qū))志一樣,具有區(qū)劃性和官修性。鄉(xiāng)鎮(zhèn)現(xiàn)在已成為我國(guó)最基層的一級(jí)行政政區(qū),其行政區(qū)劃十分明確,新編鄉(xiāng)鎮(zhèn)志的記述地域范圍也以本轄區(qū)為限,不再“越境而書(shū)”。有些內(nèi)容事涉他鄉(xiāng)他鎮(zhèn),也只是在建置沿革和橫向經(jīng)濟(jì)聯(lián)合方面提及。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修雖不在國(guó)家計(jì)劃之列,但我國(guó)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始編修鄉(xiāng)鎮(zhèn)新志以來(lái),都是由鄉(xiāng)、鎮(zhèn)政府出面主修,由各鄉(xiāng)鎮(zhèn)的黨政主要領(lǐng)導(dǎo)掛帥,成立修志領(lǐng)導(dǎo)小組,下設(shè)編志組負(fù)責(zé)編纂,也是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主持,屬于官修,靠私纂而成的鄉(xiāng)鎮(zhèn)志極少見(jiàn)到。故新編鄉(xiāng)鎮(zhèn)志較舊鄉(xiāng)鎮(zhèn)志在體例、篇目設(shè)計(jì)上減少了隨意性,總的傾向是接近市、縣志,幾乎完全套用了市、縣級(jí)志書(shū)的框架結(jié)構(gòu)、篇目設(shè)置,讀來(lái)有千人一面之嫌。如江蘇省蘇州市《勝浦鎮(zhèn)志》除概述、大事記外,分6編32章:鎮(zhèn)域(境域隸屬、境域四至、行政區(qū)劃、鎮(zhèn)村居民委員會(huì)、自然環(huán)境、鎮(zhèn)村建設(shè)、動(dòng)遷安置),經(jīng)濟(jì)(農(nóng)業(yè)、多種經(jīng)營(yíng)、水利、工業(yè)、商業(yè)、交通郵電、經(jīng)濟(jì)管理),政治(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勝浦地方組織、人民代表大會(huì)、政府機(jī)構(gòu)、經(jīng)濟(jì)組織、群眾團(tuán)體、民政勞動(dòng)、治安司法軍事),文化(群眾文化、教育、衛(wèi)生體育),居民(人口、人民生活、宗教信仰、方言熟語(yǔ)、民風(fēng)民俗),人物(人物傳略、人物名錄、先進(jìn)集體名錄)。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qū)《義橋鎮(zhèn)志》除概述、大事記外,志書(shū)主體分自然環(huán)境與鎮(zhèn)村建制、姓氏人口、土地、交通、商業(yè)、農(nóng)業(yè)(含水利)、工業(yè)、財(cái)稅金融、鎮(zhèn)村建設(shè)、黨派群團(tuán)、基層政權(quán)組織、軍事治安司法、教育科技衛(wèi)生、文化廣播電視名勝、社會(huì)生活(含民政、社會(huì)保障、風(fēng)俗、宗教)、人物共16篇,志末設(shè)叢錄(含方言)。究其原因,是因?yàn)榭h級(jí)志書(shū)修完后指導(dǎo)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時(shí)“駕輕就熟”的緣故,也有一部分是因編修縣級(jí)志書(shū)需鄉(xiāng)鎮(zhèn)提供資料,造成同步修志的緣故。但如此一來(lái)帶來(lái)了一個(gè)很大的弊病,就是新編鄉(xiāng)鎮(zhèn)志的篇目往往失之于繁,特色不能彰顯,甚至因?yàn)槭艿剑ㄊ小⒖h志)篇目結(jié)構(gòu)的限制,有些微觀(guān)資料不能入志,詳市、縣志之所略,從而失去了編修鄉(xiāng)鎮(zhèn)志的本意。
二、當(dāng)代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修方法
鄉(xiāng)鎮(zhèn)志在國(guó)家并不提倡的情況下仍有其編修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并在方志大家族中擁有一席之地,完全在于它具有省、市、縣志所不可替代的保存重要史料的功能。就鄉(xiāng)鎮(zhèn)而言,雖然其情況在所屬縣志、市志乃至省志中都會(huì)提到,但那只是一筆帶過(guò),因?yàn)槭 ⑹小⒖h志記述的層次比較高,對(duì)于鄉(xiāng)鎮(zhèn)一級(jí)的記述只能在志書(shū)的政區(qū)編或鄉(xiāng)鎮(zhèn)編略作概括,語(yǔ)焉不詳,而鄉(xiāng)鎮(zhèn)志記述的地域范圍相對(duì)較小,記述鄉(xiāng)鎮(zhèn)的內(nèi)容往往比較微觀(guān)而具體,可彌補(bǔ)省、市、縣志記載的不足,這是鄉(xiāng)鎮(zhèn)志存在的本意,它決定了與省、市、縣志的編修決不是簡(jiǎn)單地重復(fù)。誠(chéng)如常棠在《澉水志》序中所說(shuō):“郡有《嘉禾志》,邑有《武原志》,其載澉水之事則甚略焉,使不討論聞見(jiàn),綴輯成編,則何以示一鎮(zhèn)之指掌?”[1][宋]常棠.澉水志·羅叔韶序[M]//海鹽縣史志辦公室.海鹽縣檔案局.澉水志四種.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清代溫汝能在《龍山鄉(xiāng)志》序中也說(shuō):“郡之視邑,猶邑之視鄉(xiāng)。郡不能專(zhuān)而詳,必有待于邑,邑亦不能專(zhuān)而詳,不又有待于鄉(xiāng)耶!”[2][清]溫汝能.龍山鄉(xiāng)志[M]//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鄉(xiāng)鎮(zhèn)志專(zhuān)輯:3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13-14.因此,在編修鄉(xiāng)鎮(zhèn)志中,其保存史料是第一位的,此外,也要考慮到鄉(xiāng)鎮(zhèn)區(qū)別于市、縣的特點(diǎn),如鄉(xiāng)鎮(zhèn)的管轄范圍較小,事項(xiàng)必不如市、縣那樣齊全等等。綜合以上因素,我們認(rèn)為,編修鄉(xiāng)鎮(zhèn)志,應(yīng)遵循不照搬市、縣志體例,以微觀(guān)記述為主,突出地方特色等原則。
(一)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修不能照搬市、縣志體例
鄉(xiāng)鎮(zhèn)的管轄范圍較小,事項(xiàng)未必齊全,因而在體例上不應(yīng)落入市、縣志框架的窠臼,面面俱到,否則會(huì)出現(xiàn)類(lèi)目空洞無(wú)物,照搬市、縣志內(nèi)容的現(xiàn)象。應(yīng)該根據(jù)鄉(xiāng)鎮(zhèn)的實(shí)際情況來(lái)確定體例和安排篇目,鄉(xiāng)鎮(zhèn)的內(nèi)容多的可獨(dú)立成篇,沒(méi)有事項(xiàng)或內(nèi)容少的,則或并或略,可以不單獨(dú)設(shè)章立節(jié),以防止把大量共性資料濫竽充數(shù),造成與市、縣志內(nèi)容大量重復(fù)。比如,鄉(xiāng)鎮(zhèn)范圍大者不過(guò)近百平方公里,小者僅數(shù)十平方公里,方位(經(jīng)緯度)、地質(zhì)、地貌、氣候、水文、動(dòng)植物、自然災(zāi)害、方言等門(mén)類(lèi),其內(nèi)容與縣志記述無(wú)異,并沒(méi)有本鄉(xiāng)鎮(zhèn)的資料,如果生搬硬套縣志篇目,那就只能取縣志的資料來(lái)鋪陳,實(shí)不足取。事實(shí)上,這樣的門(mén)類(lèi)完全可以省略。又比如,縣志中一般都設(shè)有“民主黨派”一章,而有的鄉(xiāng)鎮(zhèn)只有一二個(gè)民主黨派黨員,這就不必也設(shè)專(zhuān)章記述了。還有,縣志中的政協(xié)、文聯(lián)、僑聯(lián)等組織,以及檢察、審判等機(jī)構(gòu),鄉(xiāng)鎮(zhèn)志中同樣沒(méi)有必要設(shè)專(zhuān)章記述。有些篇目因內(nèi)容單一,資料又少,可以相對(duì)集中。如“交通”“郵電”等可以同供電、供水、排水、道路、橋梁、住宅、綠化、環(huán)衛(wèi)等放在“鎮(zhèn)區(qū)建設(shè)”中集中記述。再有,志書(shū)中許多具有共性的內(nèi)容,諸如政治體制,組織機(jī)構(gòu),貫徹黨和政府的各項(xiàng)方針、政策等內(nèi)容,省志、市志、縣志都記了,鄉(xiāng)鎮(zhèn)志就沒(méi)有必要再記,因此,鄉(xiāng)鎮(zhèn)志中有關(guān)黨、政、群團(tuán)、軍事等具有共性的篇目應(yīng)該予以壓縮和合并。重慶永川市《陳食鎮(zhèn)志》就沒(méi)有照搬縣志篇目,而是從鎮(zhèn)情出發(fā)謀篇布局。全志除設(shè)概述、大事記與人物、雜錄外,共設(shè)地理、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4類(lèi)(編)25章。其中,經(jīng)濟(jì)類(lèi)所設(shè)“農(nóng)業(yè)”章為“大農(nóng)業(yè)”,包括種植、養(yǎng)殖、林、牧、漁及水利、農(nóng)機(jī)等內(nèi)容;不單設(shè)工業(yè)、商業(yè)章,而設(shè)“工商企業(yè)”章,同時(shí)還設(shè)置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供銷(xiāo)合作社、金融等章。可見(jiàn),編纂者是從當(dāng)?shù)剞r(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特點(diǎn)來(lái)考慮篇目設(shè)置的。
(二)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寫(xiě)必須以微觀(guān)資料的記述為主,詳市、縣志之所略
鄉(xiāng)鎮(zhèn)志立足于方志大家族的根本,是能否提供市、縣志記載以外的資料,資料是否豐富翔實(shí),這是鄉(xiāng)鎮(zhèn)志成敗的關(guān)鍵所在,因此兩者在記述范圍和記述重點(diǎn)上是有所分工或有所側(cè)重的。市、縣志是對(duì)全市、全縣總體情況的記載和概述,由于體例和篇幅的限制,只能收錄比較重要的內(nèi)容和進(jìn)行粗線(xiàn)條式的概述,對(duì)其他一般性的內(nèi)容則無(wú)法詳細(xì)羅列敘述。而鄉(xiāng)鎮(zhèn)志恰好可以在一般性?xún)?nèi)容上詳列和詳述,尤其是重點(diǎn)記載市、縣志中沒(méi)有記載或記得語(yǔ)焉不詳?shù)馁Y料,起到深化、補(bǔ)充市、縣志的作用,做到市、縣志缺載我來(lái)補(bǔ),市、縣志記略我記詳。以宏觀(guān)、中觀(guān)、微觀(guān)論,省志宜于宏觀(guān)記述,市、縣志宜于中觀(guān)記述,鄉(xiāng)鎮(zhèn)志則宜于微觀(guān)記述。章學(xué)誠(chéng)曾說(shuō),“地近則易核,時(shí)近則跡真”[1][清]章學(xué)誠(chéng).文史通義校注[M].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0:843.。鄉(xiāng)鎮(zhèn)志在微觀(guān)記述上有其自身獨(dú)特的優(yōu)點(diǎn),如鄉(xiāng)鎮(zhèn)管轄的地域范圍較小、人口不多,調(diào)查、采訪(fǎng)比較方便,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纂者大多是本地人,對(duì)家鄉(xiāng)情況比較熟悉,所記史實(shí)也多為親身經(jīng)歷,鄉(xiāng)鎮(zhèn)中人與人之間有著非族則親的血緣關(guān)系,有比城市緊密得多的地緣關(guān)系和業(yè)緣關(guān)系,相互知根知底,所以從理論上來(lái)說(shuō),鄉(xiāng)鎮(zhèn)志的記事可以做到具體翔實(shí),真切實(shí)在,少有隱諱和曲筆,即使文獻(xiàn)資料中發(fā)現(xiàn)錯(cuò)誤也容易糾正。因此,編寫(xiě)鄉(xiāng)鎮(zhèn)志,在資料選擇上要以細(xì)取勝,以深見(jiàn)長(zhǎng),要抓“芝麻”“細(xì)節(jié)”,不論是記事,還是記物、記人,都應(yīng)具體、翔實(shí)、典型。鄉(xiāng)鎮(zhèn)志也唯有細(xì)微、翔實(shí)、典型,方能補(bǔ)市、縣志的不足,才更具存史研究的價(jià)值,這是鄉(xiāng)鎮(zhèn)志編纂者應(yīng)該遵循的基本指導(dǎo)原則之一,也是鄉(xiāng)鎮(zhèn)志定位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之一。如清代上海《法華鄉(xiāng)志》記載徐光啟的事跡十分翔實(shí),比同時(shí)代的《上海縣志》《松江府志》詳細(xì)得多。重慶永川市《陳食鎮(zhèn)志》“人口”章記載明清外來(lái)人口情況,以遷入時(shí)間、獲地方式、插占為業(yè)者占地情況、出發(fā)地區(qū)、遷徙原因等目,分項(xiàng)按家族姓氏記述,記述相當(dāng)具體、明確,這是其他志書(shū)難以見(jiàn)到的。《十里長(zhǎng)街——坎墩》則在《鄉(xiāng)風(fēng)民情》篇記錄了同治九年(1870)詩(shī)人胡杰人代本地人沈其常為無(wú)力成婚而求助所撰的《沈其常助婚知啟》[2]方柏令.十里長(zhǎng)街——坎墩[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191.,使后人知道百余年前坎墩鎮(zhèn)曾有助婚風(fēng)習(xí),成為我們研究近代社會(huì)史的稀有資料。就內(nèi)容而言,鄉(xiāng)鎮(zhèn)志記載的重點(diǎn)不應(yīng)是全國(guó)帶共性的事情,而是貼近普通老百姓的事情,是檔案資料中難以找到的資料。比如市場(chǎng)上的集市貿(mào)易,農(nóng)村中紡紗織布的興衰,小鎮(zhèn)上的茶館店、手工藝品的特色,尋常百姓的收支來(lái)源和去向,鄉(xiāng)村的風(fēng)土人情,或者發(fā)生在農(nóng)村中的新鮮事物等。又如改革開(kāi)放以后農(nóng)民工進(jìn)城,農(nóng)村是勞務(wù)輸出的重要渠道,在編寫(xiě)鄉(xiāng)鎮(zhèn)志時(shí)對(duì)本鄉(xiāng)鎮(zhèn)外出打工的人數(shù)、路線(xiàn)、分布、職業(yè)、經(jīng)濟(jì)收益及對(duì)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發(fā)展的影響,均應(yīng)立目記述,從而反映本鄉(xiāng)鎮(zhèn)與外部世界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對(duì)外來(lái)勞動(dòng)力大批進(jìn)入的鄉(xiāng)鎮(zhèn),在編志中也要設(shè)目集中記述以打工仔為主體的外來(lái)人口,要寫(xiě)明外來(lái)人口的數(shù)量變化、籍貫分布、職業(yè)類(lèi)型、勞資糾紛、生活狀況、治安管理等。再如鄉(xiāng)鎮(zhèn)的老百姓祖祖輩輩生息繁衍在這塊土地上,他們創(chuàng)造了鄉(xiāng)鎮(zhèn)前進(jìn)的歷史,面對(duì)今日的繁華,每個(gè)村民都希望了解他們的祖輩,從何地而來(lái),怎樣在此扎根定居繁衍,已經(jīng)移居在外的人也有個(gè)尋根問(wèn)祖的問(wèn)題,所以鄉(xiāng)鎮(zhèn)志中對(duì)姓氏、宗族、家譜這部分內(nèi)容的記載就只能細(xì)不能簡(jiǎn),借此凝聚力量,聯(lián)系鄉(xiāng)情,共同為家鄉(xiāng)建設(shè)出力。此外,鄉(xiāng)鎮(zhèn)志還應(yīng)該在記載人物和文獻(xiàn)方面發(fā)揮其優(yōu)勢(shì)。鄉(xiāng)鎮(zhèn)志地域范圍相對(duì)較窄,對(duì)邑人之精華者可以做到如數(shù)家珍,如本籍在外地工作的高級(jí)職銜人物、軍政界、文化界人物,大中專(zhuān)畢業(yè)生就讀及流向情況等。若是市、縣志要收錄這些材料就相當(dāng)困難,甚至無(wú)法操作實(shí)施,而鄉(xiāng)鎮(zhèn)的父老鄉(xiāng)親對(duì)自己子弟在外地的情況是心中有數(shù)的,能如數(shù)家珍地一一載入志書(shū),這也是鄉(xiāng)情難阻隔的體現(xiàn)。鄉(xiāng)鎮(zhèn)范圍內(nèi)的文獻(xiàn)(包括藝文和非文藝性的檔案文獻(xiàn))較市、縣畢竟也有限,搜羅殆盡,并一一列出,理論上是做得到的。
(三)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寫(xiě)要突出地方特色
中國(guó)有句俗話(huà):“入鄉(xiāng)問(wèn)俗,十里改規(guī)矩”,說(shuō)明地各有異,民俗有別。鄉(xiāng)鎮(zhèn)志要有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就必須突出鄉(xiāng)鎮(zhèn)的特點(diǎn)和優(yōu)勢(shì),若編纂者把握不住這個(gè)重點(diǎn),籠統(tǒng)的、泛泛的,不能從比較中找出本鄉(xiāng)本土的不同點(diǎn),那么編出來(lái)的志書(shū)必然是平庸之作。由于各個(gè)鄉(xiāng)鎮(zhèn)的環(huán)境不同,其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情況各不相同,形成的文化內(nèi)涵、民情風(fēng)俗也不相同,各有各的特點(diǎn)和優(yōu)勢(shì),有的鎮(zhèn)是縣(市)城治所在地,有的鎮(zhèn)原是縣城所在地現(xiàn)在不是,有的為鄉(xiāng)村集市鎮(zhèn),有的為水陸要會(huì)、交通樞紐等等。因此編寫(xiě)各鄉(xiāng)鎮(zhèn)志,在內(nèi)容記述上不能千篇一律,應(yīng)將其特點(diǎn)和優(yōu)勢(shì)作為重點(diǎn)來(lái)寫(xiě),寫(xiě)深寫(xiě)透,以深度見(jiàn)長(zhǎng),而且這個(gè)特點(diǎn)首先要在篇目中體現(xiàn)出來(lái),讓人一看篇目就知道是你這個(gè)鄉(xiāng)鎮(zhèn),而不是別的鄉(xiāng)鎮(zhèn)。如江蘇省原無(wú)錫縣的前洲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十分突出,而華莊鎮(zhèn)則是全國(guó)小城鎮(zhèn)建設(shè)的典范,如果編寫(xiě)鄉(xiāng)鎮(zhèn)志,那么編纂者應(yīng)該在篇目設(shè)置上就把這一特色體現(xiàn)出來(lái)。突出地方特色,可以采用升格設(shè)卷、設(shè)編、設(shè)章集中記述的辦法,這是志書(shū)常用的一種做法,此外,還可以把地方特色滲透在各有關(guān)章節(jié)中反映,也不失為一種反映地方特色的好辦法。如福建省莆田市忠門(mén)鎮(zhèn)的主要產(chǎn)業(yè)是蒸籠業(yè),它不同于莆田市以鞋業(yè)為支柱產(chǎn)業(yè),因此《忠門(mén)鎮(zhèn)志》特別設(shè)置了“蒸籠”一章,與農(nóng)業(yè)、水利電業(yè)、圍墾、水產(chǎ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商業(yè)各章并列為第一層次篇目,詳細(xì)地描述了蒸籠工藝、蒸籠營(yíng)銷(xiāo)直到多元化經(jīng)營(yíng)和管理的全過(guò)程,有力地向人們陳述著忠門(mén)鎮(zhèn)這個(gè)人口眾多、土地貧瘠、經(jīng)濟(jì)長(zhǎng)期滯后的沿海鄉(xiāng)鎮(zhèn)是如何抓住機(jī)遇,依靠這個(gè)傳統(tǒng)工藝而沖進(jìn)全國(guó)市場(chǎng),發(fā)展本鎮(zhèn)生產(chǎn)力的。又如浙江省海鹽縣《澉浦鎮(zhèn)志》除概述、大事記外,主體部分共設(shè)11卷,計(jì)603頁(yè),其中旨在反映地方特色的卷、章就達(dá)到了332頁(yè)。因我國(guó)唯一集山、海、湖于一體的風(fēng)景區(qū)——南北湖坐落在澉浦鎮(zhèn),故該志特設(shè)“南北湖風(fēng)景區(qū)”1卷,濃墨重彩地記述其獨(dú)特的自然風(fēng)貌;又因澉浦鎮(zhèn)靠海,古代為著名的“海防要津”“海塘重鎮(zhèn)”“貿(mào)易良港”和“產(chǎn)鹽重地”,雖“貿(mào)易良港”因明初禁海及日漸淤塞而成為歷史的記憶,但海塘和海鹽仍是澉浦最為顯著的地域文化特征,故在卷二“農(nóng)業(yè)、水利”中繼“種植業(yè)”“林果業(yè)”“畜牧、水產(chǎn)”“水利”章之后設(shè)置了“海塘”“鹽業(yè)”兩章,彰顯了澉浦的地方特色。
三、《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篇目設(shè)置的思考
2014年底開(kāi)始,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具體由中國(guó)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辦公室、方志出版社負(fù)責(zé)實(shí)施)啟動(dòng)了中國(guó)名鎮(zhèn)志文化工程,其核心內(nèi)容為編纂《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目標(biāo)是通過(guò)創(chuàng)新組織編纂模式和體例內(nèi)容,出版一批質(zhì)量高、影響大、社會(huì)效益好、且能(相對(duì))暢銷(xiāo)的名鎮(zhèn)志,為讀志用志、服務(wù)社會(huì)創(chuàng)出一條新路。入選的名鎮(zhèn)(含鄉(xiāng)、街道)分為歷史文化名鎮(zhèn)、經(jīng)濟(jì)名鎮(zhèn)、其他特色名鎮(zhèn)三類(lèi)。其中歷史文化名鎮(zhèn)主要以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國(guó)家文物局評(píng)定的中國(guó)歷史文化名鎮(zhèn)為入選對(duì)象,對(duì)于歷史上曾經(jīng)作為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交通中心或者軍事要地,或者發(fā)生過(guò)重要?dú)v史事件,或者其歷史人物、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歷史上的重大工程對(duì)本地區(qū)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guò)重要影響,或者能夠集中反映本地區(qū)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或者作為某種文化、習(xí)俗發(fā)源地或傳承地的鎮(zhèn),也可酌情收錄;經(jīng)濟(jì)名鎮(zhèn)以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農(nóng)村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調(diào)查總隊(duì)公布的全國(guó)綜合實(shí)力“千強(qiáng)鎮(zhèn)”中有產(chǎn)業(yè)特色、其產(chǎn)業(yè)在全國(guó)占有重要地位的名鎮(zhèn)為主要入選對(duì)象;其他特色名鎮(zhèn)以獲得國(guó)家級(jí)榮譽(yù)稱(chēng)號(hào)的具有某方面特色的鎮(zhèn)為入選對(duì)象,如全國(guó)文明鎮(zhèn)、全國(guó)特色景觀(guān)旅游名鎮(zhèn)、全國(guó)農(nóng)業(yè)旅游示范點(diǎn)、全國(guó)小城鎮(zhèn)建設(shè)示范鎮(zhèn)、全國(guó)綠化百佳鎮(zhèn)等,或由相關(guān)部門(mén)或行業(yè)協(xié)會(huì)認(rèn)定,獲得“××之都”“××之鎮(zhèn)”等稱(chēng)號(hào)的特色鎮(zhèn)。
目前,這套《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已出版了11部,分別是《周莊鎮(zhèn)志》《第一關(guān)鎮(zhèn)志》《錢(qián)清鎮(zhèn)志》《冶源鎮(zhèn)志》《甪直鎮(zhèn)志》《同里鎮(zhèn)志》《三陽(yáng)鎮(zhèn)志》《楓涇鎮(zhèn)志》《李莊鎮(zhèn)志》《天穆鎮(zhèn)志》《虎門(mén)鎮(zhèn)志》,從實(shí)踐看,符合鄉(xiāng)鎮(zhèn)志編寫(xiě)的基本要求,既守住了志書(shū)的底線(xiàn),又在篇目設(shè)置上不像市、縣志那樣面面俱到,以記載鄉(xiāng)鎮(zhèn)范圍內(nèi)的微觀(guān)資料為主,詳市、縣志之所略,補(bǔ)市、縣志之不足,還注重突出地方特色,突出了名鎮(zhèn)志之名、之特。
(一)《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嚴(yán)守了志書(shū)的底線(xiàn),是符合志體的
什么是志書(shū)的底線(xiàn)呢?筆者認(rèn)為主要表現(xiàn)為敘而不論,這個(gè)一定要遵守,另外就是要有一定的時(shí)空觀(guān)念,凡例中應(yīng)對(duì)時(shí)空有所說(shuō)明,不能越境而書(shū),橫排豎寫(xiě)也要遵守,還有就是一般綜合性志書(shū)強(qiáng)調(diào)的內(nèi)容全面、系統(tǒng),“橫不缺要項(xiàng)”。《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嚴(yán)守了志書(shū)敘而不論、越境不書(shū)的原則,但由于該書(shū)發(fā)起的初衷是要在形式上創(chuàng)新,突出名鎮(zhèn)志之名、之特,不求面面俱到且要往暢銷(xiāo)書(shū)這個(gè)方向發(fā)展,為讀志用志、服務(wù)社會(huì)創(chuàng)出一條新路,因此與傳統(tǒng)鄉(xiāng)鎮(zhèn)志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門(mén)類(lèi)上是有所缺失的,為避免被人詬病為不像志書(shū),需要在篇目設(shè)計(jì)上加以平衡,即以篇目框架結(jié)構(gòu)上形似的面面俱到,來(lái)掩蓋志書(shū)內(nèi)容上的缺項(xiàng),這樣至少可以表明就志書(shū)整體而言,并不違背綜合性志書(shū)全面、系統(tǒng)、“橫不缺要項(xiàng),縱不斷主線(xiàn)”的慣例。《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采取的辦法是設(shè)置“基本鎮(zhèn)情”類(lèi)目,下設(shè)區(qū)位交通、建置沿革、自然環(huán)境、人口、鎮(zhèn)區(qū)建設(shè)、政事民生等分目,尤其是“政事民生”分目,下面不再分類(lèi),直接以?xún)?nèi)容取條目名,一事一條,既保存了有價(jià)值的微觀(guān)資料(這些微觀(guān)資料本身非常有價(jià)值,同類(lèi)事鄉(xiāng)鎮(zhèn)或與縣城處理方式不同,記載下來(lái)很有必要,這也是鄉(xiāng)鎮(zhèn)志的意義所在),同時(shí)也避免了給人門(mén)類(lèi)不齊全的觀(guān)感,因?yàn)閺睦碚撋现v,《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沒(méi)有列的黨政群團(tuán)、公安司法、軍事、教育、科技、衛(wèi)生、體育、民政、勞動(dòng)保障、人民生活、精神文明建設(shè)等門(mén)類(lèi)都可以囊括在“政事民生”分目中加以記述,只不過(guò)從鄉(xiāng)鎮(zhèn)志所記內(nèi)容應(yīng)是市、縣志記載內(nèi)容以外的微觀(guān)資料的角度出發(fā),有則記,無(wú)則不記罷了。筆者以為,除此之外,還可以采取另一種辦法來(lái)平衡篇目設(shè)計(jì),做到內(nèi)容上“橫不缺要項(xiàng)”,即將“基本鎮(zhèn)情”改為有關(guān)地理內(nèi)容的類(lèi)目,如《第一關(guān)鎮(zhèn)志》的“天工開(kāi)岳”,另設(shè)置一“雜述”類(lèi)目。“雜述”顧名思義就是其他門(mén)類(lèi)中無(wú)法放入的內(nèi)容,皆可歸于“雜述”,決不等同于舊志的只記遺聞逸事,這里可延伸為用于記載未設(shè)一級(jí)類(lèi)目的黨政群團(tuán)、公安司法、軍事、教育、科技、衛(wèi)生、體育、民政、勞動(dòng)保障、人民生活、精神文明建設(shè)等方面為市、縣志所省略的,與市、縣志所記同類(lèi)內(nèi)容有不同表現(xiàn)形式的,有存史價(jià)值的微觀(guān)資料。“雜述”類(lèi)目下也不必再劃分分目,直接以事列條目,一事一條,同樣可以達(dá)到以上的效果。如果顧慮到黨政、人大、政協(xié)的內(nèi)容放入“雜述”恐引起非議,也可考慮將黨政、人大、政協(xié)的內(nèi)容納入志首的“概述”,點(diǎn)到為止。
(二)《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很好地把握了鄉(xiāng)鎮(zhèn)志編寫(xiě)的價(jià)值重心
我們知道,鄉(xiāng)鎮(zhèn)志最大的價(jià)值是補(bǔ)充市、縣志所沒(méi)有的微觀(guān)資料,尤其表現(xiàn)在人物、文獻(xiàn)、風(fēng)土風(fēng)情上,不要求面面俱到,更不應(yīng)照搬市、縣志體例。按照這個(gè)思路,《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在文獻(xiàn)、人物、風(fēng)土風(fēng)情上用力相對(duì)頗深,基本起到了補(bǔ)微觀(guān)資料缺失的作用。人物方面,分為歷史名人(或“已故名人”)、健在人物(或“杰出人物簡(jiǎn)介”“健在名人”)、名人與名鎮(zhèn)三類(lèi),本籍(其中又分已故、健在)、客籍分得清清楚楚。歷史名人為已故名人,記載已過(guò)世的本鎮(zhèn)人或長(zhǎng)期扎根在本鎮(zhèn)的外鄉(xiāng)人;健在人物相當(dāng)于一般市、縣志的“人物簡(jiǎn)介”;名人與名鎮(zhèn)包括到此一游或短期居住的非本鎮(zhèn)名人,也包括這樣一些人,即非本鎮(zhèn)人,但在本鎮(zhèn)居住過(guò)幾年,后來(lái)從小鎮(zhèn)走向了全國(guó)其他地方,成為了名人,其后來(lái)的成名卻與小鎮(zhèn)無(wú)關(guān),這類(lèi)人也是可以記入“名人與名鎮(zhèn)”的,類(lèi)似于舊志的“流寓”篇或新志的“事略”篇。與一個(gè)鎮(zhèn)有關(guān)的名人畢竟不多,依靠當(dāng)?shù)乩先耍€是可以做到一一挖掘而不遺漏的。藝文方面,包括歌詠本地的詩(shī)文、書(shū)寫(xiě)本地風(fēng)物的楹聯(lián)、金石碑記、歌謠、文獻(xiàn)書(shū)目,其中文獻(xiàn)書(shū)目以寫(xiě)全、寫(xiě)細(xì)為要,因?yàn)檫@是今后讀者、包括國(guó)外友人對(duì)這個(gè)古鎮(zhèn)感興趣,并進(jìn)一步研究這個(gè)古鎮(zhèn)的線(xiàn)索,尤其是當(dāng)?shù)厝说囊恍┮话悴粸槿怂泥l(xiāng)邦文獻(xiàn),在修志中新被挖掘出來(lái)的,如果不加以一一盡數(shù)記載,很可能將沒(méi)有其他文獻(xiàn)對(duì)此加以記載,而為人們所逐漸遺忘。鄉(xiāng)鎮(zhèn)地域范圍比較小,域內(nèi)文獻(xiàn)畢竟有限,除了個(gè)別文獻(xiàn)鼎盛的名鎮(zhèn)如蘇州昆山的周莊鎮(zhèn)外,從理論上講完全可以做得到。至于非文藝性的原始檔案文獻(xiàn),也是非常具有存世價(jià)值的,《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將其納入附錄,符合志體,是一種很好的思路。但也可以有其他的做法,如可以將非文藝性的原始檔案文獻(xiàn)直接納入正文相關(guān)條目之后(可以字體、字號(hào)的不同顯示其區(qū)別),與正文互為引證,舊志中也有這樣做的;或者與“藝文”內(nèi)容歸并到一起,合并為“文獻(xiàn)輯存”類(lèi)目。
(三)《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注重寫(xiě)名鎮(zhèn)的“名”與“特”,突出了地方特色
比如說(shuō)計(jì)劃出的600部名鎮(zhèn)志中,江南古鎮(zhèn)所占數(shù)量不少,從大的方面說(shuō),江南古鎮(zhèn)都是小橋流水的水鄉(xiāng)古鎮(zhèn),如果不注意突出個(gè)性,在篇目上就會(huì)雷同,有千人一面之嫌。《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在編寫(xiě)中注意突出了古鎮(zhèn)個(gè)性,不僅在條目編寫(xiě)上側(cè)重于“名”和“特”,內(nèi)容有特色或有重要性則列條目寫(xiě),無(wú)特色或不重要?jiǎng)t省減,也反映在篇目設(shè)置上,類(lèi)目上設(shè)置了自選篇目,在最基本的層次條目上也尋求采用具體的事或物作為條目標(biāo)題直接表現(xiàn)出來(lái),相較傳統(tǒng)志書(shū)顯得靈活、活潑,標(biāo)題也更能吸引眼球。志書(shū)封面上的圖也沒(méi)有整齊劃一地選擇古鎮(zhèn)上最美的一幅風(fēng)景,而是取古鎮(zhèn)上最具個(gè)性的東西,如紹興市柯橋區(qū)錢(qián)清鎮(zhèn)是以經(jīng)濟(jì)名鎮(zhèn)入選《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的,有中國(guó)最大的輕紡原料市場(chǎng),被中國(guó)紡織工業(yè)協(xié)會(huì)授予“中國(guó)紡織原料市場(chǎng)名鎮(zhèn)”稱(chēng)號(hào),所以《錢(qián)清鎮(zhèn)志》封面就采用了中國(guó)最大的輕紡原料市場(chǎng)作為背景,而不是該地其他的一些自然景色如古棧道等。當(dāng)然如果有可能的話(huà),最好還是在志書(shū)的醒目位置標(biāo)注該名鎮(zhèn)是以何種類(lèi)型入選《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的。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無(wú)論是傳統(tǒng)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寫(xiě),還是《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的問(wèn)世,在今天中國(guó)仍有其現(xiàn)實(shí)的意義。方志有存史、資治、教化、興利、研究的功能,鄉(xiāng)鎮(zhèn)志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與省、市、縣志相比,在發(fā)揮志書(shū)的上述功能上有更深層次的內(nèi)涵。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變遷始終是中國(guó)歷史變遷的主體內(nèi)容,這不僅因?yàn)樵趨^(qū)位結(jié)構(gòu)中鄉(xiāng)村占據(jù)絕對(duì)的多數(shù),而且因?yàn)猷l(xiāng)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傳統(tǒng)在更深的層次上代表了中國(guó)歷史的傳統(tǒng)。即使對(duì)于整個(gè)近代史而言,近代化和城市化進(jìn)程,本質(zhì)上也是鄉(xiāng)村社會(huì)變遷的過(guò)程。20世紀(jì)以來(lái)中國(guó)歷史變革的走向、規(guī)律及其獨(dú)特的特征,如果不從鄉(xiāng)村社會(huì)研究入手,就很難真正獲得符合中國(guó)實(shí)際的具有認(rèn)知價(jià)值的認(rèn)識(shí)。鄉(xiāng)鎮(zhèn)志在反映農(nóng)村社會(huì)上有著其他文獻(xiàn)典籍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好的鄉(xiāng)鎮(zhèn)志,不僅僅是一個(gè)鄉(xiāng)鎮(zhèn)歷史與現(xiàn)狀的綜合反映,而且具有超出其本身價(jià)值之外的一般性意義,即實(shí)際上等于對(duì)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問(wèn)題作了一次深刻的調(diào)查研究和個(gè)案分析,可以為人們了解農(nóng)村社會(huì)多提供一份素材。它所記錄的微觀(guān)資料,不少是十分珍貴和稀有的資料,極具人文歷史價(jià)值,可以為今天和將來(lái)的歷史學(xué)家研究中國(guó)基層社會(huì)提供資料。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以后,尤其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城市化發(fā)展迅猛,廣大城市周邊的農(nóng)村正在逐漸被城市蠶食而消失,由此帶來(lái)了鄉(xiāng)土歷史文化的流失和鄉(xiāng)村原住民在城市化過(guò)程中的文化不適應(yīng),對(duì)于那些經(jīng)受城市化掃蕩正在消失的鄉(xiāng)鎮(zhèn)而言,鄉(xiāng)鎮(zhèn)志的編修不僅可以傳承和搶救鄉(xiāng)土歷史文化和歷史記憶,而且可以展示鄉(xiāng)鎮(zhèn)個(gè)體發(fā)展脈絡(luò),為探索中國(guó)特色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發(fā)展模式、發(fā)展道路提供歷史智慧和現(xiàn)實(shí)借鑒。鄉(xiāng)鎮(zhèn)志還可以成為聯(lián)絡(luò)鄉(xiāng)情的媒介,能夠正確而又適度地調(diào)動(dòng)人們的戀鄉(xiāng)情結(jié),幫助在外地工作的鄉(xiāng)親、港澳臺(tái)同胞及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定居的海外僑胞尋根問(wèn)祖,通報(bào)鄉(xiāng)情,傳播鄉(xiāng)音,使他們了解家鄉(xiāng)的變化,調(diào)動(dòng)他們熱愛(ài)家鄉(xiāng)、建設(shè)家鄉(xiāng)的積極性。而《中國(guó)名鎮(zhèn)志叢書(shū)》除了發(fā)揮鄉(xiāng)鎮(zhèn)志共有的功能外,還表現(xiàn)在對(duì)地方志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形式的探索,是拓展讀志用志、服務(wù)社會(huì)途徑的一次有益嘗試,或許在中國(guó)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乃至中國(guó)地方志事業(yè)發(fā)展史上會(huì)成為一個(g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chuàng)舉。
K29
B
1003-434X(2016)05-0008-07
浙江省社會(huì)科學(xué)界聯(lián)合會(huì)2016年研究課題“新中國(guó)方志編纂實(shí)踐創(chuàng)新研究(1949-2015)”(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6N2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