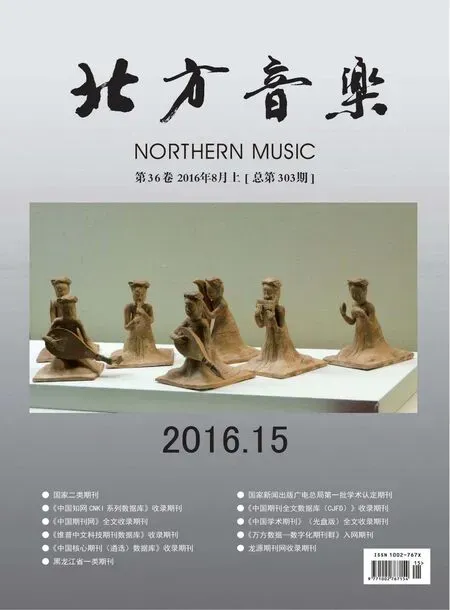從蒙古族音樂(lè)文化中探究其民族認(rèn)同屬性
薛 培
(河南大學(xué),河南 開(kāi)封 475001)
從蒙古族音樂(lè)文化中探究其民族認(rèn)同屬性
薛 培
(河南大學(xué),河南 開(kāi)封 475001)
中國(guó)是一個(gè)多民族國(guó)家,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和不確定性幾乎使每個(gè)人都有多重的身份。而其音樂(lè)文化,是在漫長(zhǎng)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創(chuàng)造和沉淀下來(lái)的,體現(xiàn)著整個(gè)民族的文化,反映著民族的歷史發(fā)展水平。本文就蒙古族特有的音樂(lè)樣式及素材,將該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主要訴諸于這種帶有民族印記的音樂(lè)文化本質(zhì)中,揭示這個(gè)馬背上民族的主要特征。并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在當(dāng)今世界同質(zhì)化的過(guò)程中,這一民族是如何理解本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
蒙古族;音樂(lè)文化;民族認(rèn)同
一、蒙古族——一個(gè)具有特殊音樂(lè)文化的個(gè)性民族
(一)特色民歌體裁——長(zhǎng)調(diào)
在漫長(zhǎng)的經(jīng)歷社會(huì)發(fā)展中,蒙古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民歌素材,代表性的有長(zhǎng)調(diào)、短掉、牧歌等,這其中以長(zhǎng)調(diào)的影響最大。“蒙古族的‘烏日?qǐng)D音道’(俗稱長(zhǎng)調(diào),即‘悠長(zhǎng)歌曲的音譯,蒙語(yǔ)音標(biāo)Urtuindoo),因?yàn)樗遣菰幕漠a(chǎn)物,在曲調(diào)形態(tài)上,其基本的節(jié)奏特征是沒(méi)有均分的節(jié)奏律動(dòng),也沒(méi)有周期規(guī)律的重音變化。由于沒(méi)有比例固定的時(shí)值關(guān)系,自然也沒(méi)有時(shí)值的感覺(jué)。其非均分的特點(diǎn)(例如前送后緊的節(jié)奏特點(diǎn))也與蒙古族的語(yǔ)言特點(diǎn)有關(guān)。”[1]由是觀之,長(zhǎng)調(diào)所具有的這種無(wú)均分特征,與其生存的環(huán)境有很大的關(guān)系。
(二)特色傳統(tǒng)樂(lè)器——馬頭琴
“馬頭琴,弓拉弦鳴樂(lè)器,因琴桿上雕刻有馬頭而得名。構(gòu)造其制作方法較為簡(jiǎn)單,但它卻能演奏創(chuàng)作曲中各種雙音和弦。 隨著馬頭琴音樂(lè)文化的發(fā)展,它已經(jīng)從蒙古走向全國(guó)各地,甚至在世界樂(lè)壇上占領(lǐng)一席之地。人們對(duì)它的評(píng)價(jià)是‘人與自然完美結(jié)合’”。[2]在蒙古族民間音樂(lè)中,常用的民間器樂(lè)有馬頭琴、四弦胡琴(又稱四胡)、三弦等。尤其是作為草原藝術(shù)代表的馬頭琴,不論是是在蒙古族民間音樂(lè),還是在現(xiàn)代音樂(lè)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三)特色人聲元素——呼麥
呼麥,又稱之為“潮爾”、“喉音藝術(shù)”。簡(jiǎn)單來(lái)說(shuō),就是持續(xù)的低音與另一高音旋律相結(jié)合的二聲部的音樂(lè)織體。這種帶有金屬質(zhì)感的唱腔,其發(fā)聲方法與聲音特色及其罕見(jiàn)。“‘潮林道’均由男性演唱,可能與原來(lái)在宗教儀式中的演唱有 固然與關(guān)......持續(xù)的低音就有可能是宗教儀式這一文化行為的產(chǎn)物,其形態(tài)也固然與一定的宗教情感、意象有關(guān)”。[3]
二、蒙族族音樂(lè)文化——民族認(rèn)同的重要標(biāo)識(shí)
(一)民族認(rèn)同概念的界定
民族認(rèn)同這一概念是認(rèn)同在民族學(xué)研究中衍生而來(lái)。也就是說(shuō)民族認(rèn)同是在民族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顯然民族認(rèn)同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美國(guó)學(xué)者斯圖沃德認(rèn)為:“民族認(rèn)同是某一民族成員將自己和他人視為同一民族,并對(duì)這一民族的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有一種接近態(tài)度。”[4]王希思在其著作《民族過(guò)程與國(guó)家》中寫道:“民族認(rèn)同即是社會(huì)成員對(duì)自己民族歸屬的認(rèn)知和感情依附”[5]由此可知,民族認(rèn)同是在民族互動(dòng)過(guò)程中形成的,從一種無(wú)意識(shí)的狀態(tài)到對(duì)本民族或它民族的有意識(shí)的認(rèn)識(shí)、認(rèn)知及認(rèn)同的情感,而文化認(rèn)同對(duì)民族認(rèn)同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一個(gè)民族所具有的獨(dú)特文化,在民族交往與發(fā)展中占據(jù)著主導(dǎo)性地位。
筆者認(rèn)為(1)民族認(rèn)同作為人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與生俱來(lái),它同民族、民族主義一樣,具有很強(qiáng)的社會(huì)動(dòng)員力量。(2)民族認(rèn)同作為一個(gè)心理發(fā)展過(guò)程,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其認(rèn)同的界限,也在不斷的做出調(diào)整與變化,當(dāng)一群體的母體文化,被另一主流文化影響甚至同化時(shí),是接受、認(rèn)可,還是抵制、反抗,取決于個(gè)體對(duì)本民族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的強(qiáng)弱。(3)名族認(rèn)同因其社會(huì)群體不一,對(duì)象不一,可被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包括族群認(rèn)同,民族——國(guó)家認(rèn)同和大眾意義上的文化認(rèn)同。
(二)蒙古族音樂(lè)文化在民族認(rèn)同中的作用
在當(dāng)前全球文化沖擊的背景下,在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大變遷中,人們很容易將自己與他者進(jìn)行比較,并發(fā)現(xiàn)自身的不同價(jià)值,從而重新思考自身的價(jià)值。不管是長(zhǎng)調(diào)、呼麥還是馬頭琴,作為蒙古族特有的民間藝術(shù),他們的標(biāo)識(shí)性就像我們提到“大歌”就能聯(lián)想到侗族,而它的認(rèn)同意義,如同維族的“木卡姆”與藏族的“囊瑪”一樣,蒙古族的這些音樂(lè)文化、民間藝術(shù)亦是如此。在華夏幾千年的歷史進(jìn)程中,漢族文化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或者少數(shù)民族文化之間,一直處于交融、摩擦、甚至沖突之中,而這些特有的音樂(lè)文化與民間藝術(shù),如同本民族的名片一樣,增強(qiáng)本族認(rèn)同感,使它在當(dāng)下社會(huì)中變得突兀、醒目。這是祖輩們留下的最的寶貴的遺產(chǎn),它們與伴隨其一生的當(dāng)?shù)匚幕讶跒橐惑w。
因此,蒙族的這些特有的音樂(lè)文化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典型性、異質(zhì)性,使得蒙族人民忠誠(chéng)的維護(hù)著本民族的特性,凸顯著鮮明的文化特征。與此同時(shí),各民族的風(fēng)俗文化交流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民族特點(diǎn)與個(gè)性的流失,極大地增強(qiáng)了本民族的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各民族豐富多彩的音樂(lè)文化在當(dāng)今社會(huì)中并沒(méi)有走向同質(zhì)化的道路,反而在社會(huì)大背景下綻放光彩,這也正是各族民族認(rèn)同與文化認(rèn)同更加趨同、緊密的根源所在。
小結(jié)
在中國(guó)多元一體的多民族社會(huì)中,很多所謂的固有族群音樂(lè)文化已經(jīng)被主流音樂(lè)文化,甚至他族音樂(lè)文化所取代。因此,作為具有鮮明特征和精神外化呈現(xiàn)出來(lái)的音樂(lè)文化,在增強(qiáng)民族認(rèn)同意識(shí)中,具有著重要的意義與作用。蒙古族的這些特有的音樂(lè)文化與民間藝術(shù),不僅是民族認(rèn)同的重要標(biāo)識(shí),更是一張顯性的歷史名片。而在今天看來(lái),作為協(xié)調(diào)和解決民族問(wèn)題不可替代的組織機(jī)構(gòu),國(guó)家擔(dān)負(fù)著歷史性的責(zé)任。解決矛盾、沖突的根本所在便是尊重各民族音樂(lè)文化、民族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實(shí)現(xiàn)我們這個(gè)多民族國(guó)家平穩(wěn)、健康的發(fā)展。
[1]修海林∶《音樂(lè)美學(xué)通論》,上海音樂(lè)出版社,2013年,第297頁(yè)/
[2]葉永剛∶《馬頭琴在草原上深情的歌唱》,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56頁(yè).
[3]修海林∶《音樂(lè)美學(xué)通論》,上海音樂(lè)出版社,2013年,第282頁(yè).
[4]張寶成∶轉(zhuǎn)引《民族認(rèn)同與國(guó)家認(rèn)同——跨國(guó)民族視閾下的巴爾虎蒙古人身份選擇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6頁(yè).
[5]王希思∶《民族過(guò)程與國(guó)家》,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頁(yè).
薛培,女,漢族,河南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音樂(lè)與舞蹈學(xué)專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