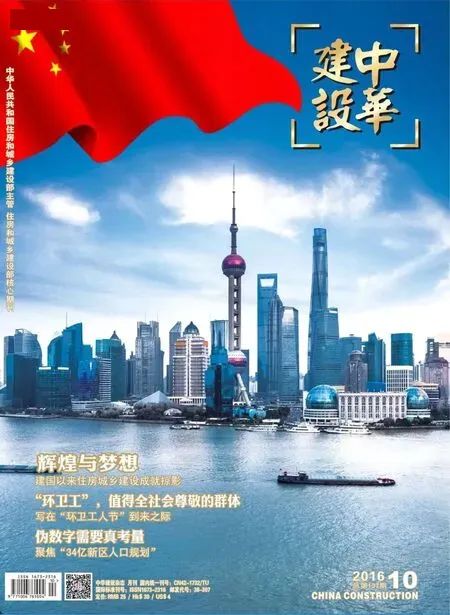銳言
評潭
銳言
郭仁忠:城市規劃需要數字化轉型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城市科學院研究會副理事長郭仁忠提出,規劃的科學性固然重要,但同時也存在連續性和周期性之間的矛盾,城市的發展速度很快,很難準確預測20年以后的發展。規劃需要一個云平臺,要有層際控制,這樣才不會產生規模失控。日益發達的計算機和通訊技術(ICT)將幫助城市規劃數字化轉型建立在線作業平臺,實現全過程實時感知和同步更新,并進行量化分析和評估,相當于所有規劃師和相關部門都在一個平臺共同工作,城市規劃轉型既是現實需求,也是未來趨勢。
李德仁:智慧城市要善用空間大數據
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德仁提出,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根據每個城市自身的特點,在做好頂層設計后進行統一規劃,建立智慧化的城市運營中心,根據實際需要,將其變成城市運行監控的指揮調度中心、智慧服務中心。這就要求城市將各類應用中的時空大數據進行有效管理,并按照實際需求進行處理、存儲、管理,提供相應服務,滿足從室外到室內、從地上到地下的各類智慧應用。在大數據時代,智慧城市要實現對人或物的感知、控制和整合,否則城市就談不上智慧。
劉太格:避免“攤大餅”,北京應分成若干個城市來建設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劉太格表明,北京是一個人口兩千多萬的超大型城市,存在“攤大餅”現象,現在像一個跑不動的腫胖的人。未來可以將北京當成一個家族來看,其中有若干個兄弟,兄弟有自己的家庭,再去繁衍孫子輩的小家庭。也就是說,應該把大北京分成若干個城市,每個城市有三五百萬人口,居民可以在其中的小城市滿足就業、醫療等需求。此外,在片區中要有較大的綠化帶,衛星城周圍有綠化帶,下面的小區周圍有綠化帶,小區中有公園。
李鐵:大城市趕走低端勞動者就是胡搞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表示,最近很多大城市都提出要控制人口,一些城市在提出這一構想時往往忽略了城市發展的基本問題和現狀。很多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特大都市,并沒有更好地利用周邊資源來疏解城市人口,很多地方提出發展高端產業,減少低端產業鏈的延伸,對低端產業有排斥,這些都是偽命題。高端人口進去之后,終究還是要低端人口為其服務。有的城市把轄區公共福利、政府補貼補助,甚至升學待遇等都作為利益固化在原有戶籍人口之間,對低端勞動者是不公平的。
鐘偉:一二線城市可先行試征收房屋空置費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提出,中國房地產稅終究是要向業主開征的,但在當下不合時宜。開征房地產稅必然是期望提高房屋持有環節的稅費,避免富裕階層購置大量住宅占據過多公共資源。因此可以考慮以水電燃氣收費部門為抓手,以房屋物業管理部門為幫手,制定如何認定空置房的標準,并對空置房征費,拒絕繳費者可能會在未來空置房交易過戶時遭遇懲罰,建議一二線城市的房屋空置費可先行先試。
馮焱東:樓市需在供給、需求兩端同時降低杠桿
民生銀行地產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馮焱東表示,目前各城市房地產市場分化十分嚴重,在上海、南京、深圳、蘇州等熱點城市,房地產調控政策應該是積極抑制需求,擴大供給,大力補庫存而不是去庫存,抑制需求的有效辦法之一就是降低按揭杠桿。供給側杠桿重點在土地款融資杠桿,熱點城市可以考慮提高自有資金比例。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兩方面降低杠桿,給樓市及時降溫,才能促進房地產和金融行業更加健康發展。
袁曉東:在農村做項目要尊重當地建筑形式和人文心理
深圳建筑設計院北京分院副總設計師袁曉東提到,新農村的改造不在于形象,而在于功能。在農村做項目,無非是對農村建筑功能的改善和形象的改善。形象改善是建筑師最愿意做的,討巧,容易出效果。農民自住房改造一般都是由農民自己花錢,參照的標桿往往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樣式,建筑師要想沖破當地人的固有概念很難,但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化,使農民不用多花很多錢而得到更好的建筑形象。建筑師在做新農村規劃、新農村的單體建筑設計時,應尊崇當地建筑的潛在規律和農民對建筑的心理需求。
馬建堂:工匠精神要與供給側改革結合
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馬建堂指出,我國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不適應,中低端產品充斥市場,優質高端產品供給不足,而工匠精神缺乏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生產高端、優質產品的企業,都是在一分一毫之間傾注了大量心血,日夜精進,進而達到了品質日漸臻于完美的境界。在過去,幾級工很自豪,可現在好技工卻很難找,這說明現在工匠的社會地位不高、收入不豐,許多優秀人才不愿加入工匠群體,因此應建立并完善“工匠制度”,形成工匠職級晉升、榮譽授予、國際交流的機制,收入分配要向能工巧匠傾斜,調動工匠“在車間完成創新”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