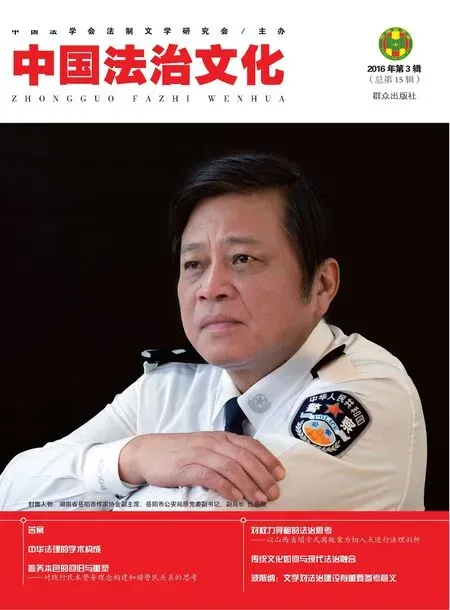中華法理的學術(shù)構(gòu)成
文/陳鴻彝
中華法理的學術(shù)構(gòu)成
文/陳鴻彝
中華法理是中華法治的靈魂與先導。研究法理,歷來是中國先民的強項,成果豐碩;但至今仍然冷藏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庫里,嚴重匱乏現(xiàn)當代的發(fā)掘與整理,這很不利于增進中華民族的法理自信與法學自尊。發(fā)掘整理中華法理,是當代中國政法界學人的應有擔當。
即使從商湯建政算起(公元前17世紀),我們也已有了四千年的治國之史了。四千年來,我們走出了一條大一統(tǒng)國家多元向心、綜合為治的治國之路;數(shù)千年的絕大部分時間內(nèi),我們總是走在文明世界的最前列。這,離開有強大向心力、統(tǒng)合力、凝聚力的中華法治文明,是不可想象的;而中華法治文明是建立在強大的法理研究、深厚的法理積淀之基礎上的。沒有高度自覺的中華法理做引導,就不可能有中華法治,不可能有歷代中華法典的連續(xù)制作和更新,也就不可能有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體的有序存在。法理,原本是中華制度文明的先行領(lǐng)域,它使中華法治遠遠超越于古代普世通行的神治神斷、血親復仇、同態(tài)復仇、司法決斗之上。要知道,在神治國度里,是容不得任何有價值的法理研究的。我們應該百倍珍愛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chǎn),抵制那種將它碎片化、邊緣化、虛無化的做法。
很遺憾,近世以來,人們把中華民族持續(xù)發(fā)展的文明史定義為“封建史”,于是“封建社會”里的一切,什么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封建倫理、封建教育……凡事一沾上“封建”,就必“批”無遺,必“臭”無疑,簡直沒有一樣好東西。更何論什么封建制度、封建法律、封建刑獄以至封建法典這些典型的“封建”事物呢?于是在他們那里,所謂“漢唐盛世”,所謂“五千年文明”,便只剩下一句空洞無物的口號。自家的東西虛無化了,于是只能倒騰“二手貨”。如目前通行的“法理學”之類的讀物,理論體系是外來的,思考資料是引進的,科研方法論是借用的,話語表達是仿造的;即使點綴一些出自本土的例證,也往往是負面的、陪襯的、零星的,多不過是穿插一些流行口號,以謀取政治合法的通行證而已;讀后,人們對中華法理是什么,有沒有值得肯定的東西,照樣茫然無知。頭腦中塞滿了外來的東西,其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心態(tài)如何,可想而知。因而認真疏理、深入研究中華法理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從先秦時期諸子百家開始,早已預制了中華法理之基礎性構(gòu)件,引領(lǐng)了歷朝歷代的法典制作與治國實踐,具有獨特的學術(shù)價值,我將其初步歸納為八個方面。
一、中華法理以天人相與、陰陽依存為哲理基礎,以陰陽對應、五行生克為思維方法論
在“天人相與”論下,人間秩序是自然秩序的復寫,人應當順應自然,與大自然建立調(diào)適共存的和諧關(guān)系,從而維護宇內(nèi)的生態(tài)平衡,維護人類社會的平衡穩(wěn)定。進一步的思考則是:人間秩序應統(tǒng)一于自然秩序,大自然是運行不息、生生不已、陰陽依存、四時代換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故國家的政治運作,政府的法紀舉措,個人的事功修為,皆須順天應人,凡逆反自然、征服自然的結(jié)果,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懲罰,故中國人要求講天理、順人心,正如《易·泰卦》所說:“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節(jié)卦》所說:“天地節(jié)而四時成,節(jié)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它講的是天理,而真正關(guān)注的是民利。
“陰陽對應”,講的是對應事物間的相互依存、滲透、轉(zhuǎn)化關(guān)系,是二者的對應、對等、對稱、對比的共存關(guān)系,絕不僅僅是對抗、對立的斗爭關(guān)系。以此來指導社會人文關(guān)系的體系建構(gòu),不鼓吹弱肉強食,不主張一方壓倒一方、吞滅一方。在父子之間、夫妻之間、長幼之間、上下之間、師生之間、醫(yī)患之間、勞資之間、體腦之間、城鄉(xiāng)之間、原被告之間、自由與秩序之間、成本與效益之間,怎么能全是對立斗爭關(guān)系呢?怎么能只講一個吃掉一個呢?如此下去,人際之間,除了人斗人、人防人、人謀算人之外,還能剩下什么?又怎么能指望有祥和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與文明高尚的精神世界呢?
“五行”學說,是前人構(gòu)建的一種思維模型,它用金、水、木、火、土之間的生、克、乘、侮關(guān)系,對世間萬事萬物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作一種模式化的形象表達。它認定:事物總是在相互關(guān)聯(lián)中求得總體的平衡發(fā)展的;任何一方的超常突破,都會帶動總體既有秩序的改變;它強調(diào)一事物的正常存在,以周圍他事物的正常存在為條件;一事物的發(fā)展,以周圍他事物的正常發(fā)展為依托。作為社會性的“人”,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不可能獨善其身;其所謀求的應是綜合效益、總體效應,而不僅僅是某一局部、某一個體的孤立存在。是故“,五行”學說可以為總體論、結(jié)構(gòu)論、參與論提供理論生長點;是故,對任何新變做宏觀考察、總體評估、前瞻性預測,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是故,以此來指導人文社科學說中各式各樣的矛盾關(guān)系的平衡處置,用來指導司執(zhí)法機構(gòu)之間的協(xié)調(diào)運作,用來指導法理學學科之概念、范疇的分析、概括與表達,才是正道。
歐美法學則以“黑白二元對立論”為哲學依據(jù),以對立、對抗/復仇為法理基礎和思維方法論,其所強調(diào)的始終是個體利益、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暴力懲治,其結(jié)局便是你死我活,一個吃掉一個。哦,這個“叢林法則”似乎也是一種“天人相與”論,然而那只是禽獸的一種生存哲學,何況它也僅僅通行于異類之間;然而,叢林論者卻把它引入了人類內(nèi)部,它鼓動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吞噬!
二、中華法理以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大德曰生為價值取向,以人命大于天為法理靈魂,一切法制運作,都從“人”出發(fā),以“人”為中心
中華法理確認人命為貴、民為邦本的法治宗旨,要求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慎獄恤刑,不侮鰥寡。它保證了法為良法、政為德政。這才是中華法理、法系的文化之根。
我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之作《易經(jīng)》有六十四卦,它反復論列的是慎獄恤刑的主張,講的全是珍愛生命、趨吉避兇問題。可貴的是,對于如何趨吉、怎樣避兇,它并不僅僅寄望于行為人的個體修為,而更強調(diào)政府應推行良法良政,更強調(diào)君子(執(zhí)政者)應慎獄恤刑。請看:《泰卦》“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卦》“君子以容民畜眾”;《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節(jié)卦》“君子以制數(shù)度,議德行”,“天地節(jié)而四時成,節(jié)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恒卦》“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履卦》“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觀卦》“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大有卦》“君子以疾惡揚善,順天休命”;《大壯卦》“君子以非禮勿履”;《益卦》“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卦》“君子以懲忿窒欲”;《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這種種良性施政要求和君子修為,都是為百姓之“趨吉”服務的。很明確,責在君子(執(zhí)政者)。
至于如何讓百姓“避兇”,則有許多叮嚀:《噬磕卦》“先王以明罰敕法”;《賁卦》“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解卦》“君子以赦過宥罪”;《豐卦》“君子以折獄致刑”;《旅卦》“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卦》“君子以議獄緩死”;《既濟卦》“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這些卦爻辭,其論議的對象是先王、是君子,其基本要求是化成天下,振民育德,容民畜眾,是不傷財、不害民。它要求在刑獄執(zhí)法中,要貫徹恤刑、慎獄、赦過、宥罪方針,要做到議獄、致刑、不留獄,要采行明罰、設教、防范措施;君子自身則應做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非禮勿履、懲忿窒欲、疾惡揚善、順天休命。果能如是,百姓還有什么“兇”不可避呢?
《易》這類主張的提出,恰恰是在普世盛行奴隸制肉刑之時。其時,廣大奴隸連“人”的資格都沒有(古希臘的“公民”概念中,壓根兒沒有奴隸的位置);在這種社會文化生態(tài)條件下,這套施政執(zhí)法主張就顯得尤為珍貴了。它是人類生命意識早期覺醒的突出標志,是中華法理的崇高起點,是后世法學界的原創(chuàng)論題,均有待闡發(fā)。
三、中華法理據(jù)以判斷是非、善惡、美丑的基準,是健全的國家觀、刑法觀、倫理觀,這也是政府實施刑賞的依據(jù)
從周秦時代起,我國就實行政教分離體制,逐步確立了中央集權(quán)、地方分治、基層自治的國家機制,就把“食貨為先,教化緊隨,不忘兵刑”的“八政”界定為國家機器的天賦職能,把“德主刑輔、德禮為先”規(guī)定為法制原則。這就預先否定了“為治惟法”論,否定了有懲無賞、不教而誅的做法。要知道:從《舊約》到《羅馬法》,都是只講“懲”而不論“賞”的。
先秦儒法兩家,思想對立,卻都以綱常倫理作為構(gòu)建群體社會的法寶,把萬千人口組織進一個有機的社會體系內(nèi),使各安其位、各守其職、各具名分,不相僭越、不相干擾、不得奪倫,這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能長期走在一起的法制密碼。當然,其森嚴的等級制需要重新評價。
正是在健康的國家觀、刑罰觀、倫理觀的指導下,后世歷代先民,不論發(fā)生怎樣的法理爭議,最后總能取得有利于社會進步的結(jié)論。例如:1.人性的善與惡;2.神權(quán)、人權(quán)、法權(quán)的關(guān)系;3.法與禮和禁的關(guān)系;4.刑與德和賞的關(guān)系;5.守法與變法的關(guān)系;6.用法與用情的關(guān)系;7.忠與奸的關(guān)系;8.防與治的關(guān)系;9.復仇與循法的關(guān)系;10.肉刑的存廢問題;11.刑審的存廢問題……一次爭論,就是法理的一次提升、一次深化。
西方人把國家觀、刑法觀建立在“暴力論”的思想理論基礎上,視政權(quán)為“鎮(zhèn)壓之權(quán)”,視法院、軍警為暴力機器,即依此建構(gòu)其法制機構(gòu),指導其立法、司法與執(zhí)法活動。盡管它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它也為“惡法”提供了生存空間。
四、中華法治的三大基本理論元素,通過先秦諸子之文獲得初步揭示,它與現(xiàn)代法治精神相通
一是“垂法而治”、“據(jù)法而治”、“緣法而治”(《商君書》)。二是“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任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三是君主治國“不淫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nèi)”,反對法外施刑,反對法內(nèi)賣恩,要求“當于法者賞之,違于法者誅之”(《管子·任法》)。這三個方面,大致上揭示出了中華古典法治的最基本的底線內(nèi)涵,它們強調(diào)的都是國家應尊重法律,依法施治,而沒有神權(quán)插足行威的余地。這與兩三千年之后的現(xiàn)代法治有精神上的相通之處,可以對接,并不抵觸。1959年在德里召開的世界法學會議上,對法治制定了三條規(guī)則:一是維護每個人的人類尊嚴,二是制止行政權(quán)的濫用,三是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同樣沒有神權(quán)擅斷主義的影子。
五、中華法理的學術(shù)優(yōu)勢,在中華法系之諸法合體、律例并行的體例上自有其特色表達
中華法典采行“諸法合體”的編纂體例和“律例并行”的審斷準則。在“諸法合體”下,法典即首列“名例”,交代立法思想、立法原則與基本刑名概念,起著“憲法”的總領(lǐng)功能;然后再分條分款地開列刑法、民法、訴訟法、行政法、治安法甚至涉外法等方方面面的內(nèi)容,起著各別法、部門法的分敘功能。這樣做,其實是“諸法合體而分肢”的。它保證了法律的全息性、內(nèi)容的自恰性與功能的綜合性,適應了歷代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大中華國家體制機制的需要,有利于調(diào)動龐大機體的各項法治資源來共同建定社會秩序,有利于調(diào)動各種法制手段恰當處置各種不同性質(zhì)的社會矛盾;這正是中國機體數(shù)千年穩(wěn)定存在的法理基因。當然,它也留下了各種個別法、部門法自身發(fā)展的巨大空間。
至若“律例并行”,實際上是律令與通例及成案的綜合應用。它既能用“律”來保證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性、原則性、穩(wěn)定性、權(quán)威性,又能以“通例”體現(xiàn)出相應的地區(qū)差別、民族差別、時勢差別,還能以成案來保證司執(zhí)法活動的針對性、實用性、可操作性。這是中華法系的一個突出優(yōu)勢,它適應了大一統(tǒng)國度里各地經(jīng)濟文化風俗民情發(fā)展不平衡的客觀形勢的需要。這就綜合了西方大陸法系與海洋法系二者的優(yōu)長而避開了它們的先天缺陷。例如:
清代明文規(guī)定:斷案要重律用例,有成案即比附成案辦理。地方“上詳”的案情審理報告,必須引用相應的律文、通例與成案;刑部在批復前,先交予其下屬的“司”去負責查對詳文中對律條、通例與成案之引用是否貼切;發(fā)現(xiàn)未引用或歪曲引用者要追究其法律責任;而引用相應的律文、通例與成案,更是判詞寫作的必備內(nèi)容。例如:
清《刑案匯覽》中有這么一個案件:“行劫衙署伙盜接贓免死發(fā)遣”。該文寫道:
“(刑部)直隸司查《例》載:‘強盜殺人放火、奸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及干系城池衙門,并積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財,斬決梟示’等語,至在外望及接遞贓物并未入室搜贓之犯,《例》內(nèi)并無‘不準以“情有可原”聲請’之文。檢查乾隆十七年陜西省盜犯范西河等‘行劫縣衙署案’內(nèi),伙盜馮大成等在外看守把風,經(jīng)本部議以‘強盜例’應分別‘法所難宥、情有可原’,并無‘干系城池衙門不準分別’之條,將馮大成等仍照‘免死減等例’發(fā)遣。在案。此案,侯三聽從王大等行劫巨鹿縣署內(nèi)、該犯在外等候接贓,其同行接贓之趙三,因另有行劫威縣李豹臣等案,審擬斬決。該犯并無行劫別案,該省審照‘情有可原’免死發(fā)遣。核與例義及辦過馮大成發(fā)遣成案相符,似可照復。”
奉批:“按例,前后兩條似應俱行斬梟,但既有成案,只可照復。”(摘自《乾隆六十年說帖》)
(今按)清律通例中原有“強盜殺人放火、奸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及干系城池衙門,并積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財,斬決梟示”等語。其中“強盜”一詞是個全稱判斷,概指參與強劫之所有成員,故有“不分首從”、“不分曾否得財”的說明,原是從重懲處之意。但在實踐中發(fā)現(xiàn):在“強盜”群體實施強劫犯罪時,是有很多分工的,即以“干系衙門”論,有入衙動手劫贓者,有入衙而未動手劫贓者,有未入衙在外接應望者,有被裹脅隨行并未作為者,有出主意、供線索而未到場者……籠統(tǒng)地不分首從,也不分曾否得財,一律“斬決梟示”,這么無區(qū)別,就沒有政策了。所以,刑部才同意將“在外看守把風”者、“在外等候接贓”者“照情有可原免死發(fā)遣”;而直隸司才敢說“核與《例》義及辦過‘馮大成發(fā)遣成案’相符”;乾隆帝也才會說:“按《例》,前后兩條似應俱行斬梟(因都是入衙搶劫之案),但既有‘成案’,只可照復。”這就提供了一個“引用成案”的判例,雖乾隆皇帝也“只可照復”。
六、中華法典以刑法為重心,兼顧民法,展示出中華法理上的全方位建樹
刑法的推行,激發(fā)了古代立法、司法、執(zhí)法領(lǐng)域各個學科的超前早熟;民法的兼顧,證明中華法典原來并不偏枯。
中華法系、法典、法例都是以護衛(wèi)人命為底線、圍繞刑法展開的。刑法所關(guān)注的核心是人命、人權(quán)、人身問題,故其司執(zhí)法原則是:法不阿貴,慎獄恤刑;疑罪從無,教而后誅;證據(jù)第一,誤判追責;它遵循三審五聽、注重證據(jù)、依法定罪、衡情量刑、分級管理、誤判追責的一整套刑審規(guī)程。適應這種嚴格而嚴密的法制要求,也就促成了中國古代刑偵學、預審學、證據(jù)學、法醫(yī)學、獄政學、司法文書學等各個法學領(lǐng)域的超前早熟,獲得了獨步世界的豐碩成果。
西歐的“羅馬法”是以民法為重心的,它把個人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占有、轉(zhuǎn)移、分配、再分配視為中心任務,人身與人命反而被視為次要的;至于中世紀在神權(quán)擅斷主義下,強調(diào)天啟、神意,凡宗教經(jīng)典、宗教教旨、宗教教條、宗教儀軌,直至主教意志、神父指令、教徒證詞,都是懲辦人世間一切官民的“權(quán)威依據(jù)”,毫無人命、人權(quán)、人的主動性可言,也就談不上“證據(jù)第一、誤判追責”等法制程序與相應的法學成果了。故西方的刑事偵查和刑事檢驗制度之類,要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方才建立起來,比中國晚了上千年,也就可以理解了。
試以中華法醫(yī)學的歷史發(fā)展為例證說明之:
(一)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就對法醫(yī)檢驗提出了驚人的科學要求。《禮記·月令》載:“孟秋之月,命理(法官)瞻傷、察創(chuàng)、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東漢蔡邕的解釋:“皮曰傷,肉曰創(chuàng),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言民斗辨而不死者,當以傷、創(chuàng)、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這說明“法醫(yī)檢驗”早已列入辦案審理程序了,更說明由官家負責人體檢驗的理據(jù)早已為社會所認知、所接受了,這在神權(quán)國度里是無法想象的。
(二)到了秦代,現(xiàn)場勘驗已法定包括痕跡勘驗、尸體檢驗和人身檢查等在內(nèi)。例如對“經(jīng)死”(上吊)的現(xiàn)場勘驗:縣政府接報有人上吊自殺時,縣令史當即約同牢隸臣與當方里典、伍老和死者血親家屬一起出現(xiàn)場。到達現(xiàn)場后,縣令史須獨立到尸體邊親自驗視:1.首先仔細查看吊索的環(huán)扣痕跡,重點察看繩索的終端,如有圈束痕跡,應察看死者舌頭出與不出,再查看頭足離繩索終端和地面各有多少距離,是否有屎尿流出。2.然后解開繩索,放平尸體,注意口鼻有無出聲“嘆氣”的樣子(上吊自殺者,喉頭必然有郁氣逸出;他殺移尸則不可能“嘆氣”)。看脖上繩印處是否有瘀血,看瘀痕形狀是半圈還是圈滿頸,試驗死者之頭能不能從索套中脫出。3.若不能脫開,即解開死者衣服,全面檢查其身、頭及發(fā)髻中有無異痕異物;如果舌不伸出、口鼻無嘆息聲、索痕處無瘀血或有無滿圈瘀痕、繩扣緊死而頭不能脫,那么,就不能認定這是自殺。4.自殺的人必然先有緣故和表現(xiàn),要查問其同居家人,來綜合判斷其死因。5.這一切診視勘驗完成后,要制作一份《爰書》,供判案用,具法律效力。這一切表明,秦人的出現(xiàn)場有必須遵守的嚴格程序。我們今天采用的現(xiàn)場勘查方法與程序,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jīng)初步形成了。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行現(xiàn)場勘驗并作法醫(yī)檢驗的國家。
(三)到了宋代,法醫(yī)學家宋慈對傳世的尸傷檢驗著作加以綜合、核定和提煉,結(jié)合自己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依循國家法典和醫(yī)學原理,在1247年冬完成了《洗冤集錄》的撰寫。《洗冤集錄》有科學性、法紀性,還有紀實性。該書包括了對各種非理非法致死致傷的情狀描述,和對于人體尤其是死體的損傷表征、生理機制、致傷外力、致傷器械的記錄,尸體現(xiàn)場的勘驗,還有刑偵人員的工作守則、工作紀律與操作原則、操作程序等豐富內(nèi)容,更有各種疑難尸傷的檢驗鑒別的技術(shù)技巧;對縊死、溺死、日曷死(中暑)、凍死、殺死、胎傷等的急救方法,都寫得簡明易懂,符合生理病理藥理毒理科學。《洗冤集錄》對世界法醫(yī)學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宋慈本人也被尊為世界法醫(yī)學鼻祖。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中華法系在重視“刑法”的同時,并不忽視“民法”的制定與執(zhí)行。
我國歷代法典中,婚姻法、財產(chǎn)法、商貿(mào)法、契約法,甚至工程管理法、生態(tài)保護法,都占著重要的比重。這里舉一個特例,比如“典權(quán)制度”:此制作為中國古代民法范疇中一項特有的物權(quán)法,它從所有權(quán)中剝離出占有權(quán)、使用權(quán)、收益權(quán),以契約形式進行交易,物產(chǎn)所有者將使用權(quán)、收益權(quán)依契約轉(zhuǎn)讓,契約經(jīng)政府公證后受法律保護。在出典期間,如物價上浮,則所有者有權(quán)要求承租方作相應的補償。這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是很先進的合法行為,且對弱勢群體有利,早在宋代就被納入國家法典《宋刑統(tǒng)》了。
再如婚姻法。宋代法律對女權(quán)較前代有更多的關(guān)照。它把女性區(qū)分為在室女、出嫁女、喪夫守寡女、改嫁女、離婚返回女等,各有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在室女有權(quán)參與父母財產(chǎn)(遺產(chǎn))按比例的分配;出嫁女從娘家所獲之“陪嫁田產(chǎn)”等,是她對親生父母財產(chǎn)的一種特殊的繼承方式,屬婚后夫婦所共有,但不參與夫家兄弟分家立戶時的財產(chǎn)分割(按:宋代,父母、祖父母在世時,兄弟不得分家立戶,不得蓄私產(chǎn),而陪嫁田產(chǎn)例外);喪夫守寡女有家產(chǎn)經(jīng)營管理權(quán),如無子(含義子)則為絕戶,絕戶家產(chǎn)收歸國家所有,但她享有終老養(yǎng)生所需的份額;改嫁女、再嫁女不再參與原夫家的財產(chǎn)分割;而離婚返回女能參與父母親的家產(chǎn)分割(比例上低于男性同輩)。
正因為有唐宋法治建設成就的客觀存在,才有效地促使粗獷強悍的遼金和后來的蒙元與清朝統(tǒng)治者,認同中華法理、法系、法典,自動地依循中華禮法來建國定制、立法施政,其作用力是羅馬法所望塵莫及的。羅馬法作為天主教廷之宗教法的仆從,其作用范圍多不過是地中海周邊那么一圈,當時,連歐陸內(nèi)地都無力輻射到,還談什么世界影響?
七、中華法理以立法定制為目標,它指導了我國歷朝歷代的法典修纂,而每次修纂都使社會文明得到一定的提升,法典自身也在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中不斷發(fā)展,不斷改善編纂技術(shù)
我國歷史上,有過關(guān)于肉刑存廢的爭論,有過關(guān)于血親復仇的爭論,也有過關(guān)于株連與大赦的爭論,無不生動地體現(xiàn)出中華刑罰思想演變的歷史軌跡,在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中,推動了刑名法理的完善化。我們曾反復遭遇過全局性的天災人禍,也曾長時期陷入分裂動蕩之中,出現(xiàn)過形形色色的反社會、反人類的“牛鬼蛇神”,也出現(xiàn)過道德滑坡、人心渙散的危險傾向,但這一切都沒有改變中華前進的步履,我國總能衰而復振、仆而又起、分而又合。這,談何容易!它,端賴先民對良法德政作了系統(tǒng)深入的探究,并將其思維成果反映到國法的制定及其有效實施上來。這里,不妨以歷代在慎獄恤刑方面的舉措為例作個說明:
上古法典中,原有墨、劓、刖、宮、大辟五刑,周公在大力推行禮樂的同時,增加了“流、贖、鞭、撲”而成九刑;這就大大壓縮了肢體刑的實施空間;其后又添設了“不傷體、不虧財”的“圜土納之”的強制勞動措施,用以懲罰“未麗于刑”而有害治安的輕微過犯。漢文帝明令廢除肉刑;隋文帝則從國法規(guī)定上廢除了斬絞以外的酷刑方式如車裂之類;唐代明確了“笞杖徒流死”新五刑,宋人則將死刑審斷權(quán)收歸中央,由皇帝作“終審裁決”,從而結(jié)束了五代軍人當政、地方掌握殺戮大權(quán)的歷史;清中葉又把懲治犯罪之“千里流放、萬里充軍”改為就地囚禁監(jiān)管……這每一次變革,都伴隨著激烈反復的法理爭議,每一次爭議都使社會文明得到相應的提升。
再說說法典編纂的技術(shù)問題。因為立法語言與立法技術(shù)的先天性局限,任何法律都絕不可能對不斷變化中的所有社會現(xiàn)象預先作出具體法制規(guī)定,在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尤其如此。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就應當考慮如何彌補立法語言與立法技術(shù)的不足,對復雜的社會行為作出有罪無罪、此罪彼罪的審斷。而唐人所謂“入罪,舉輕以明重;出罪,舉重以明輕”的主張,便是法律適用上的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說,一個事實傷害在現(xiàn)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是犯罪,但比它輕的事實傷害在刑法中已規(guī)定為犯罪,就可以采取“舉輕明重”的方法來適用法律,論定其有罪,予以入罪;某種事實傷害在現(xiàn)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不是犯罪,而判決時應作為未犯罪來處理,那就可以采取“舉重明輕”的方法來適用法律:因為較重的事實傷害都不受現(xiàn)行法律的懲罰,那么,較輕的事實傷害更應寬免,應予出罪。這樣做,對雙方當事人都是一種人權(quán)保護,都是一種利益平衡。可見它與流行的“罪刑法定主義”比起來,在立法思想的先進性、立法思維的縝密性、立法技術(shù)的完善性上講,至少是毫不遜色的。
任何制定法都不可能窮盡生活現(xiàn)象,任何犯罪者都會千方百計設法規(guī)避現(xiàn)行律條的懲處,尤其是“精熟法律”者更擅長鉆現(xiàn)行法律的空子去為自己辯護;再說,當社會處于轉(zhuǎn)型期時,社會犯罪條件、懲處機制都在激劇變動中,“成文法”永遠跟不上現(xiàn)實的發(fā)展。在這種情況下,對明顯的事實侵害不作處置,顯然有失公正。
舉個例子:《永徽律疏·二六一》載:“諸以物置人耳、鼻及孔竅內(nèi),有所妨者,杖八十。”現(xiàn)代刑法,無論中外,對“強奸罪”中“性交”的外延爭議較大,即性交僅是男女性器官的結(jié)合,還是將口交、肛交等也包含在內(nèi)?在司法實踐中,有關(guān)口交、肛交及同性交,往往有“于法無斷”的現(xiàn)象,但對人身、人格、人的尊嚴的傷害是客觀存在的,不能不予懲處。看到一千幾百年前的此類條文,你不得不佩服立法者思維的縝密與超前。
八、中華法理是以陽剛旋律、合乎邏輯地表達自己的,是本土文化,故深入人心,已經(jīng)內(nèi)化為中國人守法護法的內(nèi)在要求
中國文化界一直以陽光心態(tài)去透視一切艱難困苦、穿透一切陰霾毒霧,而以其作品的陽剛旋律振奮著人心,支撐著民族意志,持續(xù)地發(fā)揮其拒腐防害的功能。在中國文壇上,所謂黑厚之學、靡靡之音、黑幕文章及各色奢談戲說,從未占據(jù)過主流地位;同樣,在中國法學界,一切鼓吹分裂、渲染仇殺、張揚屠戮、挑動沖突、背離公理正義的謬說,也從未找到過自己的市場。
中國歷代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有效行政管理從未中斷,所以各種政治的、刑事的、民事的獄案也就一直在發(fā)生、一直在被審理,而歷代獄案在其發(fā)生、報案、受理、偵緝、檢驗、取證、審訊、上報、批復、判決、處置(處治)、執(zhí)行、追責過程中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偵緝審理、請示批復、判決執(zhí)行、甄別平反等各種公案文牘,早已匯成了引人矚目的長波巨瀾,反映著不同時代的社會生態(tài),折射著不同時代官與民的法紀生活,刻錄著歷代中國人艱難奮進的真實足跡,是中國社會持續(xù)存在、持續(xù)發(fā)展的貼切記錄,具有最典型、最真實的原創(chuàng)性文獻典籍意義。這類文章最強調(diào)規(guī)范性,都有法定的行文程式、使用法制專業(yè)術(shù)語,內(nèi)容要求與實事實情保持零距離,與國家制定法保持零距離,具有“檔案文獻”的史證性質(zhì),是本土文化產(chǎn)品,因而具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品性,是中華法理的最佳載體。
中華法理,營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信仰王法,愿為守法護法付出巨大犧牲,這便是中國先民的民族品性。而今,卻有人用“法盲”、“不具現(xiàn)代公民素質(zhì)”、“不懂得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云云。我要敦請這些自居高明者深思:那些玩法、褻法、賣法者真是不明法意的一群嗎?那些案值驚人巨大、危害史無前例者是來自社會低層的“法盲”們嗎?真正應該接受法理教育者、應該接受法律制裁者到底是誰呢?
結(jié)語
在數(shù)千年我國文明史上,中華法治、法理,既是政治推進力,又是文化輻射源,更是社會文明的提升機,還是異質(zhì)文化的兼容器,其歷史功能強大而無可替代。在中華大地上,一切分裂割據(jù)勢力,都被全民自動地排斥在政治合法性之外:無論哪個王朝,也無論何族何種軍政集團,誰都沒有也不能超越中華法統(tǒng)而實現(xiàn)自己的合法統(tǒng)治,也從無鼓吹分裂、鼓吹割據(jù)的文章或立法得到過全體國民的法理認可。它保障了數(shù)千年來最龐大民族群體之持續(xù)存在,保障了龐大社會經(jīng)濟體的穩(wěn)步發(fā)展,對內(nèi)遷各族起了融合凝聚作用,對周邊世界產(chǎn)生了強大的輻射與吸附功能。總之,它提升了中華制度文明的水準,它理應獲得后世子孫的高度尊崇。一句話:我們必須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chǎn),擔當起發(fā)掘、疏理、萃精中華法理的重任,以求無愧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這個光榮時代。
(本文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book=23,ebook=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