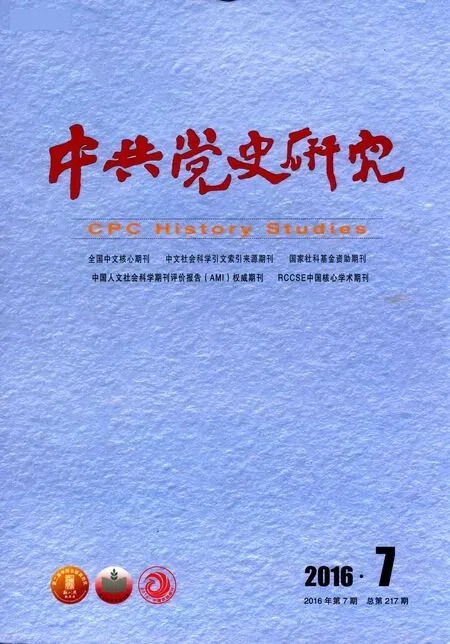從美國檔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國共內(nèi)戰(zhàn)調(diào)停問題
姚 昱
從美國檔案看一九四九年一月國共內(nèi)戰(zhàn)調(diào)停問題
姚 昱
1949年1月8日,國民黨政府向四大國提出調(diào)停照會之后,中蘇兩黨領導人毛澤東與斯大林圍繞此事展開了一次重要而又微妙的協(xié)商。這一協(xié)商引發(fā)了學術(shù)界有關斯大林此時對中國革命態(tài)度究竟如何的長久爭論。本文以美國政府解密檔案為基礎,并與已有俄文和中文資料進行比較互證,通過系統(tǒng)論述美國政府在此問題上的決策過程,嘗試說明斯大林無論是在時局的認識還是策略的設定方面都存在著問題,而毛澤東的認識與策略則更有成效,而且其事后對此事的評價也相當客觀公正。
調(diào)停;斯大林;毛澤東;美國
解放戰(zhàn)爭勝利前夕,蘇聯(lián)領導人是否曾阻礙中國革命的深入和完成,一直是國內(nèi)外學者——尤其是中俄兩國學者——討論的一個熱點。最早的學術(shù)討論源于中文資料披露的毛澤東、周恩來有關1949年上半年斯大林曾阻止人民解放軍“過長江”、想要在中國建立“南北朝”的說法①參見王方名:《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親切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1月2日。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3頁。,此后隨著一些內(nèi)容相互矛盾的回憶錄出現(xiàn),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較大的爭議②支持毛澤東、周恩來這一說法的相關資料有斯大林與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司徒雷登的記述、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對楊尚昆的訪談以及米高揚兒子的回憶記錄等。師哲的回憶錄和當時斯大林派駐延安的聯(lián)絡員N.B.科瓦廖夫回憶的米高揚訪華卻呈現(xiàn)出斯大林并未阻止過中國共產(chǎn)黨“過長江”,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72—373頁;〔俄〕科瓦廖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關系》,〔俄〕尼·特·費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著,彭卓吾譯:《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交往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67—169頁。相關學術(shù)爭論見向青:《關于斯大林勸阻解放大軍過江之我見》,《黨的文獻》1989年第6期;陳廣相:《對斯大林干預我軍過江問題的探討》,《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7、8期;王庭科:《“雅爾塔格局”對蘇聯(lián)、斯大林與中國革命關系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增刊;劉志青:《斯大林沒有勸阻過人民解放軍過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陳廣相:《對斯大林勸阻解放軍過江問題的再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由于這些回憶錄內(nèi)容較為模糊,所以在相關學術(shù)爭論中毛澤東、周恩來究竟所指何事這一關鍵性內(nèi)容始終不能厘清。但俄國學者齊赫文斯基和列多夫斯基先后于1994年、1995年公布了兩組蘇聯(lián)政府解密檔案——1949年1月初斯大林與毛澤東就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一事的往來電報和米高揚關于其1949年1月底、2月初秘密訪問西柏坡的回憶報告,*這些蘇聯(lián)檔案漢譯版見〔俄〕С.Л.齊赫文斯基編,馬貴凡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1949年1月間的電報往來》,《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1期;〔俄〕安·列多夫斯基著,李玉貞譯:《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秘密談判(1949年1—2月)》(上、中、下),《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英譯版見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6/7 (Winter 1995), pp.27-29.毛澤東、周恩來提到的蘇聯(lián)人曾阻止中共“過長江”、要中共建立“南北朝”這一問題的具體緣由得以清晰化,即1949年1月初在處理中國國民黨提出的請?zhí)K聯(lián)、美國、英國、法國四大國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問題上,中蘇兩黨領導人產(chǎn)生了較大的分歧。斯大林建議毛澤東接受他提出的有條件和談,但毛澤東認為會影響到中國革命的進程而加以拒絕。*但學界對“過長江”“南北朝”說及“劃江而治”的緣起,有不同認識。參見〔德〕迪特·海因茨希著,張文武、李丹琳等譯:《中蘇走向聯(lián)盟的艱難歷程》,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294—301頁。薛銜天:《“劃江而治”的風源》,《黨的文獻》2004年第2期。
這兩位俄國學者對兩組檔案的解讀以及作為當事人(齊赫文斯基為當時蘇聯(lián)駐北平總領事、列多夫斯基為當時蘇聯(lián)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一些回憶*〔俄〕齊赫文斯基:《1948—1949年的蘇中關系——蘇聯(lián)駐北平總領事的回顧》,《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22頁。并未讓相關討論畫上句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爭論。齊赫文斯基和列多夫斯基都認為,斯大林之所以在國民黨政府提出調(diào)停照會后建議毛澤東接受有條件的和談,是擔心美國借口中國共產(chǎn)黨不接受和平而趁機武裝干涉中國革命;而斯大林的這一建議頗為英明——既不給美國軍事干涉的借口,又讓中國共產(chǎn)黨接過了和平的旗幟;毛澤東、周恩來后來有關蘇聯(lián)領導人阻止人民解放軍“過長江”的看法實際上是誤解了蘇聯(lián)領導人的真實意圖。盡管許多學者接受了這兩位俄國學者的看法*如迪特·海因茨希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也認為斯大林建議和談并非要阻礙中國革命,而可能是出于以下三個考慮:不讓國民黨政府和美國獲得希望和平的美名、向毛澤東展示其作為國際領袖的視野、提醒中共領導人其不得不依靠蘇聯(lián)外交和政治支持的現(xiàn)實。Odd Arne Westad, “Rivals and Allies: Stalin, Mao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January 1949, Introduction by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6/7 (Winter 1995), p.7.國內(nèi)持類似看法的有王真:《斯大林與毛澤東1949年1月往來電文評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沈濟時:《關于斯大林勸阻人民解放軍過長江問題的探討》,《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但仍有學者質(zhì)疑斯大林建議中國共產(chǎn)黨接受和談的真實動機,不贊同中共領導人誤解了斯大林的說法。*如李良明、黃雅麗:《關于斯大林是否主張“劃江而治”的再探討》,《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另有學者認為這些檔案說明了斯大林的確有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的想法,見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57; 〔韓〕金東吉:《關于斯大林是否勸阻中共渡江問題再分析》,《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沈志華:《求之不易的會面: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的試探與溝通》,《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shù)爭論雖然激烈,但對于斯大林在相關電報中為證明自己建議正確而反復提及此次國民黨調(diào)停照會實為美國政府的“陰謀”這一說法的研究尚不系統(tǒng)。筆者通過查閱美國政府相關解密檔案發(fā)現(xiàn),美國方面的資料不僅可以證偽斯大林的說法,而且還提供一些有關這一事件的重要佐證,可以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國民政府的調(diào)停照會與中蘇兩黨領導人的分歧
1949年初,國民黨在內(nèi)戰(zhàn)中頹勢日益明顯。為了挽回局面,國民政府于1月8日同時向蘇聯(lián)、美國、英國和法國駐華公使遞交了請求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的照會。此時與中共保持密切聯(lián)系的斯大林收到這一照會后,于1月10日給毛澤東發(fā)電報,通知中共領導人國民政府提出了調(diào)停照會一事,并希望中共領導人能接受莫斯科為中共設計的有條件接受和談這一策略。為了論證在人民解放軍已經(jīng)取得明顯軍事優(yōu)勢的情況下提出這一策略的正確性,斯大林在電報的一開始就判定國民黨政府的調(diào)停照會實質(zhì)上是美國政府主導的一個大陰謀——“從各個方面的情況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建議是由美國授意提出的,目的在于宣告南京政府主張停戰(zhàn)和建立和平,而中共如果直接拒絕同南京進行和平的談判,則是主張繼續(xù)進行戰(zhàn)爭。”在1月11日補發(fā)的電報中,斯大林進一步闡發(fā)了這一判斷,認為國民黨要求調(diào)停并非是真的為了在中國實現(xiàn)和平,而是美國想讓中共背上“和平破壞者”罪名故意設計的一個陰謀。而蘇聯(lián)領導人提出拒絕美國調(diào)停和拒絕蔣介石等戰(zhàn)犯參加和談這兩個條件來迫使國民黨拒絕和談的策略,既可擊破美國這一陰謀,又可保證中國革命的繼續(xù)。*斯大林相關原文如下:“因此,我們預計,國民黨將拒絕在中共提出的條件下進行和平談判。結(jié)果是,中共是同意進行和平談判,因而不能夠指責它希望繼續(xù)進行內(nèi)戰(zhàn)。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將成為阻撓進行和平談判的罪人。這樣一來,國民黨和美國所玩弄的和平花招就將被戳穿,您可以繼續(xù)進行必勝的解放戰(zhàn)爭。”〔俄〕С.Л.齊赫文斯基編,馬貴凡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1949年1月間的電報往來》,《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1期。
盡管毛澤東1月13日未看到斯大林1月11日補發(fā)的電報,但當時他對斯大林第一封電報的回電說明其已經(jīng)確認斯大林所建議的是一種“迂回策略”,并認為這一策略并不符合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有利國際局勢:
我們認為,美國、英國和法國,特別是美國,雖然非常愿意參加調(diào)停工作,進而達到保住國民黨政權(quán)的目的,但是這些國家的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在中國人民當中已經(jīng)失去威信,加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的勝利和國民黨政權(quán)的滅亡已經(jīng)指日可待,它們是否愿意繼續(xù)援助南京政府,繼續(xù)欺負人民解放軍,好像也是個問題。
只有蘇聯(lián)在中國人民當中享有極高威信,因此,如果蘇聯(lián)在對南京政府照會的答復中,采取您1月10日電報中闡述的立場,美英法就可能認為,參加調(diào)解工作是應該的,國民黨就會得到侮蔑我們的借口,說我們是好戰(zhàn)分子……不過現(xiàn)在我們想據(jù)理拒絕國民黨的和平騙局,因為現(xiàn)在考慮到中國階級力量對比已經(jīng)發(fā)生根本變化,國際輿論對國民黨政府也不利,人民解放軍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進攻南京。
好像我們無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勢下,再次實行這種策略,弊多利少。*〔俄〕С.Л.齊赫文斯基編,馬貴凡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1949年1月間的電報往來》,《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1期。
上述電文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對當時國際環(huán)境的判斷與斯大林有著根本的不同,不贊成斯大林的策略。他認為在西方國家已不愿干涉中國事務的情況下,即使蘇聯(lián)只是做個姿態(tài)而表示愿意調(diào)停國共內(nèi)戰(zhàn),也將會導致西方三國趁機干涉中國革命。
毛澤東的不同意見迫使斯大林在1月14日第三次就此問題致電毛澤東,證明自己有關世界局勢的看法與相關策略是正確的。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將美國的陰謀進一步升級——美國不僅是要“幫助你們國內(nèi)外的敵人來污蔑共產(chǎn)黨和贊揚國民黨,把共產(chǎn)黨說成是主張繼續(xù)內(nèi)戰(zhàn)的好戰(zhàn)份子”,更是要尋機干涉中國革命:
這意味著您使美國有可能朝著這樣的方向改變歐美社會輿論,認為同共產(chǎn)黨媾和是不可能的,因為它不要和平。在中國實現(xiàn)和平的唯一辦法,是組織大國進行武裝干涉,就象從1918到1921年這四年間對俄國所進行的武裝干涉那樣。*〔俄〕С.Л.齊赫文斯基編,馬貴凡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1949年1月間的電報往來》,《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1期。斯大林的確一直擔心美國可能干涉中國革命,他甚至在中共要發(fā)起渡江作戰(zhàn)前夕專門致電毛澤東,強調(diào)人民解放軍要保留足夠的預備隊防止美國軍隊可能從解放軍后方登陸干涉中國革命。〔俄〕尼·特·費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著,彭卓吾譯:《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交往錄》,第169頁
斯大林提出美國是幕后黑手的判斷很快被證明是誤判——1月13日美國政府第一個向國民黨政府表示拒絕調(diào)停。盡管毛澤東1月14日公布了同國民黨進行和談的八項條件、斯大林于15日回電說中蘇雙方“問題已經(jīng)解決”、蘇聯(lián)政府也將于17日正式拒絕國民黨政府的調(diào)停請求,但斯大林卻不得不向毛澤東解釋這樣一個問題——為何他認定的幕后黑手美國政府會第一個拒絕國民黨政府的調(diào)停要求?1949年1月底,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時,就此問題指責中共方面向美國方面泄密,導致杜魯門政府了解到蘇聯(lián)對調(diào)停持否定態(tài)度而搶先拒絕了國民黨的調(diào)停。盡管這一說法遭到了毛澤東的斷然否認,但米高揚仍然堅持己見。*師哲的回憶說明蘇聯(lián)領導人是真的認為中共方面出現(xiàn)了泄密:1949年1月底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甚至懷疑中共方面會泄露其行蹤或者是中共保密工作做得很差。當時前去接他的師哲發(fā)現(xiàn),米高揚一方面要求保密,但另一方面則不斷走訪當?shù)厝罕姡蛔⒁獗C堋.攷熣芟蛩岢鲞@一點時,米高揚卻諷刺說中共方面無法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會在路透社或美聯(lián)社或其他什么通訊社的新聞消息中出現(xiàn)。”但米高揚此次秘密訪問一直未被西方覺察,為此50年代初米高揚專門就此事向師哲致歉。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372—373頁;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紅旗出版社,1992年,第41—42頁。
那么,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是否是美國政府主導的一個重大陰謀?是否存在中共向杜魯門政府泄密的可能?美國政府解密檔案證明蘇聯(lián)的看法是錯誤的。
二、杜魯門政府拒絕調(diào)停的決策過程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1月8日下午收到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吳鐵城親自提交的調(diào)停照會后,將這一照會立刻發(fā)給華盛頓,同時與英國、法國駐華大使進行了緊急磋商,以探究國民政府的真實意圖。1月9日,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了美、英、法三國大使的猜測。司徒雷登和英、法大使一致認為,由于蘇聯(lián)不太可能參加調(diào)停或即使參加也不抱善意,因此西方的調(diào)停不會對目前戰(zhàn)場上的勝利者中國共產(chǎn)黨產(chǎn)生影響。國民政府也并非真要和談,而只是借機拖延時間和挽回面子。司徒雷登言下之意很明白,是建議美國政府拒絕調(diào)停。*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以下簡寫為FRUS), 1949, Vol.8, GPO, 1978, pp.22,25.因此,如果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一事為美國指使的陰謀,則司徒雷登根本無需與英、法兩國大使進行緊急磋商。
有趣的是,1月10日司徒雷登又推翻了自己前一天有關蘇聯(lián)不太可能參加調(diào)停的猜測,反而向華盛頓提出了一個猜測——蘇聯(lián)政府極有可能是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一事的慫恿者。司徒雷登認為,當前只有蘇聯(lián)能對目前占據(jù)優(yōu)勢的中共產(chǎn)生影響,因此唯有蘇聯(lián)表示愿意進行調(diào)停,國民政府才會向四大國提出調(diào)停請求。司徒雷登還提請美國國務院注意這一點:國民黨政府的調(diào)停照會并未要求四大國進行“聯(lián)合調(diào)停”,因此非常有可能國民政府已經(jīng)與蘇聯(lián)達成了由后者進行單獨調(diào)停的某種默契。為此,司徒雷登建議國務院指令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立刻假借聯(lián)合調(diào)停的名義接觸蘇聯(lián)外交部,以探聽蘇聯(lián)對美、蘇、英、法四大國聯(lián)合調(diào)停的反應,并以聯(lián)合調(diào)停之名阻止蘇聯(lián)進行單獨調(diào)停,來避免因其單獨調(diào)停成功而獲得和平調(diào)解者的聲望。*FRUS, 1949, Vol.8, p.26.很明顯,無論是司徒雷登認為國民黨調(diào)停照會是蘇聯(lián)幕后操作的看法,還是建議美國政府為破壞蘇聯(lián)可能進行的單獨調(diào)停而向蘇聯(lián)提出聯(lián)合調(diào)停,都說明國民政府提出照會一事與美國無關。*臺灣學者注意到司徒雷登懷疑蘇聯(lián)可能進行單獨調(diào)停這一點,但未做深入研究,參見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243-244。
而華盛頓的相關決策過程也說明美國政府并未策劃國民黨政府的調(diào)停請求。在接到司徒雷登1月8日來電兩天后的1月10日,杜魯門政府決定拒絕調(diào)停。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喬治·凱南(George Kenan)從現(xiàn)實主義出發(fā),認為西方國家雖然應當進行調(diào)停,但他們的調(diào)停根本不會得到目前取得優(yōu)勢的中共的重視和同意,因此美國應當拒絕調(diào)停。負責中國及其周邊地區(qū)的遠東事務司司長威廉·沃爾頓·巴特沃斯(William Walton Butterworth)也基于此時美國正在進行的全球冷戰(zhàn)戰(zhàn)略的考慮而建議拒絕調(diào)停。巴特沃斯認為美國如進行調(diào)停則會產(chǎn)生下列負面影響:首先,美國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不利于美國此時的全球冷戰(zhàn)戰(zhàn)略。因為美國如進行調(diào)停,就要負責組建一個有中共參加的中國聯(lián)合政府,這會在已將本國共產(chǎn)黨人排除在聯(lián)合政府之外的法國、意大利、日本和遠東各地引起不利的反彈,也會影響此時正在進行的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和西方聯(lián)盟(Western Union),還會在美國國內(nèi)引起不利的反響。其次,國民黨政府的調(diào)停要求只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失敗尋找替罪羊,美國介入只會重蹈馬歇爾調(diào)停的覆轍。再次,在調(diào)停問題上蘇聯(lián)掌握了主動權(quán),但蘇聯(lián)不太可能與西方三國一起行動。巴特沃斯雖然不排除司徒雷登猜測的蘇聯(lián)單獨調(diào)停的可能性,但他在權(quán)衡利弊后建議美國政府拒絕調(diào)停,并正好借此機會澄清馬歇爾調(diào)停的歷史,與國民黨政權(quán)的失敗撇清關系。*FRUS, 1949, Vol.8, pp.26-29.
由于巴特沃斯和凱南意見一致,因此巴特沃斯擬定了一份美國拒絕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的答復草稿。這份草稿經(jīng)凱南修改后于當天上午呈給總統(tǒng)杜魯門,后者略作刪減后批準了這一草案。同時,1月11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的NSC 34/1號文件明確了美國政府當前對華基本政策是避免卷入中國內(nèi)戰(zhàn)。在了解到英國完全拒絕調(diào)停、態(tài)度稍顯曖昧的法國也愿意與美國一致行動后,美國政府于12日向司徒雷登發(fā)出了拒絕調(diào)停的答復聲明,后者又于13日晚正式遞交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吳鐵城。*FRUS, 1949, Vol.8, pp.29-30,41,47—48;FRUS, 1949, Vol.9, p.475.
實際上,國民政府也對美國進行調(diào)停不抱希望。由于美國政府一直未向國民政府表明其態(tài)度,為此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專門于1月13日約見美國代理國務卿羅伯特·A.洛維特(Robert A.Lovett)并詢問美國政府的立場。顧維鈞的表現(xiàn)說明國民黨政府已經(jīng)預料到美國不會進行調(diào)停——當洛維特答復說美國政府正在考慮這一問題后,顧維鈞特意詢問洛維特,美國如不能調(diào)停,是否可發(fā)表聲明說美國政府真誠希望和平解決等?但這一要求被洛維特當場駁回。*FRUS, 1949, Vol.8, pp.44-45.而司徒雷登在遞交美國政府正式答復時,也觀察到國民政府外長和副外長對美國的拒絕已有相當?shù)男睦頊蕚洹獌扇说姆磻歉械绞⒉灰馔?FRUS, 1949, Vol.8, pp.47-48.。與此類似,蔣介石在聽聞這一消息后也做出了“此在意料之中”的評價*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78卷,(臺灣)國史館,2013年,第500頁。。
杜魯門政府上述決策過程不僅表明美國不是國民政府調(diào)停照會一事的幕后主使,而且證明了米高揚提出的、后來為列多夫斯基所堅持的中共向美國“泄密”這一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首先,杜魯門政府上述決策過程表明其不僅未從中共方面得到任何信息,而且考慮的重點是美國冷戰(zhàn)戰(zhàn)略的進行,與國民黨撇清關系。其次,杜魯門政府的迅速決策過程說明中共領導人也不可能向美國方面泄密。美國領導人做出拒絕調(diào)停決定的1月10日,斯大林才從莫斯科向毛澤東發(fā)出了有關此事的、內(nèi)容頗為簡略模糊的第一封電報,第二天又發(fā)出了對自己意圖進行明確解釋的第二封電報,此后斯大林與毛澤東經(jīng)過交換意見,到14日才出現(xiàn)“問題已經(jīng)解決”的局面。中共根本無法將14日蘇方才確定的“拒絕調(diào)停”決定在1月10日美國政府正式?jīng)Q定拒絕調(diào)停之前就泄漏給美國人!
而列多夫斯基在其研究中列舉的一些支持所謂“泄密說”的證據(jù)也難以成立。為說明調(diào)停一事為美國牽頭的陰謀,列多夫斯基以時任蘇聯(lián)駐南京大使館一秘的歷史當事人身份提到有關美、英、法三國故意提出聯(lián)合調(diào)停以刺探蘇聯(lián)態(tài)度。但列多夫斯基的這種說法被美國解密檔案所證偽。美國政府解密檔案表明,杜魯門政府為防蘇聯(lián)人偵知美國政府在此事上的態(tài)度,從一開始就拒絕了司徒雷登曾建議的讓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刺探蘇聯(lián)外交部對聯(lián)合調(diào)停的反應,反而訓令美國在華和在蘇外交人員避免與蘇聯(lián)人接觸。同時,美國政府還向英、法兩國再三強調(diào)就拒絕調(diào)停一事要向蘇聯(lián)保密。*法國因為出于維護其在印度支那殖民統(tǒng)治的需要而對進行調(diào)停抱有一絲期望,曾于1月11日想要接觸蘇聯(lián)外交部未果。FRUS, 1949, Vol.8, pp.36,40-42.雖然法國態(tài)度略有搖擺,但英國拒絕調(diào)停的態(tài)度十分堅決,并未與蘇聯(lián)人有接觸。因此列多夫斯基的“刺探”一說至少與美、英兩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不符。特別有問題的是列多夫斯基對《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中相關重要檔案的處理態(tài)度。列多夫斯基為了證明米高揚提出的“西方大國是在明確知道有關我們態(tài)度的確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絕進行調(diào)停的”這一說法,特別援引了此份文件集中收錄的1月9日司徒雷登猜測蘇聯(lián)不可能調(diào)停國共內(nèi)戰(zhàn)的第一封電報。但此份電報并不能證明司徒雷登得出此判斷是因為中共“泄密”,因為1月9日蘇聯(lián)大使館才正式接受南京政府照會,而中共更是遲至1月10日由斯大林的電報才得知此事。同時列多夫斯基還罔顧在《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中與1月9日電報僅一頁之隔的1月10日司徒雷登第二份相關電報。在這封電報中司徒雷登本人已經(jīng)推翻前論,認為蘇聯(lián)極有可能與國民政府達成某種默契、意欲進行單獨調(diào)停,這更證偽了美國反對調(diào)停是因為中共“泄密”的說法。*〔俄〕安·列多夫斯基著、李玉貞譯:《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秘密談判(1949年1—2月)》(下),《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三、杜魯門政府眼中莫斯科的奇怪反應
既然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一事并不是如斯大林所說的是美國政府策劃的陰謀,那么毛澤東認為蘇聯(lián)有意單獨調(diào)停、而且司徒雷登也猜測國民黨調(diào)停照會與蘇聯(lián)有關的這兩個不約而同的看法是否成立?美國解密檔案中也有非常重要的相關信息。
杜魯門政府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政府最為奇怪的行為是,相比美、英、法三國駐華大使都于1月8日接受了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無論是蘇聯(lián)駐華大使還是蘇聯(lián)外交部卻都于1月8日同時回避接受這一照會。在莫斯科,中華民國駐蘇聯(lián)大使傅秉常受命向蘇聯(lián)外交部提出請?zhí)K聯(lián)進行單獨調(diào)停的口頭請求,但一直被拒見,直到1月12日才得以向莫洛托夫提出這一請求。*FRUS, 1949, Vol.8, p.85.在南京,因為蘇聯(lián)大使羅申故意稱病不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吳鐵城直到1月9日才向其提交了調(diào)停照會*羅申甚至也以生病為借口,未出席約定好的當晚與美、英、法三國駐華大使的會晤。參見〔俄〕安·列多夫斯基著,李玉貞譯:《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秘密談判(1949年1—2月)》(下),《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中華民國史事日志》也記述了蘇聯(lián)大使缺席1月8日國民政府遞交調(diào)停照會的會:“外交部長吳鐵城邀晤美英法三使,商請斡旋和平。并正式照會美蘇英法四使,征詢對于中國和平意見,是否準備協(xié)助。”參見FRUS, 1949, Vol.8, p.43;斯大林在1月10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也稱蘇聯(lián)大使是在1月9日接到的國民政府調(diào)停照會。參見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四冊: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三十八年(1938—1949)》,(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823頁。。按照時任蘇聯(lián)大使館一秘的列多夫斯基的說法,羅申之所以在1月8日避而不見,是因為他一直到2月初都得不到莫斯科的指示。但列多夫斯基的這一回憶和蘇聯(lián)外交部的表現(xiàn)恰恰說明,不同于被蒙在鼓里的美、英、法三國政府,蘇聯(lián)外交部和駐華大使館很有可能已知道國民政府將會在1月8日提出調(diào)停照會。這反過來說明國民政府極有可能已經(jīng)就調(diào)停一事接觸過蘇聯(lián)大使或蘇聯(lián)外交部,當然后者的反應也表明蘇聯(lián)對此立場仍不明確,否則羅申和莫洛托夫不會采取“躲”的方式對待國民政府的調(diào)停照會。
而此后美國駐南京和莫斯科大使館陸續(xù)向杜魯門政府報告了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和蘇聯(lián)政府一系列頗為怪異的行為。1月13日司徒雷登再次向華盛頓報告了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的奇怪表現(xiàn):1月12日,法國大使曾就中國調(diào)停要求一事咨詢羅申,但羅申未進行表態(tài)*FRUS, 1949, Vol.8, p.43.。司徒雷登隨后還發(fā)現(xiàn),甚至請求在蘇聯(lián)政府1月17日公開拒絕了國民政府調(diào)停請求之后,羅申還與1月21日上臺的李宗仁就調(diào)停問題進行接觸。*1月23日司徒雷登就甘介侯與蘇聯(lián)大使、美國大使的相關接洽給美國國務院發(fā)去一封電報,說李宗仁已經(jīng)與羅申就簽訂一項中國保持中立的條約達成了草案。參見FRUS, 1949, Vol.8, p.78.司徒雷登這一電報在《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中被公布出來后,8月23日甘介侯專門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了一封公開信,對此事進行了詳細說明。甘介侯說李宗仁的確曾想接觸羅申,討論中國與蘇聯(lián)簽訂一項在未來國際沖突中保持中立的條約,以換取蘇聯(lián)對中共施壓、在國共和談中做出讓步。不過羅申抬高價碼、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盡最大可能在中國排除美國的影響、與蘇聯(lián)建立實質(zhì)性的合作關系,但羅申并未完全拒絕甘介侯的這一提議。按照甘介侯的說法,直到數(shù)日后蘇聯(lián)大使才采取了徹底敵對的態(tài)度。不過甘介侯并未否認曾與羅申秘密接觸。參見FRUS, 1949, Vol.9.The Far East: China, GPO, 1978, pp.1401-1403.
與此同時,美國駐蘇聯(lián)大使館參贊福伊·D.科勒(Foy D.Kohler)也發(fā)現(xiàn)莫斯科在中國內(nèi)戰(zhàn)和調(diào)停問題上有許多頗值得注意的表現(xiàn),并為此推翻了自己于1月12日提出的蘇聯(lián)不會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的初步判定*在1月12日就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照會一事發(fā)給美國國務院的分析電報中,科勒認為“大使館并不預計蘇聯(lián)會對中國的調(diào)停要求作出有利的答復”。參見FRUS, 1949, Vol.8, p.38.,轉(zhuǎn)而認為蘇聯(lián)政府不僅確有可能事先與國民黨政府有所接觸,而且未嘗沒有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的打算。1月20日科勒向國務卿馬歇爾匯報了莫斯科一些很值得關注的行為。首先,在各種流言和新聞報道流行了幾個星期后,蘇聯(lián)官方通訊社塔斯社正式于1月2日否認了國民黨政府曾接近蘇聯(lián)或蘇聯(lián)正在考慮調(diào)停中國沖突的流言。但此后不久的1月8日國民黨政府卻在南京向四國提交了調(diào)停照會。*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四冊: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三十八年(1938—1949)》,第823頁。其次,雖然毛澤東在1月14日宣布了國共和談八項條件,但莫斯科直到1月19日才公布了中共提出的條件。再次,法國駐莫斯科大使于1月11日就提出與蘇聯(lián)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商談國民黨調(diào)停照會一事,但直到1月18日維辛斯基才接見法國大使,并聲稱直到前一天深夜蘇聯(lián)領導人才決定拒絕調(diào)停,但事實是前一天下午維辛斯基就已將蘇聯(lián)的答復交給了中國駐莫斯科大使。*FRUS, 1949, Vol.8, p.60.科勒還從傅秉常那里得知,后者曾于1月12日向莫洛托夫當面表達了國民政府希望蘇聯(lián)進行單獨調(diào)停的愿望,但莫洛托夫既未表示拒絕,也未表示同意*FRUS, 1949, Vol.8, p.85.。
對蘇聯(lián)政府這些看起來頗為怪異的行為,科勒做出了如下猜測:
我們認為中國局勢的快速發(fā)展超出了蘇聯(lián)政策范圍,并迫使克里姆林宮——很可能是在征詢了中共意見后——對其當前有關中國沖突的政策進行迅速的反思和決策。雖然去年蘇聯(lián)——特別是蘇聯(lián)駐南京大使羅申——向南京暗示希望進行調(diào)停,這可能是煙霧彈,但更可能是克里姆林宮錯估了中共的軍事能力和國民黨政府的弱點,并相信當時政治解決(中國局勢)是有利的。但中共軍隊奪取沈陽并取得矚目的勝利,加上毛澤東針對國民黨政府公開發(fā)表了不讓步態(tài)度,這必定令克里姆林宮要重新進行思考……本大使館認為,無論是蘇聯(lián)方面想要就國民黨政府調(diào)停要求進行決策,還是毛擔心蘇聯(lián)會贊同國民黨政府這一提議,雙方領導人可能已經(jīng)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議來決定和協(xié)調(diào)政策。*FRUS, 1949, Vol.8, p.60.
科勒上述判斷頗為精準,中蘇兩黨領袖的確就此問題展開了最高級別的協(xié)調(diào),只不過雙方是通過電報的方式來進行溝通。此后科勒又發(fā)現(xiàn)了證明自己這一判斷的新證據(jù)。2月初蘇聯(lián)兩份重要報紙《文學報》和《新時代》終于刊登了有關中國局勢的評論文章——這是幾個月來蘇聯(lián)媒體第一次對中國局勢發(fā)表看法。由于這兩份評論文章無論是在主題上還是在用詞上都與中共刊發(fā)的文章保持一致,科勒判定到1949年2月初,蘇聯(lián)領導人才終于確定了其有關中國局勢的政策路線——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此時克里姆林宮已經(jīng)與中共建立起了牢固的聯(lián)盟關系。*FRUS, 1949, Vol.8, p.105.
其他相關材料都佐證了科勒對蘇聯(lián)政府直到1949年2月初才最終明確了其對中國的政策這一看法是相當準確的。正在莫斯科采訪、十分關心中國局勢的美國左翼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也發(fā)現(xiàn),“當時在莫斯科的外國記者和外國外交人士,都對自1948年秋天以來蘇聯(lián)報紙一直對中共取得的勝利閉口不談這一點感到十分疑惑”,直到1949年1月下旬,“蘇聯(lián)報紙打破了長期以來對中共勝利的沉默,對于中國內(nèi)戰(zhàn),發(fā)表了長篇社論,而中共的勝利這時已經(jīng)繼續(xù)了三個多月了”。而一位蘇共老干部就此事對斯特朗的解釋與科勒的判斷幾乎完全相同:“我想是由于我們對中國形勢的分析,正在高級領導層中重新審議,所以在此期間,報紙保持沉默。”*參見〔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陳裕年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俄國人1949年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與中國的關系》,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第29、31頁。自1月下旬與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秘密接觸的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后來也承認,羅申一開始仍與其保持接觸并且態(tài)度曖昧,但在數(shù)日后突然采取了徹底敵對的態(tài)度*FRUS, 1949, Vol.9, pp.1401-1403.。列多夫斯基也承認,大約在2月初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才接到莫斯科有關調(diào)停一事的明確指示。此后羅申態(tài)度不再曖昧,于2月20日和21日兩次明確拒絕了國民黨政權(quán)的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與代總統(tǒng)李宗仁提出的希望蘇聯(lián)能介入國共和談的請求。作為進一步佐證的是,斯大林在再三拒絕毛澤東訪問蘇聯(lián)以討論中蘇兩黨合作問題之后,終于于1月底派出了蘇共代表、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明確表示要與中共展開密切合作,并就一系列具體合作問題展開了討論。*沈志華:《求之不易的會面: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的試探與溝通》,《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最新公布的蘇聯(lián)政府檔案證明了毛澤東和司徒雷登的看法恰恰更貼近事實。1月12日,國民政府駐蘇聯(lián)大使傅秉常根據(jù)行政院長孫科和外交部代理部長在此問題上的指示,向蘇聯(lián)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提交若干重要事項的秘密通報。其中第三項就是“上述4個國家(美、英、法、蘇)政府為恢復中國和平所作的真誠援助不一定采取共同行動的形式。如果蘇聯(lián)政府愿意單獨在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和談問題上做出友善的幫助的話,中國政府將不勝感激。”*《莫洛托夫與傅秉常會談紀要》(1949年1月1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1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351頁。而此前南京政府已經(jīng)充分考慮了蘇聯(lián)方面的可能態(tài)度——1月4日蔣介石在與行政院院長孫科討論邀請四大國調(diào)停內(nèi)戰(zhàn)時,曾特別強調(diào):“應研究蘇俄與共匪之政策有無和平誠意,以及此事之利害究竟如何?方可決定也。”*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第78卷,第374—75頁。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南京政府之所以在1月8日就試圖向蘇聯(lián)提交單獨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的照會,應當是與蘇聯(lián)有所接觸,而蘇聯(lián)的態(tài)度至少是沒有明確拒絕。
總而言之,上述來自中國、美國和蘇聯(lián)的多方資料表明,由于當時中國內(nèi)戰(zhàn)局勢尚不明朗和擔心美國對中國革命進行軍事干涉,蘇聯(lián)曾對中國內(nèi)戰(zhàn)的態(tài)度較為曖昧,并在單獨調(diào)停國共內(nèi)戰(zhàn)這一問題上應該事先與南京政府有所接觸并達成了某種默契。只是因為毛澤東的堅決反對和中國內(nèi)戰(zhàn)趨勢的快速明朗化,斯大林才最終確定了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實現(xiàn)全國勝利的基本對華政策和拒絕國民黨調(diào)停要求的立場。
四、結(jié) 論
既然美國政府解密檔案說明了杜魯門政府并不是國民黨政府提出調(diào)停請求的幕后推手、中共也未向其“泄密”,那么從毛澤東與斯大林圍繞此事展開的爭論來看,毛澤東當時對與中國內(nèi)戰(zhàn)有關的國際局勢的認識比斯大林的認識準確得多。而美國的相關文件和后來事實發(fā)展更說明,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策略中存在著一些致命的漏洞是頗有道理的。首先,毛澤東在1月13日電報中就指出,蘇聯(lián)政府若表態(tài)愿意調(diào)停,則極易為西方大國提供干涉口實。而司徒雷登為破壞蘇聯(lián)單獨調(diào)停,的確于1月10日建議美國政府向蘇聯(lián)提出四大國聯(lián)合調(diào)停,而法國當時也一直對蘇聯(lián)進行調(diào)停抱有一定幻想并試圖就此與蘇聯(lián)溝通。其次,毛澤東在1月14日回電中委婉批評斯大林擬定的進行重開國共和談兩項前提——不準美國調(diào)停和不準國民黨戰(zhàn)犯參加——不足以阻止國民黨回到談判桌前,這一點也被后來的歷史事實所證明。蔣介石下臺后李宗仁政府甚至初步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更為全面和嚴苛的八項和談條件。
基于上述事實,筆者以為,毛澤東未事先通知蘇聯(lián)領導人就于1月14日發(fā)表《關于時局的聲明》一文并公布了國共和談八項條件這一舉動,與其說是毛澤東全盤接受了斯大林的策略,不如說是毛澤東堅持自己策略為主、輔之以斯大林策略中優(yōu)點的表現(xiàn)。毛澤東通過中共單方面搶先發(fā)布要求國民黨直接與中共交涉的聲明,徹底杜絕了蘇聯(lián)發(fā)表原擬定答復而對解放戰(zhàn)爭產(chǎn)生的不利影響(當然也堵上了西方國家調(diào)停中國內(nèi)戰(zhàn)的借口),同時也補上了斯大林建議的僅包括拒絕美國調(diào)停和禁止戰(zhàn)犯參加和談這兩項而可能令中共陷于被動的漏洞,更接過了“和平的旗幟”*〔俄〕С.Л.齊赫文斯基編,馬貴凡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1949年1月間的電報往來》,《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第1期。。毛澤東的這一單方面舉動實際上是否決了蘇聯(lián)的提議,所以斯大林在1月15日回電中才不得不說兩黨之間在此問題上的分歧已經(jīng)解決。
從以上兩點重新審視周恩來與毛澤東1955年、1957年有關“過長江”“南北朝”的談話,筆者以為他們的說法是相當客觀的。兩位中國領導人都不是指斯大林主觀上要在中國建立“南北朝”而不讓解放軍“過長江”,而強調(diào)的是斯大林由于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擔心人民解放軍渡江之后極有可能引起美國的干涉,為此建議人民解放軍不“過長江”。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為,如果當時中國領導人盲目接受斯大林的建議,客觀上反而會出現(xiàn)“南北朝”。*王方名:《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親切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1月2日;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3頁。簡言之,毛澤東與周恩來認為斯大林的主觀動機并非想要阻礙中國革命,只是因為其誤判了形勢,所以其所提出的策略在客觀影響上不利于中國革命。而周恩來提到的此時蘇聯(lián)對華政策仍然搖擺、“我們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國的看法當時同蘇聯(lián)是有分歧的”這一判斷,甚至得到了當時杜魯門政府對蘇聯(lián)政府觀察的佐證,也為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所公認。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及其根源有著極其清醒的認識,但中共領導
人對蘇聯(lián)領導人的動機仍然進行了非常善意的理解。周恩來認為在當時冷戰(zhàn)已經(jīng)興起,在國共內(nèi)戰(zhàn)中的三大戰(zhàn)役尚未徹底結(jié)束的背景下,“斯大林總的出發(fā)點是要從戰(zhàn)略上穩(wěn)住美國,贏得和平建設時期”,而“中共打贏了,蘇聯(lián)背靠新中國還是高興的”。學術(shù)界也公認在這次爭論中,斯大林以較為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都事先征求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可以說正是因為這種較為平等的地位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中蘇兩黨最終較為妥善地處理了這一事件。就此而言,中國學者過去認為毛澤東、周恩來的說法證明了蘇聯(lián)故意干涉中國革命的各種看法是對毛澤東、周恩來的原意有所曲解,但俄國學者僅以蘇聯(lián)檔案為基礎、無視蘇聯(lián)領導人認識與策略上的錯誤的看法也略為偏頗。當然,要對這一問題本身及其國內(nèi)外歷史背景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仍需要以多邊相關歷史資料為基礎,以更為全面、客觀的態(tài)度來加以審視。
(本文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兼職教授 上海;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廣州 510630)
(責任編輯 張 政)
On the Mediation for the KMT-CPC Civil War in January 1949 on the Basis of the U.S.Decoded Archives
Yao Yu
After January 8, 1949, the KMT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mediation note to the four countrie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two parties, Mao Zedong and Stalin launched an important and delicate negotiation on the issue. The negotiation leads to a lasting debate about Stalin’s attitude on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academic. On the basis of the U.S. government decoded archives, and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ussian and Chinese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on this issue, and tries to explain that Stalin had some problems, whether in the situation understanding or strategy setting, but Mao Zedong was more effective in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y, and later his evaluation was quit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on the issue.
K266;D822.3
A
1003-3815(2016)-07-0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