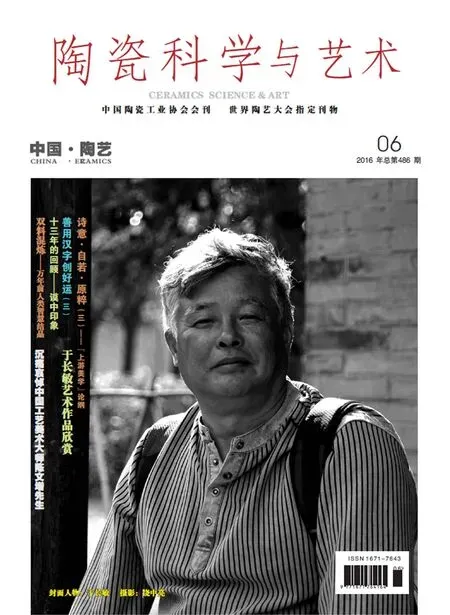詩意·自若·原粹(三)
——“上游美學”論綱
沈 奇
詩意·自若·原粹(三)
——“上游美學”論綱
沈 奇
“要上游美學”一說,系在筆者多年的美學思考基礎上,經由對包括西部詩歌在內的現代漢詩研究和西部美術理論研究與當代書畫研究,逐步引發梳理出的一個新的學術理念。這期間,還帶著這一理念,同美術評論家程征、張渝一起,共同策劃并出任學術主持,為陜西美術博物館連續成功舉辦五屆“高原·高原——中國西部美術展”,也為“上游美學”的理論思路增加了新的考量。
上游美學;詩意;自若;原粹
原 粹
“自若”是精神層面的“原粹”——保持清晨出發時的清純氣息,那一種未有名目而只存愛意與詩意的志氣滿滿、興致勃勃,從而得以“脫勢”而“就道”,“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尼采語)
當代學術產業化、藝術市場化后,一切學問,一眾文學藝術家,總難免剛剛開始種莊稼,就已經盤算著收益的多少,遂將古人前人的“見賢思齊”轉換為“見先思齊”,爭著當下之“出位”,難得“修遠”以沉著,話語盛宴的背后,是情懷的缺失、價值的虛位和主體精神的無所適從,以致成為當代學術語境和藝術語境的“暗疾”而不治。
實際上,由“宣傳”而“市場”,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下的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尤其是美術創作,大都由“自得”而轉為“經營”了——本來是藝術家之主體精神與藝術語言、藝術文本之間的“自我對話”(此為藝術創作的原初推動力),現在變成了藝術家攜帶“預謀”與“心機”,而生發的一種與“市場之神”、與“展覽之主”之間的對話,所謂“他者”性的對話。
如此傷神妨意之心理機制壓迫下,豈能有真情實意為存在寫真、為歷史樹碑、為靈魂存照、為丹青寫精神?
實則,一切學術成就和藝術成就的背后,必有其相應的學術精神和藝術精神作支撐;一切學術精神和藝術精神的背后,也必有其學術人格和藝術人格作支撐。今日為學問為藝術者,真要想脫出“形勢”、潛沉于“道”、以求卓然獨成,無非三點:立誠,篤靜,自若。亦即守志不移,靜心不變,定于內而淡于外,于朝市之繁囂中立定腳跟,“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而得大自在——身處今天的時代,讓藝術氣息和藝術語言亦即人本與文本都能回歸單純、回歸自得,不但已成為一種理想,甚至更是一種考驗:平庸或超凡,端看是否過得了這一關。
這是“上游美學”的精神源頭。
還有語言層面的“原粹”,即找回“本該如是”的“基點”;先弄清楚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再說我們到哪里去的問題。
以唯現代為是的斷裂方式,和唯新(以及“革命”)是問的運動態勢,持續百年的“新文化”、“新文學”、“新美術”之后,在世界地緣文化格局中,作為中國文化指紋之所在的詩、書、畫及其他文學藝術,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西學不如“洋人”,中學不如“古人”,“枉道以從勢”(孟子),唯“勢”昌焉,而“原道”隱遁;當年跨擁兩條長河“嘗試”(胡適)與“吶喊”(魯迅)的“新”,如今大體上只剩下西方現代化一條河流邊的徘徊,以及“不斷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糾結與焦慮,或許還有莫名的“郁悶”中那一縷“藕斷絲連”的“鄉愁”……
這樣的一種客觀認知,大概不會有多少異議。
而我們知道:一個時代之詩與思的歸旨與功用,不在于其能量即“勢”的大小,而在于其方向即“道”的通合。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一直過于信任和單純依賴主導百年的“現代漢語”之“編碼程序”,及由此導致的漢語詩性三度“降解”之弊端——
借用西方句法、語法、文法改造而“來”(“拿來”“舶來”)的現代漢語,比之以字詞思維為主的古典漢語,其“詩意運思”之本源屬性,先就降解了一層(當然,其“理性運思”的屬性也隨之上升了一層);
沈 奇,詩人,文藝評論家,西安財經學院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美術博物館學術委員。著有《沈奇詩選》《沈奇詩學論集》(三卷)及文藝評論集《文本與肉身》《秋日之書》等14種, 編選《西方詩論精華》《現代小詩300首》等9種,部分學術論文及詩歌作品被翻譯為英、美、德、瑞典、丹麥、日本及拉脫維亞等文字。
再用這樣降解后的現代漢語,去翻譯西方的經典之原典 / 元典,并且到后來還得翻譯漢語自身的古代經典之原典 / 元典,其“原典”“原道”的“原汁原味”及“原義” / “原意”,難免又降解一次(語義還原的難度之外,更有語境還原的更大難度)。
再拿這經由兩次降解后的“思想啟蒙”之思與詩,來言說現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生命體驗與生活體驗,其結果,只能導致第三次降解。
誠然,百年來我們一直在鼓吹要中西兼顧之“兩源潛沉”,但終歸抵不過現代漢語的“三度降解”而致兩源皆隔。即或因自信所失而急功近利唯西方一源為是,其實打根上也從來就沒有可能真正“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因為你一直就無法真確明晰地認知到,原本的“藍”到底為何!
于是只能是西學不如“洋人”,中學不如“古人”——如此兩源無著,后來者更只有隨波逐流而“與時俱進”的份了。
事實上,所謂“新詩”,所謂“新美術”,所謂“當代藝術”,以及等等,百年革故鼎新,一路走來,無一不面臨或“洋門出洋腔”的被動與尷尬,或既不“民族”也不“世界”而“兩邊不靠”的身份危機。是以可想而知,越到后來,尤其當代,即或真有些許個在的“創新”,也大多屬于模仿性的創新或創新性的模仿,難得真正原創而獨成格局。這樣說不是要重新回到古典的之乎者也,而是說要有所來之處的古典素養作“底背”,才能“現代漢語”出不失漢語基因與風采的漢語之現代。
作為另一個常識,我們也知道:古往今來古今中外的所謂大師,無一不是立于傳統的基礎而又能保持自由呼吸的人,而絕非只活在當下者。
由此顯而易見的是,一個造山運動般的大時代也隨之結束了——告別“革命之重”,我們無可選擇地“被”進入到“自由之輕”和“平面化游走”的困惑境地而無所適從;不是自由的行走——腳下有路,心中有數,有來路,也有去路,而是碎片化的自由漂流——無來路,也無去路,只是當下感應,即時消費。正如作家韓少功所指出的:我們的文化正在進入一個“無深度”、“無高度”、“無核心”及“沒有方向”感的“扁平時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并在一種空前的文化消費語境中,在獲得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的情況下,反而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3】
語言的“先天不足”,精神的“后天不良”,百年急劇“現代化”的“與時俱進”,驅使我們終于走到這樣一個“關口”——如何以現代中國學人和文學藝術家的眼光,去尋找傳統文化中的“原粹”基因,并在現代生存體驗、現代生命體驗和現代語言體驗的轉換中,尋求與詩性漢語和詩意中華之“原粹”基因既可化約又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故,“夢回大唐”也好,回溯“漢唐精神”也好,以及“新儒學”、“新古典”等等諸如此類的時興倡導,其立足點,其歸旨處,都該當是要汲古潤今、借古證今而以利未來的。
這里所謂“汲古潤今”的“潤”,是要汲取傳統精粹中的詩性生命意識,來作為當下物質時代的精神植被,以潤國魂;這里所謂“借古證今”的“證”,是要借體現在諸如“漢唐雄風”以及“魏晉風骨”中超凡脫俗的主體精神,來對質當下的追名逐利蠅營狗茍,以證(正)人格。
如此,方能由“枉道以從勢”返身“大道”“原道”,而正脈有承!
同時,這樣的“正脈有承”,落實于每一個個體,尤其是活躍于當代話語場中的各種什么“家”們時,有一個需要再三提醒的心理機制要點,即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藝術(一切的“詩”與“思”)的存在,并非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自我,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禮遇”自我——從自身出發,從血液的呼喚和真實的人格出發,超越社會設置的虛假身份和虛假游戲,從外部的人回到生命內在的奇跡,平靜下來,做孤寂而又沉著的人,堅守且不斷深入,承擔的勇氣,承受的意志,守住愛心,守住超脫,守住純正,以及……從容的啟示。
而作為“物質暗夜”(海德格爾語)中的“腳前燈”,在一個意義匱乏和信仰危機的時代里,真正的學問,真正的文學藝術,更要有重新擔當起對意義和信仰的深度追問與叩尋的責任:包括對歷史的深度反思,對現實的深度審視,對未來的深度探尋等,并以此重建生命理想和信仰維度,也并以此重返“詩意”、“自若”、“原粹”的“上游”之境。
結語:所謂“上游美學”
“水,總是在水流的上游活著。”(詩人麥城詩語)
作為漢語“詩”與“思”的“上游”之所在,一是已然典律化的、歷時性的、可重新認領的“上游”,如上文所提及之“漢唐精神”等;二是潛隱于當下的、共時性的、需重新探究的“上游”——此即“上游美學”之新理念的出發點。
“上游”——生命的初稿,青春與夢想出發的地方——初戀的真誠,諾言的鄭重,純粹、清澈、磊落、獨立、自由、虔敬……還有健康,尤其是心理的健康,只有健康的“詩”者與“思”者,才得以“自若”,才得以“原粹”粲然而凈空生輝,也才足以在沉入歷史的深處時,仍能發出自信而優雅的微笑。
從“上游”出發的“詩”與“思”,是回返本質所在的選擇:既是源于生活與生命的創造,又是生活與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
回溯“上游”的“詩”者與“思”者,只是僅僅樂意為“詩”與“思”而活著,絕不希求由此而“活”出些別的什么。
亦即,真正的“上游”之“詩”與“思”,不僅是對生命存在的一種特殊言說,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種特殊儀式——
遠離喧囂浮夸和妄自尊大的時代主潮,遠離閉門造車式的昏熱想象和唯功利是問的刻意造作,以及對西方現代化的投影與復制;消解功利性,消解娛樂化,消解平庸化,并重新學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生活中一切卑微而單純的事物,將所謂雄強進取之勢轉而為恬淡自適的生命形式,深沉靜默地與天地精神共往來,不再有身外的牽絆,只在生命詩意與筆墨寄寓的和諧專純,而樂于咫尺之間一臂之內揮灑個在的心聲。
回溯“上游”,再回望“下游”,自會發現那是怎樣的一種不堪——
無中心,也無邊界;無所不至的話語狂歡,幾乎蕩平了當下生命體驗與生存體驗的每一片土地,造成整個詩性藝術背景的枯竭和詩性藝術視野的困乏。看似新人輩出,且大都出手不凡,卻總是難免類的平均化的化約;好作品不少,甚至普遍的好,卻又總覺得帶著一點平庸的好——且熱鬧,且繁榮,且自我狂歡并彌漫著近似表演的氣息,乃至與其所處的時代不謀而合,從而再次將個人話語與民間話語重新納入體制化(話語體制)了的共識性語境。
而我們知道:個人的公共化只能導致個人的消失。
其根源在于:與自然的背離,與自我的背離,與自由的背離。這是所謂“現代化崛起”的必然結果。
但社會不是統一的,且分裂的各個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發展模式。丹尼爾·貝爾便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明確指出,“現代社會”分成三個服從于不同軸心原則的“特殊領域”:經濟與技術體系、政治體系、文化體系。經濟與技術領域“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其中含義是進步”。而文化領域則不同,它無所謂“進步”,卻“始終有一種回躍,不斷回到人類生存痛苦的老問題上去”。所以社會呈現出“經濟與文化復合體系”,且經濟和文化并“沒有相互鎖合的必要”。因此,對于經濟與技術一味的“現代化”進步要求,文化總會適時地“回躍”。【4】
由此導引出“上游美學”的“回躍”功能——
在失去季節的日子里,創化另一種季節;
在失去自然的時代里,創化另一種自然;
在解密后的現代喧囂中,找回古歌中的天地之心;
在游戲化的語言狂歡中,找回儀式化的詩意之光。
再由此找回:我們在所謂的成熟中,走失了的某些東西;我們在急劇的現代化中,丟失了的某些東西;我們在物質時代的擠壓中,流失了的某些東西——執意地“找回”,并“不合時宜”地奉送給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去等待時間而非時代的認領。
原生態的生存體驗,原發性的生命體驗,原創性的語言體驗——這是“上游美學”的核心理念;
內化現代,外師古典,融會中西,重構傳統——這是“上游美學”的基本理路。
至此,兩脈“上游”匯合為一,其共同的氣質與風骨便是本文關鍵詞之“詩意”與“自若”,并最終歸旨于本文另一關鍵詞之“原粹”——原粹粲然,元一自豐,而原道復歸——由此,在溯流而上的生命“初稿”中,在作為最初的旅行者的足跡中,找回復生的詩意,和“還鄉”的可能。
[1] 張志揚:《偶在論譜系》,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頁;
[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廣西師范大學2007年版,“三版自序”文頁;
[3] 韓少功:《扁平時代的寫作》,《文藝報》2010年1月20日版;
[4]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三聯書店1989版,第56-60頁;
文思路,基本本上由四個關鍵詞展開:正題中的“詩意”、“自若”、“原粹”,副題中的“上游美學”,互為關聯,構成一個“家族譜系”,相互闡釋與認證后,有關“上游美學”的理念,大體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