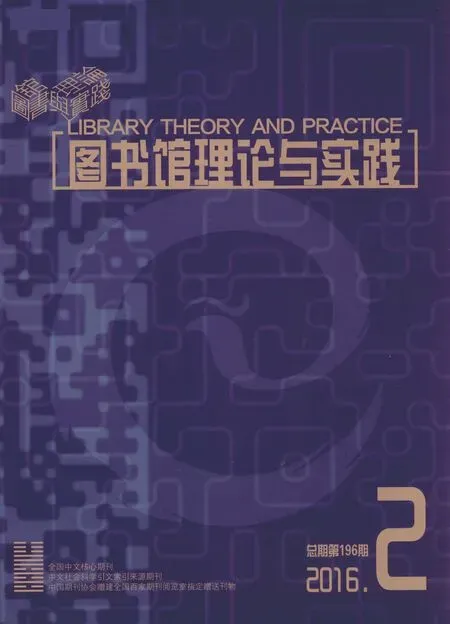試論新出“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借鑒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討論
楊 博(1.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2.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
?
試論新出“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借鑒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討論
楊博1,2
(1.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2.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
摘要:新出楚竹書“語”類文獻,既為文獻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領(lǐng)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又由于其本身主題、人物、事件等重見疊出的現(xiàn)象需要進行考辨的工作。作為一種獨特的史書體類,“語”類文獻是當(dāng)時流傳的存故實、寓勸誡和助游談的材料。一方面以作史素材被成文史書如《左傳》等所吸收,另一方面以助游談的材料為諸子書所吸納。近年來盛行的史料批判研究,可以作為考量“語”類文獻史學(xué)價值的一個重要準(zhǔn)則。通過探求“語”類文獻的構(gòu)造與執(zhí)筆意圖,對于去除附著于其上的“再回憶”與“再創(chuàng)造”等因素的影響有積極的作用。通過上述討論,可以將“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簡要歸納為對先秦文獻史料“真”“偽”的審慎認知、對春秋戰(zhàn)國史學(xué)著述的發(fā)展具體了解、對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面貌的整體把握及對其記述的先秦史事的批判認識等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
關(guān)鍵詞:“語”類;史料批判;戰(zhàn)國楚簡;史學(xué)價值
《國語·楚語上》記載春秋中期楚莊王問傅太子之道時,大夫申叔時列出了“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xùn)典”等九種所要“教之”的文獻。一般認為,“語”書作為一種文獻分類在春秋時期即已廣泛存在,傳世文獻中《國語》《新序》《說苑》等均屬此類體裁。以《國語》為例,《漢志》將其與《左傳》并列收入“春秋家”,劉知幾將其列為“六家”之一,“語”書作為一種重要的史學(xué)體裁已極顯明。1973年,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證明了“語”在春秋時期的客觀存在。近年來,以上博楚簡為代表的新出文獻中也發(fā)現(xiàn)有大量“語”類文獻,“語”類也由此深為學(xué)界所重視。如李零先生指出:“春秋戰(zhàn)國時期,語類或事語類的古書非常流行,數(shù)量也很大。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種,這是當(dāng)時作史的基本素材。”[1]
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種,這與歷史學(xué)求真求實的本質(zhì)必然存在矛盾。與之相應(yīng),學(xué)界歷來有史料考辨的傳統(tǒng),如劉知幾曾將史料分為“當(dāng)時之簡”與“后來之筆”。1984年,王玉哲先生主要以時間為序?qū)⒅袊瞎攀返氖妨戏譃樗拇箢悺#?]具體針對新出文獻而言,陳偉先生亦曾指出其存在時間上的差異。[3]史料的分類,時間是第一要素,而且這種強調(diào)形成時間的分類,存在按史料性質(zhì)排隊,條理清楚且簡明扼要的優(yōu)點,使我們可以很輕易地通過史料的性質(zhì)、形成年代判斷史料的價值,對于我們今天的工作仍具有指導(dǎo)價值。但同時需要留意的是,強調(diào)形成時間的分類似并不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種”的史料考辨問題。這似需要引入或借鑒新的理論模式來幫助我們推進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
史料批判研究又稱“史料論式的研究”,是近年來在魏晉南北朝史學(xué)界青年研究者中比較盛行的一種研究范式。其定義是“以特定的史書、文獻,特別是正史的整體為對象,探求其構(gòu)造、性格、執(zhí)筆意圖,并以此為起點試圖進行史料的再解釋和歷史圖像的再構(gòu)筑”。[4]如孫正軍先生所總結(jié),與傳統(tǒng)史料處理方式相比,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滿足于確保史料真實可靠,而是在此基礎(chǔ)上繼續(xù)追問:史料是怎樣形成的?史家為什么要這樣書寫?史料的性質(zhì)又是什么?[5]筆者以為上述思路似可為我們探討新出“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提供借鑒和幫助。
一、戰(zhàn)國時期“語”類文獻的內(nèi)涵
在討論“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之前,需要先對戰(zhàn)國時期流傳的“語”類文獻的內(nèi)涵以及與相關(guān)文獻的區(qū)別等問題作一簡單說明。
河北平山戰(zhàn)國中山國墓地中出土有中山王鼎(《集成》02840),其銘文在文首言曰:
“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銘曰:嗚呼,語不廢哉,寡人聞之,與其溺于人旃,寧溺于淵。昔者……”其后即用三個“昔者”指出了三件過去的史實和教訓(xùn),分別是中山國王年幼繼位事,燕王禪位于子之事以及越克吳事。其中又用“寡人聞之”另引用一句格言:“事少如長,事愚如智。”所謂“語不廢哉”的“語”,不僅僅是指銘文所引用的“寡人”所聞的兩句格言,而且還應(yīng)該包括“昔者”所發(fā)生的三件事情。整篇銘文,就是節(jié)錄“語”的內(nèi)容來進行說理。這樣的“語”,既有格言的內(nèi)容,也有史事的內(nèi)容,不僅可看出當(dāng)時“語”類文獻的流行,亦可看出“語”類文獻所包含的特質(zhì)。
《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的言論,有“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wù)用明德于民也”的說法,韋昭注:“語”為“治國之善語”。《左傳》文公六年有“著之話言”,孔穎達疏曰:“著之話言,為作善言遺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guī)誨,士傳言,庶人謗。”《國語·周語》亦有“庶人傳語”的說法。《禮記·曲禮上》還有“史載筆,士載言”的記載。無論是“古之王者著之話言”的“善言遺戒”還是“矇誦”“庶人傳語”“士傳言”“士載言”,經(jīng)過上下兩個渠道的采擇,這些“治國之善語”都可能通過“著于竹帛”而流傳下來。一方面保存了反映當(dāng)時社會面貌的珍貴資料,另一方面成為時人以至后人常用以勸誡的材料。
“語”與“言”“傳”“說”等同樣表示話語的詞匯,先秦時期都有可能視作記述歷史故事或傳聞的文本,或是格言匯編。但是就細微處,“言”“語”之間也存在著區(qū)別,不免有所混淆。特別是戰(zhàn)國后期以后,“傳”“說”都被用作解“經(jīng)”的文體,納入經(jīng)學(xué)體系,其區(qū)別就更為顯著。
《說文·言部》:“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可見不同于“言”,“語”具有議論的特點。《詩·大雅·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直接的訴說是“言”,相互論辯就是“語”,這種理解與《說文》完全相同。孔穎達正義:“‘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指出“言”“語”存在著說話者人數(shù)上的不同。《禮記·雜記》有:“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鄭玄注:“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孔穎達正義:“謂大夫、士言而后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為人語說也。”居喪之時可以“言”卻不能“語”,顯示出在表達上“言”“語”存在著主動和被動的差別。《左傳》莊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學(xué)者即曾指出:“主動說話叫作‘言’,與人相對答才是‘語’。”[6]此外,《國語·魯語下》記載:“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yīng)。”“與之言”清楚地指明是季康子單方面的主動說話。可見,“語”和“言”的差別是存在的。當(dāng)然,這種區(qū)別也并非絕對。
“傳”“說”也可被視作述古講史的一種文體,如《墨子·非命中》載:“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
此處的“于傳有之”可見這種敘述傳聞故事的文體也可稱為“傳”。同樣的例子還見于《墨子·明鬼下》: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速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此處“說”明顯指這個傳聞故事。《史記·五帝本紀》亦有:“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這里的“傳”、“說”、“語”皆可視作是記述歷史故事或傳聞的文本,或是格言匯編。但是,可以看出,“傳”與“說”更多的是與諸子經(jīng)傳聯(lián)系在一起的。“傳”“說”雖然都是解釋“經(jīng)”的文類,二者也存在區(qū)別:“說”“傳”處在學(xué)術(shù)傳授的不同層次中,“傳”是對“六藝”經(jīng)義直接作的闡釋,而“說”是為解釋“傳”或諸子理論而產(chǎn)生的“師說”。[7]“說”“傳”的區(qū)別可簡單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在形式上,“說”與“經(jīng)”是分開的。如《韓非子·外儲說》這種標(biāo)準(zhǔn)的“說”,經(jīng)的部分和“說”的部分是分開的,“說”更像是為闡發(fā)義理的“經(jīng)”而準(zhǔn)備的資料庫,《說林》之“林”,《說苑》之“苑”的命名,或正有這種含義。而“傳”則是與“經(jīng)”文合在一起的,《史通·補注》:“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亦猶《春秋》之傳,配經(jīng)而行也。”《漢書·五行志》顏師古注:“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如《韓詩外傳》即先言故事或闡述義理,而后引出與此段“傳”義理相通的《詩》句。
第二,就《漢志》來言,“六藝”均有“傳”,而非皆有“說”。此外,以《六藝略》為例,其敘述一經(jīng)的各種文獻順序是:經(jīng)→故→傳→(記、說、章句)。由此“說”在《漢志》存錄等級中的地位要低于“傳”,同于“記”與“章句”。在這個序列中,“說”可以敷衍“傳”,而“傳”卻不能解釋“說”。對此《漢書·五行志》在解釋《尚書·洪范》中亦提到的“五行”時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經(jīng)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jié),奪民農(nóng)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是為木不曲直。”
明了“語”與“言”“傳”“說”等同樣表示話語的詞匯的區(qū)別以外,還需要討論“語”與“書”“子”等文獻的區(qū)別。“語”與“書”可分別以《國語》和《尚書》為例。白壽彝先生曾指出,《國語》是以記言為主的書,所記的言多是賢士大夫的讜言高論,跟《尚書》記言之限于官文書有嚴格的區(qū)別。[8]而從《尚書》與《國語》之間“言”“語”的細微差別來理解:《尚書》之“言”大多是君王對臣下所發(fā)布的言論,具有不容置疑的權(quán)威性,這些言辭基本是獨白,話語的指向也是單向性的,在這個層面上王者的“主動”說話,正與左史記“言”“言為《尚書》”的記載是相吻合的。《國語》之“語”更多的是對當(dāng)政者的一種委婉警告,“語”采用對話的形式,記錄了大量辯論性的內(nèi)容。“語”者借助各種論據(jù),使用多種論證方法,希冀與執(zhí)政者成功溝通,使之接受自己的意見。《尚書》所記的言語局限在帝王或是重要大臣的范圍之內(nèi),聽眾是臣民;《論語》除了孔子的教誨外,只有少數(shù)賢弟子的言語,“語”的直接對象多是門下弟子。《國語》記載的言語不能是演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語”者社會地位降低決定的。[9]
接下來需要討論“語”“子”的區(qū)別。不得不承認,“語”類文獻本身有相當(dāng)多的一部分即是由諸子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也是“語”類文獻需要鑒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此而言,“諸子百家語”的說法是有其道理的。但是站在史料考辨的角度,以記述先秦史事為主的“語”和專在表達諸子政治思想的“子”書還是存在一定的差別。當(dāng)然,“語”書同樣可以表達政治思想,“諸子”也或被稱為“諸子百家語”,但是二者之間在外在表現(xiàn)形式和性質(zhì)上的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
首先,“子”類文獻的表現(xiàn)形式多為師徒問答,或君王諸子問對,而“語”類文獻在表現(xiàn)形式上與諸子無關(guān)。當(dāng)然,“語”類文獻也會表達某些諸子政治思想,即“語”類文獻不是以諸子如孔子等人的事跡展開的。其次,“語”類文獻多為敘述性語言,旨在通過講述一件或數(shù)件史事來說明一定道理,而“子”類文獻全文多是議論之辭。第三,李零先生曾就子類文獻的“述”古指出,“這些諸子書,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談話背景。”諸子書的談資除了借用“世”“書”外,李零先生認為主要來自“語”類作品,儒家喜歡講唐虞三代故事,墨家喜歡講夏禹故事,道家喜歡講黃帝故事,來源就是這類傳說。[1]就此意義上講,“語”類文獻相當(dāng)于一個資料庫,所以經(jīng)常為諸子所取材。這也就是諸子百家之書也可稱“語”的主要原因。
因此,對于“語”類文獻有很多互見于諸子文章的現(xiàn)象:它們或是同源材料,或是由更古之語類材料被諸子鍛煉改造,后又被從諸子著作中抽離出來的。語類文獻的這個流傳模式為:語類材料→熔鑄入諸子文章→從諸子文章中抽離(新的語類材料)。從這個層面講,諸子書中存留的故事也可為我們所取作為史料以探討其研究史實的價值。但需要留意,諸子書記錄的人與事,可能與事實拉開了一段距離,其故事性要遠勝于記錄性,是一種再回憶與再創(chuàng)造。在這樣的書中,回溯的事實取代了真正的事實。所以也可以說,在“語”類為諸子提供這樣一個交流背景的同時,諸子也以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不斷豐富著“語”的內(nèi)容。
綜上述,“語”是戰(zhàn)國時流傳的存故實、寓勸誡和助游談的材料。除諺語外,其最顯著之特征即在于“故事”性。這里的“故事”性有兩重含義:其一,是指每個篇章都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故事,基本是由故事背景+故事經(jīng)過+故事結(jié)果組成,如上博竹書《昭王毀室》,開篇“昭王為室”為故事背景,“一君子喪服……”為經(jīng)過,結(jié)果是“因命至(致)俑毀室”。
其二,也有部分篇章會引用過去明君圣王的典型事例,甚至開篇即言明其講古的性質(zhì),如清華竹書《赤鳩之集湯之屋》開篇云“曰故……”或在篇中顯示這一點,如上博竹書《容成氏》講“昔堯處于丹府與藋陵之間……”等。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正如“書”類文獻在先秦文獻中曾多次被征引作為論據(jù)的情況近似,“語”類是作史、論說的基本素材之一。如清華簡《系年》第九章記有晉襄公卒后,靈公時年少,晉人欲立長君公子雍,“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將置此子也?’”。與之相應(yīng),《左傳》文公七年曰: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其內(nèi)容不僅與《系年》互為印證,史料取材當(dāng)也以“語”為主。這些可以較明確斷定為“語”類文獻在史書中的應(yīng)用的情況,似也可以作為“語”類文獻的衍生加以討論。
二、史料批判研究的價值
如上所述史料批判研究的模式對于同樣史料奇缺、且舊說成熟的先秦史研究領(lǐng)域亦有一定的適用性。如在明確戰(zhàn)國時期“語”類文獻所包含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需要重點強調(diào)的是新出“語”類文獻及其衍生所提出的對史料考辨的新要求。上文已述“語”類的特質(zhì)是同一人物、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種。筆者將其推廣為與新出“語”類有關(guān)涉的史事記載,存在同一主題、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等重復(fù)情況,且這些情況之間還存在不小的差異。這就需要考慮“語”類史書單篇與整體的撰述背景、意圖等方面的因素。下文擬從主題、事件、人物的重復(fù)等三方面舉例說明其價值。
其一,是同一主題的重復(fù),如上博簡《魯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以及《競公瘧》等篇的共同主題,則是由于疾病、旱魃等神罰,或日食等異象的降臨,然后藉由國君的反省,“為善政”即可解除或規(guī)避災(zāi)殃。[10]而且《魯邦大旱》中“哀公問孔子”的“母題”,由《繹史·孔子類記一·哀公問》可知其材料分布于《論語》《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史記》《孔叢子》《孔子家語》《說苑》《新序》等多種典籍之中。
其二,是同一事件的重復(fù),如上博竹書《競建內(nèi)之》追述殷武丁祭祀時,有雉雊于彝前,商王召祖己詢問緣由。祖己對以先代賢君面對失政而采取求諸鬼神與修善政的措施,如今若要借祭祀求福,則需要烹煮此雉,祭祀完畢后修先王之法。高宗從之,其結(jié)果是“服者七百邦”。此事與《尚書·高宗肜日》篇相似,均是祖己針對商王祭祀時發(fā)生的異事進行評論,故有學(xué)者認為簡文是編纂者在理解《高宗肜日》基礎(chǔ)上所作的發(fā)揮。[11]就《高宗肜日》所記內(nèi)容看,其基本反映了殷代的史實,惟此篇文字如“天”“德”等是周初誥命中的習(xí)慣用語,可知此篇成書時代當(dāng)不早于周初,應(yīng)系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商書”中所記之史實。[12]亦曾有學(xué)者推知《競建內(nèi)之》與《管子》中《霸形》《戒》兩篇內(nèi)容相似,只是所涉人物與事件背景有很大差別。[13]清華竹書中亦有“語”類《赤鳩之集湯之屋》篇,講述有鳥“赤鳩”落在商湯的屋頂上,被商湯射獲。后來商湯有要事外出,臨行前囑咐小臣伊尹將這只“赤鳩”烹煮作羹的故事。
其三,是同一人物的重復(fù),清華竹書《赤鳩之集湯之屋》《湯處于湯丘》《湯在啻門》均涉及湯相伊尹(小臣),加上《尹至》《尹誥》,清華竹書中目前已發(fā)表5篇與伊尹相關(guān)之文獻。此外,上博竹書《容成氏》中對伊尹的事跡也有反映。[14]《漢書·藝文志》“道家”下有“《伊尹》,五十一篇”。班固自注:“伊尹,湯相。”現(xiàn)已佚失不存。學(xué)者亦曾注意到戰(zhàn)國文獻中存在伊尹學(xué)派之問題,[15]如李零先生指出戰(zhàn)國時期有依托商周故事講“陰謀”的一派,《漢志》將其列入道家,它以《太公》為代表作,《伊尹》等是同類著作,《鬼谷子》是其余緒。銀雀山漢簡、八角廊漢簡中發(fā)現(xiàn)的《六韜》,其實部分應(yīng)屬于《伊尹·九主》。[1]《湯處于湯丘》簡文有“以設(shè)九事之人,以長奉社稷”之語,或與《伊尹·九主》“事分在職臣”有關(guān)。[16]楚竹書中伊尹故事的重復(fù)出現(xiàn),說明了對某一典型人物的重復(fù)記述是戰(zhàn)國史學(xué)的一個鮮明特點。
按三者的區(qū)別,同一主題的重復(fù)指的是隨著說話者的需要,雖將故事敘述的模式進行了變化(如將旱災(zāi)的發(fā)生地變?yōu)橛恤敗⒂谐瞧鋽⑹龅闹黝}仍是一致的(“為善政”即可解除或規(guī)避災(zāi)殃)。同一事件的重復(fù)則指的是同一故事被處在不同時代與出于不同論說目的的說話者所不斷征引(如商人祭祀時有雉雊于彝前)。而同一人物的重復(fù)則是古史典型人物在多種歷史記述中不斷重復(fù)的現(xiàn)象。
從這些重復(fù)的情況看,一部分記述大致相同,其余很大的一部分則存在歧異。對于存在歧異的內(nèi)容,僅按照時間要素對其進行史料層面的考辨,似不能很好地分辨出具體的差異。而史料批判研究于此則顯現(xiàn)出一定的優(yōu)勢。特別是其對史傳書寫模式的討論,關(guān)注史傳中那些高度類型化、程式化的文本構(gòu)筑元素。[5]筆者推而廣之,似可將其理解為歷史敘述中的套語、典型人物事跡和著名事例的重復(fù)等多方面因素。惟需要在求真求實的基礎(chǔ)上對這些或本諸現(xiàn)實、或由史家新造的因素進行具體細致的分析。學(xué)者曾經(jīng)討論清華簡《芮良夫毖》中含有大于55%的套語成分,反映作者創(chuàng)作時多處都是拿固定的語句或結(jié)構(gòu)來套用。[17]后者有關(guān)人物事跡、著名事例等方面的認識,對于目前只能認定成文年代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語”類文獻的考辨,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辦法。對于這些文獻中所反映的史實及其與傳世記載的差異問題,學(xué)者也作了大量的研究,注意到簡文與傳世文獻敘事的差異,既和體例有關(guān),也和簡文的寫作意圖有關(guān),揭示出“語”類古書意之所在不是記史,而是說理,勸導(dǎo)讀者接受篇中講述的道理,以資鑒戒。語書“有時言辭之首,或書史以交待其背景。言辭之末,或附史事以為之征驗,皆無非是增加其說理的效果而已”。[18]盡管至戰(zhàn)國時,語書亦雜采事件,但仍保留著語書的特征。雖然如此,語書中的記事仍然是為記言服務(wù)的。[19]
所以,對于這些差異恐怕還需要從編纂過程、用途來理解,而不能直接據(jù)之以反對傳世文獻對某些史事的記載。筆者上文引述申叔時論傅太子之道時有所謂“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wù)用明德于民也”一項,以上博簡楚國故事來看,如《鄭子家喪》為楚莊王沒有在鄭子家弒君當(dāng)年就發(fā)兵討鄭尋找理由、《昭王毀室》之贊揚昭王德政、《申公臣靈王》的表彰楚靈王的政治風(fēng)度等,都會作為彰顯“先王之明德”的材料為貴族子弟所學(xué)習(xí),正是申叔時所論的題中之義,其反映的史事似未必一定會是真正史實,先君先王的美好形象確是當(dāng)時年輕子弟學(xué)習(xí)的典范。
三、“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
上文以“同時代”“類”為標(biāo)尺,將“語”類文獻從新出文獻中析分出來,而對于“語”類文獻本身,則需要具體借鑒史料批判研究中對史傳書寫模式的認識進行單篇、幾篇甚至整體的具體考辨。在上述討論的基礎(chǔ)上,似可對新出“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作一簡單的歸納總結(jié)。
第一,對先秦文獻史料“真”“偽”的審慎認知。大量“語”類文獻在主題、人物、事件上的重復(fù)現(xiàn)象,自明郎瑛起即對“秦漢書多同”這一現(xiàn)象加以注意,其后章學(xué)誠的“言公”、余嘉錫的《古書通例》及裘錫圭先生《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等相關(guān)論述,“使我們知道,我國古代大多數(shù)典籍是很難以‘真’‘偽’二字來判斷的。”[20]“語”類文獻的重復(fù)性印證了這一判斷。這就為先秦史料的考辨工作提供了審慎的前提。
第二,于春秋戰(zhàn)國史學(xué)著述的發(fā)展。一方面,新出“語”類文獻多單篇流行,同時亦有意識整理、蒐集同類文獻。如上博簡“語”類文獻,多數(shù)單篇別行以外,也有《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等兩篇合抄的現(xiàn)象。特別是郭店簡《語叢》(一)至(四)更是體現(xiàn)出時人有意識地整理同類文獻的過程。而學(xué)者針對簡背劃線的研究,指出清華簡《赤鳩之集湯之屋》當(dāng)接于《尹至》《尹誥》之前,三篇竹書原編于同卷。[21]其原因當(dāng)是時人將同屬伊尹故事的文獻匯集整理在一起。另一方面,上舉上博簡《競建內(nèi)之》追述殷武丁祭祀時,有雉雊于彝前,商王召祖己詢問緣由等事。上即可與《尚書·高宗肜日》篇相關(guān)聯(lián),下則可與《管子·霸形》《戒》相聯(lián)系,為我們提供了“語”類自“書”類取材繼而最為資料庫被“子”類涵化運用的實例。此外,上舉清華簡《系年》第九章、第十四章中與《左傳》《國語》在“語”上的相似性,則可看出“語”書作為基本素材為史書所取用的情況。凡此對于我們了解春秋戰(zhàn)國史學(xué)著述的發(fā)展情況提供了極大幫助。
第三,對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的整體把握。一方面,上揭“秦漢書多同”的情況反映的是在為天下統(tǒng)一構(gòu)畫藍圖的一致政治目標(biāo)下,諸子雖各抒己見,但由于關(guān)涉目標(biāo)相同,則不可避免會出現(xiàn)言語、思想上的雷同。“語”為“子”中的這些雷同提供了材料支撐。這些雷同的出現(xiàn),促使人們在思考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諸問題時,不得不從整個思想領(lǐng)域的問題整合考慮。學(xué)者已注意到對于先秦思想的研究似需要從一個整體來綜合考察。如劉澤華先生早年在針對先秦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曾提出注重“共識”的研究手法,[22]即“注意那些共同的資源、共同的話題,不拘泥、糾纏于學(xué)派具體的判定區(qū)分,將研究對象本身作更為細化的分析”。以色列學(xué)者尤銳(Yuri Pines)在研究戰(zhàn)國時期思想動態(tài)時,關(guān)注的就是戰(zhàn)國思想家的共同遺產(chǎn),強調(diào)的是戰(zhàn)國思想家共同關(guān)注和普遍認識的理念,從而界定出當(dāng)時諸子等人共同關(guān)注的話語范疇,并在此基礎(chǔ)上建構(gòu)戰(zhàn)國時期思想變遷的模式。[23]
第四,對其記述的先秦史事的批判認識。文獻的本身即反映出文獻流傳、整理等情況,文獻的應(yīng)用也會直接呈現(xiàn)當(dāng)時的學(xué)術(shù)思想狀況,這兩點可以通過文獻本身“類”的因素來加以析辨。而對于文獻中所記述的先秦史事,則需要通過時間——“同時代”和史料批判的方法加以綜合考量。特別是成文年代并不能很明顯地拉開時間距離的“語”類文獻,史料批判倒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辦法。
通過上述準(zhǔn)則,“語”類文獻于先秦史事研究的價值,應(yīng)該說首先體現(xiàn)在使人們進一步認識了后世文獻(也包括部分當(dāng)時文獻)對于典型人物、事跡所進行的加工與再創(chuàng)造。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語”類史料雖不排除有偽托的可能,但是其史事當(dāng)有所本,應(yīng)該依托于一定史跡,故其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價值也相對較高,不能一概否定。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其故事的敘述主干應(yīng)該是真實可靠的,所謂的“加工與再創(chuàng)造”,筆者更多的以為其體現(xiàn)在一些具體細節(jié)的處理上。再以《容成氏》為例,其所記古史圣王事跡與先秦歷史密切相關(guān),禹、桀,湯、紂,文、武的世系清晰可靠。此外,其敘事主干,如湯伐桀,武伐紂也沒有大的問題。就一些細節(jié)問題來說,則既有事實又有所演繹,如著名的紂為酒池事,普見于《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新序》《論衡》《韓詩外傳》《史記》等眾多的古籍記述,但戰(zhàn)國文獻多見“酒池”之名,并沒有細節(jié)方面的記述。《尚書·酒誥》:“在今后嗣王……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02837)銘文有:“我聞殷墜命,惟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喪師矣。”“酒池”之說應(yīng)有商末殷人酗酒的史實依據(jù),但明顯帶有演繹色彩。故子貢評價道:“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綜上述,借助有利的抓手,新出“語”類文獻于先秦史學(xué)的研究價值得以具體展現(xiàn),特別是通過史料批判研究,將史家新造的因素有效地從典型事例上剝離,從而盡可能地逼近歷史的真實面貌。
四、小結(jié)
按《國語·楚語上》記載“語”類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本身已獨自成類,這一點也日益得到了新出文獻的證明。作為一種獨特的史書體類,“語”書是當(dāng)時流傳的存故實、寓勸誡和助游談的材料,一方面,作為作史素材為成文史書。如《左傳》等所吸收,另一方面,作為寓勸誡、助游談的材料為諸子書所吸納。其與“言”“傳”“說”等同樣表示話語的詞匯存在區(qū)別以外,與“書”“子”等文獻也有較為明顯的不同。時間是史料分類的第一要素,所以“同時代”的史料為治先秦史者所重視,而對于成文年代并不能很明顯地拉開時間距離的“語”類文獻,史料批判研究中對史傳書寫模式的討論值得借鑒。通過對“語”類文獻所體現(xiàn)的再回憶與再創(chuàng)造的辨析,相當(dāng)?shù)挠浭銎绠惪梢缘玫綀A融的解讀。通過“類”“同時代”及史傳書寫模式三把抓手,“語”類史料可以對我們在史料學(xué)、史學(xué)史、學(xué)術(shù)思想史及先秦史事等眾多研究領(lǐng)域起到補史、證史的重要作用。
通過史料批判模式可以深入挖掘“語”類文獻的史學(xué)價值,也提醒我們一些新的理論、新的方法對于其他“類”的新出文獻的適用性,如敘事學(xué)中敘事角度、方式對“史”書記載的影響。如清華簡《系年》有關(guān)攜王史事的記載似屬于此種范疇。
[參考文獻]
[1]李零.簡帛古書與學(xué)術(shù)源流(修訂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297,221, 327-328.
[2]王玉哲.漫談學(xué)習(xí)中國上古史[J].歷史教學(xué),1984(2):2-8.
[3]陳偉.試說簡牘文獻的年代梯次[C]//李宗焜.第四屆國際漢學(xué)會議論文集——出土材料與新視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493-500.
[4](日)佐川英治,等.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動向[C]//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xué)者聯(lián)誼會會刊(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8.
[5]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C].“首屆古史新銳南開論壇”論文.天津,2014.
[6]陸宗達,王寧.訓(xùn)詁與訓(xùn)詁學(xué)[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255-259.
[7]徐建委.說苑研究——以戰(zhàn)國秦漢之間的文獻累計與學(xué)術(shù)史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71-74.
[8]白壽彝.戰(zhàn)國秦漢間的私人著述·國語[C]//中國史學(xué)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30.
[9]李佳.國語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系,2009:132.
[10]楊博.論史料解讀的差異性——由楚竹書災(zāi)異文獻中的旱災(zāi)母題入手[J].煙臺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5(1):80-87.
[11]李偉泰.《競建內(nèi)之》與《尚書》說之互證[M]//周鳳五.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fā)展與轉(zhuǎn)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1-16.
[12]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1032-1033.
[13]劉信芳.竹書《鮑叔牙》與《管子》對比研究的幾個問題[J].管子研究,2006(7):32-38.
[14]于凱.上博楚簡《容成氏》疏劄九則[M]//朱淵清,廖名春.上博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研究續(xù)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384-386.
[15]夏大兆,黃德寬.關(guān)于清華簡《尹至》《尹誥》的形成和性質(zhì)——從伊尹傳說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流變考察[J].文史,2014(3):213-239.
[16]清華大學(xué)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xué)藏戰(zhàn)國竹簡(伍)[M].上海:中西書局,2013:134.
[17]陳鵬宇.清華簡《芮良夫毖》套語成分分析[J].深圳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4 (2):62-70.
[18]張以仁.從《國語》與《左傳》本質(zhì)上的差異試論后人對《國語》的批評[M]//春秋史論集.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1:109.
[19]傅剛.略說先秦的語體與語書[J].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3(5):1-7.
[20]李學(xué)勤.對古書的反思[M]//簡帛佚籍與學(xué)術(shù)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32.
[21]肖蕓曉.試論清華竹書伊尹三篇的關(guān)聯(lián)[M]//簡帛(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71-476.
[22]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23]尤銳.展望永恒帝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M].孫英剛譯,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10.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Value of New“Yu”Literature
Yang Bo
Abstract:New“Yu”literature, as a new vitality to the scarce study of Pre-qinhistory, needs testification for lots of duplicated theme, characters, events, etc.“Yu”is a special kind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which was a reference for not only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Zuozhuan”but also some other materials.The popularity of criticism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riteria for historical value of new“Yu”literature and the value could be summarized from 4 aspects: prudent cogni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Pre-qin history, comprehensionofdevelopmentof historicalmaterial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overall understand ofacademic atmosphere and realization of criticism of Pre-qinmaterials.
Keywords:“Yu”Literature; Critic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huzhushu; Historical Value
[收稿日期]2015-03-25[責(zé)任編輯]李金甌
[作者簡介]楊博(1986-),男,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出土文獻與先秦史。
中圖分類號:G256.22
文獻標(biāo)志碼:E
文章編號:1005-8214(2016)02-0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