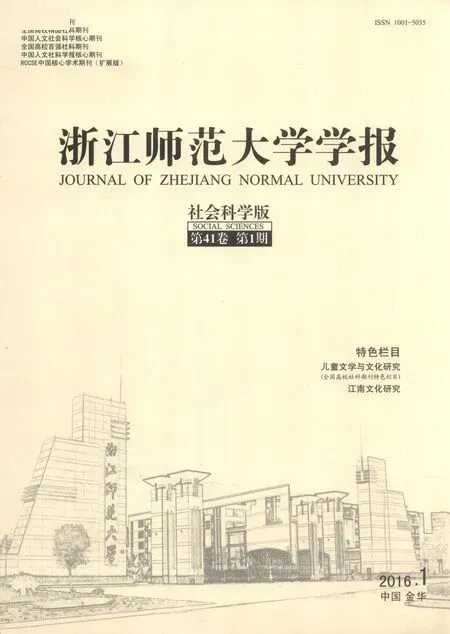從《至愛》探析莫里森筆下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
龐好農
(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200444)
?
從《至愛》探析莫里森筆下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
龐好農
(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200444)
摘要:莫里森在《至愛》里采用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從懸念設置、荒誕手法、意識流式蒙太奇三個方面把美國后奴隸制時代的黑人生存空間描寫得荒誕古怪、人鬼難辨,抨擊了奴隸制的反人類性。她以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和顛倒蒙太奇的方式把人物的意識流片段嵌入小說情節的發展之中,促成了時空與場景的不斷變換,消解了平鋪直敘的乏味感。莫里森把超現實主義的形式和內容高度和諧地統一起來,極大地促使黑人文學藝術中美學意識的升華。
關鍵詞:托尼·莫里森;《至愛》;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
美國作家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1931—)的《至愛》( Beloved,1987)以美國內戰結束后不久的俄亥俄州為背景,描寫了逃亡黑奴的心理創傷和奴隸制的反人類性。該小說是莫里森受了一個黑奴母親殺女事件的啟發而寫成的。[1]這部小說于1988年獲得普利策小說獎,十年后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著名黑人演員和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 Oprah Winfrey)主演。2006年《紐約時報》把該書列為近25年來的最佳美國小說之一。[2]莫里森在《至愛》里用豐富的文學想象和藝術夸張,對現實生活進行“特殊表現”,把現實變成一種“神奇現實”;小說里充滿離奇怪誕的情節和人物,帶有濃烈的神話色彩和象征意味,把神奇、怪誕的人物和情節,以及各種超自然的現象插入到反映現實的敘事和描寫中,既有離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現實主義的情節和場面,幻覺和現實相混,從而創造出一種魔幻和現實融為一體、“魔幻”而不失其真實的敘事風格。因此,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探討莫里森在《至愛》里所采用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懸念設置、荒誕建構和意識流式蒙太奇。
一、懸念設置
懸念是《至愛》里常見的一種敘事策略,其重要特征就是莫里森在小說中有預謀地設置一些能引起讀者強烈關注的人物或事件,但又不立即把這些人物或事件敘述清楚。也就是說,莫里森不把它們預敘出來,使其呈明顯的懸而未決的狀態,讓謎底在此后的某個情節里揭曉。因此,這些懸念有助于激活讀者的求知欲,引起讀者緊張、焦慮與期待的心緒。[3]莫里森在《至愛》中設置的懸念主要可以分為三類:剝筍式懸念、言辭懸念和數字懸念。
剝筍式懸念指的是懸念的謎底不是一下子揭穿,而是作者一步一步地揭曉謎底,引導讀者愛不釋手地讀下去,把預先設置的魔幻感或迷惘之處一點一點地清除,最后獲得一種豁然開朗的頓悟。[4]莫里森在《至愛》里描寫得最好的剝筍式懸念是“哈雷”( Halle)的身份之謎。在該小說的第7頁,莫里森描寫道,“所有‘甜屋’里的男人,不管是在‘哈雷’之前還是之后的,對她都帶有兄弟般的溫情舉動,因此讓人有一種不得不搔搔癢的感覺。”[5]7“哈雷”是誰?這個人名的出現引起懸念。在第11頁,讀者獲悉,“哈雷”是“甜屋”的一名男性奴隸,有幸被剛來的女奴塞絲( Sethe)選中為夫君。他的身世怎樣?這又構成下一個懸念。在第23頁,作者告訴讀者,“哈雷”是“甜屋”女奴貝比·蘇格思( Baby Suggs)的小兒子,他以一個奴隸的身份,通過周末打工的方式,掙錢購買了母親蘇格思的自由。在第25頁,塞絲回憶起了25年前與哈雷成婚的情景。在第69頁,保羅·D( Paul D)通過回憶講述了哈雷的情況:哈雷在糧倉的閣樓上目睹“教師”的兩個侄兒侮辱塞絲并強行吸走其奶水的情景。之后,哈雷神智失常,保羅最后一次見他時,只見其臉上涂滿黃油。在第94頁,作者進一步佐證道:塞絲逃跑時,哈雷沒有按時到約定地點來,之后也杳無音訊,這形成了小說的又一個懸念。[6]直到第224頁,作者才獲悉,哈雷已經被“甜屋”莊園的一名綽號為“學校教師”的監工開槍殺害了,“臉上的黃油”是“臉被打得鮮血直流”的委婉描述。此時,通過一層一層的懸念剝離,讀者得知了“哈雷”的身份和結局,從而得以一步一步消解此人身上的魔幻色彩。
莫里森還在這部小說里采用了言辭懸念的敘事策略。言辭懸念指的是小說人物所說的話語不為讀者馬上明白,經過小說情節的進一步發展之后,讀者才能破解其中的含義或寓意。在該小說的第15頁,保羅·D問塞絲( Sethe) :
“你背上是什么樹?”
“啊!”塞絲把碗放在桌上,然后伸手去拿桌子下面的面粉。
“你背上是什么樹?有什么東西長在你背上嗎?我在你背上沒看到什么東西呢。”[5]15
保羅·D所提及到的“樹”是什么樹呢?這在讀者的心中形成了一個懸念。在小說的第17頁,讀者從保羅的話語“他們總是拿牛皮鞭抽你嗎?”[5]17得知塞絲所遭受的苦難。緊接著,保羅心疼地用手撫摸塞絲的背。這時,讀者恍然大悟,原來塞絲背上的“樹”不是什么樹的圖形,而是奴隸監工用皮鞭抽打其背后留下的傷痕。在第128頁,保羅去塞絲上班的餐館,扭扭咧咧地對她說:“塞絲,你可能不會喜歡我要說的話吧。”之后,他自責道:“我不是一個男人。”在塞絲的再三追問下,他還是不愿把話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總覺得難以啟齒。最后,他說出口的話變成:“我想讓你懷上小孩,塞絲。你愿意嗎?”[5]128保羅難以啟齒的話究竟是什么呢?這就形成一個懸念。[7]直到第131頁,讀者才獲悉,保羅原來是想把自己與“至愛”私通的事告訴塞絲。塞絲是他的情人,而“至愛”又似乎是塞絲大女兒轉世而來的年輕姑娘。他也擔心,說出真相后,自己會永遠失去塞絲。在第132頁里,莫里森描寫了塞絲聽到情人保羅要她生孩子后的心理波瀾。“她一想到懷孕就恐怖不已。……上帝呀,饒恕我吧,除非不負責任,母愛就是殺人。”[5]132一般來講,母愛是人世間最真摯、最寶貴、最高尚的情感之一,為什么塞絲要把母愛視為殺人呢?這也形成了一個懸念。在小說的第200頁處,讀者發現:為了不讓奴隸主把自己的孩子重新送入奴隸制,塞絲曾經企圖把自己所有的孩子殺死,并且真的用鋸子鋸斷了大女兒“至愛”的脖子。這時,讀者才明白了塞絲內心獨白的真實含義。這些懸念先對讀者保密,然后通過使讀者大吃一驚的謎底來加強小說的魔幻效果。
數字懸念指的是小說中出現的數字具有特殊的含義,而這些數字在小說里最初出現時,讀者難以知曉其寓意。莫里森在《至愛》中設置的數字懸念出現在塞絲家的門牌號數上: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郊的藍石路124號。為什么莫里森把塞絲老宅的地址設置為124號呢?這在讀者的心中形成了一個懸念。從象征意義的角度看,把這三個數字相加,得到的總和是7,這個數字與“至愛”墳頭墓碑上“Beloved”這個單詞的字母數剛好相等。此后,塞絲的老宅成為被嬰魂纏繞的兇宅,全家人都難得安寧,最后蘇格思老奶奶也在嬰魂的煩擾中駕鶴西去;塞絲的兩個兒子不堪其擾,也離家出走。塞絲愛上以前的奴隸伙伴保羅·D,但在“至愛”轉世的那個年青女子的不斷干擾之下,難以梅開二度。[8]由此可見,“124”這個數字與“至愛”這個人物有了越來越直接的關系,“124號”不僅是現實生活中塞絲的家,而且還是嬰魂的魂魄寄寓的場所。另外,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讀者還可以找到這個懸念的另一個謎底:在“124”的數字排列中,缺少了一個“3”,而塞絲生下的四個孩子中,被她殺死的孩子是排行第3,塞絲住宅的“124”號就產生了“3”缺失的詭異氛圍。塞絲老宅門牌號的多種巧合的懸念增強了該小說的魔幻感,為小說情節進一步發展營造了超現實主義的氛圍。
由此可見,莫里森通過期望式懸念維持讀者的閱讀熱情,又通過突發式懸念造成小說情節和讀者情緒上的跌宕,從而進一步加劇沖突的張力。在尖銳的沖突和緊張的情節發展過程中,莫里森利用矛盾諸方面的各種條件和因素,使沖突和小說情節發展受到抑制或干擾,出現暫時的表面的緩和,實際上卻更加強了沖突的尖銳性和情節的緊張性,強化了讀者的期待心理。在莫里森的筆下,懸念和延宕交替進行,使讀者的閱讀欲望和好奇心得到不斷的激發和拓展。
二、荒誕建構
在文學作品中,荒誕作為丑的極端化表現形式,顛覆了讀者的理性思維和理性協調,以極端的形式打破常規,并且以非理性為主要表征,給讀者一種十分無奈、哭笑不得的心理感受。[9]莫里森在《至愛》中注重的是情境,而不是具體的人物和故事情節,其筆下的人物大多是沒有鮮明的個性特征,成為脫離了具體社會文化語境的抽象的人。“作為雜糅了悲劇、喜劇、滑稽、丑之因子的無序混合,荒誕的悲喜交融性是對固有審美形態的突破,它無法在傳統美學體系中作為一個獨立范疇與優美、悲劇、崇高、喜劇相并列,當然也不同于丑作為亞范疇對悲劇、喜劇、崇高等審美形態的參與。”[10]莫里森的荒誕描寫令人深省,有助于深化主題。為了展現美國奴隸制對美國黑人的精神創傷,莫里森采用了非理性的和極度夸張的荒誕手法。筆者擬從嬰魂、轉世和殺人三個方面來探究莫里森筆下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的荒誕建構。
從民間傳說來講,嬰魂指的是小孩死后所形成的一種魂靈。該魂靈是一種中陰性的物體,非人非鬼非神非魔,停留在陰陽界,直到其本身的陽壽消耗殆盡后,才能正式進入鬼魂的行列,可以輪回。“嬰魂有著比一般鬼魂更大的怨恨度和對人世的留念度,其對世間的怨恨度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不斷增加;如果其在母體身上不能得到足夠的能量,便會四處尋找對象,補給不足,甚至從陽世間的小孩處吸取生存的精華。”[11]在《至愛》里,莫里森把被塞絲殺死的大女兒設置成一個嬰魂,引領小說情節的發展。小說主人公塞絲在面臨被南方奴隸主重新抓回肯塔基的奴隸主莊園之際,為了避免遭受奴隸制的折磨,塞絲打算把所有的孩子殺死后自殺。但是,當她用鋸子鋸大女兒“至愛”的頸項時,鮮血四濺,兩個兒子嚇得驚慌而逃,黑人鄰居斯坦普·佩德( Stamp Paid)強行從她手里奪走了小女兒丹芙( Danver)。之后,被殺死的小孩變成了嬰魂,寄居在位于藍石路124號的老宅里。小說第一部的正文第一頁就寫道:“124號煞氣很重,彌漫著了一個嬰兒的惡咒。”[5]3之后,塞絲的住宅成為兇宅。蘇格思和塞絲都生活在難以自拔的自責中,塞絲的兩個兒子也生活在陰森森的氛圍里,丹芙在寂寞中只好把嬰魂視為伴侶,丹芙與嬰魂的嬉戲更加增添了小說的哥特式色彩。“她(丹芙——作者注)是那掙扎在奴隸制鎖鏈之中痛苦呼叫的冤魂,也是在奴隸制被廢除之后,仍無法擺脫其陰影的黑人的心理寫照。”[12]在莫里森的筆下,嬰魂在塞絲家的縈繞營造出恐怖、神秘、超自然的氛圍,與塞絲家庭成員的厄運、死亡和頹廢密切相關。
莫里森在《至愛》里還建構了嬰魂轉世的魔幻現象。轉世本是一個宗教術語,指的是一個人在死亡后,其靈魂在另一個人的身體里重生。“甜屋”莊園的奴隸保羅·D來投奔塞絲后,發現塞絲的住宅陰氣太重,于是采用了非洲人的驅鬼方式,在屋子里敲打門窗,摔碎瓦罐,終于驅逐走了嬰魂。于是,保羅邀請塞絲和其女兒丹芙一起去參加狂歡節,旨在開始新的生活。可是,在他們回家的時候,發現門前的樹樁上坐著一個年輕姑娘,穿著黑色的長裙,長裙下有一雙鞋,但是面容看不清楚,給讀者一種詭異的感覺。這個姑娘自稱“至愛”,這個名字與18年前塞絲在大女兒的墓碑上刻上的名字一模一樣,揭開了塞絲大女兒轉世的序幕。“至愛”的出現使保羅引導塞絲一家走出嬰魂之擾的計劃失敗。“至愛”千方百計地想把保羅趕走,甚至不惜采用引誘保羅上床的方式。事后,保羅對自己的亂倫行為感到無地自容。“至愛”住在老宅后,只關注塞絲一個人,用無聲的言行譴責塞絲早年對她的殺戮。入住塞絲家4周之后,“至愛”開始不斷追問過去的事件,旨在不斷撬開塞絲愈合的傷疤,使塞絲生不如死,猶如鬼魂纏身。在“至愛”的追問下,塞絲回憶起自己的母親;塞絲回憶往事的痛苦,換來“至愛”的高興。5周之后,“至愛”講述她的過去。“至愛”的出現具有極強的魔幻性,她走了很長的路,鞋子是新的,上面連塵土也沒有。“至愛”竭力阻止塞絲與保羅的相愛,認為這樣的相愛會使他們忘記過去。她想使塞絲永遠生活在過去的痛苦記憶之中,報復其殺女的過失。塞絲覺得“至愛”就是以前被自己用鋸子殺死的大女兒的化身,因此拼命用贖罪的方式來遷就“至愛”。“至愛”到底是不是塞絲三女兒的轉世呢?莫里森故意營造了一些不確定的因素以增強小說的魔幻感:有人傳言“至愛”不是塞絲的女兒,而是從一個白人淫窟里逃出來的受害黑人女子,但塞絲發現“至愛”對她過去的奴隸生活特感興趣,這不時勾起她不愿回首的往事。更有迷幻之感的是,丹芙居然發現“至愛”項上有疤痕。給讀者的感覺是,那個疤痕就是塞絲鋸死女兒后所留下來的,似乎“至愛”真的就是塞絲三女兒的轉世之人。從小說的情節發展來看,嬰魂從塞絲老宅消失不久,一個名叫“至愛”的女孩就出現在老宅門前;這個描寫似乎把已亡人的靈魂和世間真人的肉身結合起來,完成了轉世的步驟。“至愛”的身世之謎具有魔幻性,她聲稱自己是從水中出來的,類似孩子是從母親腹部的羊水中出來的。她搖晃的腦袋很像剛出生的嬰兒,其手和臉上的皮膚柔嫩得像嬰兒。她對母親的超常依戀非常類似于嬰兒對母親的依戀。[13]她出現后,塞絲家的狗“黑爾·鮑伊”就失蹤了,但當“至愛”從塞絲的老宅永遠消失的時候,那條狗卻回家了。莫里森通過狗與鬼不相容的荒誕傳說來營造嬰魂轉世的靈異氛圍。
在《至愛》里,莫里森給塞絲的殺女行為附上了荒誕的色彩。塞絲帶著剛出生的丹芙,歷盡艱辛地來到丈夫之母蘇格思的家,準備開始新的生活。可是4周后,“甜屋”莊園里綽號為“學校教師”的管家帶著捕奴隊追來了。他們企圖根據美國1850年頒布的《奴隸逃亡法》把塞絲及其4個子女悉數逮捕,并送回南方繼續為奴。塞絲經受和目睹了莊園管家“學校教師”的殘暴和無情,因此打算先把四個孩子殺死,然后自殺。塞絲寧愿用死的方式來逃避奴隸制的非人折磨。塞絲企圖殺死子女的動機非常類似于約翰·斯坦貝克小說《人與鼠》( Of Mice and Men,1937)中喬治殺死萊尼的情景。萊尼在自衛中掐死了農場主的兒媳,成為逃犯。喬治看見追捕萊尼的人來了,因無路可逃,所以喬治寧可含淚親手打死自己的唯一好友萊尼,也不愿讓他慘死在壓迫者的槍下。[14]因此,塞絲認為殺掉女兒的行為是為了“救”女兒,使她免遭奴隸制的毒打、私刑、饑餓和買賣。莫里森通過黑人母親“殺女兒是為了女兒好”的荒誕事件來抨擊美國奴隸制的反人類性。
在《至愛》里,“至愛”這個人物具有多重寓意或象征意義。“至愛”不僅是塞絲死去的孩子,也是從大西洋奴隸船運到美國的所有非洲人的化身。那些被迫為奴的非洲人像“至愛”一樣沒有臉,沒有名字,像“至愛”一樣在生存的空間無聲無息地消亡。莫里森關于“至愛”的嬰魂和轉世的荒誕描寫與小說贈言“獻給六千萬以上的人”的話語相映成輝,莫里森筆下“至愛”的遭遇不僅是塞絲個人的孩子的苦難,而且是千千萬萬不幸黑人母親的子女不幸遭遇的縮影。這部小說“打破了生與死,人與鬼的界限,創造出了光怪陸離的魔幻世界,對現實進行非凡的、別出新裁的神奇表現,給人以深刻的真實”。[15]因此,莫里森描寫的“至愛”具有多重寓意:小孩死后的鬼魂、無名奴隸的鬼魂和無法逃避的恐懼經歷的鬼魂。
三、意識流式蒙太奇
莫里森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在《至愛》的敘述過程中采用了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意識流動和時空倒錯的敘事手法。她把意識流手法與蒙太奇手法結合起來,把意識流描寫分為意識流片段剪輯和意識流片段合成。在意識流片段剪輯中,許多意識流片段并列或疊化而成的一個統一的意識流場景;意識流片段合成則是制作這種組合方式的藝術或過程。莫里森獨創的意識流式蒙太奇是以展示潛意識心理活動為主旨,按照情節發展的時間流程、因果關系來分切或組合意識流的小說視點或場景,從而引導讀者從哲理層面上理解小說主題。《至愛》中的意識流式蒙太奇主要可以分為三類:平行式蒙太奇、交叉式蒙太奇和顛倒式蒙太奇。
在意識流的平行式蒙太奇中,“不同時空或同時異地發展的兩條或兩條以上的情節線并列表現,彼此緊密聯系,相互襯托補充,分頭敘述而又統一在一個完整的情節結構中。”[16]莫里森是運用這類蒙太奇的大師。平行式蒙太奇有助于刪節過程,以利于概括集中,節省篇幅,擴大小說的信息量,并加強小說的節奏;其次,由于這種手法是幾條意識流線索的并列展現,相互烘托,形成對比,易于產生強烈的藝術感染效果。在《至愛》的第二部里,莫里森用平行式蒙太奇描寫塞絲與大女兒“至愛”相互沖突與深情依戀的場面:莫里森先在該小說的第200頁至204頁描寫了母親塞絲對女兒“至愛”的內心獨白,講述自己在奴隸制里受到白人管家的侄兒的凌辱后,向善良的女主人加納夫人求救,結果反而招致白人管家更殘酷的毒打,緊接著又回憶起“至愛”轉世后來到其門口的情景,然后又傾述自己殺害“至愛”的動機不是為了自己逃亡,而是不愿女兒重蹈覆轍。塞絲在心靈深處呼喊道:“當我把墓碑舉起來的時候,好想和你一起躺在那里,把你的頭靠在我的肩上,把我的體溫傳遞給你……她回到了我身邊,我的女兒,她是我的。”[5]204塞絲的內心表達了對女兒的思念和真摯之情。小說的第205頁至209頁是“至愛”的內心獨白。“至愛”講述了自己的故事:自從被母親殺死后,她就變成了幽靈,寄居在媽媽塞絲的老宅里;在保羅·D來到塞絲家之前,丹芙是她唯一的伙伴;她覺得母親殺了她,也可能殺掉她的妹妹,因此,她成為嬰魂留在老宅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護自己的妹妹。之后,“至愛”又回憶起兩個哥哥保加爾( Bulgar)和霍華德( Howard)的離家出走和保羅的到來,然后又回憶起自己的父親哈雷,她始終認為父親是一位天使般的男士。“至愛”不斷向母親塞絲打聽父親的故事,這時常使母親陷入痛苦的回憶中。塞絲的內心獨白和“至愛”的內心獨白平行地出現在這一部分造成的緊張節奏扣人心弦,有助于讀者從兩個角度來認識她們的母女情深,而不是表面的血腥殺戮。《至愛》的意識流描寫在第210頁至213頁達到高潮:這一部分是“至愛”的內心獨白,以“我是‘至愛’,她(塞絲——作者注)是我的”開頭。這一部分沒有標點符號,任由“至愛”的意識流淌,沒有作者的干預。在這一部分里,“至愛”充滿了對父親的回憶,然后又轉入對母親的回憶,最后,她在心靈深處吶喊道:
我沒死我沒有那里有房子她在那里給我說悄悄話我呆在她叫我呆的地方我沒有死我坐著太陽讓我閉上雙眼我睜開眼睛時看見了我失去的臉塞絲就是我失去的臉塞絲看見我看它我看見了微笑她的笑臉是我的是我失去的臉她是微笑中看著我的臉最后一次火熱的東西現在我們能加入火熱的東西。[5]213
這段內心獨白與前兩段內心獨白平行而成,相得益彰,渲染了“至愛”渴望通過母親塞絲找回自我的強烈愿望。
交叉式蒙太奇,也可稱為交替式蒙太奇,它將同一時間不同地域發生的兩條或數條意識流情節線迅速而頻繁地交替剪接在一起,其中一條線索的發展往往影響另外線索,各條線索相互依存,最后匯合在一起。[16]這種剪輯技巧有助于引起懸念、營造緊張氛圍,也有助于加強小說沖突的尖銳性、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在《至愛》的第215頁至216頁處,莫里森設置了塞絲與女兒“至愛”在意識流狀態中的對話,塞絲和“至愛”的意識流交替出現,似乎兩者之間產生了心靈感應式的會話。母親塞絲在意識流中對著女兒大聲地呼喊道:
把真相告訴我吧。難道你不是來自另一邊嗎?
是的。我是在另一邊。
是的。你還記得我嗎?
是的。我記得你。
你不會徹底忘記了我吧?
你的臉是我的。
你會饒恕我嗎?你會留下嗎?現在你在這里安全了。[5]215-216
在這段意識流里,塞絲表達了自己對“至愛”的真愛,希望“至愛”留在自己的身邊,永遠不分離。下一段意識流表達了“至愛”與丹芙的姐妹情深:“我們在溪邊玩耍。/我在水中,/風平浪靜時,/我們嬉戲。/烏云滾滾,/暴雨將至。/當我需要你的時候,/你來到我身邊。/我需要她微笑的臉……/她說你不會傷害我,/她傷害了我,/我將保護你,/我要她的臉。”[5]216-217這段意識流描寫了“至愛”與丹芙度過的童年快樂時光,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與母親血肉相連的關系。然后又交替性地出現了塞絲的意識流:“‘至愛’/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女兒/你是我的臉/你是我/我又找到你了/你又回到我身邊/你是我的‘至愛’/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塞絲表達了自己和女兒的血肉之情,非常欣喜女兒的轉世,把“至愛”當作自己的一部分。緊接著,下面又出現了“至愛”的意識流:“我吸您的奶/我有您一樣的笑容/我會照顧您”,[5]216“至愛”表達了對母親塞絲撫養自己的感激之情,認同與母親的血肉親情,愿意對母親盡孝道。此后,還多次出現這樣的交替性意識流片段,把塞絲與“至愛”的母女情深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從而揭露奴隸制對黑人的心靈創傷,抨擊奴隸制的吃人性和反文明性。
顛倒式蒙太奇是一種打亂了結構的蒙太奇方式,先展現故事或事件的當前狀態,再介紹故事的始末,表現為意識流描寫中過去事件與現在事件的重新組合。它常借助回憶、畫外音、旁白等方式轉入倒敘。運用顛倒式蒙太奇,打亂的是事件順序,但時空關系仍需交代清楚,意識流中的敘事仍應符合邏輯關系,事件的回顧和推理都以這種結構為基礎。在《至愛》中,莫里森主要采用倒敘式的意識流片段來補充小說情節發展所需要的信息,而且這些意識流片段在小說中出現的順序是顛倒性的、無規律性的,而且具有極強的補丁性。莫里森“沒有線性地展開情節,而是把不同時間、地點組合交織在一起。在現在與過去之間自由穿梭”。[17]塞絲、丹芙和保羅·D等人物都會在小說的不同位置出現一些長短不一的意識流片段,這些意識流片段的主題集中在三個方面:塞絲殺害女兒的自辯,丹芙懷念的姐妹之情和兄妹之情,保羅“甜屋”莊園的慘景和自己的監獄生活。顛倒式蒙太奇從不同的視點提供一些信息,雖不全面,但零星的信息拼接起來,就構成一個完整的信息,完善小說對人物潛意識層心理活動的揭示。
莫里森在《至愛》里所采用的意識流式蒙太奇使小說情節呈現出多線交叉的網狀敘事特點,打破了事件的邏輯順序,有助于時空與場面的變換,突出各條情節線之間的內在關聯,克服了平鋪直敘的乏味感。這三類意識流式蒙太奇交混使用,相輔相成。莫里森在意識流式蒙太奇手法的運用中突破時空界限,采用了大量的意識流倒插筆,倒插筆中又出現新的倒插筆,一連串的倒插,然后又回到人物當初的意識流中。對這些意識流倒插筆,莫里森并沒做任何時間上的和空間上的銜接交待,全靠讀者自己去理會。她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意識流片段都放在同一個畫面上來描寫,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實到魔幻,從生前到死后,常常重疊在一起,在同一個場景中出現。根據人物的夢境、幻覺、遐想、回憶等心理活動來組織敘事時間和敘事空間,把過去、現在、未來相互穿插、交織起來,通過多層次、多變化的時空統一體來展現人物隱秘復雜的內心世界,從藝術層面上提升了意識流式蒙太奇的魔幻現實感。
在《至愛》里,莫里森通過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把美國奴隸制社會即將滅亡的前夜寫得荒誕古怪、人鬼難辨,充滿血腥與恐怖,揭示奴隸制是一個反人類和毀滅人倫的社會史實。該小說的情節在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對真實世界的一種報道紀錄或深情回顧,然而仔細去審視的話,就會發現它們帶有一些小說技巧所無法表述的非真實性和神秘性。莫里森通過荒誕、怪異的描述手法,將現實夸張、變形,從而更深刻地描繪出美國內戰前后的黑人生存的某種現實狀況,對當時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丑陋社會現象和黑人文化中的消極因素進行批判,揭露社會弊端,抨擊黑暗現實,對黑人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做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引導讀者去領略非裔美國文學傳統的精華,尋找激發美國黑人生命能量的源泉。莫里森把超現實主義的形式和內容高度和諧地統一起來,促使黑人文學藝術中美學意識的升華。其魔幻現實主義敘事策略開拓了20世紀美國黑人小說的表現手法,使黑人魔幻現實主義敘事手法成為美國后現代小說在20世紀末的一個新亮點,拓展了現代黑人小說敘事策略的藝術空間。
參考文獻:
[1]TALLY J.Toni Morrison’s Beloved: Origins[M].New York: Routledge,2009: 54.
[2]PEACH L.Toni Morrison[M].New York: St.Martin’s,2000: 68.
[3]BOWERS M A.Magic( al) Realism[M].Abingdon,Oxon: Routledge,2004: 26.
[4]HILLS A.The Beloved Self: Morality and the Challenge from Egoism[M].New York: Oxford UP,2010: 121.
[5]MORRISON T.Beloved[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6]DRAKE S C.Critical Appropriations: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M].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2014: 23.
[7]ANDERSON M R.Spectrality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M].Knoxville: U of Tennessee P,2013: 98.
[8]CHRISTIANS? Y.Toni Morrison: an Ethical Poetics[M].New York: Fordham UP,2013: 27.
[9]MELLEN J.Magic Realism[M].Detroit,Mich.: Gale,2000: 34.
[10]范玉剛.荒誕:丑學的展開與審美價值生成[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1) : 56-61.
[11]赤雪.血嬰修神[EB/OL].[2014-01-05].http: / /www.bxwx.org/binfo/21/21162.htm.
[12]翁樂虹.以人物作為敘述策略——評莫里森的《寵兒》[J].外國文學評論,1999( 2) : 65-72.
[13]ERICKSON D.Ghosts,Metaphor,and Histor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nd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9: 123.
[14]董衡巽,朱虹.美國文學簡史:下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246.
[15]習傳進.魔幻現實主義與《寵兒》[J].外國文學研究,1997 ( 3) : 106-108.
[16]魏錦蓉.電影藝術中蒙太奇類別的分析研究[J].電影文學,2012( 2) : 30-31.
[17]王烺烺.歐美主流文學傳統與黑人文化精華的整合——評莫里森《寵兒》的藝術手法[J].當代外國文學,2002( 5) : 117-124.
(責任編輯周芷汀)
The Narrative Ways of Magic Realism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PANG Haono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In Beloved,Toni Morrison adopts the narrative ways of magic realism,and deals with the blacks’life in post-slavery days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absurdity and magic haunting by means of suspense,absurd approach and stream-of-conscious montage,making a lash-out at the anti-humanity of slavery.Based on parallel montage,interceding montage and reverse montage,she integrates the characters’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plots,leading to the constant ex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and overcoming the dullness of flat narration.Her 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surrealism is greatly conducive to the distilla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black literary arts.
Key words:Toni Morrison; Beloved; magic realism; narrative ways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非裔美國城市自然主義小說之性惡書寫研究”( 14BWW074)
作者簡介:龐好農( 1963-),男,重慶人,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
*收稿日期:2015-05-12
中圖分類號:I106. 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35( 2016) 01-0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