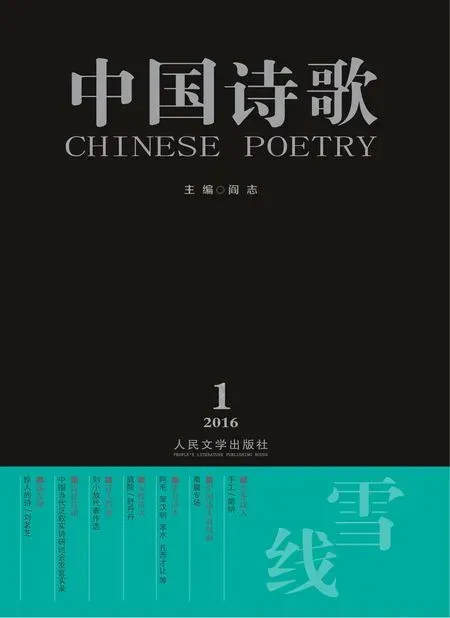弗羅斯特詩選
□唐 力/譯
弗羅斯特詩選
□唐 力/譯
晚晚行行
當我穿過收割后草場散步,無頭的再生的新草,
平滑倒伏,像帶著露水的茅草屋頂半掩著通向花園的小道。
然而,當我進入花園的空地,
肅穆的鳥兒一轟而散,
從枯萎的雜草叢,從蓬亂之上飛走,
這比任何語言,更令人傷感。
在圍墻的旁邊,一棵樹赤裸站立,徘徊在褐色中的一片葉子,
受到驚擾,我不懷疑,由于我的沉思,
它輕輕地,簌簌飄去。
最后我沒有向前走多遠我采下惟一的,剩下的紫苑
把它褪色的藍
再次帶到你面前。
群星
不計其數的星星,在夜空聚集在我們喧囂的雪花之上,
它們流動,以樹木般高大的形狀當寒風勁吹!
仿佛我們敏銳的命運,我們蹣跚幾步就
抵達白色的長眠,這長眠之地隱沒在黎明之中,
然而,既不是愛也不是憎恨,這些群星像一些雪白的
雪白的密涅瓦①密涅瓦:羅馬神話中,智慧、技術和發明之神。大理石的眼睛喪失了視力的天賦。
進來
當我來到樹林的邊緣,
聽——畫眉鳴囀!
此刻,如果林外正黃昏,
林中已黑暗。
樹林太暗了,鳥兒也沒法
扇動靈巧的翅膀
抵達更好的過夜的棲息地,
盡管它仍然在歌唱。
落日最后一縷光線
已消逝在西方
不過仍活在一首歌曲里
藏在畫眉的心房。
在矗立的黑暗深處
畫眉歌聲遠去——
幾乎像一聲召喚:進來
進入黑暗里,悲泣。
但是不,我在外尋找星星:
我不會進入樹林。
我指的是,即使邀請也不會,
何況我沒有被邀請。
春池
這些池塘,雖然在森林里,仍然
映照出整個無瑕的藍天,
如同它們身旁的花,寒冷而顫抖,
如同它們身旁的花,很快就會消亡,
但不會隨小溪或河水流走,
而是通過根莖,升到黑暗的葉簇之上。
這些樹,郁積的花蕾,擁有清泉
會加深自然的幽暗,會成為夏天的森林——
讓它們慎重考慮,在使用它們的力量之前
涂抹、啜飲、一掃而盡
這些花樣的水,這些水樣的花
來自昨天,雪的融化。
氣息——為花園墻壁題詞
風吹過遼闊而黯淡的草地;
但這堵舊墻,燃燒著明媚的臉龐。
風在墻上盤旋,虛弱,晃蕩,
難以吹動灰塵,或任何自我澄明之物;
水分、顏色和氣味,在這里變得濃郁。
白晝的時光集聚起一種氣息。
荒漠
匆匆地,夜色降臨,雪花飄落
我凝望的經過的荒漠,
大地茫茫,覆蓋皚皚的白雪,
些許雜草和殘莖裸露著。
它是它們的——樹林環抱著荒漠。
所有的動物無聲無息,躲藏在窩。
我也沒有心思去理會;
孤獨不知不覺地包裹了我。
而孤獨,實際是那種孤獨,
在減弱以前,將變得更加孤獨——
入夜的雪地,一片空茫
沒有表情,也沒有表述。
荒無人煙的群星,它們之間的距離
空曠、遼遠,并不令我恐懼。
鄰近家門,我自身的孤獨
這內心的荒漠,才令我自己恐懼。
不深也不遠
人們沿著沙灘佇立
全都轉身望著一個方向。
他們轉身背對陸地。
他們整天眺望海洋。
只要輪船從遠處駛近
船體就會不斷升高;
潮濕的地面宛若明鏡
映照出站立的鷗鳥。
也許陸地不停變幻;
但是,無論真理在何方——
海水仍然涌向海岸,
人們依然眺望海洋。
他們向外看不遠。
他們向內看不深。
但是何曾有什么遮攔
他們凝望的眼睛?
踏葉人
我整天踩踏著落葉,直到我厭倦秋天。
天知道有多少的顏色,多少形狀的樹葉,被我踏陷。
也許我釋放的力量太多,太猛烈,因為我內心恐懼。
我已穩穩地把又一年的樹葉踩在腳底。
整整一個長夏,他們都在頭頂,昂揚飄舞。
此時與我擦肩而過,飄向大地最后的歸宿。
整個長夏,我仿佛聽到他們威脅我的細細的低語。
此時他們似乎有個意愿,引領我與他們一同赴死。
他們同我內心的逃亡者談話,好像樹葉與樹葉談心。
他們用一張悲傷的請柬,輕敲我的眼瞼,觸摸我的嘴唇。
但沒有理由,因為他們走,我就得走。
現在我抬膝,踏在又一年的積雪上頭。
月亮圓規
我悄悄外出,在淋漓的間歇
在兩場傾盆大雨之間,去看黑夜的一切
而一個蒙面月亮,已經散落下圓規般的光線
在午夜的陰霾里,到達一座錐形的山,
仿佛是她的最終的估算,
正當她用她的卡鉗測量時,
高山興奮地站在它適當的位置。
因此愛將灑落臉龐,在兩根指針之間。
聲音的路徑
有些事物是永遠模糊不清。
但今晚天氣清朗,
多虧一場清澈的雨。
群山仿佛被帶到了附近,
星星們帶來了光亮。
你從前甜蜜而挑剔的語氣
再次傳來,如同你的來臨:
“因而我們不會說萬物模糊不清。”
迷失在天空
云,雨水的源泉,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為露水的源泉,提供了一道缺口;
此時我承認正用急切的視線,
在藍色的天空,尋找我熟悉的星球。
但是在那一片天空,星星稀缺,
沒有兩顆星,屬于相同的星座——
沒有一顆星,明亮得足以識別;
當然,沒有討厭,也沒有驚慌失措,
看見自己再次完全迷失,我嘆息,
“在哪里,我在天空哪里?不要告訴我!”
我呼喚云朵,“為我充分地裂開吧。
讓我,讓我在天空的迷失淹沒我。”
忠誠
內心想不出任何忠誠
能夠超過守望海洋的海岸——
堅守同一條曲線,
重復無窮無盡的演算。
小憩
那次小憩讓他意識到
他正在攀登的大山有一面斜坡
就如一本書高舉在他眼前
(盡管文稿是由植物書寫)。
矮小的茱萸、金線草,舞鶴草,
他用手指一一觸摸,就如他在閱讀,
花朵在枯萎,種子在出現,
但這些都是斜坡對他腦海的饋贈。
同樣的,閱讀有如思考,
不同于仇敵反抗,戰斗交火時,
嚴厲而冷靜的對視,
它是倔強而溫柔的空氣
可能被驚擾,因為原則與教義
但它將會有自己片刻的沉思。
在一首詩中
句子歡快地,行進在自己的道路,
并調皮地反對著韻腳
但它并不離題,它的敘述
那樣穩定,保持著節奏和韻律。
一個疑問
一個聲音說,如果在群星之中看見我
就要忠實地告訴我,地球的人啊,
是否靈魂和肉體的全部傷痕
仍不足以抵償,誕生所付出的代價。
秘密端坐
我們圍繞一個圓圈跳舞并猜測,
而秘密端坐中間洞悉一切。
保證
危險在不足一英寸的遠處
隱藏在安裝黃銅雙環的舷窗
它的平板玻璃后面
我確信感覺正確無誤。
小夜燈
在夜晚她總要把燈點燃
放在閣樓的床邊
它提供噩夢和破碎的睡眠,
但有助于上帝與她的靈魂同在
將她身上的陰霾統統拋掉。
它在我身上晝夜照耀,
還有誰,一如我想,在前面
最深的黑暗仍令人忌憚。
假如我陷入困境
在山上,在高遠之地
我以為不再有路,
一盞刺眼的車燈,強光閃移
開始蹦跳著彈下,花崗巖的階梯
像一顆星星閃亮地劃過天空
我走在對面的樹林里
為這些陌生的光線所打動,
并使我感覺到不再孤寂,
因為旅行者并不能給我慰藉
假如今晚我陷入黑夜的困境中。
冒險
在燦爛的星空下,一邊行走
一邊謹慎地仰望,難道我
就可能不被擊中,當星星飛速墜落?
這是個風險,我必須承受——再承受。
屋頂上的尖塔
假如是我們生活的屋頂上的尖塔
使我們生活的房子,變成了神圣的房子
假如它印證永恒,將會怎樣?
在夜晚,我們不用上那兒睡覺。
在白天,我們不用上那兒居住。
我們永遠不需要上那兒生活。
尖塔和鐘樓,出現在屋頂
這意味著,靈魂出現在肉體上。
天生的氦氣
宗教信仰是最適宜填充的氣體。
緊密壓縮后,它在我們
封閉的體內旋轉,使我們擺脫重力飛升——
仿佛輕盈的鳥兒體內,骨骼薄如紙翼,
給了他們飛行中更多的浮力。
有些氣體必定是天生的,比如氦氣。
現在關上窗戶
現在,關上窗戶,讓原野的一切靜寂;
如果必須,就讓樹木靜靜搖曳;
現在,沒有鳥鳴,如果有,
就讓我錯失吧。
這將是漫長的,在沼澤重現之前,
這將是漫長的,在最初的鳥鳴之前:
所以,關上窗戶,不要聽風,
但要看到所有風的吹起。
啟示
我們把自己帶到一個偏遠之地,在嘲弄與蔑視,閃亮的詞語后面,
但是哦,顫抖的心,直到有人真正把我們發現。
這令人惋惜:如果現實需要(大約我們會這樣說),終于
我們說出一些文字,去啟迪一個朋友的認知。
但是一切都是這樣,從捉迷藏的
嬰兒,到遠方的上帝,
所有把自己隱藏太好的人必須說話,告訴我們他在哪里。
花束
我離開你,在早晨,
在早晨的霞光中,
你曾走在我旁邊的道路
使我因離別而傷痛。
你知道嗎?我在黃昏,
憔悴、黯然、滿身漫游的風塵
你沉默,是因為你不理解我,
或是因為理解而沉默?
一切因為我?并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凋謝的花朵,就能
輕易地從你的身邊,帶走我
一天的全部時辰?
它們是你的,并成為尺度:
它們的價值,來自你的珍惜,
這時光細小的尺度
卻包含著我漫長的遠離。
花園中的螢火蟲
真正的星星來臨,布滿高空,
地上飛來模仿的螢火蟲,
雖然在大小上,他們從未與星星相同,
(在本質上,他們永遠不是真正的星星)
有時獲得一個星星般的開始。
當然,這個角色,他們也難以勝任。
中途
道路上升到高山之巔
似乎就要結束
而后飛起,進入云天。
在遙遠的彎曲處
它仿佛進入了一片林地,
那永遠寂靜的地方,
如同那些樹木,長久站立
但這是虛幻的愿望,
那些礦石渣土,迅速增長
迫使我載重的汽車
限制在公路上,
遠和近,它們都能連接,
但幾乎束手無策
對于那絕對的飛躍和靜止
那普遍的藍色
和局部的綠色的暗示。
被偶像化
波浪吸回,帶著最后的水
它卷起一綹海藻,纏繞我的雙腿,
帶著沙礫殘渣急速涌動
沖刷我赤裸的雙足,我搖搖欲墜
如果我不邁出幾步,就將被掀翻在場
如同某個迷亂的情人的偶像。
黑暗中的門
從房間到房間,在黑暗中穿行,
我盲目地伸手拯救我的臉,
卻掉以輕心,忽視了,應該交叉
我的十指,圍攏我的手臂成為弧形。
一道細長的門突破我的防御,
并給予我的頭部,猛烈的一擊
我天然的比喻不再一致。
所以,人與物不再匹配,而以前
它們搭配得多么和諧自然。
眼中的灰塵
如果,真像他們所說,灰塵飛入眼睛
將阻止我的言辭變得過分聰明,
我并不是一個放棄論證的人。
讓它勢不可擋,掀翻屋頂
繞過角落,降下灰塵的暴風雪,
如果必須,就讓我瞬間失明。
五十所述
我年輕的時候,我的老師是老人。
我為形式放棄火焰,直至我變得冰冷。
我忍受著,像金屬被鍛制。
我去學校,向老年人學習過去。
現在我老了,我的老師是青年。
所有不能被重鑄的,必須摔破、打散。
我利用合適的功課縫合修改。
我去學校,向年輕人學習未來。
熟悉黑夜
我已是一個熟悉黑夜的人。
我在雨中出走——又在雨中回來。
我越過最遙遠的城市之燈。
我看到城市的小巷最悲哀。
我經過敲更的守夜人
我垂下眼睛,不愿辯白。
我靜靜站立,止住腳步的聲音
遠處一聲被中斷的叫喊,
從另一條街道傳來,越過房頂,
不是叫我回去,也不是說再見;
在更遠的高處,遠離凡塵,
一個發光的時鐘,懸掛天邊
宣告時間并無正確錯誤之分
我已是一個熟悉黑夜的人。
碎藍
為什么制造這么多破碎的藍
零星地,或鳥,或蝴蝶,
或花,或佩帶的寶石,或睜開的眼睛,
當天堂呈現于片片純粹的色澤?
因為大地就是大地,也許,不是天堂(至今為止)——
盡管一些學者們,讓大地包括天空;
但在我們之上,藍色如此高遠,
它只賦予渴盼藍色的我們,一種激勵。
離去
現在我正逃離
世界的荒漠,
我的鞋子、我的襪子
再不會傷害我。
我把好朋友
留在身后的城里。
讓他們暢飲美酒
醉倒在地。
不要認為我走向
外面的黑暗
就如同夏娃和亞當
被趕出樂園。
忘記這個故事。
沒有一個人,與我
同時離去
也沒有人,驅逐我。
除非是我的過失
我只是聽從:
“我——決定——離去!”
這首歌的鼓動。
而我可能會回來
如果我從死亡那里
了解到的安排
并不令我滿意。
十間磨坊
預防
年輕時我從不敢激進
因為擔心年老時它會使我保守。
生命的跨度
這只老狗倒退著吠叫,并不靠近。
我還記得它是狗崽的情形。
萊特兄弟的雙翼飛機
這雙翼飛機是人類飛行的雛形。
它的名字或許最好是第一架摩托風箏。
它的制造者的名字——時間可不能犯錯,
因為它在天空鐫刻:有兩個萊特飛行。
消除邪惡傾向
枯萎病將會毀滅栗子樹?
農民應當認為不會。
只要讓文火在根部,持續熏燒
不斷催生出,新鮮的幼苗
直到另外的寄生物
到來,消滅這場枯萎病。
佩蒂納克斯①佩蒂納克斯(Publius Helvius Pertinax,126年8月1日出生于愛芭,193年3月28日逝世于羅馬市)是193年內的五位羅馬皇帝之一。佩蒂納克斯在位僅三個月,在此期間發生了多次兵變和陰謀。193年3月28日由于士兵毫無紀律造成的混亂狀態導致叛亂而被殺死。
讓混亂的風暴,來臨!
讓陰霾的幻影,云集成群!
我等待著形成。
黃蜂般的
一則謎語
在優雅彎曲的,光滑的鋼絲上,
他最大限度地挺直身體,趾高氣揚。
他靈巧的翅膀,自信地振動。
他尖利的螫針,氣勢洶洶。
可憐的自大者,他決不會知道
他和時人同樣糟糕。
他眼里有灰塵,他翅翼如風輪,
一腿交叉,他以此歌吟,
一口帶色的染料,代替一枚螫針。
記賬之難
永遠不要問錢花在哪里
只要花錢者認為它應該花出去。
永遠沒有人會在意
去記載或記憶
他是怎樣花掉每一個分幣。
并非完全在場
我扭過頭來跟上帝討論
關于世界的絕望;
卻把糟糕的事情弄得更糟
我發現上帝并不在場。
上帝扭過頭來跟我討論
(誰也別發出笑聲)
上帝發現我也不在場——
至少大半早已脫身。
在富豪的賭館
已經是深夜,我還在輸錢,
但我仍很鎮定,并沒有埋怨,
只要《宣言》能夠保證
在牌數上,我的權利平等,
我無心關切誰在經營賭館。
讓我們看看另外五張牌面。
恐懼的風暴
當風暴在黑暗中針對我們,
與大雪一起襲擊
低矮房屋東邊的窗口,
當風暴的野獸用窒息的沙啞聲,
嗥叫,
“出來!出來!”——
不要出去,這無需內心的掙扎,
啊,不!
我計算我們的實力,
兩個大人一個孩子,
我們沒有睡意,克制著不去留意
當爐火滅盡時,寒冷是怎樣躡手躡腳——
積雪是怎樣在堆砌,
前院和沒有平整的道路,
甚至連令人寬慰的谷倉都變得遙遠,
我的心中有個疑問
是否風暴每天都會在內心出現
而我們只能獨自拯救自己。
藍蝶日
這是春天,藍色的蝴蝶日,
這些天空的碎片,在風中上下翻飛
翅翼上的顏色,更加純粹
超過了經歷多日,徐徐綻放的花卉。
但這些飛翔的花朵,不會歌唱:
此刻沒有了欲望纏身
它們在風中合翼,停歇于
車輪剛剛刨切過的,四月的泥濘。
播種
今晚你來,從勞作中,接我回去,
晚餐已擺上桌面,但我們還要看看
我是否能停止掩埋白色的
柔嫩的,從蘋果樹上掉落的花瓣
(是的,柔嫩的花瓣,并非無用,
光滑的蠶豆、皺褶的豌豆,夾雜其間;)
陪同你一起回去,在你忘記
來干什么之前,不然你會如我一般,
以春天般的激情,成為大地的奴隸。
這種愛是多么熾熱,在播種期間
在等待它早些出生的日子
在那時,土壤因雜草而灰暗,
堅定的幼苗,弓身而出
承擔它的道路,抖落大地的塵土。
無限的瞬間
他在風中停住,但——那是什么
在遙遠的楓林,那蒼白的,不是幽靈?
他站立在那兒,用三月來對照他的思想,
可這最美的景色,令人難以置信。
“噢,那是綻放的天堂。”我說;
的確,花朵如此動人,
讓我們在三月里,在心中假想
我們的五月,雪白而繁茂的美景。
在一個陌生的世界,我們在一個瞬間停留,
我自己被自身的假象所蒙蔽;
然后,我說出了真相(我們繼續前行)。
一棵年輕的山毛櫸緊緊抓住它去年的葉子。
接受
當疲乏的太陽在云層上吐出光線
然后落下,在深淵里燃燒,
世界靜寂,沒有聽到大聲的哭喊
為所發生的事情。至少,鳥兒們知道
天空正在轉入黑暗。
一只鳥兒,埋首胸膛,細語呢喃,
開始閉上一只暗淡的眼;
一只流浪的鳥,碰巧它的巢穴太遠,
就匆匆地低低飛過小樹林
恰好及時地撲進,它牢牢記住的樹冠。
它最多會思考或輕聲啼鳴,
“安全!現在讓黑夜為我而黑暗。
讓黑夜太黑,讓我看不見
未來。讓一切自愿呈現,呈現。”
曾經太平洋邊
被砸碎的水發出薄霧的喧囂。
巨浪審視著,其他的上漲的波濤,
并思考著,怎樣才能到達海岸:
那些海水從未抵達的地面。
在天空中,云層低垂而蓬亂,
就像幾綹頭發,在閃亮的眼前吹散。
你難以分辨,但看起來是
海岸如此幸運地依傍著峭壁,
峭壁又依傍著大陸;
看起來好像黑暗的夜晚意圖
降臨,不只一個夜晚,而是一個時代。
有人做好了準備,為憤怒的到來。
這里將會有更多海水碎裂
只等上帝最后宣告:把光熄滅。
喪失
我以前在哪里聽見過風聲
變成如此低沉的轟鳴?
它為何會容許我站立在那里,
把住開著的,動蕩的門,
俯視山岡下波浪翻滾的海濱?
夏天過去了,白晝過去了。
西部天空,已經堆滿昏暗的烏云。
在門廊下陷的地板上面
樹葉起身,盤旋著,嘶嘶有聲,
盲目地攻擊我的膝蓋,但未能如愿。
某些邪惡暗藏在它的腔調里
告訴我,我那注定泄漏的秘密:
它說,我獨自一人在屋
不知為何,必須在他鄉旅居,
它說,我一生孤獨,
它說,我除了上帝,無人可依。
洪流
血流比洪流更難以筑壩圍阻。
正當我們以為,已將它安全地關押
在新筑的墻壩后面(讓它沖刷!)
它突然掙脫造成新的殺戮。
我們寧愿相信它是被魔鬼釋放;
其實是血自身的力量釋放了血。
它的流逝如洪水奔瀉
高高掀起如此反常的巨浪。
它需要一個出口,無論嶄新或陳舊。
戰爭的武器、和平的工具
都不過是它找到的發泄的依據。
現在,又一次浪潮奔流
峰巒失色,它裹挾著落葉一掃而過。
哦,血要奔涌。不可阻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