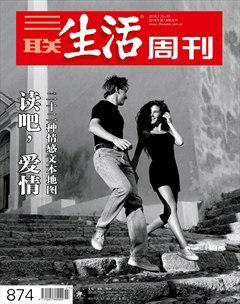夏多布里昂:以“魅惑者”之名
曾焱

在波爾多擁吻的一對城市戀人

夏多布里昂(1768~1848)
《墓中回憶錄》
我們來談?wù)勸v羅馬大使館,談?wù)勥@個意大利,我一生的夢想。在繼續(xù)我的敘述之前,我應(yīng)該談?wù)勔粋€女人,一直到這部《回憶錄》的結(jié)尾,人們總能看到她。她和我之間開始了從羅馬到巴黎的通信:應(yīng)該知道我給誰寫信,我是在什么時候如何認(rèn)識雷卡米夫人的。
她認(rèn)識一些登上世界舞臺的不同社會地位、多少有些名氣的人物;他們都崇拜她。她的美把她的理想生活融進我們歷史的物質(zhì)事實之中:一束平靜的光照亮了一幅風(fēng)云激蕩的畫。
讓我們再一次回到逝去的歲月;讓我們憑借我落日的余暉試著在天上畫一幅肖像,這個天空,我那臨近的夜就要布上陰影了。
1800年我回到法國之后,《水星報》上發(fā)表的一封信使斯達爾夫人震驚。我的名字還未從流亡者名單上劃掉;《阿達拉》使我不再默默無聞。……我記不起是克里斯蒂安·德·拉莫瓦尼翁還是《科麗娜》的作者把我介紹給了她的朋友雷卡米夫人。當(dāng)時雷卡米夫人住在她那位于勃朗峰街的家里。我剛從森林里走出來,剛剛有了點名聲,還完全是個野人;我?guī)缀醪桓姨а弁晃槐怀绨菡甙鼑呐恕?/p>
大約一個月以后,一天早晨我去斯達爾夫人家里;她一邊梳妝一邊接待我;她讓奧利佛小姐給她穿衣,一邊說著話,手指間繞著一小段綠樹枝。突然間雷卡米夫人進來了,穿一件白色的袍子;她在一張藍絲絨的沙發(fā)中間坐下。斯達爾夫人一直站著,繼續(xù)侃侃而談,詞鋒甚健;我不大應(yīng)聲,兩眼只望著雷卡米夫人。我從未想象過會有那樣的人,我也從未如此灰心喪氣:我的贊嘆頓時變成了對我自己的怨恨。雷卡米夫人出去了,我再次見到她已是12年之后了。
12年!什么樣的敵對力量這般切斷和浪費了我們的光陰,將其揮霍于被稱作眷戀的冷漠,以及美其名曰幸福的苦難!讓人哭笑不得。然后,還有更可笑的,當(dāng)它敗壞和耗費其最珍貴的部分之后,它又將您帶回到您奔走的起點上去。它是如何將您帶回去的?執(zhí)著于一些奇特的念頭,一些糾纏不已的幽靈,一些對一個不曾給您留下絲毫幸福的世界虛假或不完整的感覺。這些念頭、幽靈、感覺橫亙在您和您還有可能品嘗的幸福之間。您回來了,內(nèi)心受著悔恨的折磨,對年輕時的錯誤感到遺憾,在知道羞恥的時候回憶起這些錯誤是多么地讓人不堪啊。我就是這樣回來的,在到過羅馬、敘利亞之后,在見過帝國消失之后,在變成一個風(fēng)云人物之后,在不做沉默的人之后。雷卡米夫人她做了些什么?她的生活是什么樣子?
…………
蒙田說,人目瞪口呆地走向未來的事情。我另有一癖,對過去的事情目瞪口呆。一切都是愉悅,尤其是掉轉(zhuǎn)眼睛看看親愛的人的早年,一個被愛著的生命于是延長;他把感覺到的溫情擴展至他一無所知卻又重新喚起的歲月;他用現(xiàn)在美化了過去;他重構(gòu)了青春。
[節(jié)選自《墓中回憶錄》,(法)夏多布里昂著,郭宏安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
浪漫主義的“酋長”
“我覺得愛情是別的東西:我已多年不見勒內(nèi),然而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尋歡作樂中找過他的厭倦的秘密。”
1833年9月,在威尼斯穆拉諾島上,夏多布里昂漫步街巷,為他希冀傳世的《墓中回憶錄》寫下又一個章節(jié)。
“勒內(nèi)”是他的名字,弗朗索瓦-勒內(nèi)·德·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e de Chadeaubriand)。每當(dāng)懷念起多年以前住在布列塔尼的孤獨古堡里的年輕人,他就是這樣憐惜地稱呼自己。當(dāng)然,在他曾大受歡迎的小說《勒內(nèi)》中,主人公也用到這個名字。所以我們也可想象為,他或許是在小島上想起了那個帶給他法蘭西文學(xué)光榮的“勒內(nèi)”。
勒內(nèi)和“勒內(nèi)”,現(xiàn)實和想象,兩個不同文本里的主人公共同結(jié)構(gòu)了夏多布里昂的完整世界。本性、理智和道義,既主宰著他兼而為政治家和文學(xué)家的極其復(fù)雜的人生,也主宰了他一生的激情。
《勒內(nèi)》明顯帶有自傳色彩,夏多布里昂讓主人公“勒內(nèi)”講述了他和姐姐艾美莉一起度過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在荒原古堡里,欲望混淆于親情給他們以可怕誘惑。為了擺脫禁忌之愛,艾美莉避居到了修道院中,勒內(nèi)航海到美洲大陸去撫慰年輕的絕望和失敗感。在密西西比河上,“勒內(nèi)”獲知了姐姐的死訊,最終在一個基督教士的引導(dǎo)下,他重新面對敵對而真實的世界。他描繪憂郁,也創(chuàng)造了憂郁,整篇文字“像是從傷口中噴出來”。讀者在一個災(zāi)難的年代中看到一個心碎的年輕人,如何在心靈和感情的極度慌亂中去往他者之地尋求救贖。
《勒內(nèi)》寫于1802年,法國大革命的狂飆之末。早一年發(fā)表的還有他另一本愛情小說:《阿達拉》,講述“兩個野蠻人在荒漠中的愛情”。《阿達拉》里面仍然有“勒內(nèi)”,不過這次他不再是講述者而是一個故事傾聽者。年輕的法國人“勒內(nèi)”流落到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在那里遇到一個印第安老人沙克塔斯,聽他講了一段因為宗教而分離,最終通過死亡才得到實現(xiàn)的愛情故事:沙克塔斯20歲的時候,在一個印第安部落里被美麗的阿達拉搭救,兩個年輕人相愛了。阿達拉其實是西班牙人的女兒,從小在信仰基督教的環(huán)境下被秘密撫養(yǎng)長大,并被母親發(fā)誓獻為終身童貞。阿達拉雖然很想和沙克塔斯一起生活,卻寧死不肯違背母親的誓愿。最后她自殺了,臨死前請求愛人改信基督教。沙克塔斯沒有聽從神父的布道,他把愛人的遺體放到一個巖洞入口,讓她在鮮花和樹枝之上回到自然中。
小說一發(fā)表即大受歡迎。整個19世紀(jì)上半葉,無數(shù)法國人迷戀他語言的魅力,被文字中飛揚的尊榮和自由、沉思和激情所打動。少年雨果在作文中寫道:“要么成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無所成。”17歲的喬治·桑覺得自己的志向“被浪漫主義詩意的魅力重新鍍了金”。
現(xiàn)實生活中的夏多布里昂,1890年的想法也是到美洲去。他回憶:“我那時和波拿巴一樣,是一個完全不知名的少尉。我們同時從我們的卑微地位出發(fā),我到孤獨中去尋找我的聲名,而他到人群中去尋找光榮。那時,我并不迷戀任何女子,令我夢縈魂繞的是我的女精靈。我把同她一道去探索新世界的森林當(dāng)作最大的幸福。由于另一天性的影響,我的愛情之花,我的阿爾莫里克森林的無名幽靈變成佛羅里達樹蔭下的阿達拉。”而這兩本愛情小說,實際上是對同時期的另一部思想著作——《基督教真諦》的“小說方式的闡明”。夏多布里昂同時在頭腦里、在血液中孕育著《阿達拉》、《勒內(nèi)》和《基督教真諦》,前者甚至就是后者里面的章節(jié)。三本書都得到了一夜間轟動巴黎的巨大成功:運貨馬車車夫在自己住的客棧貼上印有書中主要人物的版畫,塞納河畔舊書攤的木箱子里陳列著他的人物蠟像。作者被大堆灑了香水的信件淹沒,就像盧梭寫出《新愛洛伊絲》后收到無數(shù)女人表白愛情的信件。
這就是我們從他文字中了解到的,敏感而憂郁的貴族青年夏多布里昂:出于階級的忠誠和道義,他在18世紀(jì)末大革命的動蕩中選擇加入保王軍隊,為國王路易十六而戰(zhàn),受傷后流亡英倫。19世紀(jì)第一個年頭,他在拿破侖的重臣、至交封塔納的幫助下回到巴黎,帶回了在流亡中完成的書稿《基督教真諦》。憑借天縱之才,他如愿以償?shù)貙⒆约旱拿謴馁F族流亡名單上抹掉,并且,在法國文壇和上流社會贏得了“魅惑者”之名。
單就情節(jié)而言,《阿達拉》和《勒內(nèi)》到了20世紀(jì)就顯得并不出色,但在那個時代卻都奇特而具異域色彩。對于法國,美洲是流亡之地和夢想之地,于冒險主義者有致命吸引。小說里面的愛情、死亡和毀滅,則是那些與社會敵對的年輕人的肖像。有評論者指出,法國浪漫主義文學(xué)不同于德國浪漫主義的地方,在于他們是一種“災(zāi)難式的浪漫”、“異域情調(diào)的浪漫”。夏多布里昂作為浪漫主義“酋長”,他寫的愛情故事作為文本來看是極其典型的,死亡、歷險、宗教、西班牙酋長、原始之地;愛和痛苦,痛苦和愛……最后死亡作為結(jié)局,完成法國浪漫主義的全部歷程。
總之,當(dāng)夏多布里昂走進著名的德·博蒙夫人家里為她朗誦《阿達拉》片段,這個身軀瘦小、腦袋卻長得很美的布列塔尼人一時間迷住了她。她把身邊人評論盧梭的話送給了作者:對觸動精神的肉體,對肉體與精神結(jié)合的快樂,他使我產(chǎn)生的印象比任何人都深。
身為盧梭主義的追隨者,夏多布里昂熱愛自然并服從激情,尤其服從愛情的驅(qū)使。但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聽聞親朋被斷頭臺和監(jiān)獄吞噬,他極度痛苦,終在母親病故后恢復(fù)了宗教信仰,決意以文學(xué)捍衛(wèi)基督教義。但同時,在思想上他仍是一個反對專制的自由主義者。他曾激情地寫道:“正是在大地、自然和愛情的美好之中,您找到生命和力量的成分,以便把光榮歸于上帝。”
夏多布里昂指出,那些母親般的天才似乎孕育和撫養(yǎng)了其他天才:對于法蘭西,拉伯雷創(chuàng)立了法國文學(xué),蒙田、拉封丹、莫里哀是他的繼承者。至于英國,到處是莎士比亞留下的痕跡,“他把他的語言借給拜倫,把他的對話借給司各特”。而夏多布里昂本尊,法國的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小說兩大源頭從此都落在他身上。后面的時代,跟隨他的偉大名字有雨果、拉馬丁、貢斯當(dāng),還有普魯斯特——當(dāng)人們談?wù)摲▏F(xiàn)代文學(xué),通常是說,“從夏多布里昂到普魯斯特”。他劃分了時代。
夏多布里昂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文學(xué)野心,這也是令一些同時代的名人憎惡他的原因,比如司湯達、巴爾扎克。夏多布里昂宣稱:“我像初戀,像愛一個女人那樣,愛上了榮譽。”1811年,在位于巴黎西郊的鄉(xiāng)間小屋“狼谷”中,他開始寫《墓中回憶錄》的第一章。“我僅僅生活了幾個小時,而時代的重負(fù)已經(jīng)在我的額角打下了烙印。”從第一句開始,他就緊握住了法蘭西史詩的光榮,親手為自己打造出一座“絕美的墳?zāi)埂薄?/p>
《墓中回憶錄》是他一生最宏偉的著作,共44卷,斷續(xù)寫了30多年,直到他去世前兩年才改完最后一個句子。這并不是普通回憶錄,他把個人命運的回憶置于時間的廢墟之上;他的痛苦和激情,與王國的毀滅、人的命運、歷史的悲劇交織在一起。

法國畫家雅克· 路易·大衛(wèi)的油畫作品《雷卡米夫人畫像》

位于法國伊勒維萊訥省貢堡的夏多布里昂故居
他大半生愛慕追求的貴婦雷卡米夫人,晚年破產(chǎn),寄住在巴黎城區(qū)的一個林間修道院;每天晚上,她的客廳都是這座城里名士和權(quán)貴聚集的地方,而尚未完成的《墓中回憶錄》就在這個房間里被一章一章地朗讀出來。夏多布里昂有悅耳迷人的嗓音,但他自己并不參加朗讀,害怕過于激動。他只是坐在旁邊,微笑地傾聽贊揚或批評。書稿節(jié)奏優(yōu)美,適合法國文學(xué)沙龍高聲朗讀的傳統(tǒng),低回處幽深,高昂起來又明亮又雍容,溢滿酒神頌式的激情。那些抨擊他自大、虛榮、多變的批評者也承認(rèn),其文優(yōu)美高貴,令人無法假裝視而不見。而作者本人自恃更高,“隨著浪漫派的誕生,在我身上開始法國文學(xué)的一場革命”。
當(dāng)我重讀18世紀(jì)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時,我對他們的聲名和我從前對他們贊賞感到羞愧。或者語言進步了,或者語言退步了,或者我們向文明靠近了,或者我們變得更加野蠻,肯定無疑的是,在這些年輕時我欽佩不已的作家身上,我發(fā)現(xiàn)了某種衰退的、過時的、灰暗的、僵死的、冷漠的東西。甚至在伏爾泰時代的那些偉大的作家當(dāng)中,我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缺乏情感、思想和文筆的東西。
回憶錄法文名《Memoires doutre-tombe》,直譯是“墓畔”或“在墓那邊的”回憶錄。1997年,國內(nèi)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郭宏安譯本《墓中回憶錄》——夏多布里昂說他是活人來寫死人的記憶,“墓中”在字面上可以有這一重理解。該譯本惜為簡版,僅挑出片段章節(jié)編譯,約占150多萬字里面的19萬多字,難以從中領(lǐng)略到夏多布里昂汪洋恣肆的文體魅力——現(xiàn)實和過往在他筆下交錯流轉(zhuǎn),創(chuàng)造了浪漫主義的、現(xiàn)代的新形式。2003年的花城出版社三卷本取名《墓后回憶錄》,幾為全本,但三卷各有譯者而良莠不齊,唯有第一卷保住了幾成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義詩意。
騎士之愛和危險關(guān)系
法國有名的龔古爾文學(xué)獎,創(chuàng)立者是19世紀(jì)作家龔古爾兄弟。他們對夏多布里昂貶多過褒,其一埃德蒙·德-龔古爾晚年卻在《日記》中表示,他愿以自有人類以來的所有詩篇換取《墓中回憶錄》頭兩卷。在反對者眼里也如此迷人的兩卷本,正是夏多布里昂講述他在布列塔尼的貢堡生活的部分,一段少年孤獨和危險關(guān)系。
就像大多數(shù)貴族青年,夏多布里昂自少年起便信仰了中世紀(jì)宮廷遺留下來的“騎士之愛”,即以光榮的道路開辟通向情場的勝利。所以,他后來才會在回憶錄里嘲笑大革命時期的那些流亡貴族,“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那些只能充當(dāng)副官的最漂亮的男人,懷著愉快的心情在那里等候勝利的時刻……這些杰出的騎士與古代騎士相反,以情場的勝利開辟通向光榮的道路”。
“騎士之愛”對于法國貴族而言有著古老傳統(tǒng)。從12世紀(jì)法國南部始,最后流行到整個中世紀(jì)的歐洲,“說法語的宮廷中都在發(fā)生這種誘惑的故事”。這種愛情故事若說有“劇本”,那也是遵循著固定主角和既定規(guī)則:帶著馬和劍的游吟詩人——包括貴族,也不乏出身低微的騎士——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詩歌形式,用來贊頌?zāi)澄皇苋俗鹁吹馁F族女性,她必定年長且美貌,并已嫁了某位貴族丈夫,游吟詩人一生的目標(biāo)就是要將她征服為自己的情人,為此不惜臣服于貴婦,甚至獻祭榮譽和生命。這就是后人從法國早期詩歌作品中所認(rèn)識的“騎士之愛”,它創(chuàng)造了丈夫、貴婦和騎士之間的三重典型關(guān)系,也是幾個世紀(jì)以來一類文學(xué)作品仿效的模本。
12世紀(jì)初,阿基坦公爵紀(jì)堯姆九世在他用普羅旺斯語寫成的游吟詩歌里,第一次造出了“歡愉”(Joy)一詞,“騎士之愛”從此便意味了肉體和靈魂的兩重享受,而肉欲在其中地位重要。但是,當(dāng)這種游吟詩歌和愛情故事流傳到法國北部,從諾曼底的特魯維爾到夏多布里昂出生地布列塔尼,卻演變出了幾乎迥異于南部的地域風(fēng)格。或許是氣候和習(xí)俗的差異所致,南部詩歌中那種期待在現(xiàn)實中索取回報的強烈肉欲被隱匿了,北方游吟歌手“強調(diào)對愛的渴望,而非愛的實現(xiàn)”。他們中有一位著名的加斯·布呂雷這樣唱道:我甘愿遭受這些痛苦/好讓我變得更加崇高。
欲望、尊重、忠誠,這是“騎士之愛”模式的基本法則。以通過文學(xué)方式傳頌流傳的層面來看,它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僅限于貴族的情感模式。夏多布里昂《回憶錄》中有關(guān)愛情的篇章,包括他兩部小說《阿達拉》和《勒內(nèi)》,都證明他有意無意地在模仿并遵循著這樣一種“騎士之愛”的準(zhǔn)則。他的愛情對象幾乎都是貴婦,他的愛情在婚姻之外,這和他的出身,少年時見到的婚姻模式以及受到游吟文學(xué)熏陶大有關(guān)系。
1768年,夏多布里昂出生在布列塔尼圣馬洛鎮(zhèn)的一個貴族家庭。著名傳記作家莫洛亞證實,夏多布里昂的祖上兩次與英格蘭王室結(jié)盟,一次與西班牙王室聯(lián)姻,和14世紀(jì)一位權(quán)重法蘭西的元帥的家族也結(jié)過三次親,“他們主持布列塔尼三級會議,替法蘭西歷代君主充當(dāng)保證人”。但到夏多布里昂這里能夠記得的,只是略有薄田卻難以養(yǎng)家糊口的貴族親戚。在他3歲時,他擁有騎士頭銜的父親依靠危險的海上生意重振家業(yè),以34萬法郎購回一塊祖上的領(lǐng)地——貢堡。那是一座僻鄉(xiāng)古堡,面積倒是大到可容100名騎士及其家人同住。整個青少年時期,夏多布里昂除了到城里上學(xué),大半時間都隨父母和尚未出嫁的兩個姐姐生活在古堡。他們盡力維持著體面,家里有一個廚師、一個侍女、兩個男仆以及一個馬夫構(gòu)成的仆從隊伍,外加馬廄里的一條獵狗和兩匹老馬。夏多布里昂在回憶錄里暗藏驕傲地提及一個細節(jié):姐姐呂西兒入修道院后,向巴黎某個著名的教士會申請接納她,教士會要求提供“四代血統(tǒng)的嚴(yán)格證據(jù)”,而她最終通過了審核。言外之意,他們家族確是真正的法蘭西貴族,“因為貴族是時間的女兒”。
至于貢堡四周的景物,有位19世紀(jì)英國旅行家曾路經(jīng)此地,在他的游記里寫過一筆,數(shù)年后被流亡英國時期的夏多布里昂讀到。旅行家描寫這片地區(qū)無邊荒涼,沒有任何富裕生活的景象,但是,美麗而高貴的貢堡卻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城堡主人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此君何許人也?就在一堆慘不忍睹的貧困中,有一個漂亮的湖泊,湖泊周圍是那郁郁蔥蔥的森林。”
“城堡主人”就是夏多布里昂筆下性格憂郁的父親。他在回憶錄里說,一家人沉悶地住在古堡里,只有星期天才和村里的自由民、鄰近的貴族聚聚會。他的父親木訥而孤僻,夏天獨自釣魚,冬天獨自散步,而他的母親,每天都待在光線陰暗的祈禱室里打發(fā)幾個小時。祈禱室里掛滿了繪畫大師的作品,其中有一幅是意大利16世紀(jì)畫家阿爾巴內(nèi)(Albane)的銅版畫《耶穌之家》,夏多布里昂離開貢堡后一直帶在身邊。
古堡有四個塔樓,在北塔有一個“克里斯蒂娜皇后”的套房專供外鄉(xiāng)客人下榻,里面有大床七尺見方,以雙重綠紗和紅綢床幃裝飾,四個鍍金的愛神支撐著床幃。堡里還有鬼魂出沒的傳說,當(dāng)?shù)厝讼嘈庞幸晃蝗倌昵叭ナ赖哪就鹊呢暠す舨粫r出現(xiàn),而他的木腿,會單獨同一只黑貓散步。
獨自睡在孤寂塔樓上的少年,就在這樣的荒原和海水之間,被造就了高貴的勇氣和敏感豐富的想象力。“我的想象力一經(jīng)點燃,到處擴散,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足夠的食糧,可能會吞噬天空和大地。”
最小的姐姐呂西兒是家里唯一和他親密的人,也是后來小說《勒內(nèi)》中艾美莉的原型。他們常在城堡旁邊的阿爾莫里克森林中散步、交談,是呂西兒引發(fā)了夏多布里昂對詩歌的興趣。“我把自己的寫作看作是一種邪念。我嗔怪呂西兒在我身上誘發(fā)了這種不幸的傾向。我擱下筆,哀嘆我未來的光榮,就像人們哀嘆自己失去的光榮一樣。”多年后,他在“狼谷”披露了這段少年心事,包括青春期最生澀的苦惱。
夏多布里昂并非家中長子,上面還有一個大他許多的哥哥。按照路易王朝規(guī)制,他沒有資格承襲家族頭銜和財產(chǎn),成年后只能和兩個姐姐分享年金。但也因為有兄長經(jīng)常出入路易十六宮廷,加上姐姐與其他貴族家庭聯(lián)姻,因此他在少年時即見過一些未來將被法國大革命歷史記載的美麗面孔,被她們埋下一生情感歷程中的“魅惑者”基因。
大革命前,他的三姐朱莉在貢堡舉行了婚禮。儀式上,還是中學(xué)生的夏多布里昂見到了一位貴婦,第一次,他感受到少年的悸動:
我碰見了德·特隆若利夫人,她后來以她在斷頭臺上的勇氣令人矚目。她是德·拉魯埃里侯爵夫人的表妹和密友,卷進侯爵夫人的陰謀活動。在此之前,我只見過家中的女性,當(dāng)我看見一個外面的女子如此美麗時,有點感到不知所措。生活的每一步向我展示一個新的前景。我聽見充滿激情的既遙遠又迷人的聲音向我走來。我被這新鮮的美妙聲音吸引著,急忙朝這些美人奔去。當(dāng)時,我像埃勒吉斯大主教,對每位神靈奉獻不同的香火。但是,焚香的時候,我唱的頌歌能否和祭司一樣,被稱為“馨香”呢?
從那時起,少年夏多布里昂隱約發(fā)現(xiàn)“以一種我不了解的方式愛和被愛應(yīng)該是至高無上的幸福”。他被“激情波浪”沖擊,陷入幻想之中。以自己見過的所有女性為基礎(chǔ)——女鄰居的身材、頭發(fā)和微笑,村中某個少女的眼睛,掛在城堡墻上的弗朗索瓦時代、亨利時代和路易十四時代的貴夫人的畫像給他提供了不同的風(fēng)韻,甚至從教堂的圣母像中竊取了某些嫵媚——他臆造了一個理想的伴侶“拉·菲爾德”,寄托自己全部青春的詩情和幻想。這種愛的譫妄狀態(tài)從1784年持續(xù)到1786年,占據(jù)了18歲到20歲的時光。
夏多布里昂的所謂“理想伴侶”,完全是一種柏拉圖式塑造,因襲了中世紀(jì)以來法國北方游吟詩人的那種理想化的“騎士之愛”。他內(nèi)心充滿了渴望,但并不奢求現(xiàn)實中的實現(xiàn)。他用文字準(zhǔn)確地描述著那個少年,如何以一種孤獨、古怪、奇特但充滿快樂的方式打發(fā)日子:
古堡北面是一片荒原,荒原上布滿了德羅伊教祭司的巨石。日落時,我找一塊石頭坐下來。金黃的樹頂、霞光燦爛的大地,透過玫瑰色云彩閃爍的金星使我又陷入遐思。我真希望能夠同令我夢牽魂繞的理想伴侶一起觀賞這美麗的景色。我凝神注視夕陽。我把我的美人托付給它,讓它領(lǐng)著容光煥發(fā)的她去拜謁宇宙。晚風(fēng)摧毀昆蟲在草尖上織的網(wǎng),云雀在卵石上歇腳,眼前的情景讓我回到現(xiàn)實。我心情憂郁,神情頹喪,踏上回城堡的歸途。
1789年,21歲的夏多布里昂走出貢堡,被兄長引薦到巴黎宮廷,等待獲得一個職位。巴士底獄被攻破前夕,在凡爾賽小圓廳的望彌撒的時間,他見到了路易十六的王后和她的兩個孩子。“王后微笑著朝我瞥了一眼,以優(yōu)雅的方式向我致意,就像我被引見那天一樣。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那不久之后就要消逝的目光。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微笑的時候嘴的形狀非常迷人,令我不能忘懷。1815年,經(jīng)過發(fā)掘,人們發(fā)現(xiàn)這個不幸女人的頭顱;對她的微笑的記憶(多么可怕呀!)讓我認(rèn)出公主的下頜骨。”
他在回憶錄中寫到這個難忘的場面。來自王后的優(yōu)雅的記憶,對他在大革命中如何選擇是否產(chǎn)生了影響?可以認(rèn)為是。那還不太可能是愛情,而是具有尊嚴(yán)的美好事物對一個青年的震撼。革命發(fā)生之初,作為盧梭的信徒他也并非革命的反對派。如果革命有秩序并且十分純潔地進行,也許他會加入進去。但是當(dāng)他站在臨街房間的窗口,看到暴徒們用長矛挑著可怕的人頭血淋淋地走過,立刻覺得一切都很可憎。他當(dāng)場憤怒地咆哮,也清醒地預(yù)見到即將產(chǎn)生的街巷專政。1891年他決定航行去美洲,就像小說《勒內(nèi)》中寫到的那樣,只是混亂的情感并非他的唯一理由。他希望在新舊時代殘酷撕裂的一刻逃開,遠離革命和反革命兩個陣營。一年后,當(dāng)路易十六國王一家被捕的消息傳到美洲,他卻冒險返回法國加入勤王之戰(zhàn)。他決心獻祭于自己的出身,某種意義上,正如騎士獻祭于他們的愛情。
在夏多布里昂的時代以及他死后的將近半個世紀(jì),在整個法國思想界,啟蒙時代以及法國大革命都因成了文明進步的象征而幾乎無人公開質(zhì)疑。1877年雨果的長篇小說《九三年》是為數(shù)不多的反思之作,也比夏多布里昂晚了30年。是夏多布里昂最早在回憶錄中公開而激烈地反思大革命中的暴力,尤其對群眾運動的毀滅性他有超越時代的見解。
他批評:“從整體看,人民是詩人,他們演出或別人叫他們演出的喜劇的作者和熱情演員。他們的過激并非出自天生的殘酷本能,而是被演出陶醉的人群的癲狂,尤其當(dāng)上演的是悲劇的時候。”他懷疑:“請跨過這條將舊世界和新世界分隔開來的血的河流。你正在走出舊世界,你將死在新世界的入口。”
那些著名文人的咒罵,大多是針對政治角色的夏多布里昂,因為伏爾泰的追隨者無法容忍這樣一個要與歷史潮流逆行的文人:他反對理性精神,毫無顧忌地站在自以為的思想高地,批判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捍衛(wèi)君主制,并且還讓文學(xué)染上“宗教圖景的色彩”。
然而,當(dāng)20世紀(jì)的法國知識分子開始具有規(guī)模地反思大革命甚而啟蒙時代,人們看待君主政體和宗教的目光也變得更加多元和寬容的時候,夏多布里昂也就成了超越他的時代的人。在《墓中回憶錄》中他好像已預(yù)見到了這一切。卷末他寫道:“在后代的眼中,我們當(dāng)今的爭論都會顯得毫無意義。經(jīng)驗和年紀(jì)的權(quán)威,出身或天性,才華或道德,一切都將被否定,一切都將蕩然無存;某些人爬到廢墟上,自稱為巨人,可是卻像侏儒一樣滑溜溜地滾了下來。只有二十來個人幸存,因為他們湊巧在穿越黑漆漆的大草原時抓到了一個火把……”夏多布里昂下面這段自畫像也比他人的評判更為準(zhǔn)確:“我生活于兩個世紀(jì)之交,仿佛在兩條河流的匯合處;我扎進翻騰混濁的水中,遺憾地遠離我出生的舊岸,懷著希望向一個未知的岸游去。”
情感教育
《基督教真諦》讓夏多布里昂成了巴黎上流沙龍里的紅人兒。他見到很多著名人物。在德·居斯蒂娜夫人的馬雷城堡里,他甚至有幸遇見過啟蒙時期最傳奇的德·烏代托夫人——盧梭曾在《懺悔錄》里表白這是他真正愛戀的唯一女人;他寫給她的情書,也許比《新愛洛伊斯》中的信更加熱烈。她和她的社交圈,是近在他眼前的伏爾泰時代的紀(jì)念物,夏多布里昂卻表示對這個時代“一點也不懷念”。
他有自己的傳奇。主角是19世紀(jì)最著名的兩位女性:偉大的思想者斯塔爾夫人(Madame Stael);傾倒巴黎的雷卡米夫人(Madame Recamier)。
斯塔爾夫人是日內(nèi)瓦大金融家雅克·內(nèi)克的獨生女兒。路易十六曾將她父親召回巴黎擔(dān)任財政大臣。她那時剛20歲,嫁給了瑞典一位大使男爵。這門戶相當(dāng)?shù)馁F族聯(lián)姻,以后被她明確地分隔在了愛情之外。憑借對文學(xué)的卓越見解和不盡熱忱,斯塔爾夫人很快成為巴黎最著名的沙龍女主人。她寫了大量令人驚嘆的文論,在政治上也充當(dāng)著聚集在她家中的自由貴族和憲政派的聯(lián)系人。當(dāng)人們談?wù)撍颊J(rèn)同她是那個時代最令人難忘的女性。許多名士往來于她的客廳,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騎士”是小說家邦雅曼·貢斯當(dāng),他們的動蕩關(guān)系長達15年。分手后貢斯當(dāng)以名作《阿道爾夫》復(fù)刻了這段故事。
夏多布里昂見到斯塔爾夫人,已經(jīng)是在他結(jié)束流亡生活的1800年,他32歲,斯塔爾夫人34歲。夏多布里昂之前公開發(fā)表文章激烈攻擊過她,斯塔爾夫人仍對這個剛剛贏得文壇大名的年輕人充滿好感。“她頂不住這么大的榮耀的誘惑,把行獵的興趣一直擴展到獅子身上,甚至生出讓他一口吞下自己的快感。”傳記作家莫洛亞描述他們的見面。
正是在斯塔爾夫人家里,夏多布里昂見到了巴黎最美的女人——雷卡米夫人。在繼續(xù)講述雷卡米夫人之前,不妨先來了解一種所謂“情感教育”的法國愛情觀念。美國斯坦福大學(xué)克萊曼性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瑪麗蓮·亞隆(Marilyn Yalom)指出,法國人把年長女性對年輕男子的性啟蒙稱為“情感教育”。這種傳統(tǒng)的根源可以上溯到中世紀(jì)和文藝復(fù)興。前面提到中世紀(jì)的騎士之愛推崇年輕騎士對貴婦的愛慕,而到18、19世紀(jì),這種形態(tài)在上流沙龍里強化了女性的主動性,演變成為沙龍女主人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的保護,他們因此得以進入上流社會并獲得職業(yè)機會。瑪麗蓮·亞隆認(rèn)為,年輕人愛上年長女性的主題帶有典型的法國色彩,而在其他歐洲國家,如德國、英國、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亞或美國文學(xué)中都很少能找到這類作品。
不管她的結(jié)論是否過于片面,至少我們在夏多布里昂的故事中找到了類似關(guān)系。與他生活的時代隔得不遠的一些大作家,如盧梭、司湯達、巴爾扎克,包括我們前面提到的貢斯當(dāng)也無不成為例證。1801年夏天,夏多布里昂在修改書稿《基督教真諦》期間接受了德·博蒙夫人提供的住所,和她有過一段隱秘的同居關(guān)系。在他的《回憶錄》中,德·博蒙夫人的容貌并不大好看,但作為路易十六外交大臣的女兒,在父親喪命于斷頭臺后,“她有著高尚的靈魂和巨大的勇氣,為了一個世界而生,她的精神出于選擇和不幸而退居其中”。
至于雷卡米夫人,她的美貌太過有名。在文人筆下,她13歲就和一位銀行家結(jié)婚卻不曾“被環(huán)境敗壞”,有著優(yōu)雅、單純和趣味純正的感覺,那是真正的天生高貴。她偏愛隱居,然而當(dāng)她間或也去劇院看戲或者公園散步,少有的幾次露面都成了真正的事件,驚鴻一現(xiàn)而光彩奪目,“她的腳步時時被圍觀的人所阻延”。她和斯塔爾夫人關(guān)系親密,處事風(fēng)格卻完全不同。她的生活方式讓人根本不知道在哪個聚會中肯定可以再見到她。因為她從不在家中見客,也尚未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子,追求者想要取悅她卻不知何去何從。這樣一個“當(dāng)代最美的面孔”加上神秘,令拿破侖的三弟呂西安·拿破侖也為之神魂顛倒。

1806年,夏多布里昂在去往希臘的旅途中
在畫家那里,大師爭相為美人立像。“一些船只還把她的畫像帶到了希臘的各個島嶼。美貌回到了人們原先編撰的地方。”新古典主義權(quán)威大衛(wèi)(Jacques-Louis David)給雷卡米夫人畫過一幅未完成的小像,現(xiàn)在收藏于盧浮宮。炙手可熱的宮廷肖像畫家熱拉爾(Francois Gerard)為她畫了一幅斜靠坐像,收藏在小王宮,并被視為他的杰作之一。如果認(rèn)為兩位大畫家為后人想象她的美貌保留了證據(jù),那么滿懷妒意的夏多布里昂會告訴你們,兩幅畫毫無相似之處。他對熱拉爾被公認(rèn)的杰作也不喜歡,因為模特的輪廓雖然畫對了,神情卻完全見不到了。總之在他眼里,雷卡米夫人的美是不可描繪的。
直到1814年,在德·斯塔爾夫人家里見過一面的夏多布里昂,對于絕代美人來說還只是一個模糊的印象。雷卡米夫人當(dāng)時避居那不勒斯,夏多布里昂在巴黎“狼谷”寫他的《墓中回憶錄》,彼此沒有交集。1817年斯塔爾夫人病重,在她的最后時刻,夏多布里昂在病榻前再次見到了雷卡米夫人,距離他們第一次見面已有12年。斯塔爾夫人逝世后,大作家開始常去探望雷卡米夫人。到了1823年,他們已經(jīng)熟識起來,“成為可以在一起談?wù)劻_馬的廢墟的朋友”。在長久的分別之后,兩個幾乎變成路人的漂泊者聚在了一起。對于兩人之間微末進退的情感變化,夏多布里昂有小夜曲一般溫柔的描述:
我去看望雷卡米夫人,先是在墻角街,后來在安茹街。當(dāng)一個人又碰上他的命運的時候,他以為從未曾離開過:按照畢達哥拉斯的說法,生命不過是一種回憶而已。誰不曾在其歲月之流中記住某些與人無干的小事,偏偏只關(guān)心能夠想起這些事的人呢?在安茹街的那幢房子有一個花園,花園里有一條椴樹廊,當(dāng)我等著雷卡米夫人時,我瞥見樹葉間瀉下一縷月光;我不是覺得這縷月光是屬于我的,我若是站在同樣的綠廊下又會瞥見它嗎?
夏多布里昂的婚姻關(guān)系是早年為了美洲之行而締結(jié)的,在貴族之間以聯(lián)姻做利益分配十分常見,他當(dāng)時希冀妻子獲得的家族遺產(chǎn)可以籌足他的旅費。他們并非為愛而結(jié)合,卻也從沒有分離,直到兩人生命盡頭。但在《墓中回憶錄》里,夏多布里昂把他忠誠的騎士之愛全部獻祭給了雷卡米夫人,將她描述為“我的感情的一個隱秘的源泉”。晚年的雷卡米夫人不再有美貌,她一目失明且生活困窘,但她在精神上仍舊優(yōu)雅而尊嚴(yán),擁有老朋友們尤其是夏多布里昂的愛慕:在走向末日的時刻,他表示他曾經(jīng)珍視的任何東西,都是與雷卡米夫人分不開的。“她支配了我的感情,一如上天的權(quán)力在我的本分之中放進幸福、秩序與寧靜。……她若來這回憶錄中漫步,在我匆匆建成的大教堂的拐角處,會見到我在此奉獻給她的小教堂;她或許會喜歡在那里休息,我在里面留下了她的畫像。”
(主要參考書目:《墓中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墓后回憶錄》三卷本,花城出版社;《夏多布里昂傳》,安德烈·莫洛亞著,浙江文藝出版社;《法國人如何發(fā)明愛情》,亞隆著,上海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