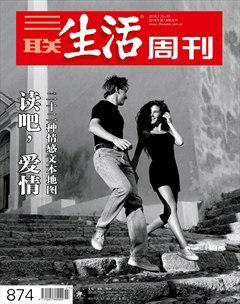別了,大陸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開局
劉怡
2015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復興路7號的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地八一大樓,習近平主席將三面軍旗交到新成立的解放軍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以及戰略支援部隊負責人手中,宣告了1955年以來中國力度最大的一次國防和軍隊改革正式開局。兩個星期之后,2016年1月11日,經過調整改組的中央軍委機關15個職能部門的負責人亮相,標志著始于1958年的軍委四總部領導體制走入歷史。而在1月17日,北京軍區善后辦副政委馬譽煒少將已證實:該軍區將改為中部戰區。這意味著脫胎于蘇聯模式的大軍區制在運行60年之后,將逐步被更集約的戰區制所取代。從作戰指揮系統到領導管理體制,解放軍正在經歷一場顛覆性的變化。
這種變化的總體目標與主要任務,集中體現在2016年1月1日印發的《中央軍委關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中。《意見》明確指出,軍隊改革要遵循“管、建、用”分離的原則,將過去由四總部統管的作戰指揮和軍隊建設兩大職能分離開來,軍兵種管理體制、大軍區制和軍事行政機關也要做相應的調整。在領導管理方面,要形成“軍委—軍種—部隊”的新模式,使四大軍種司令部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從專業化角度統籌部隊的訓練、管理和建設。在作戰指揮方面,則要構建“軍委—戰區—部隊”的三級架構,在軍委和各戰區分別設置聯合參謀部以及多軍種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以提升部隊的反應速度和實戰效能。最終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格局,并將部隊總規模由230萬人削減到200萬人。
與此前大致以新裝備、新任務為導向的軍兵種建設改革和機構調整相比,本輪軍改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告別了影響我國國防戰略方針和軍隊管理、指揮體制超過60年的“大陸軍主義”,按照新的國際形勢和已經大大擴展的經濟、安全利益,打造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通過將師承蘇聯大陸軍傳統的軍委四總部制調整為多部門制,既能強化軍委對核心職能的管理,又能整合相近職能、避免管理中的本位主義和“煙囪效應”,也是對軍紀、政法建設的一次提升。新組建的15個職能部門中,聯合參謀部將以“作、情、通”為核心,兼任平時的條令編制和戰時的作戰指揮職能;過去由四總部分別辦理的軍事行政事務,則將逐步轉移到擴容之后的國防部。而一度由四總部統一行使的陸軍管理職能,已經正式移交給新組建的陸軍司令部;過去僅作為獨立兵種的第二炮兵,亦升格為與陸、海、空三軍平級的火箭軍。四大軍種地位平等、齊頭并進,方有可能實現全面發展、聯合指揮。各軍種在訓練、裝備、編制等問題上,也可以做出更專業的決策。
在戰役方向和作戰任務上,將七大軍區制調整為更集約的五大戰區,同樣有擺脫“大陸軍主義”的用意。大軍區制的優勢在于,在國土作戰中可以很方便地改組為方面軍,并領導作為輔助力量的海、空軍部隊;在和平狀態下,擁有龐大行政機關的軍區亦可行使日常管理職能。但這種合成化程度較低、地域分割過細的模式已不足以應對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平戰轉換也不夠迅捷。通過組建覆蓋面積更大、具備戰役級聯合作戰指揮功能的戰區,就實現了主要戰略方向上軍種力量的健全化和作戰指揮中心的下移,符合國際潮流。而戰區司令員和四大軍種首長的決定權皆須由中央賦予,則從縱橫兩個方向上強化了軍委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更重要的是,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作為2013年以來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之一,與經濟、市場、財稅、法制、文化諸領域的改革措施接續提出的。它的開局,是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乃至國際利益分布的變化在安全領域的反映;而它的成效,將決定未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限度。

2015年9月3日,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上接受檢閱的反坦克導彈方隊

2015年6月17日,黑龍江省軍區邊防某團偵察兵進行實彈射擊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