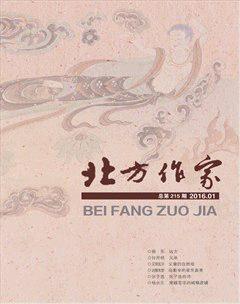穿越蒼涼的城鎮廢墟
2016-02-19 14:04:58楊永生
北方作家
2016年1期
關鍵詞:人類
楊永生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閱讀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廢墟》一文時,有這樣幾句話印象很深:“廢墟的留存,是現代人文明的象征。廢墟,輝映著現代人的自信。”之所以重溫余先生有關廢墟的話語,是因為我在走向草原冰川的途中,一次次穿越了或大或小的城鎮廢墟,讓我的思緒纏繞在廢墟的上空,久久盤旋,一種寂寥、落寞和惋惜的情緒,無以名狀,欲說還休。
當我們的車隊又一次穿過位于阿克塞縣博羅轉井鎮的老縣城廢墟時,我的心還是微微顫動了一下。坐落于阿爾金山東段北坡中腰,海拔2600米的阿克塞老縣城,在她作為現代文明的城市生長繁育時,我曾多次光顧于她,熟悉她的街衢、脈絡和氣味,熟悉她民族的滾燙豪情和堅韌的精氣神韻。我曾在阿克塞老縣城鋼筋水泥鑄就的樓前院落里,見到了悠閑自在踱著方步的羊群;在山坡的草地上聽到了冬不拉彈唱的哈薩克民歌,看到了羊群在音樂聲中陶醉吃草的優雅景致;還是在這座小縣城中我吃著鮮美的羊肉,在哈薩克朋友優美的歌聲中喝完了一杯又一杯美酒,穿著她們民族的服飾,搖搖晃晃地翩翩起舞。這些人類和牲畜和諧生活的場景,隨著1998年因海拔過高而將這座城市遺棄,瞬間的廢墟便接踵而來,鋪天蓋地,勢不可擋。有時候就連我們人類自己都吃驚,我們建設一座城市時是那樣的艱辛和漫長,世世代代,祖祖輩輩,子子孫孫,薪火相傳呀。可是,破壞一個世界,廢棄一座城市卻是如此之快,輕而易舉。……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哈哈畫報(2022年4期)2022-04-19 11:11:50
大科技·百科新說(2021年6期)2021-09-12 02:37:27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6:54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8期)2021-01-18 05:13:32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8期)2021-01-18 05:13:26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7期)2021-01-18 05:07:18
好孩子畫報(2020年5期)2020-06-27 14:08:05
小學科學(學生版)(2020年2期)2020-03-03 13:40:16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50
童話世界(2019年14期)2019-06-25 10: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