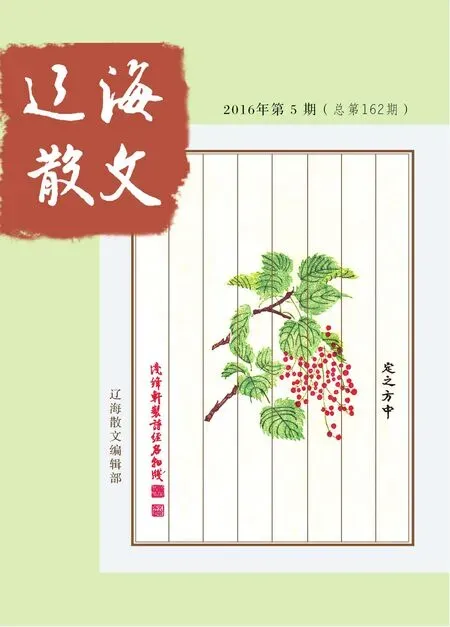我家的臘八節
李長鎖
我家的臘八節
李長鎖

李長鎖
祖籍河北遵化魯家峪,出生于京東玉田縣許莊子,下過鄉,當過兵,轉業到鞍山物資局,常有新聞稿件和理論文字散見于中央和省市級報紙雜志。退休后常趴在電腦桌上學習碼字,偶有小說散文見于文學期刊和報紙副刊。現為遼寧省散文學會會員,鞍山作協理事。
剛進臘月,那些赤橙黃綠、五色繽紛,源自天南地北制作臘八粥的各種干鮮果品、黍豆雜糧,早已擺上大小超市的食品攤位,走街串巷的流動攤販“和田大棗、云南紙皮核桃”的叫賣聲不絕于耳。那股股臘八粥的馨香,迅速向家家戶戶彌漫開來,一年一度的臘八節到啦!
在數九寒天的臘八節,倘若再喝上那么一碗香甜可口、回味濃郁的臘八粥,那種溫馨,那種靜謐,真是令吾輩陶醉不已。
據考,臘八節乃從天竺傳入,釋迦牟尼出家修行六年之久,每日只食一麻一粟,待得菩提樹下悟道成佛,恰逢是那年臘月初八。眾僧侶不忘佛祖成佛之苦,將每年佛祖成佛之日定為臘八節,喝臘八粥以示紀念。自此,華夏兒女援引祖輩習俗,每年臘八家家團聚喝粥,并借此祭祖、敬神、逐疫。
兒時,我家經營一爿當地小有名氣的“慶豐德”糕點作坊,平時一日三餐均由媽媽打理,但每逢臘八粥的制作非爸爸莫屬,因為他從小在餐飲行業拜過師學過藝,那會兒不僅是糕點作坊的“大掌酢”,還是餐飲業的一把好手,當地人稱“大廚李”。盡管年根兒糕點業忙得腳打后腦勺,但爺奶不依,因爸爸熬制的臘八粥有其獨到風味。
熬制臘八粥應該是一臺綜藝節目。因我家經營糕點作坊,各種食材應有盡有,什么南方產的桂圓、白果、酸梅、糯米呀,北方產的大棗、核桃、栗子、葡萄干呀,地產的粳米、小米、黍米、花生以及各色豆糧,爸爸都是親自挑選,親自配比,親自浸泡。就連燒大灶的劈柴,爸爸也是精挑細選,自己動手劈制。為了讓全家人按時喝上臘八粥,每每臘八的午夜時分,爸爸就開始刷鍋添水燃灶,將頭晚清洗泡發妥當的干鮮果品、黍豆雜糧等,根據粥料成熟難易程度,分批次倒入堂屋的那口大鍋。爸爸說,這樣熬出的臘八粥盛到碗里能讓食客分清臘八粥料,逐一品嘗出各種料香。
灶膛內劈柴噼噼啪啪爆響,紅紅的火苗不時竄出灶門兒。鍋內的水汽,頂得鍋蓋啪嗒啪嗒顫動。盡管室外被冰天雪地包裹著,室內卻溫暖如春。爸爸的臉膛被灶膛的火烤著,被鍋邊冒出的熱氣熏著,盡管汗漬淋淋,但那股喜悅滿足感卻溢滿整個房間。他一會兒添粗劈柴,一會又換軟柴。為防粥料粘鍋,爸爸還時不時地掀開鍋蓋,用長木鏟一會兒攪動攪動鍋邊,一會又攪動攪動鍋底。就這樣,大火之后改文火,那咕嘟咕嘟的翻騰聲,淡淡飄出的臘八粥香氣兒,不由得你不咽口水。
爸爸在這邊熬制臘八粥,那邊媽媽也沒閑著。家鄉的風俗是“葷冬至、素臘八”,因此,媽媽燴制的是一色清淡菜,炒豆芽、燉豆腐、拌芫荽根、浸芹菜梗,再用杏仁、花生仁、芝麻、松子仁配菜,佐以蔥姜蒜末蓋帽,輔以香油壓頂,看上去清清爽爽,吃進嘴里那才叫香醇可口呢。
粥菜做好后,爸爸帶著我,恭恭敬敬地將擦洗干凈的細瓷碗盛滿臘八粥,連同筷子,端放在先祖的靈位和佛龕前,然后上香,祭祖祭神。母親則領著姐姐,端著盛放臘八粥的缽盆,逐一給家中飼養的騾馬、牛羊等家畜家禽的食槽分發,讓它們和我們一起過臘八節。禮畢,家人才團團圍坐一起,開始喝臘八粥。直到現在,那臘八粥的香味,父母忙碌的身影,還有過臘八節的畫面還印在我的腦海里。
北齊詩人魏收在《臘節》一詩中寫道: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宿心何所謂,藉此慰中情。長大后,我離家上學、參軍,又轉業進城。爸爸媽媽在這期間,先后離我而去了。但對于每年過臘八節、喝臘八粥的習俗,我們依然樂此不彼地遵循著,因為那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更是我們做人做事的根基。
責任編輯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