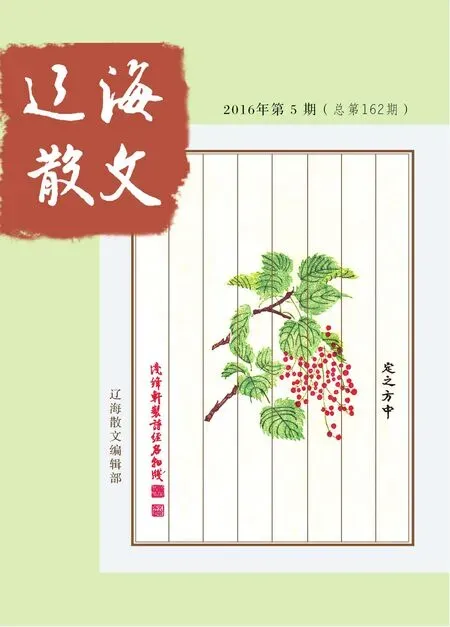十二粒酸棗
張正華
十二粒酸棗
張正華

張正華
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散文學會會員。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有散文、小歌劇、小說、報告文學、調研報告發表在《遼寧日報》《沈陽日報》《老同志之友》《老年報》等各種報紙雜志上,《父親》獲沈陽日報“咱爸咱媽”征文一等獎,2002年7月出版散文集《千思集》。
酸棗紅了。
每當酸棗紅了的時候,我就想起了楊奶奶。
1992年,我來到了闊別30多年的楊家莊。剛下汽車,仿佛置身于仙境,飄霧的群山若隱若現,紅瓦在余暉中顯得格外奪目。我沿著小路,直奔楊奶奶家,群山、小河、小草都讓我感到親切,連路邊的石子我都要撿起來撫摸一下。滿山遍野的酸棗在群山和村舍的點綴下,給人一種無比閑適的心情,就像紅色的珍珠點綴在綠色中,我曾經享受過它的賜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
邁進記憶中熟悉的小院,楊奶奶正在喂雞,看見有陌生人進來,她先是一愣,然后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高興地一下抱住我,嘴里不停地說,小華,可見到你啦。看見滿臉皺紋的楊奶奶,那一幕幕景象過電影似的在眼前重現。
30多年前,父親下鄉來到楊家莊,當時我正念高中,一到寒暑假,我就去父親那兒幫他干農活,因為沒有房子,父親就住在楊奶奶的下屋,楊奶奶成了我家的房東,在那個年代,所有人都不敢接近我們,唯有楊奶奶不怕,缺個油米柴鹽的,楊奶奶都給送過來。
楊奶奶是苦命人,抗日戰爭時丈夫和兒子都犧牲在戰場上,她和孫子相依為命。因為她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團結群眾分田地,支援解放戰爭,她用一雙小腳爬山越嶺,磨得鮮血淋漓竟不知疼。
那是1962年的一天,父親出工修水庫去了,家里剩我一個人。隊上出工送糞,男女老少齊上陣,我和社員抬一筐糞,100多斤,往返2公里,一天抬8趟。我肩上漸漸磨出了血泡,扁擔一挨肉,針扎似的,我就在肩上墊上一團布,咬牙堅持著。
突然間,雷聲大作,狂風驟起,風夾著雨點向人們砸來。我被淋成了落湯雞,冷得上下直打牙,趕緊回家躺下。這時楊奶奶來了,看我滿臉大汗面色通紅,忙問:“小華,你病了,讓雨淋壞了吧?”她用手摸了摸我滾燙的臉,然后消失在雨夜中。不長時間,她找來赤腳醫生,一量體溫,40多度。那個時候,人連飯都吃不飽,哪能有藥。這時,我身上一會冷一會熱,蓋了幾床被子,嘴上還燒出了許多水泡。
楊奶奶回到房里,拿出12粒酸棗,找來小鍋,抱柴添火熬水,熬好后扶我喝下,頓覺清爽多了,她又把棗仁碾成粉末,也讓我喝了下去。楊奶奶說:“酸棗是個好東西,雖然味苦酸,但山里人對酸棗特別有感情,記得在打小鬼子的時候,一個傷員發燒,我也是給他熬的酸棗湯,有清熱解毒的功能。”
隔了一天一夜,我感覺不怎么燒了,就是全身像抽筋一樣,出奇地乏,下床走兩步就感到頭重腳輕,只好又回到床上。楊奶奶一直陪著我,喂水、喂飯、蓋被。又隔了幾天,病情逐漸好轉,是楊奶奶的精心照顧,把我從死神的邊緣拉了回來。
病好后,我要回沈陽了,楊奶奶又來到我的屋,拿著鞋量了又量。第二天,她一直送我到汽車站,我穿著楊奶奶給我做的新鞋,看著她慈祥的面龐,好多要說的話說不出來,淚水在眼里轉來轉去,最終掉在鄉間小路上。
直到現在,我的眼前還經常出現這樣的畫面:群山之間,酸棗樹旁,一位老奶奶正步履艱難地行走著……
責任編輯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