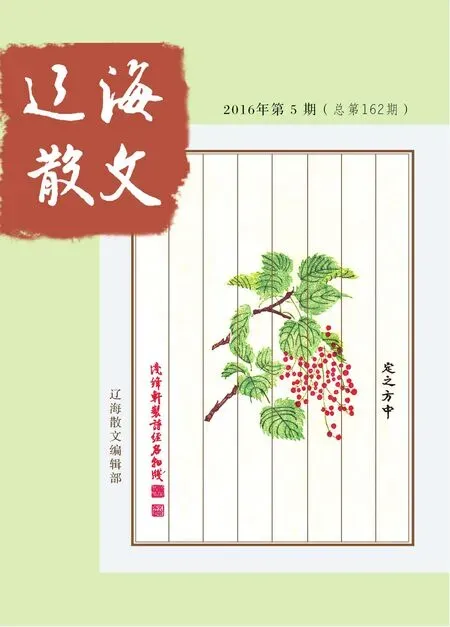贛州:一座不沉的城市
江洋
贛州:一座不沉的城市
江洋

江洋
葛江洋,退役軍人。現為遼寧省散文學會秘書長。20年前出過散文集《盜火集》,并加入遼寧省作協。近年出版散文隨筆集 《凈水微瀾》《盜火者說》。
我的祖籍是江西贛州。那是個著名的水上之城,它兩面環水,交叉而過的章江和貢江像兩只臂膀將它擁抱,它又像一只船在兩條江水的簇擁下前行。兩江匯合后稱為贛江,一路北上,到南昌又托起了滕王閣,再從那里流入鄱陽湖。江西簡稱“贛”也由此而得名。
800多年前,南宋愛國將領辛棄疾滿懷國仇家恨來到贛州城外的賀蘭山上,俯瞰著不舍晝夜滔滔東流的江水,寫下了那首憂國天下、憂民眾生的千古絕唱《菩薩蠻》: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從此,這座始建于唐朝中葉的郁孤臺也因此揚名,一改“隆阜郁然孤峙”的沉悶,成了著名的旅游景點。后人在郁孤臺附近還修建了四賢坊牌樓,上面刻印了趙抃、周敦頤、劉彝、文天祥的名字,左右兩側的楹聯寫明了四人的主要成就:“趙抃疏險灘劉彝福壽惠千古,濂溪創理學文山丹心昭日月”,足見這四位先賢對贛州做出的文化貢獻。
上述四人中周敦頤和文天祥已名聞天下,周敦頤的《愛蓮說》膾炙人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經典格言,可贛州歷史上還有常常被忽略的官員,那就是宋代的知州劉彝,他主政期間建造的一項堪稱世界一流的政績工程福壽溝至今令人稱道。
據史料記載,北宋熙寧年間(公元1068年—1077年),福建人劉彝到贛州做知州,他看到城區常年飽受水患,決心為百姓做些實事。經過反復思考和實地踏勘,根據城市西南高、東北低的地勢,規劃并修建了贛州城區的街道。同時根據街道布局和地形特點,采取分區排水的原則,建成了兩個排水干道系統。以州前大街為排水分界線,西北部以壽溝,東南部以福溝命名。并在城墻腳下開設水窗12間,視水之消長,利用水力使閘門自動啟閉——貢江水位高于水窗水位時,借江水之力將閘門關閉;當江水低于水窗時,借水窗內溝水之力將閘門沖開。福壽溝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辦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為了保證水窗內溝道暢通和具備足夠的沖力,劉彝采取了改變斷面,加大坡度等方法。這樣確保水窗內能形成強大的水流,足以帶走泥沙,排入江中。從城市環保和山形地勢上因勢利導,又從城市風水學的角度,把福、壽兩溝線路走向設計成“縱橫紆析,或伏或見”,作為龜背紋古篆體之形嵌在贛州龜形城的龜背上,充分地考慮了贛州城的永固和廣大人民的福祉,寄托了他的美好愿望。因為兩條溝的走向形似篆體的“福”“壽”二字,故名福壽溝。
封建王朝的官員,絕非都是等閑之輩,干好了同樣可以加官晉爵,劉彝就因此調入京城,當了一個相當于水利部副部長(“都水丞”)的官。而百姓的眼睛更是雪亮,他們記著劉彝的功德,把他奉為贛州的“李冰”,并專門在上海為他鑄造了一座高2.7米、重1噸的青銅雕像,栩栩如生,凜凜英姿,安放在贛州市宋城公園的古城墻旁,以彰顯劉彝建福、壽兩溝的偉大歷史功績,左邊的石碑上刻著光緒年間勘測繪制的“福壽二溝圖”,成為江南古城的又一亮點。
900多年來,全長12.6公里的福壽溝作為贛州的地下排水設施,佑護著10多萬舊城區名居民使用至今,為贛州市民造福。2010年夏秋之交,我國南方江西、廣東等省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一次次刷新百年記錄,此時廣州、南昌、南寧等城市都成了一片澤國汪洋,而三面環水的贛州城區卻如一艘不沉的方舟,市民生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專家不得不承認,這個原本只能在遺址中看到的歷史遺跡,依然在造福后人,當時的科學設計、前瞻思維、求實態度和質量標準都是世界城建史上的一個奇跡。
贛州的福壽溝——讓贛州成為一座不會被淹沒的城市。
值得贛州記憶的還有一位近代官員,那就是蔣家大公子蔣經國。當年蔣經國攜妻子從蘇聯回到國內,老蔣就把他放在了贛州“實習”,從舉辦培訓班開始,到后來成了主政贛州的地區專員,時間達5年之久,現在贛州仍然有保存完好的蔣經國舊居。
據說,蔣經國在贛州期間展示了他的理政才能,時值全國抗戰之際,可日本人也不知為何,只打到吉安止步,給了這個大公子充分的時間和空間。他滿懷理想,躊躇滿志,一到贛州,就提出“建設贛南即建設江西乃至建設新中國偉業”的口號,嚴令禁賭、禁煙、禁娼,凡有違反者,無論是誰,一律嚴辦。曾經有一個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處在縣城的中正公園陣亡將士墓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6個月。還有一個國家銀行的主管老婆,偷偷在屋里聚賭,門口還安排了衛兵站崗,結果被蔣經國發現后,立即派人抓捕,連同守衛當場擊斃。
那些日子里,外界稱贊他的治亂用重典,一掃往日霧霾,甚至說他在蘇聯時是“帶有國民黨性質的共產黨”,而回到國內則成了“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蔣經國聯系群眾,體貼民情,有時乘車外出,見到窮苦百姓就停下車子攀談,經常走街串巷,微服私訪,在贛州留下許多佳話,被百姓譽為“蔣青天”。
當然,他的那段風流韻事也發生在贛州,那就是遇到的紅顏知己章亞若。章亞若是南昌的進步女青年,她響應蔣經國舉辦培訓班號召前來報名,被蔣經國看中后選到身邊當秘書,一來二去,成了蔣經國的“小三”,中間還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蔣經國的元配夫人蔣方良雖然是蘇聯人,在蔣經國危難之時對他有救命之恩,但對蔣經國的茍且之事卻無能為力,好在有老蔣在遠方為兒子的前途、事業把關。最后,即將承擔國家大任的蔣經國,在江山和美人之間選擇了前者,他毅然切斷與章亞若的綿綿情絲,將她送到廣西桂林藏進來,直到后來章亞若不明不白地死去,留下兩個兒子以“章”姓在臺灣成長,直到蔣經國辭世,才得以面對世人。
如今的贛州以占地面積、人口數量和經濟增長成為江西第二大城市,著名的紅城瑞金、于都、興國、寧都都屬贛州,如今贛州正在精心打造紅色故都、江南宋城、客家搖籃、生態贛州的文化工程,這艘經歷千年的航船,正以改革的姿態前行,只是我擔心它的內在,那些文化的精華能否得以傳承?據說,贛州地下有大量稀有金屬,國家給予了優厚的開發政策,那些嗅覺靈敏的開發商們紛紛進入,一夜狂風吹來了贛州的繁榮。但愿這不是泡沫,但愿如今的官員也能夠學一點1000多年前的劉彝,或者學學70多年前的蔣大公子,給后人留下一點好口碑。
剛剛得知,贛州前任市委書記在調任內蒙后不久落馬,是在贛州任上犯的事。一位不到55歲的省級官員,主政贛州8年之久,竟有如此答卷,實在令我驚悚不已,于是我為贛州擔憂!
我常常以為自己是贛州的后代而自豪,甚至想過在退役之后能為家鄉建設盡些綿薄之力,可惜時代沒有給我機會。我崇敬它是一座不沉的城市,在歷史的滄桑中不沉,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沉,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不沉,并且面對挑戰,永遠乘風破浪!
盡管那位為民造福的劉彝和福壽溝、那憂國憂民的文天祥和郁孤臺,還有那曾經的“青天老爺”蔣經國與我并無太大關系,然而,家鄉水的靈性已經傳承于我,我與贛州有一種天然的親近和交融,類如我的名字中是因了贛州而有水,或許這是上蒼賦予我的靈性,我飽含淚水,充滿感激和關注。
責任編輯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