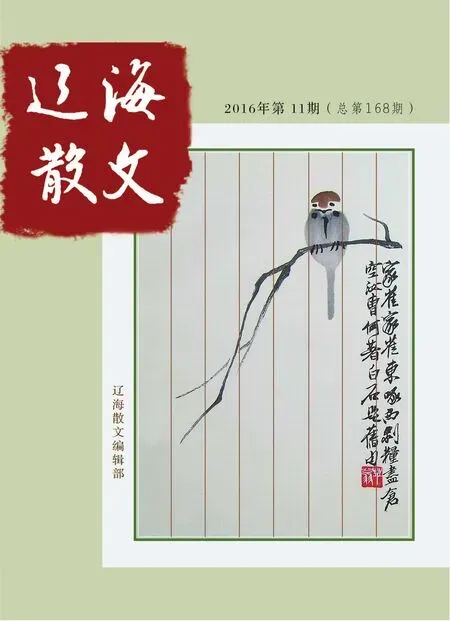母親的刺繡人生
紅塵一笑
母親的刺繡人生
紅塵一笑

紅塵一笑
原名劉靜。中國散文詩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副秘書長,《中國散文詩年選》副主編,中國詩賦學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遼寧省散文學會會員。在《中國文學》《中外文藝》《中國詩賦》《遼寧日報》《鴨綠江》《中國散文詩》《中國散文家》等全國幾十家報刊發表作品近千篇。著有散文集《花開,只為傾城》《靜聽心海》,詩集《那夢,那時光》。
記憶中,母親是一直坐在那臺老式縫紉機前的,低著頭,聚精會神地踩著縫紉機;或者左手舉著繡花繃,右手拿著繡花剪,對著陽光欣賞并修剪她的刺繡作品。
她的身影永遠是忙碌的,她的表情永遠是癡迷的。
從我記事起,母親就與繡花為伍,那個時候,生活中流行的不是現在的手工十字繡,而是縫紉機刺繡。市區附近,有一家大型刺繡廠,專門承攬各種刺繡業務,如門簾、枕套、床單、被罩,甚至還有孩子的兜肚。廠里把刺繡用料發到分散在各地的繡工手中,再收回刺繡好的成品投放到市場。當時,為了貼補家用,附近許多婦女加入了繡工行列,母親就是其中一員。
機繡是個精細煩瑣的活兒。從刺繡廠發過來的“花樣子”是透明的蠟紙,用于繡花的布料基本都是的確良布,白色、藍色、紅色,也有粉色的。母親先把花樣子附在布料上,為防止筆跡打滑變形,先用大頭針把四個邊角別好,然后在蠟紙和布料間放置一張復印紙,最后再一筆筆將蠟紙上的圖案繪印到布料上,算是完成了刺繡前的首道工序。接下來要做的便是配線,因為刺繡廠對每個圖案所用線號都有嚴格要求,而許多線顏色又非常接近,不仔細分辨是看不出的,所以這一環非常重要,稍不留意便會出差錯。就這樣,母親經常要為一種線,搭車跑到幾十里外的刺繡廠去選配,有時,刺繡廠線號短缺,母親便要跑遍附近的十幾家集市,挨家尋找。在那個交通不便利的年代,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
接下來,就看母親的手藝了。從針碼大小,再到針腳的縱橫,母親都做了專門的研究。有時為了把某個部位繡得恰到好處,她甚至拿著放大鏡去觀察。拆了繡、繡了拆,一直到自己滿意為止。因為她態度認真,繡品質量好,深得刺繡廠的器重,每次廠里有重要的活兒,他們都要母親牽頭示范。她繡出的富貴牡丹、嫦娥奔月、鴛鴦戲水,達到了活靈活現的地步,被刺繡廠選送到國外。
漸漸地,母親有了名氣,村里誰家娶了媳婦,誰家生了小孩兒,她都會送上親手繡的喜慶門簾、枕套或吉祥兜肚,鄉親們也為能得到母親的刺繡作品而感到榮耀。母親生性善良,家里經常會有學員來向母親討教,母親不厭其煩地上機示范,一遍遍講解,直到人家懂了為止。記得當時鄰村有個劉姓女子,跟著母親學刺繡,剛開始不得要領,急得直哭。母親便天天手把手教她,把自己的全部技巧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她,遇到雨雪天便留她在家吃住,常常感動得她熱淚盈眶。后來那女子也練就一手絕藝,成了母親最得意的門生。
對于刺繡,母親是癡迷的,有很多時候刺繡廠活計催得緊,母親便夜以繼日趕活兒,白天顧不上吃飯,晚上在燈下一忙就是半宿。那時候,父親在電業局上班,無暇顧及家里,母親白天忙家務,晚上要刺繡,常常是我一覺醒來,她還在縫紉機前忙碌。那些年,家里生活并不寬裕,但因為刺繡的額外收入,我們姐妹三人的衣食住行一直都是無憂無慮。直到我們成家立業,母親才放下刺繡的行當,放心地頤養天年。但由于常年低頭刺繡,母親落下了嚴重的頸椎病,至今無法痊愈。
日子如白駒過隙,漫步在歲月的長廊,我們往往一邊走一邊懷想。母親用一技之長撐起半個家,為兒女打造了一方自由飛翔的天空。母愛的恩澤,如同燈塔閃耀,給人念念不忘的溫暖;又像涓涓細流,甘甜潤心。
責任編輯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