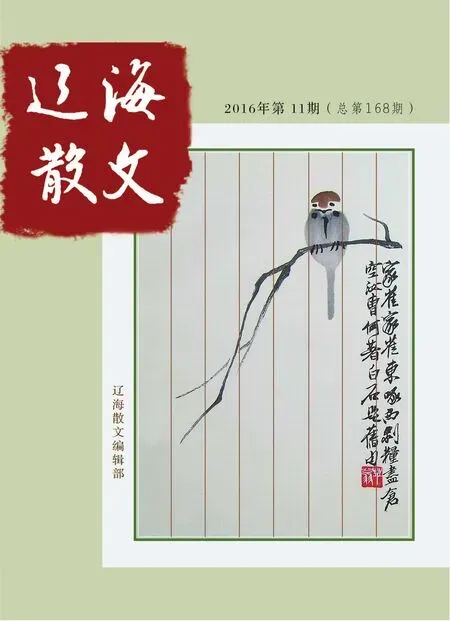阿里山上檜木林
雷振民
阿里山上檜木林
雷振民

雷振民
1931年9月生,遼寧臺安人。沈陽市人民政府經信委離休干部。沈陽市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新詩學會理事,遼寧省散文學會會員,遼寧省詩詞學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多種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和詩歌。出版個人詩集 《流云》《瀟瀟雨》《瑟瑟秋風》《反腐倡廉的歌》《后花園的神話和傳說》等。
我和女兒加入一支由16人組成的旅游團,到臺灣已經3天了。我們在臺北,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故宮博物院,拜謁了國父紀念館,登上了101大廈,俯瞰了臺北市美麗的街景;在臺中和南投,參觀了中臺禪寺,游覽了日月潭……深感大開眼界,收獲頗豐。此刻,大家心里最盼望的是能夠盡快到阿里山一游。多年來,我讀過阿里山的報道,聽過阿里山的故事,阿里山的美麗吸引著我,阿里山的神秘呼喚著我,阿里山時而閃現在我的夢境中。
這一天,我們到了南投縣的埔里鎮,邵族的青年男女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邵族是臺灣14個少數民族中最小的一個民族,現在只有283人,人們說它是“袖珍族”,要比大熊貓還少。說起來,這個民族和阿里山是有不解之緣的。傳說,400多年前,獵人追逐一只白鹿,翻山越嶺來到了這里,而后又帶來了一些獵戶,落腳在阿里山地區,后來就形成了具有獨特語言和生活習慣的邵族。今天看到了邵族青年的熱情和美麗,我的心中為之一振,他們先是大聲歡迎祖國來的親人,而后又用歌舞慰勞我們。聽到“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的吟唱,我仿佛已經走進了阿里山,也許,這該是暢游阿里山的“前奏”和“序曲”吧。
是日,大家起得很早,從云林縣的土庫鎮到阿里山有幾個小時車程。我們的旅游車開得很快,也開得很穩,但去往阿里山的路是難走的,難在多彎上。據說,登山的路,空間距離只有15公里,但是順山道一層一層地繞上去,要走72公里。這比上廬山“躍上蔥蘢四百旋”還費力氣。我們的車子繞來繞去,忽上忽下,有的人不適應,開始頭暈了。我不暈車,而且興致很高,目不轉睛地看著車窗外的風景。那一片片的椰子林,一排排的檳榔樹,一塊塊的香蕉園……似乎在招手,歡迎我們的到來。山間青枝綠葉,繁茂可人,這和此時正處在“千里冰封”的北國風光是迥然不同的,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下車了,天有點陰,但沒有下雨。我伸開雙臂,高興地說:“終于登上了朝思暮想的阿里山,我圓夢了!”說起阿里山,也有一個美好的故事。相傳很早以前,有一位酋長叫阿巴里,他英勇驍悍,能騎善獵,只身翻山越嶺,來到了這里,見山林茂密,獵物很多,留戀不已,而后常帶一些族人前來狩獵,且戰果輝煌。人們很敬仰他,于是借用他的名字,把這里叫作“阿里山”。其實,阿里山并不是一座山的名稱,而是一個山脈,是臺灣最高山玉山山脈的支脈。它是地跨南投、嘉義兩縣的大武巒山、尖山、祝山、塔山等18座大山的總和體,最高處達2600多米。
我們在導游的引領下,走進了阿里山檜木林。阿里山是盛產檜木的地方,特別是紅檜木。它生長在海拔1700多米以上的高山上,色澤淡紅,質地細膩,木性堅實,耐朽力高,是世界上的珍貴樹種。它在世界上的產量很少,只有中國臺灣、韓國、日本和北美的一些地方出產,是稀有的古生植物,被稱為活化石。說起阿里山的檜木,特別是紅檜,曾遭受過莫大的劫難。100多年前,日本有位名叫琴山河合的林業博士,發現了阿里山的檜木林,興奮不已,于是千方百計地想把這里的檜木盜伐下來,運往日本。但他考察來考察去,覺得這些檜木難以運出,一籌莫展。正在這時,他遇到了山里的一位農民,談及此事,于是農民出了個修筑小鐵路的主意,這使他茅塞頓開,從而下了很大的力氣,開通了小火車,把阿里山的檜木,源源不斷地運出了大山,運到了日本。這一來就是30多年,到二戰結束,這里的檜木已被日本砍伐殆盡。這位林業博士盜伐阿里山的檜木,對于日本來說,“功不可沒”,當時還給他立了一塊紀念碑。我們在山林中看到了這塊實為恥辱柱的石碑,上面寫著“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在這幾個字當中,不僅看到這位林業博士為日本大肆掠奪效力的一面,也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因為他覺得作為日本的林業博士,遠不如臺灣的一位農民。因此,他在碑中“博士”的“博”字上少寫了一點,意思是我這個博士還差一點;把 “旌功”的“功”字右邊的“力”字寫成了“刀”,意味著“功”也差一點。其實功勞越大,只能說明賣的力氣越大,對臺灣的掠奪也越嚴重。不論怎么說,這塊石碑,都是日本侵略者掠奪臺灣物資的罪行鐵證。
在偌大的檜木林中,原來有一棵樹,被譽為阿里山的“神木”,那是一棵有著3000多年樹齡的紅檜,日本人在1906年發現了它。它樹高53米,直徑4.66米,樹干接地處周圍有23米,得十幾個人才能合抱。這棵檜木,無論是樹齡和胸徑均為亞洲第一。可惜,1956年被雷擊毀。此后,臺灣當局整理出28棵巨大的檜木,有的樹齡在兩千年以上,稱為“千歲檜”。阿里山的人民精心地保護著這些檜木,使之枝繁葉茂,生生不息。有一句話叫“不看神木,就不能稱到過阿里山”。遺憾的是,原來的神木早已作古,我們只能欣賞第二代第三代的尊容了。
我們在大山中,還看到了許多當年被盜伐留下的檜木樹根,形狀各異,有些還長滿了青苔,既給人一種地老天荒的滄桑,也給人一種千姿百態的美感。有一處景點,被稱為“三代木”,爺爺輩的老樹根已經死去,兒子輩的再生樹也已失去生機,現在只有長在原處的孫子輩的檜木,郁郁蔥蔥,欣欣向榮。我在“三代木”前站立良久,端詳著這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情景,感觸多端。在一處叫作“象鼻樹”的大樹根前,我撫摸著它的滿臉皺紋,似乎也看到了它的老淚縱橫,不禁有點心酸。阿里山中,還有兩棵裸露的樹根搭在一起,極似牽手狀的“永結同心”樹,有兩棵樹根交織在一起的“龍鳳樹”,有三棵樹是同根的“三兄弟樹”……在“檜木博物館”里,我看到了一些檜木家具和檜木工藝品。那些栩栩如生的雄雞、綿羊,那些美麗誘人的瓜果、花卉,那些體態傳神的仕女和佛像,無不展現著檜木的質地之美、品位之高,令人愛不釋手。
人們心目中,阿里山有四景:日出、云海、晚霞和森林。我覺得日出、云海和晚霞到處都有,唯有那郁郁蔥蔥的檜木林,才是阿里山最珍貴的景觀。下山時,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我想,這該是檜木林在和我們淚別吧!
責任編輯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