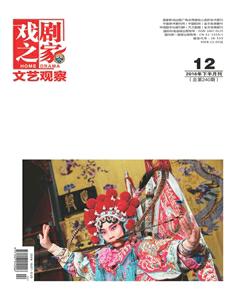從《邊境上的波旁威士忌》看克里奇的黑人民權(quán)意識
閆 麗,白錫漢
(陜西理工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 陜西 漢中 723001)
從《邊境上的波旁威士忌》看克里奇的黑人民權(quán)意識
閆 麗,白錫漢
(陜西理工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 陜西 漢中 723001)
當(dāng)代美國黑人女性劇作家帕爾·克里奇的戲劇無不展現(xiàn)了她的黑人女性思想及民權(quán)意識,揭示了黑人反抗白人壓迫、黑人探索民權(quán)平等之路所經(jīng)歷的從覺醒到反抗的艱難歷程。本文通過分析她的《邊境上的波旁威士忌》中黑人為實(shí)現(xiàn)人身自由、民權(quán)平等所付出的努力,挖掘民權(quán)運(yùn)動影響下的美國黑人自我反抗意識的覺醒,以及為自由和平等抗?fàn)幍臎Q心。
民權(quán)意識;種族歧視;覺醒
20世紀(jì)初的美國正處于社會動蕩不安的時期,隨著白人文化及思想觀念的逐步滲透,黑人因膚色、種族等原因遭到白人不公平對待,失去了平等的民權(quán)。在這種社會浪潮的影響下,涌現(xiàn)出許多非裔美國作家,他們運(yùn)用文學(xué)為黑人的自由和平等權(quán)利吶喊,非裔美國文學(xué)隨之逐步興起并從邊緣走向中心。作為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壇上的杰出代表之一,帕爾·克里奇以其獨(dú)特的視角和發(fā)人深省的作品,帶動了美國文學(xué)和文化領(lǐng)域的新思潮。她劇中所關(guān)注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反霸權(quán)、爭取公正和正義等問題可以跨越國界,對任何存在男性知識霸權(quán)和種族優(yōu)越感的地區(qū)都有實(shí)際意義。同時,她是一個用現(xiàn)實(shí)來說話的女性作家,面對黑人的一切痛苦和遭遇,她用樸實(shí)的語言將黑人生活狀況和身心壓迫真實(shí)地展現(xiàn)給讀者,細(xì)致地將20世紀(jì)60年代民權(quán)運(yùn)動下美國黑人渴望自由和平等的反抗心理以戲劇的方式加以呈現(xiàn)。她的作品既表現(xiàn)了黑人對白人的憎惡情感,又剔除了懷舊的美好愿望,用自己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毫不避諱地探索了民權(quán)運(yùn)動的黑暗面。她的《邊境上的波旁威士忌》正是展現(xiàn)其作品主題和風(fēng)格的代表作。該作品以出人意料的結(jié)局為其增添了獨(dú)特性;她沒有讓黑人與白人的斗爭以一種完美的結(jié)局收工,而是讓這種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和非人性的殺戮罪惡永遠(yuǎn)無法得到彌補(bǔ),從而揭示種族歧視造成的傷害對于黑人個人、家庭乃至整個黑人種族而言是不可原諒的。這種悲劇色彩與人道主義貫穿于劇作始終,使得對正義的呼喚、生命的樂觀和人性的剖析成為美國黑人女性文學(xué)領(lǐng)域的主旋律,也表現(xiàn)了黑人民權(quán)意識在那個時代的覺醒。[1]
一、誓死捍衛(wèi)黑人尊嚴(yán)的激進(jìn)分子——查理
查理(Charlie)和梅(May)像霍華德大學(xué)里的很多活躍分子一樣,在校園結(jié)識,因有著為黑人而戰(zhàn)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走在了一起。他們一起去密西西比嘗試登記黑人選舉,以獲得選舉權(quán)。提起密西西比州,它當(dāng)時是一個黑人備受壓迫的象征地,生活在那里的黑人深受種族歧視觀念的迫害,各種隔離政策使黑人生活窘迫到極致甚至被殘暴殺害,而對于當(dāng)時備受壓迫的美國黑人而言這些只是冰山一角。查理和梅作為當(dāng)時激進(jìn)分子中的學(xué)生代表之一,憑借他們的薄弱力量,要做到這一切付出相應(yīng)的代價(jià)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在爭取選舉權(quán)的時候不幸被白人警察逮捕。那些白人警察要求查理用鞭子抽打梅,否則他們就強(qiáng)奸梅。很顯然這種非人的做法查理做不出來。然而,喪失道德準(zhǔn)則的白人警察最終不僅用鞭子毒打梅,甚至就在梅險(xiǎn)些被打死的時候,他們當(dāng)著查理的面仍然無情地強(qiáng)奸了她,致使她從此失去生育能力。眼前白人警察的所作所為對查理而言無疑于晴天霹靂,他內(nèi)心的無助讓他無所適從,根本沒有能力保護(hù)心愛的人。白人對待他們的這種殘忍粗暴的折磨手段更加劇了他內(nèi)心對白人的極端憎惡,讓他認(rèn)識到美國政治制度和法律布滿了種族歧視的烙印。
在查理和他鄰居泰倫(Tyrone)的對話中,查理告訴他,“當(dāng)白人警察把他扔進(jìn)洞里的時候,他們說獲得公平的前提就是要為他們服務(wù),當(dāng)然也可以繼續(xù)堅(jiān)持反抗意識,兩者之間由他決定。”[2]很明顯他們在分散查理的注意力,查理深知他們口中所謂的公平就是把黑人當(dāng)成奴隸為白人服務(wù)。因此他繼續(xù)保持抗?fàn)幍降椎臎Q心,沒有向他們代表的白人邪惡勢力低頭。查理在監(jiān)獄里忍受著心理和身體上的摧殘,種族暴力的存在時刻沖擊著他的內(nèi)心世界,最終導(dǎo)致其精神世界的崩潰。查理在走出精神病院后舉目無親且遭受著經(jīng)濟(jì)危機(jī),但他對白人的憎惡感從未削減。在遭受了白人的重重打擊之后,他意識到只有通過武力反抗才能爭取黑人民權(quán)、贏得黑人尊嚴(yán),因而他又冒著風(fēng)險(xiǎn)報(bào)復(fù)殺害白人。盡管他犯了謀殺罪,采用暴力方式殺害白人,但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人們對他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因?yàn)檫@一切行為只是他在爭取民權(quán)和遭受折磨后的正常反擊。雖然其做法與美國倡導(dǎo)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意識相違背,但作為激進(jìn)分子,他的潛意識行為展現(xiàn)的則是所謂的美國式“民主”的惡性后果。查理和梅浪漫而又悲劇化的愛情既展現(xiàn)著愛的偉大,為他們帶去了溫暖與愛意,又揭露了美國社會的丑陋面目,折射出種族歧視問題的突出。查理用死亡結(jié)束生命,表達(dá)了他反抗種族壓迫和歧視的堅(jiān)定決心,喚醒了種族歧視下美國黑人民權(quán)意識的覺醒,讓黑人民族充分認(rèn)識到只有實(shí)現(xiàn)真正的民權(quán)平等,才能消除種族歧視、重塑黑人自信、提高黑人的社會地位。
二、為民權(quán)吶喊的黑人女性——梅
在劇中,梅作為查理的所愛之人,在他們的不斷反抗之下還是無法擺脫被美國白人警察強(qiáng)奸的事實(shí),不言而喻這是蹂躪婦女、踐踏女性的非人性做法。對美國黑人女性而言,她們不僅要反對性別歧視,而且還肩負(fù)著另一種使命,即同黑人男性站在反對種族迫害和種族歧視的同一戰(zhàn)壕里。[3]
非裔美國文學(xué)中的人道主義情懷無不滲透著對黑人女性的關(guān)注和對黑人民權(quán)的呼吁,克里奇在《邊境上的波旁威士忌》中對梅這個人物的刻畫便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白人警察在查理無助的情況下殘忍地強(qiáng)奸了梅,并且肯定這一做法會激怒查理,如此違背人道主義的行為讓讀者明顯感覺到他們在玩弄、侮辱黑人。當(dāng)梅迫使自己忘記這段悲痛記憶的時候,鄰居羅莎(Rosa)在不了解梅的心理感受的情況下提到這個敏感的話題深深地刺激了梅。在羅莎問梅,“你總是在談查理的狀況,那你呢?”很顯然,她不懂查理對于梅的意義。“我活下來了,他卻沒有”是梅對羅莎的回答,言語中充滿著梅痛苦的心情。但是羅莎不可能理解白人警察對梅身體和精神的折磨到底有多么深,只有在梅細(xì)述了她和查理在白人警察手里遭受的非人待遇,告訴她“沒有什么事情是他們干不出來的”時候,羅莎仿佛才懂得白人的暴力方式對梅來說真的是毀滅性的傷害。羅莎內(nèi)心為此很不是滋味,用“真的很抱歉”安慰梅,但梅無奈說到,“你抱歉什么?對不起什么?對不起查理遭遇如此糟糕的境況嗎?對不起他們深深地傷害了我未出世的孩子嗎?對不起他們在密西西比州的那個夏天徹底毀滅了我們的美好生活嗎?”[2]克里奇在此運(yùn)用排比及反問的手法將此時梅內(nèi)心的復(fù)雜心理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字里行間流露出梅的憤怒和無奈,有著梅對查理的無限思念,對羅莎不理解自己心情的煩躁,更多的是梅對白人的深深恨意,它就像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在梅的內(nèi)心深處。作為黑人女性,這些慘痛的傷害不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從她們心中抹去。在民權(quán)運(yùn)動中,梅同很多不知名的黑人一樣將永遠(yuǎn)記得種族戰(zhàn)爭中遭受的創(chuàng)傷。然而身處壓迫與欺辱下的女性又是如此勇敢、偉大,正如劇中尼爾·盎格撒魯(Nell Irvin)這個畫家所說,“女性為了證明她們成功超越了為種族而服務(wù)的壓迫,常常希望抑制這種遭遇不幸事件后的無奈感。”[2]為了減輕黑人種族在壓迫中所遭遇的種種傷痛,黑人女性成為了黑人和白人戰(zhàn)爭之間的犧牲品,這也讓讀者更加體會到黑人女性對于整個黑人種族的貢獻(xiàn)之大以及對黑人早日獲得平等和自由的渴望。
三、散發(fā)人性的光輝的鄰居泰倫
泰倫作為羅莎的男朋友,查理的鄰居,當(dāng)他聽見查理說被白人警察侮辱甚至人身攻擊的時候,他說道,“該死的混賬(白人警察)。老兄,那是無休止的暴力折磨,當(dāng)他們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必須反擊!”[2]從他坦誠而直接的語言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畏懼白人勢力,流露著他對白人的憎惡和對查理的關(guān)心,但他不知道查理的反抗在強(qiáng)權(quán)的白人警察面前顯得那么無力,因?yàn)椋绮槔硭f的,“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警察所得到的一切財(cái)富,都是通過剝削黑人所獲得的,這種行為如此卑鄙,我也不想看見他們。”[2]鋒利的語言猶如一把利劍,抨擊了白人剝削壓迫黑人的卑鄙行為,揭露了白人的虛偽丑陋面目,同時將查理內(nèi)心的無助和憤怒之情,以及泰倫對查理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對種族歧視的憎恨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查理被白人警察逮捕后遭受著身體的折磨、精神的崩潰、親人的遠(yuǎn)離,但泰倫并沒有因?yàn)椴槔淼牟恍以庥龆柽h(yuǎn)查理。作為查理的近鄰,泰倫用真誠給無助的查理以精神力量和心理安慰。當(dāng)查理最后一次從精神病院放出來的前三個禮拜,在泰倫的幫助下查理成為一名卡車司機(jī),這讓查理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情況漸漸好轉(zhuǎn),也讓查理在冷冷的黑夜里看到了愛的光芒,看到了當(dāng)時黑暗之下人性的溫暖與感動。
四、結(jié)語
被認(rèn)為是美國歷史上“第二次內(nèi)戰(zhàn)”的美國“民權(quán)運(yùn)動”不僅啟迪了美國黑人作家,也激發(fā)了克里奇的創(chuàng)作靈感并為其提供了創(chuàng)作素材。在《邊境上的波旁威士忌》中,克里奇以嚴(yán)肅的藝術(shù)態(tài)度從生活中提煉材料,描寫出當(dāng)時社會背景下美國黑人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展現(xiàn)了黑人為自我權(quán)利而抗?fàn)幍挠X醒意識。她筆下刻畫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們有著普通的人生目標(biāo)和人生態(tài)度,有各自獨(dú)特卻為所有人所熟知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作品將黑人的真實(shí)一面實(shí)實(shí)在在地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真實(shí)而普通,不夸張、不討好、也不自卑。這樣的理性認(rèn)識使所有人都意識到黑人不是原來白人眼中的“怪物”、“洪水猛獸”,而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們不應(yīng)該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對待。對于美國黑人種族而言,民權(quán)運(yùn)動下黑人民權(quán)意識的覺醒和反抗精神是一種自我維權(quán)的主觀意識的體現(xiàn),不僅對后來美國黑人的命運(yùn)產(chǎn)生重要影響,賦予他們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平等權(quán)利,也對所有美國人的意識形態(tài)產(chǎn)生深刻意義。民權(quán)運(yùn)動推動了黑人民權(quán)意識的覺醒,也為黑人贏得一定程度上的權(quán)利。它把美國從一個容忍種族主義、歧視黑人的社會轉(zhuǎn)變?yōu)橐粋€不論膚色、宗教、種族如何,承認(rèn)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民權(quán)的社會,從而逐步改變美國人的思想觀念。
[1]楊玲.20世紀(jì)美國黑人女性小說的人道主義情懷[D].湖南師范大學(xué),2007.
[2]Pearl Cleage. Bourbon at the Border [M].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1997.
[3]梁昕.她們離天堂究竟有多遠(yuǎn)——淺論20世紀(jì)美國黑人女性文學(xué)對“自我”的追尋[D]. 南京師范大學(xué),2007.
第一作者:閆 麗,女,陜西省寶雞市人,陜西理工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英語專業(yè)本科;
第二作者:白錫漢,男,陜西省漢中市人,陜西理工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國女性戲劇。
J805
A
1007-0125(2016)12-0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