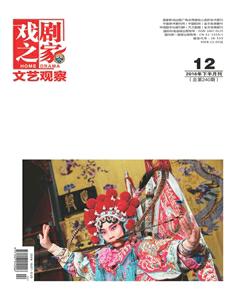譚恩美小說《喜福會》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蘇虹蕾
(吉林省社會科學(xué)院 吉林 長春 130033)
譚恩美小說《喜福會》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蘇虹蕾
(吉林省社會科學(xué)院 吉林 長春 130033)
華裔作家譚恩美,將創(chuàng)作的視角聚焦在中國母親以及女兒身上,講述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母親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成長的女兒,在思想、價值觀、婚戀觀以及具體生活細(xì)節(jié)等方面的矛盾與沖突。作品既涉及到異國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碰撞,又真實展現(xiàn)了移民生活境遇等問題。譚恩美小說的中心人物,往往都是女性。本文從母親的身份困境、女兒的身份構(gòu)建、母女關(guān)系由沖突到和解等三個方面,對《喜福會》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分析。
譚恩美;《喜福會》;母女;女性形象
譚恩美,美籍華裔作家,是美國當(dāng)代文壇女性主義作家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品有《喜福會》《灶神之妻》《接骨師之女》等。譚恩美將創(chuàng)作的視角聚焦在中國母親以及女兒身上,講述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母親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成長的女兒,在思想、價值觀、婚戀觀以及具體生活細(xì)節(jié)等方面的矛盾與沖突。作品既涉及到異國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碰撞,又真實展示了移民生活境遇等問題。
譚恩美小說中所反映的問題是每一個移民都有可能遇到的問題,在世界移民人數(shù)明顯遞增的情況下,譚恩美的作品無疑具有一定的指導(dǎo)和借鑒意義。其在某種程度上,是廣大海外移民們在身份構(gòu)建以及文化認(rèn)同過程中自身遭遇的真實反映。這類作品在出版之后不僅在美國本土獲得了廣泛的關(guān)注,而且在中國也引起了一股閱讀熱潮,高居暢銷書榜首,成為國內(nèi)學(xué)者研究的熱門問題。國內(nèi)對譚恩美小說的相關(guān)研究開始的較早,研究范圍也比較廣泛,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針對小說主題的研究。研究者從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入手,探尋異國語境下移民文化身份的獲得、自我身份的定位等問題。第二,從女性主義出發(fā),研究從湯婷婷到譚恩美等華裔女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演變等問題。第三,研究小說的敘事特征。從現(xiàn)代主義、拼貼手法以及復(fù)調(diào)小說等角度出發(fā)來解構(gòu)小說的結(jié)構(gòu),探究其結(jié)構(gòu)特征。身為女作家的譚恩美,其小說的中心人物,往往都是女性。本文即以此為切入點,從母親的身份困境、女兒的身份構(gòu)建、母女關(guān)系由沖突到和解三個方面,對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分析。
一、母親的身份困境
必須承認(rèn)的是,在當(dāng)代社會,家庭地位正在被邊緣化。通訊技術(shù)的進步帶來的社交領(lǐng)域的擴大(而這一點在經(jīng)濟、科技更為發(fā)達的西方社會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家庭對私人生活的影響正在縮小。但家庭依然是絕大多數(shù)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學(xué)熱衷表現(xiàn)的對象之一。在譚恩美的小說中,家庭是敘事核心。《喜福會》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講述了四個中國移民母親以及四個華裔女兒在美國的生活,以及母親們在培養(yǎng)下一代的過程中如何面對文化沖突、身份認(rèn)同,以及與作為第二代移民的女兒在相處過程中情感上的問題。
首先,移民母親們在美國的生活狀況以及她們在融入主流文化過程中的心路歷程是小說《喜福會》探究的主要問題,譚恩美對她們的身份和命運十分關(guān)注。與大多數(shù)既不被美國社會接受,又不認(rèn)同母國文化的大多數(shù)移民不同,在譚恩美的筆下,以《喜福會》中的母親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身上還保留著較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子。母親們在中國經(jīng)歷過各種各樣的苦難,在苦難的生活中領(lǐng)悟到人生的真理,這些真理受用一生,支撐著她們在異國他鄉(xiāng)的苦悶生活。小說中的四位母親各有各的不幸,她們的內(nèi)心是千瘡百孔的。在踏入美國國土之前,在中國都有過慘絕人寰的經(jīng)歷。美國是母親們苦難生活中的“救命稻草”,是希望的象征。他們滿懷著希望來到美國,但現(xiàn)實情況卻并非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母親們只身一人來到異國他鄉(xiāng),語言不通、文化不同,大多數(shù)情況下她們只能從事一些卑賤的工作,生活在美國社會的最底層,無法融入到主流社會中去。而對于美國人來說,中國是作為異質(zhì)文化來審視、接受的,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形象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歷經(jīng)了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但多數(shù)人的認(rèn)識都走向極端化,要么理想化,要么妖魔化。而《喜福會》中的背景,則是“黃禍論”有甚囂塵上之趨勢,彼時中國人難以收到美國主流社會的認(rèn)同是自然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母親們對祖國、家人的思鄉(xiāng)之情就會更加強烈,母親們的生活是苦悶的,她們大多數(shù)時間內(nèi)只能在東西方文化的夾層中生存。
其次,身份焦慮與身份危機問題是每一個移民都會遇到的問題,尤其對于第一代移民來說這個問題顯得更為棘手。小說中的母親大都在青年或者中年時期來到美國,沒有任何關(guān)系可以依靠,一切從零開始。她們在青年時期所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勢必會與美國的主流文化價值進行碰撞,因而導(dǎo)致她們對自我身份的困惑和疑慮。遠(yuǎn)離了賴以生存的文化,就如同切斷了她們生存之根本,在這種情況下又被異質(zhì)文化所拒絕,這
樣的生活無疑是苦悶的。在這個過程中她們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情感上的痛苦和掙扎,重新認(rèn)識自我、重新定位自我,由排斥異質(zhì)文化,到逐步被其同化,再到認(rèn)同,與中國文化融合貫通,這一過程是極其漫長的。小說中母親們所經(jīng)歷的迷茫是現(xiàn)在所有移民所共同經(jīng)歷的,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二、女兒的身份構(gòu)建
《喜福會》中的女兒們是帶有華人血統(tǒng)的美國人,她們雖然出生在美國,是法律意義上的美國人,但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使她們在身份構(gòu)建過程中仍然遭遇困惑,一如她們的母輩一樣。在西方人眼中,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人的形象也會發(fā)生變化,但種族偏見卻是很難消除的,這也成為《喜福會》中的女兒面對的藩籬。
首先,小說中的女兒們是第二代移民,她們出生、生長在美國,她們接受的是西方價值觀念,操著一口地道而又流利的英語,她們思維方式完全是西化的。女兒們對故鄉(xiāng)的感覺是陌生的,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往往嗤之以鼻。關(guān)于中國的記憶完全來自于母親。母親們往往不厭其煩地向孩子講訴她們的母國,以此來強化她們對母國的認(rèn)同感。這種做法往往恰得其反。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兒們從未把自己當(dāng)中國人看,甚至極力否定自己的中國血統(tǒng)。女兒們?yōu)榱顺晒θ谌胫髁鞯奈幕瑪[脫作為二代移民被排斥和歧視的處境,她們絕對認(rèn)同美國主流文化以及價值觀,因而他們對于母親絮絮叨叨的中國文化的灌輸相當(dāng)反感,并加以反抗。吳精美與媽媽的一段對話清晰地展現(xiàn)了二代移民對自己母國文化的排斥:“當(dāng)時我強烈否認(rèn)在我的體內(nèi)有哪怕那么一點點所謂中國性的東西。那時我是舊金山伽利略高中二年級學(xué)生,我所有的白人朋友都同意,我和他們完全一樣,與中國人沒有絲毫相同之處。”這段簡單的話語犀利而又發(fā)人深省,反映出第二代移民在身份構(gòu)建過程中的焦慮與極力擺脫母國文化影響的強烈愿望。
其次,女兒與母親在擁有兩種不同文化氛圍的社會環(huán)境中成長,差異是不可避免的。但女兒們身上遺傳著來自母親的基因,這一點又是不能夠否認(rèn)的。盡管第二代移民在身份構(gòu)建的初期極力否認(rèn)母親所攜帶的母國文化的影響,但卻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響,這在小說《喜福會》中有所表現(xiàn)。女兒們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正是母親們具有神秘東方色彩的人生哲理指引她們走出困境,領(lǐng)悟到生活的真諦。其中一位女兒露絲因為離婚備受打擊,失去自我。正是來自母親的深切關(guān)懷幫助她走出低谷。而母親對她的教誨卻是她多年來一直排斥、鄙視的。盡管這樣,她們也無法從真正意義上理解中國文化,終其一生,她們與中國文化之間始終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復(fù)雜關(guān)系。
三、母女關(guān)系從沖突到和解
小說中的母女關(guān)系經(jīng)歷一個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以生活在美國的女兒對華裔母親的排斥到理解為轉(zhuǎn)折點,是社會意義上的中西方文化融合、同化的必然結(jié)果。這也就意味著小說中母女關(guān)系的沖突到緩和的過程是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所面對的共同問題,這一創(chuàng)作特色普遍存在于華裔女作家筆下。
首先,從本質(zhì)上看,母女關(guān)系沖突的實質(zhì)是中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以東西方教育觀念上的差異為例,媽媽們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鮮明地體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她們把全部的愛給予女兒,將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她們能夠擺脫這種“外來者”的身份。于是母親們在生活上和情感上試圖全面掌控女兒的人生,希望她們能夠出人頭地,試圖把自己的缺失或者遺憾在兒女身上得到彌補,這是典型的“望女成鳳”的中國式父母。女兒薇弗萊在下棋方面有驚人的天賦,獲得了無數(shù)榮耀。其母感到無比高興,逢人便夸耀自己的女兒,甚至在大街上拿著一本以女兒作為封面的雜志向行人炫耀。而女兒對其行為卻極為反感。西方教育以鼓勵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主旨,女兒認(rèn)為榮譽是她獲得的,與母親無關(guān),母親是沒有權(quán)利這樣做的。類似于這樣因為教育觀念不同引發(fā)的沖突,在小說中比比皆是,這也是導(dǎo)致母女關(guān)系疏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文化及思維方式的差異,母女之間也常常產(chǎn)生一些隔膜和沖突。從某個層面上看,《喜福會》中的母女在精神上是相互疏離的。女兒吳精美在媽媽去世后才發(fā)現(xiàn),母女二人似乎從來沒有走入過對方的內(nèi)心,她們經(jīng)常從自己的立場出發(fā)來揣摩彼此的意圖,卻從未有過深入透徹的交流和溝通。女兒對母親身上的種種中國“陋習(xí)”既不理解又強烈不滿,母親對女兒的西化行為有時也表現(xiàn)出反感。比如,小說中的一個女兒交了男朋友,卻怕得不到媽媽的認(rèn)可,因而采取叛逆的態(tài)度。而事實上,媽媽對他的男朋友是喜歡的。二人卻從未就這一問題進行溝通,因而導(dǎo)致沖突的發(fā)生。小說的最后,母親關(guān)系得到緩和,女兒們逐漸了解她們的媽媽,愿意傾聽和溝通,這意味著女兒們開始接受媽媽所代表的具有中國色彩的文化,是母女關(guān)系緩和的重要前提條件。
譚恩美通過小說中母親和女兒的遭遇,來審視整個華裔群體在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社會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尷尬,以及其過程中的辛酸冷暖。從美國人的視角講述發(fā)生在移民身上的悲歡離合,與中國人描寫中國文化的視角區(qū)別巨大。
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閱讀體驗,在族裔文學(xué)的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程愛民.美國華裔文學(xu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
[2]程愛民.論譚恩美小說中的母親形象及母女關(guān)系的文化內(nèi)涵[J].南京師大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1,(4):107-113.
[3]包麗麗.華裔美國女性文學(xué)的興起與譚恩美的《喜福會》[J].當(dāng)代外國文學(xué),2003,(3):73-76.
蘇虹蕾(1982-),吉林省長春市人,吉林省社會科學(xué)院(社科聯(lián))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文學(xué)理論。
I06
A
1007-0125(2016)12-026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