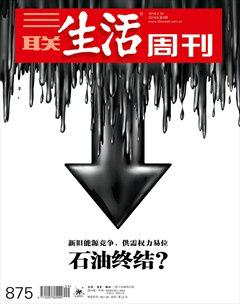石油:被重置的供需關系,以及不可逆
吳琪

美國阿帕奇公司在得克薩斯州帕米亞盆地投資的天然氣勘探基地
“撿漏”的石油個體戶們
1998年年末,對于喬治·米切爾來說,人生到了最為艱難的時刻。他創辦了52年的米切爾能源公司的股票在這一年內跌了50%,跌破10美元。也正是在這一年,這位79歲的老人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需要接受一系列痛苦的治療,而他的妻子辛迪亞則被診斷出老年癡呆癥。股價暴跌后,銀行開始要求米切爾還貸或者增加抵押物。為了籌措資金,米切爾甚至違反合同,中止了向慈善團體的捐款,面臨著被起訴的風險。
喬治·米切爾是美國的第二代移民,他1940年拿到石油工程的學位,1946年和哥哥一起開辦石油鉆探公司。他從沒預料自己會參與改變歷史,卻成為歷史轉折點上一小群人物中的一員。在《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格雷戈里·祖克曼的書《頁巖革命——新能源億萬富豪背后的驚人故事》里,祖克曼用紀實手法,寫下了能源行業里新一批淘金者的故事。
“二戰”以后,美國一些人涌入喬治·米切爾所在的得克薩斯州,干起“石油個體戶”。所謂個體戶,是相較于石油巨頭埃克森公司和雪弗龍公司等而言,這些人單槍匹馬或是簡單結合成小團體,米切爾這樣的技術公司負責找油,投資人提供運轉資金。
能源市場的價格時好時壞,米切爾的小公司經常在風浪中起伏,管理層之間總是發生沖突,互相吼叫,他們自嘲為“靠分貝的大小來管理公司”。米切爾很早就意識到天然氣將會有市場,于是避開多數人競爭的油田,專心尋找天然氣。1957年,他的公司幸運地獲得了一份給芝加哥輸送天然氣的20年合同,負責芝加哥10%的天然氣供應量,這項業務成為米歇爾能源公司的生命線。1977年該合同得以續約,但是到了1995年,米切爾的主要客戶——美國天然氣管道公司——提前兩年買斷了他們之間長達20年的合同。
米切爾失去了最大的客戶,而市場上天然氣的行情不斷走低,他壓力陡增。多年來,米切爾還一直干著不被行內人看好的事情——用壓裂的方法,試圖從頁巖層里開采出天然氣。到1998年危機來臨時,他已經投資了近3億美元、苦干了17年。數年來,他在自己認為富含天然氣的頁巖地帶,不斷以低價租下土地。但是即使在公司內部,也幾乎沒有人贊同米切爾的做法,包括他的兒子。開發頁巖層,看上去是愚公移山式的蠢事。
地表以下的巖層是一層一層疊加起來的,像是千層餅,頁巖是千層餅最底部的一層,埋在地下兩英里處。鉆探的工人們一直認為,要想在美國任何地方鉆探頁巖都是徒勞的,盡管里邊很可能有天然氣。幾十年來,石油開采都集中在近地表的巖層,20世紀80年代,近地表巖層中越來越難找到大的油床和氣床,所以米切爾對開采深層巖層有興趣。
在行業內的人們看來,頁巖是基礎巖石,它是大多數在地表發現的石油和天然氣的來源基地。但是幾乎沒什么地質學家主張直接開采頁巖,雖然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鎖在里邊,可是從這些堅硬無比的石頭里開采,顯然成本太高。它們在億萬年的地質運動中,被壓縮得太厲害了。當人們在常規油氣田里就能開采資源時,誰愿意去非常規油氣層里碰壁呢?
美國的石油巨頭們,早就不屑于在國內找油田。在美國于上世紀70年代達到國內油田產量的高峰之后,石油巨頭們在80年代紛紛轉向去海外市場盈利。它們堅信美國本土上的“大象”油田已經枯竭。于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主要油田都是由石油個體戶們發現的。像米切爾這樣的“個體戶”,在石油巨頭們看來就是撿漏的,在大公司不屑于去做的事情中尋找機會。在頁巖里尋找機會,則更是被他們嘲笑為缺乏常識的事情。可是執著的個體戶們的特質是,大公司越鄙視他們,他們就越要頂風而上。
米切爾對頁巖氣的執著,一方面緣于他多年鉆探而獲得的模模糊糊的感覺,另一方面也是供氣的壓力所迫。對于石油個體戶們來說,不管機會多么渺茫,他們也樂于鼓吹,直到拿到資金購買土地,等著石油和天然氣抽出地面。
油氣鉆探的技術也發生著變化。多年實踐之后,人們開始由垂直鉆探變為傾斜鉆探,到后來發明出水平方向鉆探。這種新技術把鉆頭垂直打入地下數千英尺,然后像蛇一樣慢慢轉向,直到把鉆頭調成水平方向。這樣就可以鉆入狹長或者是多層的油氣庫,找到大量的油氣。水平鉆探的費用很高。當垂直鉆探的一口油井只需要35萬美元的時候,水平鉆探需要投入200多萬美元。“個體戶”之一的奧利克斯能源公司成功將成本降至65萬美元,使得水平鉆探值得一試。
多年的嘗試,使得米切爾和他的手下掌握了壓裂技術。這是一種非傳統的鉆探技術,他們用壓裂的方法將水、化學物質、沙子等灌入巖層,希望巖層受到沖擊后,石油和天然氣能從氣孔里釋放出來。米切爾并不是唯一的一個試吃螃蟹者,可是這些膽大的個體戶們并沒有突破性的進展,直到米切爾聘請來了年輕的技術負責人施泰因斯貝格爾。他比一般人更大膽,也更抗壓。施泰因斯貝格爾受到其他人啟發,決定以水為主要的原料來壓裂,而不用試驗了多次的昂貴的化學物質和膠狀物,他要使用潤滑水壓裂法。但專家們激烈反對他的做法,因為頁巖里有泥,很像是硬了的泥巴,如果往泥巴里加水,泥就會吸水膨脹,反而堵住了氣孔,天然氣冒不出來。
險中求勝
此時米切爾公司的財務狀況非常緊張,施泰因斯貝格爾想替公司省錢,他說服大家讓他降低成本來試一試。一開始,以水為主要原料的壓裂法打出的三口井,看上去與以往的井差別不大。但是慢慢地施泰因斯貝格爾發現,一般方法開采的氣井產量衰減很快,他用新方法打出的井,雖然產量不算大,可是一直沒有衰減。他和同事摸索著改進方法,壓裂出巖石的更多裂縫。終于他和老板米切爾一起,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潤滑水壓裂法不僅成本比使用化學膠狀物方法低,而且效果更好。頁巖并沒有像其他人預期的那樣吸水后膨脹,反而在高壓液體的沖擊下像玻璃一樣裂開,釋放出天然氣。以前使用的膠狀物把巖石的裂縫給粘住了,氣反倒出不來。
但也就是在技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這一步,米切爾能源公司卻陷入1998年的最低谷。公司已經負債累累,債權人不想再提供貸款,并且對于開采頁巖能否真的帶來利潤表示懷疑。好在1999年石油天然氣價格走高,米切爾下令公司繼續租地,并且把已經打過的井再打一遍,因為新的技術能從頁巖里打出更多的氣。此時80歲的米切爾由于癌癥影響,心不甘情不愿地準備賣掉公司。
可是,似乎沒有人對他的公司感興趣:他的技術太新了,他押寶的巴尼特地塊到底有多大潛力,難以評估。投資者害怕巴尼特頁巖雖能夠短期飆升產量,但很快就會衰減。肯特·鮑克是另一個執著于頁巖開采的人,他認為米切爾能源公司受到冷遇還有其他原因:“我們是在‘樹林城市(米切爾開發的一個地產項目)里的一群笨老頭,我們不是高智商的天才。我們只是從俄克拉荷馬州和得克薩斯州大學技術學院畢業的,只想保住米切爾的生意而已……我們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穿大褂的研究員,也沒有哈佛大學的頂尖畢業生。”當時正值美國網絡泡沫的頂峰時刻,隨便一只高科技概念的公司就能受到投資人追捧,米切爾這樣老老實實的能源公司卻被冷落。
米切爾于是在2000年放棄了賣公司的念頭,偷偷租下巴尼特地區更多土地。到了2001年8月,德文能源公司同意出31億美元買下米切爾能源公司,并承擔米切爾能源公司4億美元的債務。這個價位高出米切爾能源公司股份的20%,米切爾終于找到一個相信他的價值的接盤者。
米切爾和他的團隊接下來證明了自己的更大價值,他們押寶的得克薩斯州的巴尼特地區,將成為美國本土最大的天然氣產地,僅2013年的產量就占全國產量的6%。另外一些執著的個體戶們,接著又發現可以從頁巖里開采出大量的石油。大公司們開始關注美國市場了,他們終于開始明白,為什么米切爾20年前對頁巖那么興奮了。米切爾賣掉公司后,個人身家達到20億美元。他后來又和兒子聯手租賃土地,尋求到了新的財富,于2013年以94歲高齡去世。
但并非所有卷入這場變革的個體戶們都有這么好的運氣:有人投進全部家當,卻在勝利前一刻落敗而逃;有創始人因為公司政治被排擠出局;橫向打井技術的開發者因為買錯債券而讓自己和公司陷入困境……
當頁巖革命帶來的大勢已定時,大佬們在2011和2012年才開始爭相入場。倫敦的英國石油公司、挪威的國家石油公司、法國的道達爾公司都花了幾十億美元來收購、買進、合資經營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俄克拉荷馬州、得克薩斯州、阿肯色州還有其他地方的頁巖。一場由美國開始引發的頁巖革命,成為能源行業里引人注目的旋風。
產油國的“囚徒困境”
頁巖油氣大大改寫了美國的能源面貌,從頁巖中開發的能源屬于非常規能源,儲量比常規能源大得多。如果說過去開采常規能源,好比人們只會吃不帶刺的魚,現在有了新辦法,能夠吃帶刺的魚了,那么人們的食物來源就大大擴展了。石油產業發展到現在,可以說是把樹上掛下來最低的果子都摘了,現在只能不斷增加梯子的長度。在沒多少人看好的頁巖層,喬治·米切爾們改變了歷史。
2013年中,美國的石油日產量已經達到750萬桶。產量如此之高,一部分正是得益于使用了水平鉆探和多階段壓裂,使得得克薩斯州的帕米安盆地起死回生。另外,頁巖油含量豐富的巴肯和鷹津地區的產量也在持續升高。到了2015年7月,美國日產石油達到了950萬桶,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美國在1973年達到的920萬桶的峰值,并且美國原油庫存創歷史新高。2015年9月,美國解除了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對于傳統產油國來說,市場上又多了一個強勁的競爭者。美國作為曾經長居世界第一的石油進口國,2015年將此位置讓與了中國。

2011年坎布里奇能源研究協會年度論壇上,米切爾能源與發展公司前總裁喬治·米切爾獲頒終身成就獎

中國石油大學國際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龐昌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
當油價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暴跌時,市場上的供需關系再也難以支撐高油價。美國作為一個重要的砝碼,在供需的蹺蹺板上悄悄往供應方在移動著。頁巖油氣的開發不僅大大提升了美國油氣的產量,更重要的是,它展示出一幅完全不同于“石油峰值論”的前景:頁巖油氣儲量巨大,中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頁巖油氣儲量靠前。中國目前探明的頁巖氣多分布在崇山峻嶺間,地質條件復雜,美國、墨西哥的頁巖氣多分布在平坦地區,開采起來更容易。一旦頁巖油氣的技術在其他國家成熟,中東、俄羅斯等產油國面臨的壓力就更大。它們不僅面臨著常規化石能源的競爭,還面臨更為龐大的非常規化石能源的競爭,更何況其他新能源技術也隨時可能突破。能源看起來并不是越用越少,技術的突破和人們的危機意識,使得能源供給變得相當樂觀。如果一樣商品不再稀缺,誰還用只看供應者的臉色行事呢?
從歐佩克的角度來說,上世紀70年代禁運美國的霸氣早已不再。歐佩克作為一個價格的卡特爾存在著天然的經濟脆弱性。卡特爾的經濟學特征,使得成員因為偷偷增產享受固定定價帶來紅利從而趨向于卡特爾瓦解成為必然。80年代中期,由于歐佩克成員對生產和分配石油缺乏有效約束,結果使世界石油價格猛跌,西歐、日本和美國經濟受到震蕩,沙特經濟也受到重創。歐佩克先后通過產量配額監督、部長級監管委員會來監督、外部獨立機構監督等做法,但也無法完全杜絕成員國增產的情況。即使限產對大家都有利,也難以保證合作,各個國家的最佳利益,并非團體的最佳選擇,囚徒困境在此得不到破解。
而當世界油氣主要供應帶由“中東-蘇聯”一家獨大轉變為“中東-中亞-俄羅斯”與“美洲”兩帶并存時,情況變得更加復雜。歐佩克連約束成員國都不容易,更不要說與非歐佩克成員國達成一致。
2014年下半年油價下跌之始,與烏克蘭危機后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在時間上相重合。美國和沙特聯手拉低油價、借此拖垮俄羅斯的言論一度十分流行。但是隨著油價遠遠低于俄羅斯的承受范圍依舊毫無止跌之勢,美國的頁巖油氣企業壓力重重,沙特財政收入急劇減少,油價的“跌跌不休”本身粉碎了各種陰謀論的猜想。“地緣政治曾經是影響油價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2015年9月俄羅斯對敘利亞“伊斯蘭國”基地進行空襲,并沒有引起油價的反彈,這說明石油的供需失衡是重要因素,以至于油價對地緣政治不像以往那么敏感,低油價將是新常態。”中國石油大學國際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龐昌偉對本刊分析說。在他看來,美國2010年后的頁巖革命與烏克蘭危機疊加,再加上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需求減弱,成為2014年油價下跌的主要推手。
油價進入下行通道后,雖然產油國明知供大于求的局面,但是由于害怕喪失市場份額,沒有人愿意減產。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董事長Khalid al-Falih的表態,代表了產油國的心態:沙特不會減產,除非非歐佩克國家一起加入減產行動。如果其他產油國愿意合作,沙特也愿意合作,但沙特不會承擔平衡目前結構性失衡的角色。Khalid al-Falih說,沙特不會為了推升油價而放棄自己的市場份額,“我們不會接受撤走我們的生產而給別人騰出空間”。而美國開始出口原油、伊朗重返國際石油市場,都為產油國的競爭增加了變量。
根據路透社的調查,2016年1月,包括印尼在內的歐佩克石油產量按月增加29萬桶/日至3260萬桶/日,為近期歷史最高水平;1月伊朗石油產量增加15萬桶/日至305萬桶/日;1月沙特石油產量為1025萬桶/日,去年12月為1015萬桶/日。根據彭博社的數據,盡管油價跌至12年新低,2015年12月,俄羅斯原油和凝析油日均產量約為1082.5萬桶,比11月創下蘇聯解體后最高單月紀錄的產量還高出0.4%。
全球能源和金屬行業里較權威的資訊來源伍德麥肯茲的報告則認為,盡管油價已經低迷了一年有余,然而全球原油產量僅因此而下降了0.1%,低油價只擠出了這么少量的產能,足以證明傳統石油行業“負隅頑抗”能力之強。這份報告暗示,油價需要進一步下跌,或者在低位維持更長時間,才能引發全球范圍的實質性減產。
石油與頁巖油氣對決盈虧點
當產油國擔憂石油的供給將永遠充沛時,沙特等石油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開始試圖以價格戰逼退高成本的競爭者。每個國家生產石油的成本相差明顯,在這場消耗元氣的戰斗中,看誰能撐得更久。中國石油大學國際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龐昌偉對本刊分析說,一方面產油國之間在競爭,看低油價時誰能撐得更久,撐不住的就得給其他供應者讓出市場份額。另外沙特這樣的產油國也在與美國的頁巖油競爭,一旦油價持續低于頁巖油井的盈虧點,就可能把它們擠出市場。歐佩克希望借助自己的低成本優勢將高成本競爭對手從市場上擠出去,以此減少供應繼而平衡市場并提振價格。
按照龐昌偉的估計,如果不算前期的勘測開采成本,僅僅從油井1~5年內的盈虧點來看,沙特石油的盈虧點低于5美元,俄羅斯為15美元,中國為50美元。而美國頁巖油的盈虧點為40美元,所以油價低于40美元是有利于沙特打壓美國頁巖油的。
但是從現實來看,美國頁巖油的價格靈活性,遠遠高于市場的預期。2015年初,當油價跌至50美元時,分析人士對美國頁巖油行業的末日言論就縈繞市場。當時分析認為,美國頁巖油氣企業平均開采成本在65~75美元/桶。油價到40美元以下時,僅有不到10%的頁巖油企還能盈利;若油價維持在60美元以下兩個季度,三分之二的企業將經營困難,不得不減產。以石油顛覆者姿態出現的頁巖油,將告別高速增長的繁榮時代,進入痛苦的破產重組。油價如果持續低迷,這些企業就要面臨艱難抉擇:要么破產,要么債務減記以便讓債權人做出更大的讓步,或是在潛在買家舉棋不定的時候賤賣資產。
但是從現實來看,沙特想用低價石油擴張市場份額,擠出邊際生產商的想法已經比當初困難多了。彭博行業研究分析師威廉·弗里斯和安德魯·科斯格雷夫指出,因為最新盈虧平衡模型顯示,即使油價跌至30美元以下,美國得克薩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頁巖油生產也能保持盈利。其中,主要產區得克薩斯州的鷹灘德威特縣頁巖油開采成本為22.52美元/桶。里夫斯縣開采成本為23.40美元/桶。但不同產區的成本差異較大,導致無法準確估計美國頁巖油生產成本的整體水平。但毋庸置疑,低油價下的美國頁巖油公司,日子十分艱難。2015年1月,因貸款人拒絕提供更多資金,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家私營的石油公司WBH Energy LP及合作伙伴申請破產保護。
過去幾年,由于美國能源業繁榮,美國油氣公司不斷加大債務量,即使油氣生產商的支出超過收入,他們也能獲得資金去鉆井。正是由于大量借來的資金,才使得油企能填補資金缺口,在得克薩斯州、北達科他州、科羅拉多州進行頁巖油氣開采。2010年,美國油氣生產公司負債總計為1280億美元,而最新季度數據顯示,他們的負債總計為1990億美元,大漲了55%。這些公司負債累累,因此即使油價暴跌至50美元下方,他們也選擇繼續生產。然而,低油價令油企資金緊張問題愈發嚴重。美國頁巖石油業者今年已無法再進行避險操作,再加上信用市場也對業者抽緊銀根,一些負債沉重的頁巖油從業者將倒閉。
在某種程度上,處在困境中的沙特正在效仿美國頁巖油生產商,利用廉價債務融資進行大規模擴張。石油巨頭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伊格·謝欽認為,美國頁巖油在1500億美元債務的支持下,以破竹之勢對全球石油市場產生影響。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沙特正準備在國際債券市場上舉債,從而為石油大戰進一步提供資金,以保衛自己在世界石油市場的份額。
在這種局面下,世界油氣供需正從“供給支配”向“消費驅動”轉變,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對世界油氣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在石油消費轉向了買方市場之后,產油國的共謀更是不可能達成。
新能源版圖下的地緣政治
在頁巖油氣引領的新一輪能源競爭中,美國仍舊成為領跑者。這種領跑帶來的能源獨立前景,將使美國在地緣政治中更為超脫。美洲崛起為世界新的能源供應中心,同時亞洲成為新的能源消費中心,全球能源貿易流向發生逆轉。中東、俄羅斯等國家對傳統石化能源的依賴,反而使它們在新一輪的革命中失去了探索的動力。
由能源危機恐慌、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壓力而形成的環保意識,也正在改變著人們對于能源的需求。2006年開始,美國人開始不喜歡開大型車輛了,大型車輛銷量下滑,孩子們為父母開耗油車而覺得難為情。2007年喬治·布什簽署法律降低車輛的油耗率以來,能源需求的下降變得明顯了。美國政府在2009至2014年間有1500億美元的撥款是致力于綠色能源開發的,包括風能、太陽能還有其他可再生能源。喬治·米切爾的兒子托德說,如果他父親的努力阻礙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使發明家來不及去改進風能、太陽能或其他清潔能源,那么他父親的努力就會對世界造成負面影響。
在龐昌偉看來,誰能突破能源稀缺的魔咒,誰就將引領新一輪的發展潮流。美國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后,一直在尋求能源獨立的道路,國家的鼓勵政策與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使得美國再次脫穎而出。但是對于中國來說,石油儲備仍然是一個國家戰略。中國還處在減煤、穩油、增氣的階段,到2025年時,如果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里,煤炭占比50%~55%,油氣占比35%,新能源占比15%~20%,就比較理想了。中國現在已經成為第一大石油進口國,在石油供應將長期充裕的境況下,中國的議價能力將明顯增強,買家會成為產油國競相爭取的對象。
而頁巖油氣能夠在美國迅速發展,也得益于它的金融體系。美國廉價債務融資等方法使頁巖氣企業得到大量資金支持,發展迅猛。但是一些研究者提醒說,美國近幾年的能源行業吸引了大批投資者,在花樣繁多的金融衍生品的包裝下,能源行業會不會像美國在本世紀初的網絡科技泡沫、2008年房地產的次貸危機一樣,最終將偏離理性發展的軌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向本刊分析說,隨著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一旦美元出現貶值,所有以美元定價的資源則會價格上升,反之亦然,美元與原油價格存在著負相關波動。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的歷史來看,每一次石油價格的大幅波動,都與美國的經濟行情相關。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優先穩定國內金融市場,但是往往會對國際能源市場產生副作用。
美聯儲治理國內經濟通脹的辦法是打開貨幣水龍頭,大規模刺激經濟,這必然引起美元貶值,石油、黃金等成為最好的抵抗通脹的避險品種,價格大漲。最近這一輪油價暴跌的推動因素之一,則是美國經濟回暖引起了美元走強。美元走強、資本回流對美國是好事,但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債務人,又會面臨著債務增加的煩惱。回流的資金是否能夠進入美國的實體行業,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丁一凡認為,隨著石油金融化的屬性越來越強,美國的貨幣政策會極大影響投資人的預期,油價某種程度上在脫離真實的供需關系。而對于美國金融機構來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缺乏好的產品進行投資。頁巖油氣的變革一旦引起資本市場的注意,會迅速吸引大量資金。全球經濟金融化和期貨化的特征越來越明顯,連工業產品也在期貨化。一些垃圾債券也在這輪風潮中掛上新能源的名目打包出售,這其中到底有多少泡沫,累積了多少金融風險,缺乏有效的認知和監管。金融市場成為美國的雙刃劍,這種力量已經不是政府意志能夠控制的。“現代貨幣成為主權信貸,持有美元等于持有美國的債務,美國對債務管理得好不好,決定了人家對它的信心。”丁一凡說,在這種認知下,歐洲國家脫離美元霸權的動機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比以往更好。龐昌偉也認為,這輪低油價使得俄羅斯需要對經濟結構進行更深入的改革,也應該能促使中國和俄羅斯在“一帶一路”等事務上實質性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