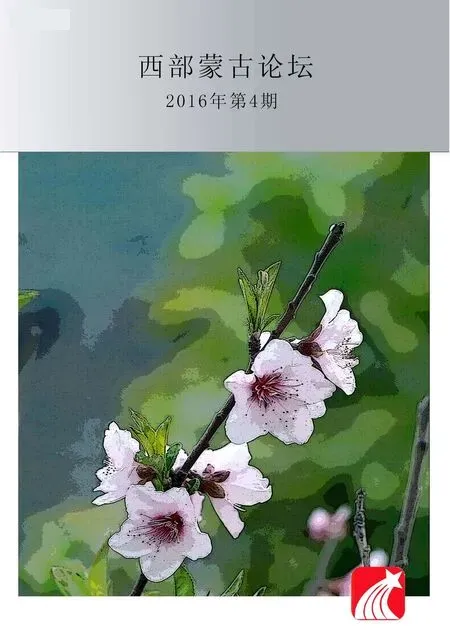昂嘉恩喇嘛與密教在卡爾梅克蒙古中的發展*
(俄羅斯)巴圖·克惕諾娃著達麗譯*
(北京市 海淀區 100195)
昂嘉恩喇嘛與密教在卡爾梅克蒙古中的發展*
(俄羅斯)巴圖·克惕諾娃著**達麗譯***
(北京市 海淀區 100195)
本文在認真研讀創作于19世紀早期藏文手稿——《衛拉特蒙古佛教史手稿》基礎之上,對衛拉特蒙古的著名高僧——昂嘉恩喇嘛在西藏哲蚌寺的求學經歷及對藏傳佛教在衛拉特蒙古中的發展做了分析和研究。本文的作者巴圖·克惕諾娃系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世界史系主任,長期致力于衛拉特蒙古佛教史的研究。
昂嘉恩喇嘛 密教 卡爾梅克 發展
卡爾梅克(亦稱衛拉特),是世界上唯一因遷徙常與包括佛教在內的許多宗教觀念相碰撞的佛教國家。在西部蒙古中,密教和豐富的瑜伽儀軌尤為重要,在佛教中稱這種修行傳統為金剛乘。通過該修煉方法可以使修行者早日成佛,進而避免周而復始的輪回轉世。俄國學者捷連季耶夫(A.A.Terentyev)正確地指出密教對操蒙古語民族以及圖瓦、阿爾泰人等的影響,他認為這些民族的佛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均受到密教影響。①見《詞典》,莫斯科,1992年,第89頁。
由于衛拉特蒙古高僧乃濟托音(Neiji Toin)②乃濟托音一世(1557—1653年),本名叫阿畢達,是土爾扈特蒙古首領墨爾根·特木納之子,曾師從四世班禪學經,后在班禪指點下前往漠南蒙古弘揚佛法。乃濟托音主要側重于密宗的修持和宏傳——譯者。的積極弘佛活動,大威德金剛體系之神秘主義和陀羅尼經咒成為衛拉特蒙古佛教信仰的重要內容。③(德)海希西著:《蒙古的宗教》,英國:倫敦亨利中心,1987年,第39—40頁。關于不同理論和教義的密教,特別是在操蒙古語民族中的時輪金剛和香巴拉,俄國學者伯金(Berzin)認為,他們之所以深受蒙古及圖瓦人的熱忱歡迎,很有可能源自于他們與神秘的香巴拉國度之間的聯系。④(美)白樂山著:《接受時輪灌頂》,俄國:圣彼得堡,2002年,第42頁。
遺憾的是,有關準噶爾蒙古和伏爾加河卡爾梅克蒙古的密教及其寺廟的歷史至今仍是東方學研究中的未知領域。正如我們先前的研究所示,衛拉特及卡爾梅克僧人的歷史充滿了神秘色彩,出奇地與中國、俄國及其他國家的歷史相互交織,令人驚訝。
接下來,本文在仔細研讀創作于19世紀早期的藏文手稿后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①該手稿名為《衛拉特蒙古佛教史手稿》,由土爾扈特女貴族德瓦·寧布贈與美國學者吉普森,后吉普森將手稿由藏文譯為英文,并刊登于《中亞雜志》(1990年第34卷),第83—97頁——譯者。該手稿是關于密教在衛拉特和卡爾梅克蒙古部中如何傳入并得以傳播的稀缺歷史文獻之一。基于美國學者吉普森(Gibson)的譯文,在此我們僅對其中一些具體的事實作出說明。吉普森根據他個人的早期研究在譯文中提供了注釋。從其注釋中我們可知,手稿作者系為克列特蒙古部中享有盛名的江巴巴格西喇嘛(Jama Bakshi)。該手稿由現居住于美國的土爾扈特女貴族迪娃·寧布贈與吉普森,她希望吉普森能夠將其出版問世并“將文獻所含有的信息留存下來”。
該手稿是記載卡爾梅克喇嘛昂嘉恩(Anjja)(又稱Anjjatan、Ancithan)在西藏生活的罕見文獻。這位著名的卡爾梅克喇嘛與同一時期另一名叫沙庫爾(Shakur)的準噶爾部喇嘛共同對佛教在衛拉特蒙古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該手稿中有關三大重要事件的描述,對研究佛教在衛拉特蒙古中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些重要事件主要與昂嘉恩喇嘛離開土爾扈特故土伏爾加河前往西藏學習和出生于伊犁河準噶爾蒙古統治家族的堪布喇嘛②堪布喇嘛,即譯文中所提到的來自準噶爾部的沙庫爾喇嘛,因其出身于貴族家庭,亦稱“堪布喇嘛”或“諾言堪布”——譯者。抵達西藏哲蚌寺有關。他們的尊師為阿旺宗哲(ngag-dbang-brtson-'grus),著名的密教老師,哲尊嘉木樣協巴(rje btsun'jam dbyangs bzhad pa')轉世系統的開創者,在格魯派歷史上曾發揮過重要作用。嘉木樣協巴,常與格魯派宗教領袖三世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等相提并論。俄國學者舍爾巴茨基(Stcherbatsky)認為嘉木樣一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他的著作涉及所有佛教理論,足以建立一座圖書館。③(俄)謝爾巴茨柯伊著:《佛教選集》,俄羅斯:莫斯科,1988年,第109頁。
根據俄國學者崔比科夫(Tsybikoff)研究,阿旺宗哲出生于西藏北部安多地區。公元1669年,20歲的阿旺宗哲赴西藏中部學經。④(俄)貢博扎布·才別科維奇·崔比科夫著:《崔比科夫選集(卷1)》,俄羅斯:新西伯利亞,1991年,第50頁。由于才能卓越,1700年,他被任命為哲蚌寺郭莽扎倉堪布。⑤Pagsam-Jonsan著:《西藏歷史年表》,俄羅斯:新西伯利亞,1991年,第136頁。崔比科夫在20世紀初期指出“他對神學的詮釋首次作為指導性手冊被引入郭芒扎倉,如今仍被安多、蒙古以及后貝加爾湖地等地區的所有神學人士視為經典”。嘉木樣協巴和衛拉特蒙古各部之間有著密切聯系,早在公元1703年,衛拉特貴族噶爾登·額爾德尼濟農(Galdan-Erdeni-Jinon)(很有可能是和碩特蒙古部汗王——作者注)⑥據《安多政教史》載,邀請嘉木樣一世返回安多地區修建寺廟的應為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齊之子博碩克濟農第三子察罕丹津——譯者。邀請嘉木樣協巴返回其故鄉安多地區并為其修建了一座寺廟。⑦(俄)貢博扎布·才別科維奇·崔比科夫著:《崔比科夫選集(卷1)》,俄羅斯:新西伯利亞,1991年,第50頁。公元1710年,嘉木樣一世與七世達賴喇嘛共同接受了清政府的冊封。⑧嘉木樣一世與七世達賴喇嘛接受清政府的冊封應為公元1720年。是年,康熙帝冊封嘉木樣一世為“執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罕”,賜給金印,并準穿黃馬褂;正式冊封七世達賴,賜給金冊、金印,印文為“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之印”——譯者。公元1714年,他因完成《怖畏論歷史》而名噪一時。兩年后,他組建了扎西奇寺密宗學院的僧侶班子(即由他修建的位于安多地區的拉卜楞寺——作者注),完成了《佛歷表》。①Pagsam-Jonsan著:《西藏歷史年表》,俄羅斯:新西伯利亞,1991年,第137頁。根據松巴堪布的記載,嘉木樣協巴,這位偉大的佛教人物圓寂于1722年。②Pagsam-Jonsan著:《西藏歷史年表》,俄羅斯:新西伯利亞,1991年,第138頁。
公元1700—1707年,嘉木樣協巴擔任郭莽扎倉住持,這一時期他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及的兩位衛拉特蒙古喇嘛的精神導師。這一觀點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位喇嘛應在他們抵達西藏后不久,便被引薦至時任郭莽扎倉住持的嘉木樣協巴。
昂嘉恩喇嘛在西藏學習和生活25余年。在他抵達西藏之前,那里就有卡爾梅克喇嘛。手稿提到了郭莽扎倉的土爾扈特米村(mi thang)。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到米村寺廟學習的喇嘛均來自于相同部落或族群的同一地方,每個米村均有各自食堂、臥房(khams tshan)以及集會廳堂(tshogs chen,lha khang,or'du khang)。手稿中關于土爾扈特米村的記錄表明,衛拉特蒙古人去西藏地區學經的歷史悠長且從未中斷,亦因如此,在格魯派寺廟中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米村。
關于這一點,崔比科夫在他的著作中正確而詳盡地對哲蚌寺僧人的內部生活和組織機構進行了描述。他指出,在寺廟里,每一位僧人根據自己所屬的部落加入相應社團(互助會),這個社團被稱為“康村”。一般大的康村依據部落之間的關系再細分為若干“米村”。因此,當蒙古地區的喇嘛抵達西藏各大寺廟后則加入相應的康村,如哲蚌寺的郭莽扎倉,色拉寺的哲巴扎倉及甘丹寺的絳孜扎倉。而后,在這些扎倉中,當其他蒙古各部加入Khamdon時,喀爾喀蒙古部的喇嘛則加入了桑洛康村。最后,在這些康村中,喀爾喀蒙古組建了其獨立的喀爾喀米村;土爾扈特蒙古組建了土爾扈特米村,衛拉特蒙古其他諸部(土爾扈特部除外)則形成宗喀米村,漠南蒙古、滿族也有其獨立寺廟。③Pagsam-Jonsan著:《西藏歷史年表》,俄羅斯:新西伯利亞,1991年,第151頁。由此可知,當準噶爾部的堪布喇嘛在宗喀米村時,昂嘉恩喇嘛則生活于土爾扈特米村。
昂嘉恩喇嘛和堪布喇嘛必須通過老師安排的三次考試。而后,老師將依據考試結果預測佛教在其家鄉弘傳時間的長短。
有意思的是,這篇文章只提到了一個菩薩——文殊菩薩。仁波切向他的兩位門徒解釋說曼殊室利這位超能的神,能夠將他們的業力與志向相結合。對文殊菩薩意義的評價和研究方法,使我們想起了時輪金剛體系中的第六世香巴拉王,他因創作了時輪金剛兩部主要文獻之一(簡稱時輪密法)而備受尊崇。很有可能,上述兩位年輕的喇嘛都對時輪金剛之教義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據文獻記載,堪布喇嘛在準噶爾汗國修建過一座密教寺廟。與此同時,著名的準噶爾部吉雪活佛阿旺丹增稱勒曲旺扎巴(Agvan Tan-chen Changle Deva)(1639—1681)也在汗國內修建過若干座密教寺廟。④陳慶英,丁守璞主編,烏力吉巴雅爾著:《蒙藏關系史大系·宗教卷》,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328頁。因此,昂嘉恩喇嘛也很有可能在卡爾梅克草原上修建過寺廟。
經過多年對佛教教義的系統學習,昂嘉恩喇嘛獲得了佛學最高學位(拉布占巴)后返回伏爾加河。離開之前,他前去拜謁了達賴喇嘛并得到達賴喇嘛親贈的唐卡。在此需要糾正一點,即昂嘉恩喇嘛所會見的達賴喇嘛并非該手稿譯者吉普森所認為的六世達賴喇嘛,因為在手稿中,作者明確提到準噶爾喇嘛與嘎貢噶哇仁波切的會面(該名系七世達賴喇嘛的別名),而這個嘎貢噶哇仁波切即為七世達賴喇嘛。
遺憾的是,由于缺乏對昂嘉恩喇嘛的生活和宗教活動的研究,學界至今無法明確這位喇嘛回到故土的確切時間,也無法對其所從事的宗教事業進行討論。但是,在卡爾梅克草原上那座名為色特卓思格林(gser gtag chos gling)的著名寺廟,極有可能為昂嘉恩喇嘛所修建。這座寺廟又稱昂嘉恩庫熱,在當地民眾中盡人皆知,這也反映了人們對這位喇嘛深深的敬意。
該文獻的藏文作者認為,昂嘉恩喇嘛培育的學生后來均成為那一時期卡爾梅克草原上最優秀的喇嘛,藏傳佛教的真正追隨者。該文獻一開始就介紹了所有土爾扈特人生活的國家(不如說是地區),而準噶爾汗國只在文章的中間部分略有提及,而文獻結尾部分則對土爾扈特汗國進行了特別闡述,這也許是作者試圖在卡爾梅克汗國和準噶爾蒙古藏傳佛教、昂嘉恩喇嘛和堪布喇嘛在佛教教義的精神傳承之間劃出一個明確界限。準噶爾汗國的衰落使其藏傳佛教失傳,土爾扈特汗國的藏傳佛教卻依舊在延續。公元1771年,昂嘉恩喇嘛的門徒們返回了準噶爾蒙古地區。
通過文獻我們可以推斷,在昂嘉恩喇嘛親授的學生中有七名喇嘛成為了土爾扈特汗國著名的宗教人物。他們分別是克列特旗的哈留恩和努蘇哈;查騰旗的曲日木和永丹;巴潤旗的阿日布克;沙畢納爾旗的奧爾根金畢以及和碩特部的羅熱桑布。他們中一些喇嘛,很可能是這些學生的學生,而后均追隨渥巴錫汗離開伏爾加河前往準噶爾地區。這些追隨者中,有在文獻的結尾處提到的喇嘛羅卜藏土道布,他是新疆薩姆騰卓林寺廟(bsam gtan chos gling)住持,正是在這位喇嘛的指示下該文獻得以撰寫。
17世紀初,衛拉特蒙古從準噶爾地區的陸續到來,紅教喇嘛開始出現于卡爾梅克草原。正如我們前面所述,這些衛拉特蒙古是首批噶舉派和薩迦派等不同派別的追隨者。與此同時,一些蒙古分部對于特定佛教傳統變得不再忠誠,杜爾布特蒙古部中開始涌現出很多著名喇嘛。因此,深入研究卡爾梅克佛教史從其傳入至17世紀70年代的發展歷程,將有助于我們清晰勾勒出在卡爾梅克這片草原上,藏傳佛教不同教派之間以及藏傳佛教與已吸收諸多佛教元素的薩滿教之間相互斗爭、相互沖突的歷史脈絡。
[責任編輯:那次克道爾吉]
K827
A
1674-3067(2016)04-0021-04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西域佛教研究史”(11&ZD118)的階段性成果。
**譯自(俄)巴圖·克惕諾娃(Baatr U·Kitinov)著:《13—18世紀佛教在西部蒙古諸部中的傳播》第六章第一節,紐約:戈德文·梅侖出版社,2010年。
***[譯者簡介]達麗(1979—),女(蒙古族),新疆博湖縣人,博士,研究方向為新疆藏傳佛教歷史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