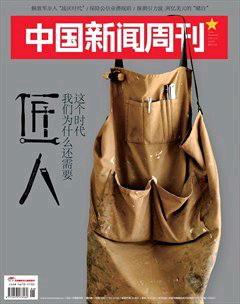楊兆霖:關于面粉的執念
龔龍飛
楊兆霖平日待客有兩樣必備的,一是武夷山的大紅袍,二是清汆紡面。面湯清淡,面條晶瑩剔透,本身有少許咸鮮,加上一點簡單澆頭,面本身的美味與口感柔韌而筋道,唇齒間都是麥香味,那種兒時的味道有些熟悉,有些遙遠,令人難忘。
楊兆霖總會補上一句,“慢點吃,自家的東西,管夠。”他的這碗面條,每斤售價460元,市場上當季的面條早已全部售罄。
楊兆霖今年55歲,河套人,中等個子,身形略瘦。他穿著一件對稱規矩的中式皮衣,扣上了風紀扣,鏡架兩側的黑發紋絲不亂,發根則俱是雪白。10年前他一夜白頭,所以,隔些時間,他就要把頭發一遍遍地染黑。
過去20年,身在異地的他始終放不下故鄉的土地,試圖為它找到更好的出路;直到最近3年間,他似乎找到了河套面粉的價值。
種中國最好的小麥
巴彥淖爾位于北緯40度、內蒙古的西端,與全球同緯度的內陸地區一樣,干旱少雨,以“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歌留名于世。
因黃河從這里繞道而過使得這片荒原有了生機。明朝中葉以來,這里成了諸省災民的逃生門,史稱“走西口”,有“黃河百害,為富一套”的說法。特別是1959年由蘇聯援建落成的三盛公水利樞紐更是讓巴彥淖爾發生了巨變,到2015年,巴彥淖爾的可耕用地達到了1000萬畝。這片土地成了“塞上江南”。

楊兆霖。圖/受訪者提供
“走西口”不僅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也將各地的種子與農耕技術帶到河套地區,這里的玉米、葵花、密瓜等農作物聞名全國,其中尤以硬質小麥最為出名。
楊兆霖是在1995年開始關注農業,這位1988年就下海的中學老師,在短短7年間,養過長毛兔,賣過電子鞭炮,搗鼓過電腦公司,還成了巴彥淖爾的第一位房地產商,市場的風云變幻讓他備感疲倦。既然巴彥淖爾具有農業優勢,風險小又可持續,正迎合了這位教書先生骨子里的保守。
1996年,國家高層第一次提出了“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當地政府也不斷給出政策紅利,1997年,楊兆霖在距離烏梁素海不過4公里的阿力奔鎮承包下了6000畝地,因為靠近風口,更準確地說那是6000畝沙丘。
楊兆霖種過地,他心里清楚“好地熟地自然歸了農戶,沙丘底下都是好地,用3到5年種樹固沙,打上水就能種出糧食”。
但治沙難度遠超他的想象。
流動沙丘使得拖拉機無法進入,只能靠人和驢來背樹種,風沙之大,第二天就埋掉,樹死了,只能接著種,沙又接著埋。楊兆霖找到他的發小梁永文,梁家世代都在毛烏素沙漠里種樹,梁永文記得第一天早起出門查看樹種,忘記插門。不到一小時,床被沙堆蓋住,里頭還窩著躲風的蛇與蝎子。
梁永文的辦法是圍起欄桿,減緩風力,控制流沙速度,搶時間種下樹,種活了,再將圍欄前移,步步為營。人進沙退,人退沙進的狀況僵持了許多年。
基地內是楊兆霖花了2800萬從韓國引進的硬件大棚,加上以色列的滴灌技術,2000年以后,這里陸陸續續地種出了鮮切花,七色柿子,甚至還有芒果,這成了河套農業的奇觀,也成了當地政府接待貴賓的必去之地。但楊兆霖心里清楚這是“叫好不叫座”,帶有實驗性質的奇瓜異果數量少,很難產業化。而且的經濟發展條件,高端市場還沒空間。大棚建起來,卻不接“河套”的地氣,每年預算就虧損50萬,此時,他將目光投向了河套小麥。
河套一直有種小麥的歷史。而相較于其他作物而言,小麥因為用水量少,對于漫灌造成的河套地區土地次生鹽堿化也有很大幫助。
就氣候而言,這里干旱少雨,晴天多。年均日照時數長達 3000小時以上,居全國前列;地勢高,太陽輻射總量僅次于青藏高原。這種氣候,一方面非常適宜農作物的糖分積累,同時對于農作物的淀粉、蛋白質和有機物質的積累都有很大幫助。就土地而言,這里的灌淤土年久熟化,格外肥沃,速效鉀含量高,遠勝于全國其他地區。
1973年,寧夏永寧縣良種繁殖場用墨西哥小麥與國產小麥雜交而成了“永良4號”,在河套地區試種,大獲成功。產出的硬質小麥,質硬而透明,含蛋白質較高,達14%~20%,面筋強而有彈性,有“玻璃體”之美譽。在小麥的五項品質指標,即粉質指標,拉伸指標,蛋白質含量,面筋值含量,與沉降值含量。中國農業科學院博導、小麥研究專家魏益民認為,“‘永良4號在5項指標上都表現優秀,可以說是5項全能冠軍。”
“永良 4 號小麥,明顯優于黑龍江省、山東省等我國小麥主產區 79 個優質小麥品種,其中尤以面團品質和烘烤品質最為突出。”巴彥淖爾市農牧局小麥所所長張建成解釋說,我國小麥主產區集中在華北幾省,由于氣候地理自然條件的原因,從北到南,小麥質地由硬趨軟,即便是華北地區的麥粒含蛋白質也僅有8%~10%,與河套小麥相比,麥粒軟,面筋弱,更不用提南方小麥了。可河套小麥的缺點在于產量較低,畝產為350公斤,華北小麥可達500到600公斤之間。
“在主糧中,小麥比較特殊,營養最為全面,基本上可以滿足人的所有需求,但基因極為復雜,不像水稻,玉米迭代頻繁,小麥品種培育周期長,迭代緩慢,且非常穩定。”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巴彥淖爾市從建國以來,至今一共進行了6次品種輪換,現在是全國唯一的高筋度硬質小麥種植區。”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河套面粉一進市場就一炮打響。楊兆霖還記得,當時適逢雙軌制改革,面粉買賣也還需要批條子,批條內的一般面粉的售價在1.8毛一斤,河套面粉卻要3毛一斤,而投放到自由市場的更賣到8毛錢一斤。每年中秋到春節,一直都是河套面粉的銷售旺季,全國各地的采購員都會拎著各地特產“巴結”河套面粉廠的銷售員。
楊兆霖看到了硬質小麥在全國小麥市場的稀缺性,2002年他開始改種植小麥,他希望像五常大米那樣,河套小麥也能成為最貴的小麥。
但改變來得漫長而曲折。
苦心經營
作為主糧,小麥始終維系在價格較低的水平,河套較有規模的面粉廠過去長期都屬于國營糧食企業,經濟效益不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小麥與其他農作物的經濟效益漸漸拉開差距。
在當地,農民越來越不愿意種小麥了。面粉廠出現了原料缺口,為了降低成本,一些面粉廠低價收購外地的軟質小麥,到河套摻兌當地小麥,在巴彥淖爾市各面粉廠門口,“豫”和“魯”的運粉車比比皆是。雪花粉的招牌岌岌可危。
楊兆霖明白,只有與農戶建立新的合作關系,市場上成功了,再價格反哺農戶,形成良性循環,河套小麥才有希望。
2003年,當時巴彥淖爾市最大的國有面粉廠恒豐面粉廠因經營不善,出現了虧損,希望由民營企業進入控股,該廠的“河套牌雪花粉”,在2002年仍是面粉行業唯一的中國馳名商標品牌。楊兆霖看準機會,為了集資購買股權,他幾乎是孤注一擲。
他將原有的數家電腦公司半賣半送地處理掉,并以300萬元的低價割售了他在烏海市特有的焦炭廠。
2004年,巴彥淖爾市政府為招商引資,有意將恒豐“送”給一家港資企業,市委書記要求楊兆霖在規定時間內離開“恒豐”,開出賠償600萬的條件,就這樣,楊兆霖被一紙行政命令“離職”了。
港商來了不久,卻因水土不服,投資沒多久匆匆撤資。
楊兆霖希望二度入主“恒豐”,也以失敗告終。
但幾經折騰,楊兆霖在巴彥淖爾苦心經營的口碑,身上的光環,也消失殆盡。
這一年,除了基地還在運營之外,楊兆霖遣散了團隊的大部分人,他進入了人生最低谷,不久,他的頭發全白了。他離開了巴彥淖爾。
但楊兆霖始終相信,河套面粉是稀缺資源,他不愿意割舍這個和故土最后的牽連。他讓梁永文堅持治沙,平整土地,為種麥做好準備。
到2009年,阿力奔終于出現了一片蔥郁的樹林,碗口粗的白楊樹讓楊兆霖頗為感慨,整整12年過去,阿力奔的沙丘終于治住了。風平沙靜,這一年,小麥的念想終于出現了轉機。
他打聽到,鄭州糧食學院教授范崇旺一直在研究新的制粉技術,可能為制粉帶來“革命性”的變化。范崇旺提出,用石碾工藝低速低溫地加工面粉,這個手法可以改變現有的石磨面粉與鋼磨面粉的缺陷。但苦于沒有啟動資金和團隊。楊兆霖與范崇旺一拍即合,楊兆霖召回之前遣散的團隊,決定“再來一次”。他出錢出人,雙方聯合研究。
研發過程并不順利。2010年冬,第一代石碾機在河南實驗時表現良好,樣機千辛萬苦運到河套后,不想“玻璃體”的河套小麥比河南小麥硬許多,石碾壓不開麥粒,大量麥麩還依附在麥粒上,碾碎的麥粒呈顆粒狀,不成粉末。
2011年,楊兆霖將河套小麥送到鄭州的河南工業大學(鄭州糧食學院合并后的大學)的實驗室又進行了反復實驗,他們就吃住在實驗室里。這一年年底,團隊終于找到了解決路徑,突破了技術壁壘。雙方聯合申請了技術專利后,迅速進入生產流水線。
到2015年年底,第三代全封閉的石碾機在楊兆霖的加工廠里安裝調試完畢,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石磨面粉與鋼磨面粉的技術缺陷。
每分鐘500到800轉的轉速,會使得鋼磨產生高溫,不僅破壞了面粉的營養,還加快了芳香氣體的揮發,缺失麥香味。石碾的轉速僅為33轉/分鐘,溫度低于30攝氏度,小麥在碾壓中,基本完全保留了麥胚的香味以營養成分。
而石磨制粉是利用上下兩片開齒的磨盤,通過運動,利用上下磨盤的石齒相互咬合,使進入磨盤內的小麥反復研磨,重復篩理后制成面粉。雖然溫度不高,能保證營養成分,但巨大的摩擦很容易把石粉帶入面粉中,使得灰分超標,食用時牙磣,不利健康。
楊兆霖他們研制的石碾技術,是正壓力碾壓而成,比石磨產生的灰分小很多。石碾的石頭也費盡心機,他們選取了河南某山地的特殊石源,堅硬而有韌性。
為確保品質,楊兆霖嚴格控制出粉率,將出粉率控制在60%以下,而一般面粉廠的出粉率在75%左右,越高出粉率,需要壓緊磨輥軋距,使得磨輥溫度過高,容易燙傷面筋,使面粉的柔韌性受損,面制品發脆,容易破裂,同時大量細微的麩皮細屑刺穿面團中的微氣室,造成面團塌癟,就是常說的“死面”,嚴重影響口感。
可石碾的慢速也使得其效率極低,24小時工作,一條流水線只產18噸面粉。但石碾技術的成功給團隊帶來了很大信心。
不過楊兆霖心里清楚,有機小麥的種植更為關鍵。
只做一件事
而種植小麥,在現在的河套,正逐漸成為稀缺。2014年,一畝小麥的盈利400元,玉米是700元、番茄是800元,葵花籽是900元,正因為利潤微薄,河套的小麥種植面積正在大幅縮減。2000年,河套800萬畝耕地面積中,小麥的種植面積一度超過300萬畝。到了2015年,現有1000萬畝耕地中,小麥的種植面積不足100萬畝。
有機小麥基地更為稀少。由于土地要求均為處女地,以確保無化肥、無農藥的有機認證。介于黃河水可能被污染,楊兆霖決定打取地下100至150米深的礦泉水,采用全封閉的滴灌節水系統,一方面減少了黃河水帶來的草籽,另一方面確保了水源的充足和清潔。
他們還在礦泉水中發現微量元素“鍶”,富鍶礦泉水,讓有機小麥的營養成分更為全面。
按照歐盟的有機種植管理要求,為了維護土地的系統生產力,有機地塊實行三年一個輪作種植制度,豆科作物作為培肥地力的作物之一,必須安排一茬。所以,楊兆霖的20000畝的種植基地,實際每年只種植6000畝有機小麥,有機小麥的畝產不過200公斤。
在楊兆霖的太陽廟農場,不遠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雞鹿塞”遺址,昭君與小單于在此臥薪嘗膽,“犁其地,種黍麥”,最終復國,楊兆霖有所啟發,就注冊了這個商標。
2013年夏天,“雞鹿塞”面粉通過德國色瑞斯認證機構的歐盟有機產品認證,同年年末,被中南海選定為國宴招待面粉。
2015年,楊兆霖和巴彥淖爾市農牧局聯合成立了河套小麥產業化研究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小麥育種專家趙振東在這里成立了院士專家工作站。也在這一年,楊兆霖與巴彥淖爾市農科院聯合選育的新品種“巴豐七號”通過了內蒙古自治區品種審定委員會的審定,他的第一個小麥品種誕生了。
盡管進入農業領域有20年,楊兆霖從未盈利過。數以億計的資本和時間無休止的投入,在面粉之路上他曾經越走越難,而今終于越走越遠。
現在,楊兆霖把他的有機面粉賣到了每公斤30到260元不等的價格,可以說是中國最貴的面粉。
他說,就像在阿力奔沙丘里的樹,好些年不長葉子,也不枯萎,它所有的變化全在它看不見的根系里,那是它堅持的理由。
2016年,楊兆霖的新名片又要更換一些信息。但有一句話,在過去10年間都沒有變過,“我們的過去,現在,將來,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做全世界最好的面粉。”

2013年6月,河套小麥正進入關鍵的灌漿期。楊兆霖(中)在6000畝的阿力奔有機小麥基地內,觀察小麥生長情況。這是楊兆霖團隊第一年大面積種植有機小麥。圖/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