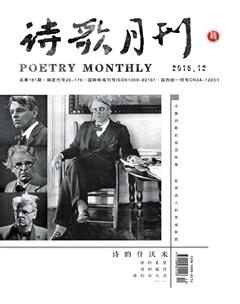從“泣血之痛”到“時光之思”
馬啟代
閱讀一個人,就是打開一扇窗戶,藉此可以窺探一片新的原野或領空。讀完《時光之碑》,對于詩人許敏的印象愈加清晰。梁小斌說他是一位“手握青草在宣告”的人,祝鳳鳴說他“繼承了一種田埂般哀婉凄切的音調”,黃書泉說他“不僅僅是一個鄉村生活的敘事者,更是一個抒情者。”在我所感受到的影像里,許敏是一位雙足立于廣袤大地的赤子,他安靜、憂郁、低頭沉思,盡管有細雨霏霏,他仍沉浸在天地澄明之境,合著古老傳統和現代文明的節律真情地吟唱。他由鄉村體驗到精細的呈現,由反觀到反思,由一位抒情者到思想者。長詩《時光之碑》,沿襲一以貫之的主題和核心意象,從“泣血之痛”到“時光之思”,標準著他由抒情歌手到精神哲人的轉變。因此,《時光之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懷親詩歌。
許敏作為現代意義上的“鄉土”詩人,我認為他倒更像是一位為“鄉土”精神唱著挽歌的流浪藝人,是一位搖著經幡四處播撒信仰與愛的智者。在宏觀的關于“許樓村”的書寫之上,對于“母親”的描述,在許敏的作品系列里構成了一條延綿不斷的情感和美學視線,成為他內心堅守的甚至是不自覺的行為,零星地拼貼出歷史的、想象的、多層的“母親”形象,就我有限的閱讀,我看到了許多讓人錐心的詩句,如“冬天是一爐火。/母親用干牛糞/把稀飯燒開/蒸氣里有股甜香。”(《冬天是一爐火》、“母親洗刷陶壇。之前,她要我們把大大小小的腌菜壇子/搬到河沿上。……母親一身舊衣,戴著護袖,系著灰布圍裙/把冰冷的河水灌進陶壇,用竹制的刷把不停地洗刷/一顆草葉的心就在這粗陋堅硬的陶壇里融化”(《又過年了》)、“火苗暗黃/燈光像水紋一圈一圈地擴散/撲哧一聲燈花笑了/笑得母親有些心酸難忍/燈芯一點一點地縮短/就快接不上燈盞里的煤油了/像一個內心孤單的人/悲傷蔓延/在破損的老屋里/母親撐起這份孤單/第二天頂著大雪去趕集/歸來時手里攥緊一根燈芯(《一根燈芯》)、 “夜風舔噬燈盞一遍遍地/燈火終于暗下去/夜已經很深/像黑咕隆咚的窟窿/村莊一點一點地陷進去//夜風很緊/想起我和大哥仍在回家途中/母親起身/撥亮燈火/又將村莊一點一點地從黑暗深處拽回來” (《燈火暗下去》)、“風從長城以北吹來/走累了也不肯在許樓村的樹杈上/小歇一會兒外婆邁著小腳/去灶間煮雞蛋謹慎地取出花瓷大碗/往里面加一勺黑乎乎的紅糖/母親已經不那么驚慌了/這是她的第三次生育”(《1976年的大雪》)、“陰雨天。火柴皮濕了。/母親擦了兩根,沒擦著/就心疼得不忍去擦第三根了·一/她去鄰居家引火,攥緊一把柴禾/又從柴堆里抽出一把,以作酬謝。/看著母親匆匆的背影/轉過墻角,那么低矮/像一朵由淚水構成的暗黑的火焰。”(《簡單的一天》)等,這些以“回憶”和想象組成的凡俗的生活畫面,多以“冬天”和“夜晚”為背景,把在生存層面辛苦勞作的母親和在精神層面經受命運鍛打的母親升華為詩中的藝術形象,其平靜的語氣和略帶哀婉的語調,結合白描式的筆法和簡潔、富有張力的語句,蘊含著無盡的愛憐和憂傷,這個階段的許敏已在情感控制和內斂書寫上值得贊許。如果說這些以“敘事”為主要基調的作品為《時光之碑》保留下母親生前生命片段溫度的話,那么,一些以“懷念”為主的作品,則為許敏的長詩寫作積累了許多情感和思想資源,如“荒野里/風彎腰撿拾什么/火苗一顫娘/那是你五十年人世間抽搐的背影”(《泥土里的燈》)、“我寧愿陪你跪在地上,撿拾被打翻的米粒/我寧愿今生是螞蟻,背著種子陪你下地/我寧愿自己是默默的淚水,陪著你一遍遍地流/我寧愿再穿一次血污之衣,把臍帶接上”(《母親,如果一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領著母親的亡靈去看海》一詩,讀來讓人心痛不已:“母親我想領著你的亡靈去看海/看看你靈魂企及不到的那片凈水/被螢火以及被蛙鳴驚濕的我倆/靜靜地坐在海邊/讓海風吹我孤單的靈魂/讓海風吹你一生的疼痛/讓海認識一個中國農婦和他的兒子/讓海心酸過后說我倆的幸福是多么的不合時宜”。盛敏說: “這首詩描述的是詩人內心持久不變的對象一一母親,與詩人自己從表層進入里層的特征化的情感,整首詩營造的氣氛是寬闊而又悲涼的,是擴大的描寫對象的歷史和母子之間絕對情感的吟唱。”(《回憶牽引出內心美麗的吹送一一鄉村的傾訴者許敏的詩歌寫作》)另一方面,許敏幾乎與生俱來的天然的抒情氣質,使他一開始的寫作就貼近自然和人性,與萬物和神靈建立起了息息相關的感應,一些關涉其他主題(我并非主張現代寫作的主題論)的詩篇為《時光之碑》的寫作準備了必要的詩藝經驗的儲備。試舉幾例,如 “村莊是人間的小站,牛羊低喚兩聲/大多數時光/你小如一粒塵埃/把簡單的快樂/一半給了天空/一半給了我們”(《細雨中的油菜花》)、“水泥船晃動一圈一圈的光影/拆開縫合又敏感而沉靜地向外推送/像極細小的精靈在水面閃耀幻滅/我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如果水泥船繼續晃動/我便覺得春天是真實的也是疼痛的“(《水泥船》)、“泥土的心跳藏在螞蟻細微的呼吸里/一條路的韁繩,牽出一座村莊/牽出塵世廣闊的牧場”(《吹送》)、“像驅逐盲人眼中持久的白霧和黑夜,/大地剛剛側身,壓扁的乳房一一山巒/有寂靜之美,湖水與之并排躺下。”(《孤島》)、“蟲聲,細柔了下來。被月光碰碎之前,/它們是锃亮的黃銅、絢爛的絲織品,/是一群穿花裙子的小姑娘擠在槐樹下躲雨。”(《憶桂花》),特別是他的《風吹浮世》《獻詩》等,堪稱許敏的代表作。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許敏作為一個成熟的詩人,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已經為《時光之碑》做了大量情感和技藝的準備。
作為紀念母親的扛鼎之作,猶如涓涓細流匯成的一排巨浪,浸透了許敏的心血和希冀。“許樓村東南l公里處,早地斜坡,立一墓碑/上書:翟恩鳳,生于1944年,卒于1994年。一一題記”,作品一開篇,地點、方位、環境的介紹,將我們拉入“許樓村”這一具有詩學符號意義的氛圍籠罩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碑文,50年的滄桑凝聚在短短的時光背后,轟轟烈烈無法忘卻的除了時代背景上的波詭云譎,一個普通母親的生平只有幾個冰冷、簡潔的生卒數字。只有面對碑文的詩人,心中和筆下不由涌動起時間的波濤。接下來,許敏從《光陰重現》入筆,以“江水浮上來,映照/清涼的瓦檐。”開篇,奠定了詩的基本語感和抒情音調,通過《童年,樹枝折斷》《陽光,饑餓的青春》《婚姻,大雪中》《鄉村畫夢》《日頭的暴烈》《蟋蟀,我以為是你》《飼料機,與光陰對峙》《平靜的入海口》《槐花,潔白的骨頭》回顧和反思了母親的一生和那50年的歷史。縱觀全詩,除了我們已經知道和說過的許敏詩歌的特點外,我認為《時光之碑》在構思謀篇和表達設置等方面均有許多可資借鑒之處。當下,很多人的長詩是不講構思的,一氣下來,成了一首肆意拉長的短詩或短詩的注解,甚至基本就是短詩的簡單組合,看不出抑揚,也沒有頓挫,更有的盲目進行跨文體組裝,以貌似先鋒的探索實驗成為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等的拼裝,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點是詩人缺乏真實情感的創作積累,使長詩成為炫技的表演秀。而許敏的《時光之碑》不存在這個弱點,對母親刻骨銘心的愛、對鄉土血脈相認的親情、對藝術忠貞不渝的堅守,使這首長詩成為在歲月、內心和技藝中長期熬煉、精雕細刻而成的藝術品,渾然天成中暗含著大樸素。首先,它采用“現實”一一“回憶”一一“現實”的結構,其間不斷往復,形成“從現在走向過去”和“從過去走向未來”的線性軌跡。自“題記”開始,許敏通過母親幸福的童年、橫來的厄運、饑餓的少年、以及無可奈何的婚姻、無休無止的勞動、養兒育女的艱辛和積勞成疾的病痛,再逼近眼前的“墓碑”。看似平常的傾訴中不斷嵌入現實的視角,給時光以理性的透析。其次,它從三條視線來推進敘述,強化個人、社會與當下的關系。一是“母親”這條主線,自無邪童年到變成一塊石碑,留下許多耐人回味的辛酸記憶,二是作為兒子的“我”這條副線,如果說“我”記事之前母親的生活情境是聽來的和想象的,那么我記事之后對“母親”的描寫就是真實的回憶。詩中通過“我”的童年和青年的經歷,從“我”的角度烘托出更為立體化的“母親”。,如《鄉村畫夢》《蟋蟀,我以為是你》中的集中抒寫。三是作為詩人的“我”這條副線,詩人的“我”有了更為全面和細密的體察和感悟,這條視線在詩中存在的表現就是那些選取生活特寫鏡頭和偶發的議論,如《槐花,潔白的骨頭》中所顯現出的對歷史和現實的有力詰問。我個人認為,兩條副線的出現避免了一勞永逸的平鋪直敘(這在當下很多親情長詩中多有此弊病),增強了作品的鮮活性和感染力。再次,《時光之碑》選取了一個貼近許敏抒情基調的顏色:白色。這與他本色的抒情基調天然契合,還與“母親”那些生活鏡頭渾然一體。為了強化這一大寫意般的視覺效果,詩人在開篇以“媽媽,你是晨光之露”渲染后,又以“紅”與整體色調加以對比(紅布,紅糖,紅雞蛋……/粉嘟嘟的一張/小臉),正是這些美好的影像成為“母親”一生在“白色”中歷經磨難的注腳,那張稚氣的“小臉”此后在俗世里如何一步步變皺、變老、經歷了人間的悲苦哀樂。你看,月光和江水都是白的(“月光比江水更白”)、屋脊是白的(“灰白的屋脊上,露珠下滴”)、骨頭是白的(“44公里山路裸著駭人的白骨”)、頭發是白的(“今夜,我用早生的白發祭奠你”)、更有白熾燈、白玉蘭、白花花的太陽……,而長時間彌漫在詩行中的是白色的雪(盡管它與“大紅喜字”形成又一次對比和反諷),我掩卷沉思,留在腦海中的是白色的時光、潔白的雪和骨頭、白色的刀子(還是寒刀)。詩中寫道:“時光碎了,媽媽/我看見雪白的墻,雪白的床單/托著你的病體。”、“槐花,潔白的雪/潔白的骨頭,重返人間”。盡管有一瀉千里的油菜花和淡藍色的天幕,那都是為著廣闊的情感而留下的襯托。此外,《時光之碑》中通過紀念母親個人命運所涉及到的歷史事件讓整首詩成為一個包含寓言、象征的巨大隱喻。生于1944年的母親,在暴風驟雨(土改中只有幾畝薄地的外祖父被化為富農)中結束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在餓殍遍地中度過了青年(“風像飄散的黃裱紙/不忍擦去以下的畫面:/祖父、舅舅浮腫,外祖母餓死,你是眼睜睜地/看著她離世,嘴角流出膽汁,家里沒有一粒米”),在公有制的背景下艱難度日(“勞累已使浩浩江水麻木/你在清湯寡水里與它和解”),直至“50歲,仍頂著風霜、厄運/前行”,仍是“人海里,漂浮的幸存者/一次次穿越黑暗的地洞/一次次蚯蚓般地尋找光亮”,“陷入無邊的漩渦與刑期,用一個傷口/去堵塞另一個傷口”,而“黑夜的傷口永不愈合”,所以詩人問:“你是否想到戲弄你的光陰”?最后我還要指出的是,許敏有著優秀的物我合一的感受和表現品質,這與他的古典詩學修養和東方哲學素養密不可分,如“春天/院子里的一株白蘭花替你生長/寂靜,緩慢,時時遭遇驚恐/途徑的杏樹,桃樹,梨樹,石榴樹/無花果樹,都是無根的植物,流淚/不開花,關閉嘴巴。”、“風,空手而來,又/空手而歸。云/體虛得如一條沒有魚類的/清冷冷的河流。因為羞恥,棗樹也不肯/結下青果。”、“麻雀以一顆善心,撿拾地上谷粒”等,特別是這樣的一些詩句,在藝術美之外,所帶來的蒼涼和思想的銳利更讓我們有欲哭無淚的深切痛感:“一群烏,從廢墟里飛出/披著霞衣,給不辨真相的世界/深深地鞠躬;河流/陰冷,枯瘦,像你的病體,蜷曲起來/裹緊河床,不再敘述痛苦”,藉由詩人對“不變真相的世界”的質疑和批評,我們窺見到詩人給這個時代的定性:“媽媽,你原諒了他們/原諒了這個時代的不知所措,也原諒了/它的假面、殘忍以及無力奔跑的淚水”、“幫你服下,也順便給這蒼涼的人世療傷”,而“世界的一角一一/許樓村被雨水沖刷得干干凈凈”。“不變真相”、“不知所措”、“假面”、“殘忍”、“蒼涼”正是逼近本質的寫照,故此,詩人用“墓碑沉重/抬著它的村民齜牙咧嘴一一/腳下是濕漉漉的新泥”來結尾,留下的是無盡的浩嘆和發問。至此,也是《時光之碑》的精魂呼之而出,直飛蒼天,昭示世人。
我與許敏匆匆一面,未及深談,容他信任,將《時光之碑》托付于我,以上粗淺之論,恐掛一漏萬。如果說許敏那些以“緬懷”母親為主要視角的詩作,表達的是“泣血之痛“,體現的是“感恩”和“熱愛”的意緒,那么《時光之碑》主要以“回憶”和體驗的方式,融入了對命運、時代和未來的思考,具有了社會學、哲學和宗教學意義上的俯察和體悟,整體上轉入“時光之思”;如果說之前許敏通過不間斷的抒寫,已經在詩學意味上開始為母親塑像,那么《時光之碑》通過半個世紀風雨苦難的母親的經歷,已在為中國婦女、為那個時代提供有力的證詞。可以欣慰的是,在我很不滿意的當代長詩創作的序列里,在以“母親”為主旨意象的作品中,就表達個體情感而言,許敏做了很有啟示意義的實踐。他說:“光陰是一把永不卷刃的利刀”,它在毀滅著一切,也在成就著一切。我們每個人的碑文都只能由光陰來雕刻,而我們首先“必須在時光的身體上刻下聲音”(摘自我的拙作《我必須在時光的身體上刻下聲音》),以此與許敏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