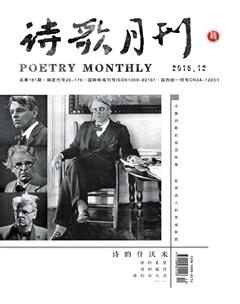林季杉的詩
林季杉

哈密爾頓的早禱
早晨
有光送來風
有風送來的光
秋天的哈密爾頓與我一齊蘇醒
靈魂里的躁動開始緩緩披戴寧靜
有一種低語或吟唱
在身體里悄悄進出
天使在一旁端坐
天父在默默看我愛我
樹木在陽光下變幻色彩
圣母的憂傷灼燒了我一季的寒冬
圣靈輕輕環繞輕輕到來
如同少女輕快的芭蕾舞步
在天梯上伴隨音樂旋轉上騰
失語
這是一場空洞的旅行
注定兩手空空毫無收獲
兩個年老色衰的女人在高談闊論
我必須小心翼翼繞道后院
看兩朵紫色的小花
在草地上悄悄地開放
靜止的紫色和悲傷的豎琴籠罩了我
我好像走在一條送葬的路上
步伐沉重
悼念自己的靈魂
一雙手在大地騰空
捧起我的遺像
在異鄉的路上
每一個路上的行人都帶墨鏡
自己向自己的死亡或黑暗致敬
在這個白人或黑人的世界
我是失語的黃種人
禮貌和距離一樣遙遠
任何嘗試深入的交談都是粗魯的
新英格蘭之地
優雅古老的白色房子
樓下接待賓客富貴而美麗
我住在樓上一個狹窄的空間
隔壁是廁所是書房窗外是樹林
我日夜在地板上蜷縮我的身體
細算樹木光影和印第安人的命運
終于到達了要離開的日子
離鄉偶記
對于我這樣短壽的人
人生大概過了一半
我依然在別人的故鄉尋找家鄉
克服與生俱來的恐懼
遙望當年離家的日子
井邊擺放一雙破舊的繡花鞋
鄉間小路彎曲著父母的心
下過雨的泥濘泥濘著我的呼吸
有人在林子里費勁地砍樹
砍我積累多年的傷口
我日夜在異鄉的黑暗里
像鴕鳥一樣笨重地奔跑逃逸
偶爾把頭埋在泥土里,尋找安息
一路上有背叛的飛鳥
故作姿態的美麗的喘息
晶瑩剔透的魚或翅膀
白色凝固的大象
脫落閃亮的鱗片和巨大的憂郁
少女的手纖細無力
巖石撫摸青苔風親吻溪水
景泰藍青花瓷靜靜的擁抱
來吧,共赴一場異鄉的盛宴
獵人和頑固的狗和狗
披戴麻布孝衣深情對望
搞不清是一場輕浮的葬禮
還是重復多次無聊的婚禮
斷頭臺已經架好了
嚴肅一點,家鄉的黨員在開會。
現在,請閉上雙眼
向全世界道聲(他媽的?)晚安
瘋狂的石頭
——誕生記
媽媽,
這是個孩子,不是石頭
從她出生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我不再是個孩子
疼痛原來如此盛大
疼痛又如何?掙扎又如何?
慘叫還是呻吟又如何
生命的到來就是要經歷死亡的痛苦
我選擇的也是一種別無選擇
然而,比起疼痛更疼痛的是疼痛的記憶
肉體不斷地替換掉肉體
肉中的肉,骨中的骨
說不清是破裂還是繼續破裂?
一個毛茸茸的肉團團
裹著一層憂郁又粘稠的蜜
赤裸地依靠在我胸前
好像沒有眼睛
卻在心里看著我
羞澀地吮吸著我的乳頭
醫院的消毒藥水
麻醉著我的嗅覺
被縫上的傷口孤寂地慢慢滲血
潔白的紗布草莓醬面包
破碎的毛細血管,扭曲的臉
剪掉臍帶吧,孩子的父親
這個孩子是個瘋狂的石頭
你種下的性感的石頭
不久以后
這個黏在身上粉嫩的小面團
會長成一只不可靠近的刺猬
以滿身的尖銳宣告長大
充滿能量四處亂竄
向我們索要訓練無素的愛
或是訓練有素的傷害
脆弱如何喂養脆弱
這是一場撫養?
還是有人正在醞釀一場
更為長久的成人的陰謀?
波士頓地鐵偶遇友人
下一站,Harvard Squard
越南菜比中國菜正宗
三十二歲時我與自己
交換彼此的口味和大腿
一只蒼蠅,Waiter拿出
菜譜和三張菜譜
冰水和三杯冰水
夏日的末了
過時的陽光踩過對面過時的男人的臉
不是衰老勝似衰老
他的女人也是女人
金發碧眼的女人
素食主義者嬉皮士后代
熱衷信佛、打坐和詩歌
飯后來一壺西湖龍井
煙霧裊裊中對視,窺視
整個世界都酒足飯飽
野地里的一頭發情的公牛打嗝
冷靜的蜥蜴趴在巖石上等待機會
迅速伸出細長的舌頭
親吻黑的白人,白的黑人
而我是黃色或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