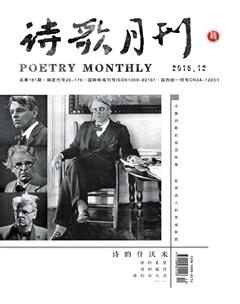凹漢的詩
凹漢

逝者如斯
一個山村音樂人曾慶超畢業于著名音樂院校
早已失去了架子鼓王的霸氣
多年雄壯的男高音,也已經變得越來越沙啞
他每天召集村里幾個
熱愛音樂的留守中年男女翻山越嶺
背著裝在木箱里的音響、架子鼓、電子琴、吉他……
為山村各個喪事喜事送去最美祝福
他豐滿而美艷的老婆曾跟隨他一起能歌善舞多年
可是現在老婆逝去,女兒也遠嫁到重慶
他只有一個人繼續留守山村甩甩長發氣運丹田
一個個輕盈而靈動的多來米發梭拉西哆
為多少山村逝者送去子在川上日:
生命就是時光的流水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奠
在大巴山山村路口,遭遇很大一個奠字
奠字下面沉默、鞠躬、下跪、后退、向前、磕頭……:
一些靈旗素妝的人群,紅腫的瞳孔
一些撩人心碎的悲傷從一排排嗩吶孔吹出來
把滄桑歲月吹盡,生生世世吹無
把逝者一部辛酸的人生歷史吹進天國地府
那其實并不是有什么鬼神在召喚
而只是千百年來,大巴山人最虔誠至親的祝福
割草
在茫茫大巴山的母親墳前雜草叢生
我不得不彎下腰,單膝跪地
右手握緊母親生前用過無數次的鐮刀
左手抓住一把把半米多高的
苦蒿草、狗尾巴草、絲毛草、野燕麥草……
鐮刀變得越來越薄,越來越窄
所含的鐵質成份越來越少
曾經尖利如牙的鋸齒
也被風雨打磨得越來越扁平、銹鈍
我割得手心起繭,額前冒汗
我知道把瘋長的野草終于全部割完
也不代表就歸還母親灰塵滿面的一份干凈
但是看到艷陽當空照
把每一寸光芒,照在母親翹首的墳頭
我還是從心里上感受母親
生前怕冷的身體,好像多增添幾絲溫暖
泥人
穿行在大巴山峻嶺的每道坡,每道坎
你我都是用巴山之土捏成的一個泥人兒
泥的胳膊,泥的雙腿,泥的眼睛,泥的嘴唇
泥的肉體,泥的魂魄
被無數風雪之刀雕刻過,艷陽之火淬取過
被一片片冰涼的月光剖過開思想的鋒芒
當又一個泥人兒在鑼鼓鞭炮聲中魂歸大巴山啊
也只不過是生于塵來,歸于土去
也只不過是為大巴山蒼白的身子輸入一份血液
那么不經意,打完了自己一個泥土的圈兒
聆聽父親談起母親
父親的聲音像一枚繡花針落在地上
很輕,像是怕驚動了已在山那邊的母親
談母親嫁給他的第一天腸胃就疼痛
他趕幾十里的山路去找老中醫
吃完一個多月的中藥湯劑后完全治好
為什么現在,還是會死于一場胃病
談母親趕場下街不舍得花錢去吃一回館子
每次做肉吃,都會讓他吃得多些
最后父親談到母親臨死時在他面前流眼淚
他的瞳孔才無端的格外濕潤起來
他心甘情愿為母親做一把支撐的雨傘
而母親突然就這么走了讓他說不出一句話
感覺整個大巴山,都搖晃了起來
亡靈書
對于大巴山,每一個鄉親的死亡的儀式之上
還是能在短暫的臘月或者正月
呈現出一場最原始的白事當紅事,喪事當喜事
一口沉重的靈柩內,找回了他們的失落之魂
在每一個鄉親悲痛的生死告別祭文中
一場草木為止震顫,河水為之斷流的嗩吶聲聲
一個穿越過奈何橋的小調音符吹吹打打
死之極樂的伊甸園卻有悲盡喜真來
對于逝者節哀的一生之苦短啊!一生又何求
在趕往大嶺鄉的中巴車上
滿滿一車從外地趕回來過年的老鄉們
一上車就用廣味、京昧、上海味等南腔北調
來掩飾自己某種身份的尷尬
土生土長的大巴山麻辣味,只剩少許咸酸
一件西裝遮蓋曬得黝黑的身體
一雙油亮的新皮鞋遮蓋磨出老繭的腳底
興奮表情,遮蓋凍得通紅的臉龐
一個藍色發型的八零后也在炫耀一天三百塊
只有坐在我前面的那個瘦弱之人
力氣可以移動一座山,汗水可以匯成一個潭
但他這次從廣州急急忙忙趕回來
還來不及團圓,必須先湊足十五萬做胃癌手術
外婆
不知為什么,每次聽到故鄉傳來死亡的消息
我的心就像置于一場冰天雪地中
就會想起我那留守在大巴山苦命一輩子的外婆
想起那時她滿頭的鬢發蒼蒼
滿臉的皺褶縫隙,似乎閱盡了人世滄桑
想起小時候春節拜年我去她四十平方米的破木屋
一定要吃她剛殺的過年肥豬吃得直打飽嗝兒
爸爸說:她在臨死前還一直念叨著我
是不是還牽掛我曾滿口答應要給她買一雙新棉鞋
她一輩子穿著舊布鞋的腳心冰塊一樣冷透骨
慈祥的等待
他經常把故鄉的方言,故意拉長成小謠曲
慢慢聲聲滋潤一片黑夜肝火
他也經常在蒼茫的田野中半蹲下
聆聽著一縷清風是怎樣在谷穗之間傳遞秘密
他喜歡在一袋劣質旱煙中吧嗒吧嗒
讓飄起的煙圈兒,一圈又一圈兒繚繞成幸福
他遞給過孩子們糖果獻給過孩子們親吻
2008年12月的某個夜晚卻被一場咳嗽發燒絆倒
被一次小小的醫療費用絆倒
撲通一聲跌到在春節的團圓飯大燈籠爆竹聲聲……
他冷卻的心臟依然,不爭斗不急躁
村組長
四年之前還與他一起在飯桌上闊擺龍門陣
當十年村組長,從來沒貪過一分錢
還帶著百多名鄉親大面積造田開荒戰勝大旱災
把土地一丈一寸精確測量到了每家每戶
身體除了為一點肩周疼痛犯愁幾乎再無其他問題
一把鋒利鐮刀就疾馳行走在他硬朗的骨頭中
他的力氣可以像大巴山一樣綿綿無盡
2009年春節時卻不小心被山崖邊一棵枯樹墜滑
數十米深的峭壁下他的腦漿迸裂開花
他血淋淋的一雙大腳掌卻還穿著兒子
剛從廣東寄回來,一雙油光滿面的嶄新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