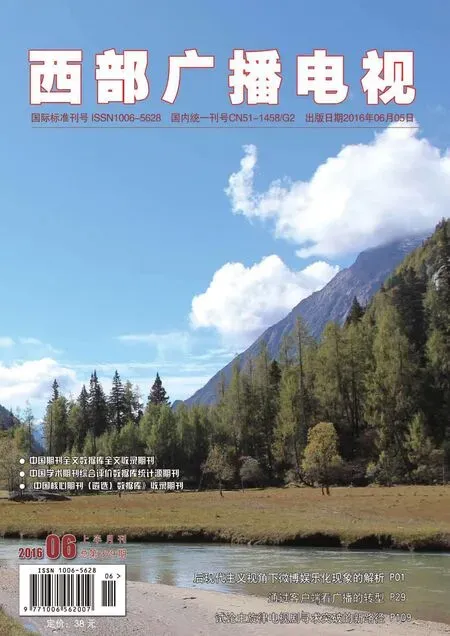青春網絡劇里的集體記憶狂歡
——以《最好的我們》為例
宋愛玲(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
青春網絡劇里的集體記憶狂歡
——以《最好的我們》為例
宋愛玲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
本文擬從集體記憶、懷舊元素、碎片化敘事等角度對青春網劇《最好的我們》進行文本分析,探討其不同于以往青春劇的特點和熱播背后的受眾心理,以及該劇是否有利于對當代青年群體作出正確的價值引導。
青春網絡劇;最好的我們;集體記憶;懷舊;
《最好的我們》是愛奇藝的自制網絡劇,該劇接檔2016熱播韓劇《太陽的后裔》,很多觀眾表示,與《太陽的后裔》那種驚心動魄的愛情相比,他們更偏愛《最好的我們》中耿耿余淮的青春,這部劇被當作順延《太陽的后裔》熱度的“超級網劇”。
1 重構集體記憶:植根現實主義創作
馬丁·澤爾歐德指出,以往的媒介與社會記憶研究通常聚焦于媒介史而非媒介理論當下的發展,研究過于碎片化,且失之于悲觀。一些學者擔心現代社會變得明顯只重當下,忘記了過去。
近年來,隨著各種青春劇的熱播,似乎青春懷舊題材的電影或電視劇都能大獲成功。有些導演甚至將沒有墮胎當成一個對外宣傳的噱頭,的確,國產青春劇正經歷著從懷舊、傷感的基調向純愛、真實轉型。不同于以往男主主角的感情被現實打敗等傷感題材,《最好的我們》主打勵志牌,在第一集中,大伙一起在教室偷看劉翔比賽,以后劇集中的“一二·九”大合唱、話劇排練、物理競賽、軍訓,為了物理競賽不參加合唱的余淮,喜歡小團體拉幫接派的耿耿、余淮、簡單、貝塔,將這些情節置身于“非典”“奧運”這些社會大事件的背景下,充斥著曾經風靡的《那小子真帥》、周杰倫的《晴天》等元素,并配合盡情去玩而不是去演的90后演員們,其展示了90后真實的青春,更能喚醒90后的記憶。對比《何以笙蕭默》的劇情,一個事業有成的黃金單身男子為了初戀苦苦等待七年,這似乎讓置身于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社會里的觀眾難以置信。
2 懷舊與碎片:重塑青年亞文化
懷舊,是因現實失意而對過去美化性的回看,而青春時期的“夢想”恰恰對比著現實的無情。當受眾沉浸在挑選、美化后的個人及集體的青春記憶中時,就形成了一種暫時的“焦慮消逝”了的“欣快癥”。青春題材作品因此獲得強烈的、集體的情感。
在這部劇以真實取勝的時候,我們也要對青春文學有所反思,其雖然可以風靡一時,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記憶,但由于其缺乏戲劇性和沖突性,使之不可能像經典名著一樣不朽。比如哈代的《還鄉》,所有的主角和矛盾都聚集在了女主角準備和情人私奔的那個灰蒙蒙的夜晚,那個夜晚讓矛盾沖突白熱化,那晚之后,所有的故事情節都發生了巨大的轉折。而《最好的我們》這部劇沒有太大的重復觀看的價值和引發人深省的思考,因為太過平淡。
不同于青春懷舊劇特有的碎片化的敘事方式,二十四集的《最好的我們》以友情、師生情、愛情為主線,從入學軍訓到文理分班,再到最后主角們紛紛離場,恰似整個高中生活的完整呈現,這部劇是一個很好的現實教材,它教會了我們怎樣更好地度過高中三年。高中時期是一個人一生中非常關鍵的時期,也是價值觀念形成的重要時期,一部好的勵志青春片能讓那些尚未開啟高中生活的孩子們打開視野,使其學會正確對待青春期萌發的正常感情。與此同時,以校園為背景的電視劇又和現實社會有一定程度的割裂,只聚焦于校園這個小環境,容易遮蔽對現實社會的思考。文藝作品反映了時代,電視劇對大眾文化的導向與影響力,如果文藝作品脫離了現實社會,容易吞噬年輕觀眾對現實的認知。
正如某知名學者所言:“我們對現在的認知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換言之,我們是在一個與過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聯系的脈絡中來體驗現在的世界的。”
3 觀影主力:反設置議程
阿斯曼指出:“當互聯網創造出一個無遠弗屆的交流框架時,文化記憶也創造出了一個穿越時間長河的交流框架。”“實時”“當下”、淺思考、淺交往消解了集體記憶的歷史縱深感以及附著其上的情感、審美品質、倫理和信仰價值。在80后和90后早已成為觀影主力的時代背景下,互聯網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虛擬交往社區,互聯網和現實生活的雙重議程設置,加深了我們對話題的關注度,周圍朋友的強力推薦往往是我們去觀看一部劇的主要原因,這個原因甚至比虛擬社區議程設置的能力還要強大。被身邊的朋友推薦,本來在看,后又不看,看到別人看,和自己有了共同的興趣又開始看,周圍朋友的討論所以開始看,媒體的話語討論也增加了其傳播力度。
4 結語
《最好的我們》在樹立青春網劇新標桿的同時,給予了我們理性懷舊的機會,提供了正確對待逝去的過去的視角,更啟迪了我們去發掘生活中的真善美,但同時,其也存在著青春題材同質化、敘事單一碎片化、與現實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脫離等缺陷,青春網劇應該正確反映時代,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1]趙靜蓉.懷舊—永恒的文化鄉愁[M].北京:商務印書出版社,2009.
[2]李顯杰.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 [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