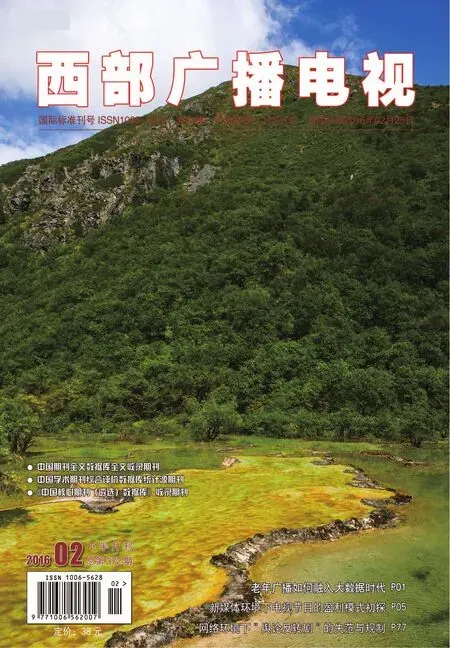網絡環境下“輿論反轉劇”的失范與規制
鄭 睿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
網絡環境下“輿論反轉劇”的失范與規制
鄭 睿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摘 要:進入自媒體時代后,網民群體日益擴大,表現出其特有的群體特征,并且對網絡輿論環境乃至于整個社會輿論環境造成了顯著的影響,加之多方的介入,導致近幾年頻繁發生“輿論反轉劇”。本文結合當前網絡現狀和相關案例,參考了勒龐《烏合之眾》中關于群體行為的相關觀點,從網絡群體的特征和網絡輿論領袖兩個方面,簡要分析了近幾年網絡輿論當中的顯著現象——“輿論反轉”,并提出了一些應對策略。
關鍵詞:輿論反轉;網絡群體特征;輿論領袖
1 “輿論反轉劇”之熱演
勒龐對法國大革命中群眾的行為和心理進行了研究,創作了群體心理學的開山之作《烏合之眾》,揭露了“多數人永遠正確”這一錯誤觀點。很顯然,“烏合之眾”的說法絕對不僅適用于18世紀的法國,同時也適合現代的網絡社會。網絡具有隱匿的作用,遮蔽了個人在現實中的身份,造成了網絡身份和現實身份的不對應。媒體時代的到來,使網民形成的網絡群體的行為影響力日益擴大,甚至成為了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關鍵因素。近幾年,從“云南的導游惡意辱罵乘客”“女大學生扶老人被訛”“成都女司機遭暴打”到“哈爾濱天價魚”事件都引發了網絡熱議,這些網絡輿論當中出現的吊詭的新興現象,體現出網絡群體在看似自相矛盾的行為中,展現出的翻云覆雨的巨大力量,他們使網絡輿論環境不再僅是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而是使整個輿論走向一極。這打破了“沉默的螺旋”觀點,變成優劣勢觀點地迅速反轉,輿情態勢如同蹺蹺板一般,短時間內滑向幾乎是完全對立的一方,造成輿情撲朔迷離。
2 無意識從眾而排他——網絡群體的特征
在勒龐看來,心理學上的群體是在某些給定的環境下,群體的情緒和觀念選擇了同一個方向,自覺人格消失,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也就是說,在網絡這個特殊的環境下,當我們漫無目的游蕩在網絡當中時,此時我們并不是勒龐所說的群體;但在特定的環境下,由于受到某些強烈刺激,比如關切公眾自身利益的社會現象或者話題的討論,人們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為暗示在互相之間傳染,體現出《烏合之眾》中認為的“群眾等同于無意識集體,因為無意識,所以力量強大。”
在“輿論反轉”的初期,網友們常常容易受到碎片化信息的刺激,如同勒龐所言“刺激群體的因素多種多樣,群體總是服從于各種刺激,因此它們也極為多變。”而且這些信息往往和網友對社會現象和某些群體的心理成見相符合,或者和網友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同情對象相一致,使得他們先入為主,進而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進行先一輪的討伐。也就是勒龐所說的群體容易被暗示,由類似經驗引發的貼標簽的思考方式,產生一系列的行為暗示,使得他們并沒有做長遠的打算和思考,只是一哄而上,以粗放的方式,感性化、情緒化的進行簡化看待。比如在“云南導游辱罵乘客”的事件中,網友對旅游團的脅迫消費行為早已積怨頗深,導游從旅客口袋中獲得回扣的糟糕形象也令人印象深刻,再加上被曝光的導游一方處于道德劣勢方,便使公眾盲目地任憑這個刺激擺布。更甚者,如果事件的參與方有著“富二代”“官二代”的標簽,網絡群體更是會成為這種“標簽刺激下的奴隸”,一定會認為當事人是道德敗壞的紈绔子弟。比如網絡瘋傳的“義烏開寶馬的年輕媽媽拒絕砸窗救幼子”事件,當網友發現那是一輛寶馬車后,就將這個標簽貼在這位媽媽的身上,斷定其惜錢如命,不顧幼子的安危。甚至還有網友主動為指責方貼上標簽的,比如在“成都的女司機遭暴打事件”當中,最后網友們已經成為無法理性分析個體差異的群體,紛紛認為女司機一定有“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的背景。
網民群體的心態因受到變化的外部刺激影響,造成群體行為的變化,如同勒龐所說“他們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發,但是他們又總是受當前刺激因素的影響”。在反轉鬧劇中,當真相浮出水面,成見被打破,簡單的事件暴露出復雜的內幕,群眾的情感受到當下最新刺激的影響,而且戲劇性的轉變更加吸引人的關注,此時就會掀起更大的輿論浪潮,網絡群體在反轉中陷入兩種極端。比如他們對待在日本故意“碰瓷”的老太太前后的態度,由呵責“丟人丟到國外去”變為同情,關注她的傷情病勢。雖說事實的真相水落石出,但是反轉的過程自始至終都體現出網絡群體被外部刺激所擺布,從而顯示出盲目從眾性。
在“輿論反轉”的過程中,當輿論討伐進行到高潮階段時,經常伴隨發生極端的“人肉搜索”事件,因為網絡群體容易沉溺于神秘而強大的集群力量中,從中獲得一種安全感和行為的正當性,這便更容易產生極端的越軌行為,如同勒龐認為的孤立的人“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搶劫的念頭,并且會立刻屈從于這種誘惑”。比如在“成都的女司機被暴打”的事件中,網友們最開始紛紛譴責男司機“喪心病狂”,并爆出其工作單位及現居住的宿舍地址。但是當行車記錄儀曝光之后,女司機也是責任方的證據確鑿,反轉產生的沖擊力使此次的“人肉搜索”較上次更為瘋狂,爆出女司機盧某的多次違章記錄,甚至是開房記錄。相比之下,人們在現實當中就會比較謹言慎行,我們很難會去搜索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的信息,但是群體放置到網絡環境中,這份沖動,急躁,好奇心就會發揮到極致。而且當一個消息經轉發產生了較大影響時候,群體的力量賦予了個人無形的力量,使個人力量被虛假放大,加之網絡環境賦予的隱匿性和法不責眾的事實,人們會容易參與其中。而且,因為“輿論反轉”的特殊性,使得“人肉搜索”的對象波及到兩端,無論事件中的受害者還是被害者,都會遭受到干擾和隱私的暴露,從而給網絡環境帶來極大的沖擊和破壞。
3 輿論的駛舵者——網絡輿論領袖
烏合之眾就像溫順的小綿羊一樣聚集在領袖的身邊,在網絡環境下,充當領袖的人都擁有一定的名望和公信力,可能是利益相關者,也可能是媒體及領袖型網民。首先來看利益相關者,他們往往為維護自身利益,發表對自己有利的言論,比如雇傭大量水軍,網絡推手來歪曲輿論導向。曾經有一則名為《成都男買20張火車票送女友,丈母娘聘禮減半》的報道在網上瘋傳,大家紛紛贊揚其為“搶票哥”,但真相是某搶票軟件企業炮制的虛假新聞。這些都是利益直接相關者運用各種手段引導輿論,迎合網友在一票難求的春節期間極度渴求車票的心理,推波助瀾進行暗示傳染,以形成利己的局面。
其次來說媒體,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但也有部分媒體為了自己的利益,迎合大眾主流意識,報道了含有自身價值取向的新聞。在反轉劇中,部分記者為了搶新聞而不顧真實性,僅講究時效性,導致碎片化的信息四處流散。比如在“北京老外撞大媽”這一出反轉劇中,最開始導致輿論失實的就是一位攝影記者,他本人在并不了解真相時就臆斷其有無,導致貼標簽式討伐大媽“碰瓷”事件再度重演。在“成都女司機遭暴打”的真相水落石出之后,媒體更是立馬發表了《蓉男司機打人前后真相曝光女司機挑事》,用“挑釁”“自食其果”等詞語,語氣失衡,刺激網絡群體迅速將槍口對準女司機。但是無論是哪一方,在這次事件中都有責任,媒體不應為了吸引眼球而將矛盾激化。網絡平臺的發達,使很多媒體在紙質刊物出版之前就會在網絡平臺上發表言論,而網絡平臺時效性強,傳播速度快,一旦各大網絡媒體“斷章取義”,就可能造成錯誤的導向,而這時候,相對規范的傳統紙質媒體因為出版的耗時,以及購買的滯后,無法及時跟上網絡快速傳播的浪潮,導致錯誤的偏激的媒體報道占據上風。
最后來說領袖型網民,比如大V人士,多由較高地位,或者有專業見解的網民構成。他們的觀點往往被人稱為權威觀點,引來很多人的跟帖熱議,就如勒龐所說的“他們迫使自己身邊的人接受他們的觀念和情感,人們對他們俯首帖耳,就像吃人不眨眼的野獸對馴獸師服服帖帖一樣。”在網絡的環境下,不論是被迫還是主動,領袖型網民的觀念更加容易通過暗示和傳染,從而馴服一批人不自覺接受某些思維。比如在“女子為保護女童被狗咬”事件中,很多名人紛紛轉發募捐,最終籌集八十萬善款。權威的存在本身就對輿論導向有特殊的作用,所以,在網絡規范中,領袖型網民要樹立好良好的輿論導向作用。特別是在網絡環境中,由于評論字數的限制,人們更傾向于用簡潔有力的語言表達自身的觀點,從而加深了群體的服從欲望,如同勒龐所說的“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此時,雖然每個人都可以發聲,但是發出的聲音總體上看已不一定符合實際的心聲。
4 結語
當前的網絡時代并不單純是情緒化爆棚的環境,也有很多持有正確觀點的人勇于發聲。而且,由于網絡的存在,公眾議題得以擴大范圍,跨越階層、地域的討論,讓更多的社會正義得以伸張,民意得以反映,增強了民眾的主人公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但是,跨越一個世紀的勒龐的理論,仍舊不能被忽視,網絡上的群體相比于現實生活更加不理智,這是一個事實,否則就不會動輒出現“人肉搜索”、謠言滿天飛的亂象。在這種喧囂的環境中,作為網民來說,應該保持個體的冷靜,慎重對待媒體、權威發布的信息,進行理性獨立思考,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不妄加評論,在真相揭示之后不沖動討伐,保持言語文明,對待新聞不應貼標簽式地簡單機械看待,對當事人要持有最基本的尊重。特別是領袖型的網民,更要時刻銘記自己的加V符號代表的責任,不偏聽偏信,發揮正確的引導作用。而媒體相比網絡群體更應該保持理性,首先,不撰寫帶有自身傾向性的新聞,“在使用新聞語言時,要極力避免簡單化、沖突化、符號化,在新聞文本中應該注意新聞用語的規范,不能任意夸大,語氣失調”。其次,不迷失在情緒膨脹的環境當中,而應該保持冷靜,探尋其本源,補全信息,正確引導觀眾。特別是在反轉新聞產生的初期,媒體的引導對輿論的走向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媒體要及時調查澄清,“切實當好‘把關人’‘瞭望者’的角色和任務”,將會大大減少反轉新聞的發生。特別是在傳統媒體加速與新媒體融合的進程中,更是要運用好自己權威的力量,保持自身的專業性,注重發揮新媒體時效性的同時,也兼顧準確性,保持傳統媒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身處網絡的環境中,保持理性,既是我們應該踐行的,也是我們應該秉承的態度。
參考文獻:
[1]蘇雨,楊璐.淺析“輿情反轉”的成因及媒體責任——以“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為例[J].傳播與版權,2015(7).
[2]敖陽利.傳播學視閾下輿情反轉事件研究[J].新聞研究導刊,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