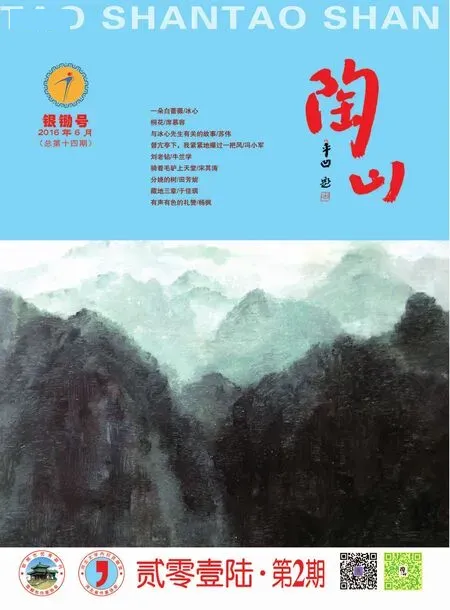大姐有福
◎劉臘梅
大姐有福
◎劉臘梅

我從來就沒有和大姐聯系過,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偶爾聽別人說起過她的閑話,不好聽,卻無關痛癢。畢竟小民,滄海一栗,誰有心思與你較真?
我在學校工作的時候,每天從大姐店門前經過,都看到她在打麻將,嘴里嗑著瓜子兒,也空出來嘴說大話粗話,贏了罵兒子,輸了罵老子,喜歡與不喜歡都用罵來表達,任何一句話從她嘴里出來都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好像這樣說話特別過癮,特別有力度,停頓的標點都帶著狠勁兒。肉嘟嘟的指節上箍著八個金光燦燦的戒指,十指在麻將堆里撥來劃去,便是一片眼花繚亂的光。大姐不用上班,她男人能掙錢,大姐的錢夾子里輸贏都風光。笑聲也爽朗,任何一件事或者一句話都有笑的由頭,是大男子的氣場,有點江湖的作派。他們的話我是不敢接的,也不甚明了,像行話,所以,我從來不和大姐說話,她也從來不和我說,我們像平行的兩條道,心照不宣,各行其道,誰也不礙著誰,見面也就是蜻蜓點水似的笑,算是招呼。后來聽說大姐離婚了,也不知詳情。
眼看天氣一天一天轉涼,日歷上說是立冬了,盡管太陽偶爾還是嬌艷,卻是虛張聲勢,我開始給自己準備冬需物品了。
那天去超市買被子,看到儲物柜處站著一位面熟之人,寬額闊臉,生得特別大氣,是大姐。我準備好了一副可有可無的笑,不濃不淡,沒有甄別,禮貌得很,對付誰都得體。剛走近,大姐就來了個大而夸張的問候,有點他鄉遇故知的熱情,聽得出是極度壓抑過的高興:“啊呀,劉老師啊,你來買什么?”“我看看被子。”“你兒子在哪里上學?聽說你到城里工作好久了,難怪很久都沒有看到你了。”我十分不習慣別人公眾場合的過份熱情,簡單對答了兩句。“我幫你看看,那邊有個熟人,可以給你打折,你等我下。”說完,也不待我表態,大姐招呼同行幫她看著活計,自己拉著我來到一堆五顏六色的被子前,一邊向我介紹各種被子的質地,一邊向售物員拉人情要折扣,想來大姐在這里很有人緣兒。我選中了一款被子,大姐兩句話值兩百塊。我有點受寵,說了一些理所應當的感謝話。
走的時候,大姐讓我常聯系,有事兒找她,好像我倆從來都在聯系。我突然愧疚得慌,平白無故受了人家如此這番厚意,人情債欠大了。
大姐知道我的名姓,知道我有個兒子在上學,甚至還知道我工作的變動,我于她,是立體完整的。而她在我,僅代表性別與年齡,是一個平面,我沒有問她來這里上班多久了?是否一個人過?孩子在上學還是在工作……問與不問我都怕傷人,我覺得自己特別和自己過不去,由感動而生出心虛,不僅是人情債這樣簡單,是良心債了。離開的時候,竟然忘記了留個電話,更不好意思問大姐姓名。
大姐熱情爽性,樂呵大方,有錢的時候可以戴十個戒指打麻將,沒錢的時候可以站十個鐘頭賣東西,無論生活的軌跡怎樣改變,臉上依舊陽光,笑場還是海闊天空,那份豁達簡單的快樂,實誠潑烈的血性,如初。或許,生活本應如此,簡單而真實,得此真諦,大姐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