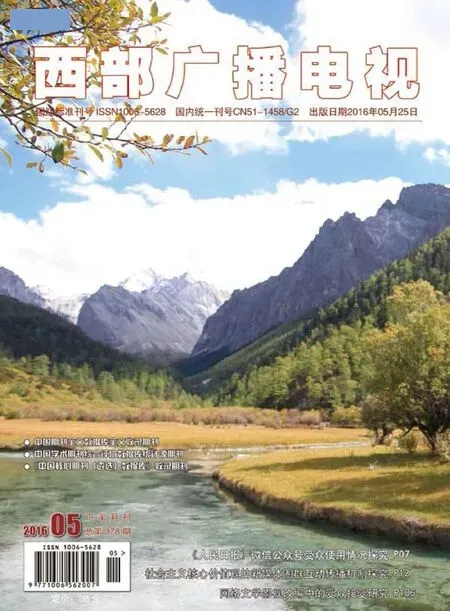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革命——從《一江春水向東流》看蔡楚生導演的個人風格
張馨月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革命——從《一江春水向東流》看蔡楚生導演的個人風格
張馨月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蔡楚生是中國近現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他的《漁光曲》《一江春水向東流》均深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體現了電影的“人民性”,表現了其極強的個人特點。同時,以群眾喜愛的“苦情戲”的形式表現電影主題,使得他的很多作品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
蔡楚生;個人風格;“苦情戲”;現實主義;電影
1 苦情戲題材受歡迎
蔡楚生導演被認為是最擅長表現苦情戲的導演。苦情戲在中國一直很受歡迎,即使在現代的電視熒屏上仍充斥著很多黃金檔苦情戲,而且這些戲多以民國時期為背景。近代的中國承載了太多的苦難,封建社會在瓦解的同時,帝國主義侵略,軍閥混戰,政府腐敗,人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因此,當這些現實映射到電影中時,那些苦難便戲劇化地表現和深化出來,給人一種切膚之痛的感覺。
“苦情戲”之所以能在中國長期盛行,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特別擅長“苦情戲”,“苦情戲”的素材非常豐富。同時,由于“苦情戲”具有較強的感染性,其在熒屏上具有很強的表現力;第二,觀眾特別愛好“苦情戲”,仿佛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然而,在《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一片贊揚聲中,田漢曾直言不諱地批評說:“《一江春水向東流》這部影片,雖然作者企圖‘從一個人的遭遇看中國抗戰’,但我們很遺憾地還不能從它看到真正中國民族抗戰的悲壯的史詩。毋寧又看到一個以抗戰為背景或‘配角’的古老的《琵琶記》型的人情戲。”
從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14日,《一江春水向東流》連映三個多月,創造了解放前中國電影賣座率的最高紀錄,觀眾達70余萬人次,連盲人亦要買票去電影院聽戲。當然,“苦情”絕不是這兩部影片叫好又叫座的最主要原因。蔡楚生導演的寫實風格以及時代背景所反映出的現實問題,才是電影廣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2 故事結構宏大又嚴密、覆蓋層面廣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詩性的電影宏篇巨制。整部影片時長三個小時,在時間跨度上,從八年抗戰一直到結束,長達八九年之久;在地理位置上,從上海到武漢再到重慶再回到上海,根據戰火的不斷延伸以及后來的消逝,蔓延了長江上下游幾千里的距離;在社會涉及的廣度上,影片主角一戶人家的所有家庭成員,涵蓋了當時的上層社會、中等階級和底層人民,導演通過表現主角一家的命運,深入細致地揭示了當時社會各個階層人們的生活狀態,從而展現了一幅現實社會的全景圖。而這一宏大圖景的每條線索都跟主要人物張忠良有關,結構嚴密又不失每個故事的獨立性。故事講述了抗戰前期女工素芬和飽含愛國熱情的夜校老師張忠良的故事,二人相愛并誕下一子后,張忠良跟隨部隊一路西撤,在戰火中顛沛流離,而素芬則帶著兒子和婆婆回到了鄉下。
3 獨特的兩條平行敘事線索
從表現手法上來看,蔡楚生導演用了兩條平行敘事線索。一條以素芬為線索,通過素芬在婆家的經歷,展現了淪陷區人民的悲慘命運和艱苦卓絕的抗爭。被鬼子壓榨而代表鄉親們去求情的公公被殘忍殺害后,素芬帶著婆婆和兒子從上海來到了鄉下,再從鄉下到上海,顛沛流離,受盡磨難,一心癡盼丈夫張忠良能回來。“逼上梁山”的弟弟張忠民加入了游擊隊,后來跟隨游擊隊回鄉剿滅了殺害父親的鬼子。最后,他與同學,同時也是游擊隊隊員的婉華結婚,這二人是本片所有人物中唯一讓人覺得有希望,有未來的人物。或許也是蔡楚生導演故意做了這樣的設定,不至于讓人全然喪失信心。本片在人物設計上均有很強的獨立性,這也是這部片子的一大特點,眾多配角有自己的存在空間和生活環境,既不顯得繁雜,也能因此展現更廣闊的現實。
另一條線索展現了張忠良在重慶的生活,在蔡楚生導演的鏡頭下,他與淪陷區的妻子在鏡頭之前相互切換,運用平行交叉蒙太奇,將兩條線索的情景形成強烈的多層次對比:張忠良的背叛和素芬堅守的對比;張忠良本人前后的對比;張忠良兩任老婆加一任情人的對比;張忠良和素芬的愛情以及張忠民和婉華愛情的對比等。同時,還運用閃回等鏡頭,表現了張忠良前后的巨大差異。
本片采用開放式結局,這正是蔡楚生導演最擅長的一種表現形式,和《漁光曲》一樣,其中一位主人公死亡,剩下一片人或唏噓,或控訴,或傷痛。開放式的結局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或許苦難就此終止,世界開啟全新的篇章,或許苦難還將繼續,幾個主人公繼續在時代和欲望的夾縫中沉淪掙扎……導演并沒有正面給我們講述故事的結局,而是把它作為一個禮物、一個巨大的想象空間,送給了臺下千千萬萬的觀眾,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千千萬萬的中國觀眾或者說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觀眾,都能從這部經典之作中收獲他們最有感觸的部分,延伸出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最好的結局”。這或許就是經典之作歷經幾十年依然打動人心的奧妙之處。
[1]李少白.憶蔡楚生并說其創作[J].粵海風,2005(5).
指導老師:陸慶平
張馨月(1991-)女,漢族,河南南陽人,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播音與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