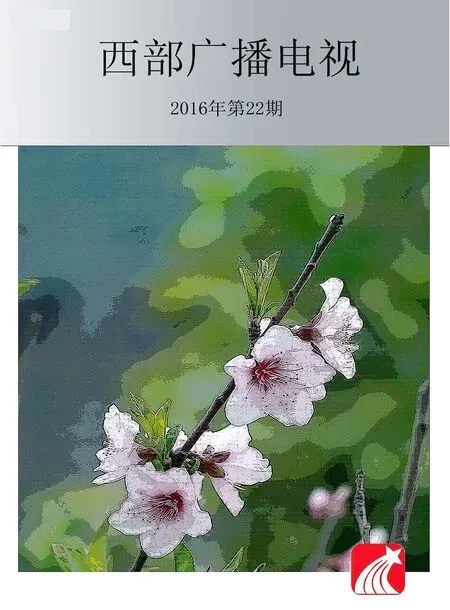孔子思想的傳播學解讀
楊 偉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孔子思想的傳播學解讀
楊 偉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傳播理論家和傳播實踐家,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化傳播時曾稱他為“無冕之王”。他曾為中國古代的教育傳播提出了具有重大歷史影響的理論。本文主要從受眾思想、傳播符號、傳播模式等方面以傳播學的視角解讀孔子的傳播思想。孔子的眾多傳播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通過分析,以期用傳播學的理論來解讀孔子的傳播思想。
孔子思想;傳播學;受眾符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創辦學校,著書立說,游學演講,為春秋時期文化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孔子傳播了古代思想文化,成為了中國文化傳播的先驅。現代社會,人們依舊研究孔子的傳播思想,因為其思想的深刻含義及時代價值,在現代社會,對于人際規范及傳播規律仍可以帶來新思考與啟示。
1 孔子的傳播思想
1.1 “知溝”理論與分眾理論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政局的動亂,新的社會階層——“士”開始出現。此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獲取文化知識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需求。在此情況下,孔子提出了新型的傳播理論,他把人的知識結構分成了“生知”“學知”“困學”和“不學”四等。他在《論語·季氏》中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意為:天生就懂得的人最聰明,通過學習而懂得的人次一等;遇到困難才去學習的人又次一等;遇到困難還不學習,就是下等的愚民。孔子根據社會文化的分化,看到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知識結構,主張對不同知識結構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傳播方式。這一點與傳播學的分眾理論有相似之處。分眾指的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將具有共同點的受眾分為同一群體。而且分眾不僅僅體現在受眾的社會關系結構中,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也呈現出專業化及分眾化的趨勢。
分眾理論是傳播學受眾觀的重要內容,孔子在古代時代就提出了傳播應因人而異,針對不同的受眾采取不同的傳播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孔子意識到傳播方法及效果因人而異,具有顯著的時代意義。
1.2 傳播規范:“仁”與“禮”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由于戰爭的動亂及生產力的發展,原有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成為時代發展的主題。在孔子看來,維護舊有的社會制度,確立嚴格的等級制度,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因此,孔子思想體系的中心是“禮”,他對周禮進行理論思考,在此過程中提出了“仁”的觀念。隨著社會階級的分化和變化,孔子提出了以“禮”為核心的實踐理性學說,作為傳播思想“禮”的具體化。
孔子說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就是要求在傳播的一切手段和方式中都要貫穿“禮”的規范。一個人如果不懂得“仁”,就根本談不上“禮”,也談不上“樂”。[1]孔子對于“仁”有著多種解釋,例如:“仁者愛人”,強調傳播的主體之間的關系,也是對傳播者及受眾的個人品德的要求。此外,“仁”中的“禮”也包括著言行的禮儀。一切以維持傳統禮制為前提,以“禮”攝“仁”,以“仁”輔“禮”。“仁”既包含著仁愛,也涵蓋了禮儀。孔子強調的“禮”建立在封建等級制度上,也是人際傳播的規范,人們之間進行交往的基本的禮儀。
人際傳播是孔子傳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際傳播中,孔子又將道德傳播的“仁”與知識傳播的“知”相結合。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孔子以山和水來比喻“仁”和“知”的靜動變化關系,非常生動形象。“仁”是指人際傳播的內在思想具有內在的本質屬性和穩定性,“知”是人際傳播的外在表達,具有外在的形式特征與靈活性。
此外,孔子也以“仁學”來規范傳播活動,“仁學”所包含的六種美德——勇、恭、寬、信、敏、惠既是傳播者應該具備的素養,也是受眾應該具備的。“仁學”在道德傳播中,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有著豐富的內涵和付諸實踐的行為。在孔子的傳播思想里,“仁”不僅是傳播觀念,也是人生觀念,是人終身的奮斗目標。
1.3 傳播符號:“正名”思想
孔子認為知識的傳播和禮儀的傳播都必須名正言順,一個國家的體制要符合名分,一個人的言行也要符合自己的名分。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涉及播學中的傳播符號。符號學最早由索緒爾提出,符號是表現事物的意義的載體。能指和所指是符號學的兩個重要概念。孔子強調的“正名”思想,實際上指出了符號的重要意義。
孔子一向把傳播歸于政治理念的范疇。他認為執政的要務,以“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所正的“名”,主要是辨證政治倫理上的名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認為“名”是“知”的定位,如果對客觀事物無知,那么就不可能有準確的命名。所以在“正名”的傳播思想下,“學”“知”“言”構成了完整的傳播體系。
在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禮儀是傳播的過程,其中涉及的許多禮儀制度及象征物也是傳播符號的代表。孔子對于以“禮”為核心的傳播符號的推崇,是為了實現社會秩序的重構。不同的社會群體具有不同的“名分”,“名”是社會地位及權力的代表。在孔子看來,社會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平等。
根據傳播學理論,傳播的符號的規范化及統一性利于提高傳播效率,增強傳播效果。語言作為一種傳播載體,是傳播符號的重要體現。孔子時期,提倡在公共場合使用“雅言”而非“方言”,這利于語言文字的統一及民族融合。其中,“雅言”的含義除了語言形式的規范外,還包括思想內容的規范和行為的規范,所以,孔子一方面讓“禮”的概念系統來規范人際傳播,來統籌人們的日常傳播行為;另一方面用“雅”的概念系統來規范言語傳播,達到傳播的效果。語言是傳播的工具,也是傳播的符號。孔子強調的傳播的語言,深化了傳播符號的作用。
1.4 傳播模式:“人際傳播”與“內向傳播”相結合
美國傳播學者邁克爾·羅洛夫指出,人際傳播的“第一個特征是,人際傳播發生于有關系存在的環境里。他們進行交流的方式是由關系的約束所決定的。有些關系被人們認為著重于彼此扮演的角色,關系雙方的相互行為既基于本人扮演的角色,也基于對方扮演的角色”。[2]而孔子對古代人際傳播提出了許多規范,體現了孔子的人際傳播的思想。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孔子認為,在進行人際傳播時,傳播的言語要根據傳播者及受眾進行調整。語言要慎重,而且要注意傳播對象。“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包含了兩個側面,一是內容,一是形式:即禮儀教化要靠規范的言語傳播,言語傳播更需要禮儀教化的結果。
孔子還提出:“名之可言,言必行。”凡是心中可以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用言語表示出來,凡是用言語表述出來的內心思想都必須付諸行動。孔子的這一思想,實際就是內向傳播向人際傳播轉化的過程,“學—知—名”是內向傳播過程,即接受視聽信息、綜合認知——進行傳輸、處理信息——加工分析、形成概念;“言—行”是人際傳播過程,即自我表達——社會價值體現,孔子強調的基本是自我認知和自我表達系統內的傳播模式,但無論是內向傳播還是人際傳播的自我系統,都是與他人和一定的社會價值或行為規范有聯系的,所以孔子在《論語·憲問》中對“言”與“行”的關系做了這樣的分析。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指出思想內容與言語表達之間的條件關系,有思想道德的人說的話一定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能說會道的人未必是有思想道德的人;指出言行與個人的修養的關系。孔子還認為雖然“言”和“行”是內向傳播向人際傳播的轉化,但它們的真實性和可信性必須采取慎重態度,不可輕信、盲從。
此外,《論語·鄉黨》描述了孔子在人際傳播中身體力行,竭力履行自己在不同場合的社會角色,這也折射出了他的一些關于人際傳播的思想。
2 對孔子傳播思想的評價
2.1 創建傳播模式
孔子要求學生將人際傳播與內向傳播相結合,他的弟子曾參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孔子提倡在三個方面把人際傳播所獲得的信息進行內向傳播的思考,特別強調“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因此可以說,孔子創立了早期傳播的基本模式——“傳—學—習。”“傳”就是傳播者(信源),也包括傳播的訊息;“學”就是受傳者,也包括經過媒介環節把各種要素綜合起來的訊息;“習”就是自我反饋,即受傳者對接收到的訊息在人內傳播中的積極反應,這是形成知識的不可忽視的環節。
2.2 以“禮”為核心
孔子的傳播思想的核心是“禮”,強調禮儀制度與人倫觀念。在這個意義上,“仁”的傳播思想得到了具化。孔子強調的“仁”與“禮”,均為實踐與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孔子傳播思想對“禮”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封建的等級制度和尊卑。傳統具有文化感召的力量,孔子強調對傳統的學習,而且將其付諸“有教無類”的實踐活動,無疑對文化的普及和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孔子的傳播思想對輿論主體人格方面的塑造和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與現代意義上對新聞從業人員的控制原則十分吻合。在現代社會,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傳播速度不斷加快。一些新聞從業者傳播信息片面追求速度,忽視了真實性的檢驗,出現了一系列的失實報道和假新聞;還有一些新聞從業者為了追求點擊率和瀏覽量,弱化了對內容的把關,許多報道內容缺乏規范。所以,對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的要求再次被提上日程。借鑒孔子的傳播思想,應以“禮”為核心,規范傳播者的傳播行為,使傳播者從“善性”出發。
2.3 發展為傳播網絡
隨著歷史的發展,以孔子思想為基礎的儒家傳播思想得到不斷的發展與強化。傳播秩序達到加強,社會信息實現整合。后人對孔子及《論語》傳播思想的研究不斷擴展和細化,向微觀、專門化方向發展。
此外,儒家的傳播理論由孔子開創,得到了孟子、荀子的繼承和發展。他們借鑒了孔子的學術思想及總結方法,同時也結合時代背景提出新的思想,使儒家思想不斷豐富和發展,也維系了封建社會的穩定。
2.4 傳播學本土化的重要資料
傳播學的根源理論來自西方,這一學科的本土化是學科的重大問題。引自西方的傳播學一直面臨本土化的問題,研究孔子的傳播思想,以歷史的視角與現代中國傳播學發展相結合,仍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在研究過程中,以國際的視野,本土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決相應的學術問題。
2.5 缺乏“求真”
孔子的傳播思想強調主觀對世界的看法,忽視了以理性的精神探求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存在“天命觀”,對于天人關系,有一些消極觀念。“天”仍然是宇宙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支配社會生活和人的命運的力量是“命”。其實,在權威的意識形態下,也應發揮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做到“求善”與“求真”相結合。
2.6 對人的權利不夠重視
孔子宣揚的“禮”的前提是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信息的傳播和接受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平等的。傳播權的前提是熟諳傳播技巧和禮儀道德本身,并不是權利。這使民主和平等資源極為稀薄。
孔子認為,活動的成敗的主要原因是“天命”,“天道”是無法改變的。孔子的“尊天”的思想與“敬鬼神”有一定的聯系。
[1]余志鴻.中國傳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153.
[2][美]邁克爾·E·羅洛夫.人際傳播——社會交換論[M].王江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