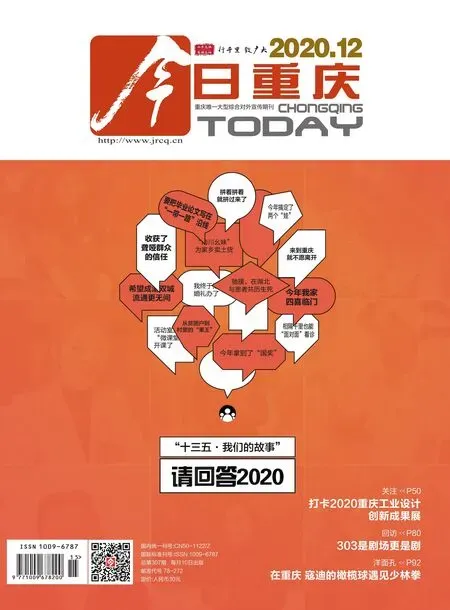開滿金銀花的村莊
◇ 文|本刊記者 董 茜 實習生 胡 婷 圖|受訪者提供
開滿金銀花的村莊
A Village Full of Blooming Honeysuckles
◇ 文|本刊記者 董 茜 實習生 胡 婷 圖|受訪者提供

關鍵詞:一個已脫貧的村
壩芒村,秀山縣隘口鎮一個開滿金銀花的村莊,當貧困在金銀花的搖曳里漸行漸遠,這個摘下貧困帽的村莊,并未躺在金銀花的懷抱里享受,而是用持續的付出憧憬未來。
“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這是沈從文筆下《邊城》里詩意的文字。
這種詩意遭遇了曾經貧困的現實,又從貧困走向另一種詩意,那就是扶貧、脫貧。
壩芒,這個渝東南秀山縣的小村,書寫的正是這種輪回式轉換的詩意與現實。已整村脫貧的壩芒村,日子悠然地浸潤在漫山遍野的金銀花里。
邊城山間的芬芳
行走于秀山的美景山水之間,興許你能找到更多當年沈從文感受到的秀山之美。如今的秀山大街小巷中,除了有山水秀麗景致相依,還有那一抹淡淡的金銀花香。
“秀山不缺的就是山。過去秀人人靠山吃山,開采錳礦。如今的秀山人還是靠山吃山,但是這吃法更加環保更加生態,靠著天然的高山資源,吃著金銀花帶來的效益和財富。”秀山中藥材產業辦公室主任劉朝敏,正在金銀花地里指導農戶修剪花枝。劉朝敏的實話,如秀山一般帶著某種詩意。
劉朝敏被秀山人稱為“金銀花王”,對金銀花種植有相當的研究和實踐。他穿著灰色棉夾克,顧不上花枝擦掛了衣裳,像個孩子一樣竄來竄去。看著壩芒村山腰上這一大片金銀花田,劉朝敏能夠想象10年金銀花種植技術研發帶來的“香甜”,他眼前晃動的,常常是因金銀花種植增收脫貧的貧困戶們臉上的笑容。
但10年前并不是這樣。“金銀花喜歡陽光充足溫潤的環境,秀山的高山地帶很適合它生長。加上它的藥用價值高,大面積種植再加上有效的技術支持,一定是一條脫貧致富的路子。”10年前,劉朝敏就看準了這一點。但依托這朵花脫貧致富的想法,卻并不被當地農戶接受。
被當柴火燒的花苗
劉朝敏是從無盡的尷尬與艱難中走過來的。
扛著一捆捆花苗,爬坡進村。10年前的劉朝敏,大汗淋漓地把花苗挨家挨戶搬到了隘口鎮壩芒村的農戶院壩中。“老鄉,你相信我嘛。種植這個收益可以,一斤至少可以賣幾塊錢。”挨家挨戶推廣金銀花種植技術的劉朝敏,當時被看成是一個“異類”。光憑嘴巴說能掙多少錢,似乎難以打動農戶的心。
那時,壩芒村也好,附近的干川村也罷,每逢趕場天就會引來周邊不少農戶兜售自家種的蔬菜瓜果。“一筐蘋果,幾挑蔬菜,賣個幾塊錢,買米買油又成了兩個包包一樣重。”劉朝敏的記憶里,那時的壩芒村和干川村都窮得叮當響。所以,農戶看著他抱來的花苗,多數都不耐煩聽他說教。壩芒村特困戶李老頭做得更徹底,見劉朝敏把花苗放在院壩里轉身走了,李老頭立馬把花苗拿到灶房當柴火燒了。
打擊遠未結束。劉朝敏回村里準備乘車回家,竟然看到有些金銀花苗被扔在了田坎上。
“我曉得農戶也有擔憂。雖然有了現成的花苗,也有人愿意為他們提供技術,甚至肥料錢都有補貼。但是對貧困戶而言,如果種金銀花,一年多才有產出,而且到底能收益多少,他們心里也沒底。”劉朝敏期待著吃螃蟹的人出現。
還真出現了,那是個叫張勝海的漢子。

金銀花下的產業鏈
初冬的壩芒村,山間云霧繚繞。山腰連片的500多畝金銀花培育種植基地,雖已過了采收季節,但此時的上肥、冬管卻成了來年是否豐收的關鍵。
這片花田的主人張勝海正和幾個種植專業戶忙著上肥。山上有點清冷,但三月產花五月收成的場景,似乎還可尋見。
“今年的收購價還是比較理想,一斤花可以賣到4塊錢。”10年前回鄉創業,張勝海帶頭搞金銀花種植,現在是壩芒村最大的加工業主。山頭上連片的花田,是他一步步帶著農戶種起來、又看著一季季采收的。按市場收購價,一畝地的金銀花產值約2000—3000元。張勝海算了算,一畝地的成本也就800多元。村里農戶將土地流轉給專業種植戶,每年不僅有租金收入,懂行的農戶還進入基地幫忙,也有一筆勞務收入。現在的壩芒村,金銀花種植戶一年收益至少6萬元以上,足以讓貧困戶脫貧。
這是壩芒村的現在:沿著兩車道的公路,從村頭走到村尾,公路邊蓋起了小洋樓,喜歡來點花樣的農戶,還用羅馬柱裝飾著自家樓房的門楣。每年逢收購季,農戶們將自家的金銀花晾曬在院壩里,滿村的花香浸入鼻腔。
“滿車的金銀花從這里出發,一天之內就可以到全縣70多家加工廠。”張勝海的老家其實不在壩芒村,而是在龍池鎮水源村,老家一個叫“狗爬巖”的地方,是進出村的必經之路,也是張勝海記憶里的痛。現在,跟秀山其他村莊一樣,壩芒村、水源村都因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改變了舊模樣,也成就了金銀花產業的再生長。
秀山金銀花產業鏈已大致形成,從種植、初加工到金銀花茶、飲料等高附加值產品,產業鏈逐步延伸。2016年全縣金銀花產量達到兩萬多噸,銷售收入1.6億元。
脫貧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如何做到脫貧之后的可持續,這已經是共識。壩芒村只是一扇窗,透過這扇窗,或許我們能看見更多脫貧之后的“可持續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