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小倆
◎鄭永濤
老小倆
◎鄭永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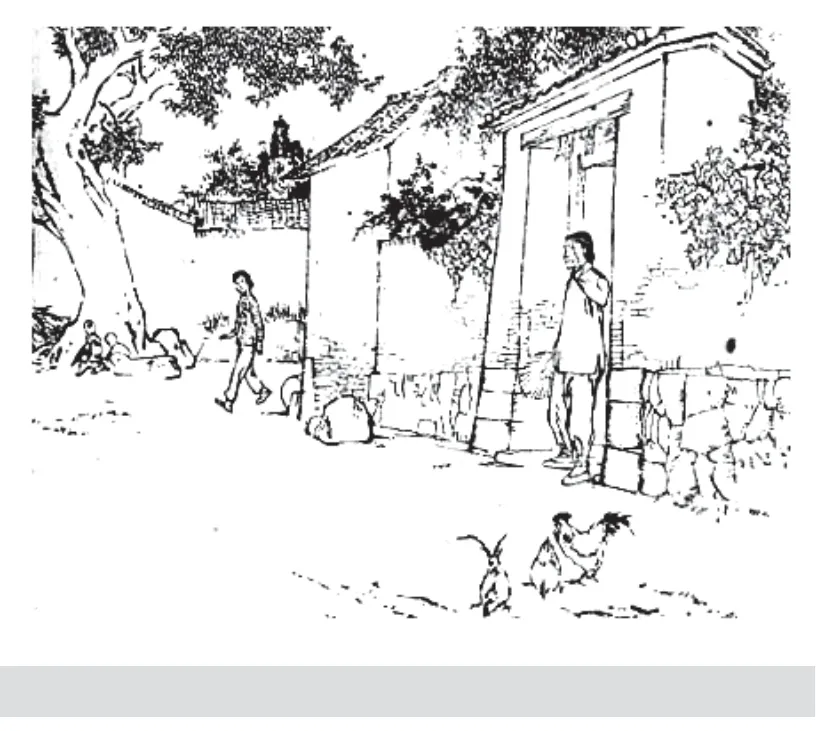
老小倆中,小的是我,那時只有三四歲;老的叫王會明,那時大約七十多歲,老伴已經不在了。他有兒孫,但我很少見到他們,因而沒什么印象。說是老小倆,但其實我跟他之間并無血緣關系,兩家也不同姓,僅僅是兩家都住在村東頭,離得相對近一些罷了。他跟我的曾祖父一個輩分,按輩分我應該叫他老爺爺。我跟他之間的緣分,很淡,很偶然,但也似乎有著一絲的必然。
小時候,父母忙于農活,幼小的我常常無人照看。而他作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平時除了幾只山羊外,也便再無其他伙伴。于是,兩個孤單的生命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彼此之間,是需要,也是被需要。而在這其中,他照看我的成分大概占的更多吧。從此,一老一小、一高一低的兩個瘦弱的身影便常常結伴而行,行走在村里村外。
他中等個頭,身形瘦弱,背微駝,頭發花白,下巴總是留著一綹胡須。他眼睛不大,眼神總是很平靜,很溫和,很慈祥。他是個慢人,總是不慌不忙,慢慢悠悠,仿佛這世上沒有令他心急的事。
他養著幾只山羊,每天吃過早飯后便會出去放羊。趕著山羊經過我家門前時,便會喊上我一同前往。有時我家吃飯早了,父母便會讓我去他家里找他,就像找自己的爺爺。我的爺爺在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時就已經離開人世了。到他家后,見他坐在板凳上吃飯,我便會站在他的身旁背著小手默默地看著他吃飯。時間一點一滴地靜靜流淌,但我們似乎都不太急著出去,他照樣是慢慢地吃,我照樣是耐心地看。他微微抬著下巴,每一口飯都要細細地嚼上一會兒才肯咽下去,似乎覺得自己年齡大了,想細細品味每一口飯的味道。我睜著黑黑的大眼睛看著他咀嚼,感到既安詳又有趣。
吃完飯,他從樹上解開羊繩,那幾只山羊便連跑帶躥地沖出家門了。他跑不動,于是我便會幫他追山羊、拽山羊。待我們拽著山羊,或者說山羊拽著我們來到村南的大坑里,悠閑的時光便開始屬于我們了。他是老人,有著那么多的生活經驗。他從草叢中捉到蝗蟲或螞蚱,然后用細長的草莖系住大腿給我玩。等腿掉了或被我玩死了,他便很快又捉一只給我。我雖也很想自己捉一只,但因為性子急,動靜大,總也學不來他的捕捉技巧,因此試了很多次都捉不到。他試圖教我,但我很難成功。等到我終于學會了,捉到了,他高興得不得了,將我摟進懷里,用他的長胡子來回撫弄我的額頭。
太陽曬得厲害時,他會扯一些長草莖編兩頂草帽子來戴。兩頂草帽子一大一小,粗粗的草環上伸出密密的草莖,遮陽效果很好。而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草帽的有趣。戴上草帽,我便歡起來了,好似成了電影中機智斗敵的小英雄,抓根棍子當槍來回跑個不停。有時,我還會把他當成敵人,用棍子沖他“砰砰”開兩槍,這時他總會配合著癱坐到地上。
不放羊的時候,他常常會帶我到村南的田地里玩。到了紅薯地里,他會折幾根紅薯葉莖,掐去葉片,左一下右一下地將每根嫩莖折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兩條莖鏈,莖皮相連,形似項鏈。他有時會將兩條綠色的莖鏈掛到我的兩只耳朵上充當耳墜,有時會將幾條莖鏈連接起來戴在我的脖子上當作項鏈。我常常開始時還覺得頗為有趣,但不一會兒便會感到乏味,于是便把這簡樸的耳墜和項鏈摘下來丟到地上。
若是碰到頭年干透了的高粱稈兒,他便會折下來剝去葉皮,用高粱稈兒為我插一副眼鏡,抑或一頂帽子。他插的眼鏡我最喜歡,總是戴不夠,回家后還要小心地摘下來收好。
春天的時候,他會給我制作柳笛來吹。他帶我來到村頭的柳樹下,伸手折下柳樹低處的一根細柳條,拿小刀切割好,然后用手指將嫩綠的樹皮耐心地擰松動,接著用力把光柳條猛地抽出,最后用小刀修理一下笛嘴,一管柳笛就做好了。他將柳笛放進自己嘴里試吹幾下,然后遞給我來吹。和煦的春風中,我吹著嫩綠的柳笛,溫潤的笛聲隨風飄揚。而單薄瘦弱的一老一小,也在這春風中綻開笑臉。
夏秋季的時候,他會常常到坑邊地頭給我找野果子吃。最常見的野果是龍葵,我們那里叫黑姑娘。他找到黑姑娘后,會和我一同將黑紫色的漿果采集起來,然后供我一個人享用。有時候,他也會放嘴里嘗幾顆。黑姑娘的味道是酸酸甜甜的,很鮮美。還有一種開紫花的野草,花朵就像一支支小喇叭,我們當地稱之為老婆酒。他尋到老婆酒后,我會爭搶著將紫色的花朵摘下,然后含在嘴里吸吮里面的糖分。老婆酒甜絲絲的,于我而言,就是一枚天然的糖果。
他也會常常帶我到他家里去。在他家里,我來回跟著他,就像是他縮小了的影子。在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里,我會不慌不忙地看著他靜坐,看著他打盹兒,看著他踱步,看著他抽旱煙,看著他吃藥。他每每吃完一小盒藥,就會把那圓圓的小鋁盒送給我玩,里面還有一把白色的小塑料勺。而這個小鋁盒和這把小塑料勺,通常能讓我玩上半天。金色的陽光慵懶地投射在院子里,將時光照慢。而無所事事的一老一小,就在這閑散的下午,將安靜的時光和彼此的身影悄沒聲兒地收進各自的生命中……
我們在一起時,話語并不多。跟他一起玩耍時,并沒有太多的語言交流,似乎已是很默契了。跟著他走路時,也是不說什么話,只有偶爾的提醒我小心什么的。然而雖然話不多,但我們卻是快樂的,那些時光是快樂的,因為至少我們都有個伴。
時光不緊不慢地悄然流逝,他越來越老,我也一天天長大。兩年后的一個夏日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樣去找他,還沒走出院門就被母親喊住了。母親說,你都這么大了,該上學了,以后不用再跟著他了。我想起了他,正想著要不要去跟他說一聲,母親便拉起我的小手朝村西頭的小學走去。路過他家門口時,我朝院子里望了望,但沒有看到他。
小孩子都喜歡新鮮,到了小學,我很快就喜歡上了眾多小伙伴在一起的熱鬧,而把他漸漸淡忘在了腦后。從那以后,我沒有再跟過他。
后來,他的身體漸漸不行了。再后來,他謝世了。他的謝世,并沒有給小小的我帶來多少悲傷。對于那時的我而言,他的謝世只不過是村里又走了一個老人,唯一不同的是這個老人曾經跟我很熟悉。我記得他下葬那天,我還從分發的祭品中搶到了一個糖人,為此我高興了好一陣子。他謝世以后,就徹底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好像從未給我的生命留下什么痕跡。
我和他,沒有合影。再后來,我甚至忘記了他的模樣。
在這人世間,在這長長的人生中,總有一些東西能夠經得住時光的滌蕩,甚而會愈加深刻,愈加難忘,愈加珍貴,甚或會成為我們的精神寄托。隨著年齡的增長,那個陪伴我度過了兩年童年時光的他,漸漸地出現在我的回憶中。在我長大后,在我踏上社會以后,在我經歷了那么多的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之后,他更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每每孤單時,每每被傷害時,每每感情脆弱時,我總會想起那個和藹可親的老人,想起與我無半點關系卻待我如親的他。他所帶給我的記憶是閑散的,安靜的,有趣的,快樂的,溫馨的。這些記憶總能在我脆弱時慰藉我備受創傷的心靈,使我感受到人世間的溫暖,使我更加眷戀這充滿溫情的人世。
就是那么偶然,就是那么必然,幾乎沒有任何關系的兩個人,兩個同樣孤單的生命,年齡相差七十歲的一老一小,就那么走到了一起,共同度過了兩年的靜好時光,親如祖孫。在這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在這爾虞我詐的成人世界里,這一絲單純的感情是多么難以找尋。他使我相信,陌生人之間,也能有真情,也應該有真情。
在我們的生命中,總有那么幾個人,不是每天想起,卻從來不曾忘記。
多少次,在夢中,老小倆,放羊去……
鄭永濤,筆名土生,男,1984年11月26日生,河北邯鄲人,畢業于江西大宇學院中文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邯鄲市作家協會理事,南昌市文學學會會員。作品散見于《解放軍報》、《空軍報》、《戰友報》等國內多家報刊和網站,并被收入多種文學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