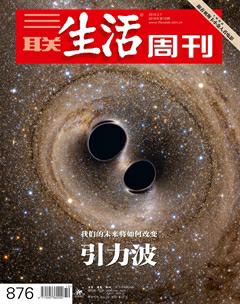物價將漲
邢海洋
借著南下的西伯利亞冷氣團,春節期間的物價隨風漲,元宵節后還尾大不掉。“天涯”上曬物價,坐標寧波4個丑橘27元,坐標常州韭菜10元/斤。不過,青菜水果畢竟是小錢,房價一起跳,就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大數目,繃緊了大城市居民的神經。如果再考慮到1月銀行信貸急劇放量,一輪通脹周期或臨門一腳了。
春節期間的物價,標志性的沖擊波是豬肉。豬價最高達到19元/公斤。即便如此,屠宰、零售等流通領域的經營者還感嘆生意難做,豬肉的利潤全被養殖戶賺去了。此時的生豬收購價,比去年同期普遍多出48%,而一頭仔豬的價格比一年前貴出73%,以當前的價格,養一頭豬毛利600多元,占到售價的1/3,養豬業又回到了2011年時的暴利狀態。追溯本輪物價的上漲,“豬周期”是不可回避的關鍵詞。本來,豬肉價格一般是一年漲、一年平、一年跌,然而,2013年、2014年價格的持續下跌,讓眾多養殖戶幾乎破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2011年那波大行情讓眾多產業資本進入養殖業,大資本一擁而入,成千上萬頭規模的超級養豬場出現了。生豬市場本來是個小農戶聚合的快進快出的市場,資本卻有著小農們沒有的耐力,于是豬周期被拉長。自2015年5月豬肉起漲,據預測,2016年的生豬供應長期難以恢復,大幅度上漲將出現在5~8月,肉價的降溫要等到2017年上半年了。
大資本介入后,去庫存周期被拉長,但同樣補庫存也困難重重。如果說農民買頭豬仔就算補充了庫存,這里不妨舉一線城市房地產的例子。這個春天,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又回到熱火朝天的狀態,“北上深”的去化周期均降到了10個月以下,深圳更低到了4個月。按理說,商品房賣了出去,開發商從拿地到建好房子的周期只有兩年時間,深圳去年初房價就開始上漲,庫存很快就降到了六七個月的水平,但深圳早在2013年就無地可賣了。深圳無地可賣與其是新型城市、區劃面積小有關,但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區劃面積在全世界的大都市中都罕見,偏偏也低價暴漲,兩年前就“面粉貴過面包”,這就不能不歸因于融資成本低廉的大型國企的介入,他們推高了地價,排擠了中小規模的開發商。以至于政府試圖改弦易轍,用街區制取代大塊土地的整體開發。當然,地價高昂的根本原因還在于政府的土地拍賣制度。
回到豬周期,即使資本進入養殖業,能夠通過仔豬價格暫時維持供不應求的局面,但養豬業的大方向畢竟是規模化,通過規模化養殖,美國生豬價格只是中國的一半。但在美國,蔬菜價格卻遠比中國高。大部分傳統蔬菜的種植和采摘不適宜機械化,都需要人工的手工勞動,而勞動力成本卻是剛性的。新年期間城市寫手們返鄉帶回來大量當代農村生活報告,從中不難看出廣大農村土地撂荒、青壯年出走、留守兒童與老年人相依為命的凋敝景象。蔬菜大棚里種菜,夏天高溫高濕,冬天雖不艱難可蔬菜生長緩慢,即便能掙到打工一樣的收入青壯年也不愿干。隨著中國勞動力從過剩到緊缺的過度,蔬菜價格的長期上漲趨勢很難改變,氣候變化只不過加劇了波動。
自2014年8月CPI跌入2%以下,物價已連續18個月低位徘徊。今年通過調整食品權重,新年前的食品躁動也被數字掩蓋住。可兩年間GDP增速步步走低,廣義貨幣供應量(M2)卻遠高于實體經濟成長。正如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說,通貨膨脹在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如果說前年和去年大宗商品暴跌和去產能背景掩蓋了人工成本因素,今年基數效應消失加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發力,通貨膨脹回升已經明白無誤地展現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