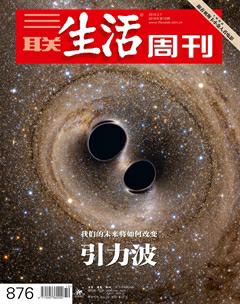時裝秀:以奧斯卡之名
楊聃
重要的是曝光率?
其實,品牌是想成為你的幻想。
網絡直播紅毯現場

從當地時間2月28日上午11點04分開始,《洛杉磯時報》網站上同步直播了整個奧斯卡的進程,其中不僅包括臺前幕后的花絮,還不時穿插著評論性的文章和明星們的Instagram信息截屏。有了前一天的彩排,氣氛沒有想象中的緊張。明星們都已練過走臺和獎詞提示器,工作人員也調整好了攝影機鏡頭的切換設置。一切都為呈現一場看上去自然流暢的直播準備就緒。
下午16點半左右,紅毯逐漸熱鬧了起來。若要設置一個紅毯造型最持久獎,《瘋狂的麥克斯:狂暴之路》的導演喬治·米勒一定榜上有名,他的那件燕尾服已經穿了35年了。“我第一次參加奧斯卡頒獎的時候買了這套衣服,后來的每年都穿著它。”喬治對《洛杉磯時報》說。然而,并不會有這種獎項,時尚界巴不得天天刮起瞬息萬變的風潮。
作為第一批踏上紅毯的女明星,艾麗西卡·維坎德(Alicia Vikander)有望上榜“紅毯最佳造型”。這件點綴灰色花紋的黃色(dusty yellow)路易威登禮服把她打造成了迪士尼動畫中的公主。繼金球獎后,艾麗西卡第二次成為紅毯上的焦點。這多虧了造型師維多利亞·塞克麗爾(Victoria Sekrier),《紐約時報》把她列為改變紅毯魅力的三位新晉設計師之一。
當凱特·溫斯萊特挽著小李子走上紅毯的時候,有一種《泰坦尼克號》再現的即視感,一向喜歡簡潔而有設計的禮服的凱特,選擇了一條拉夫勞倫液態灰色(liquid gray)長裙。71歲的夏洛特·蘭普林(Charlotte Rampling)依然光彩照人,小格紋及踝長裙延續了她的風格——優雅、簡潔和單色。
相比去年的淺色風,今年紅毯上的深色禮服明顯增加了,海軍藍、深紫色和獵裝綠都有出鏡。代表這一類型的女演員有穿著Marchesa的索菲婭·維加拉、身著Calvin Klein的西爾莎·羅南,以及選擇阿瑪尼的娜奧米·沃茨。即便如此,全白色仍是很多明星的安全之選,而奧斯卡金色無論作為主色還是配色都顯得非常出挑。
網絡直播的形式同時具有高回報和高風險。《每日女裝》認為:“奧斯卡紅毯就像高中的自助餐廳,社交媒體就是里面那些通曉所有八卦的學生,一邊看熱鬧一邊幸災樂禍。”傳統的奢侈品行業對社交網絡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他們習慣緊握言論的主導權,不允許一點失控。
然而,那些接受社會媒體為合法營銷工具的人已經取得了一部分成功。就在去年的奧斯卡,Zuhair Murad在推特和Instagram的活動讓其增加了3000關注者。無疑,社交網絡讓關注者比紅毯照更近距離地感受到了服裝的細節,同時讓品牌成為人們持續的話題。
不僅是品牌,媒體也在善用這種形式,《華爾街日報》就專門開設了讀者與資深記者對奧斯卡獎項的討論區,每一位參與的讀者都能及時得到回復。伊坦(Idan Lahav)對《每日女裝》說:“要想在社交媒體中獲利并不容易,你需要創新,要有趣,要在對的時間談論時下熱門,同時還要分析之前的數據。”
奧斯卡的時尚經典
奧斯卡能有如此高的關注度,說明了它從1929年那屆只有270個業內人士參加的頒獎典禮發展至今,從來就不是業內人的專利,觀眾對參與者的關注度不亞于獎項本身。
第一屆最佳女主角的獲得者是珍妮·蓋諾(Janet Gaynor),要不是看影像資料,很難想象她當時居然穿著一件普通量產的彼得潘領(又稱娃娃領)針織連衣裙。這條裙子貌似是件童裝,因為珍妮嬌小的身形一時很難找到適合的衣服。“第一屆的時候并沒有所謂的背景和傳統。”她曾回憶說,“如果那時我知道,在幾年后這個獎意味著什么,我一定會不知所措吧。”
1938年,路易絲·賴納(Luise Rainer)并沒有出席頒獎典禮,她前一年已經領回家一座小金人了,路易絲萬萬沒想到自己會再度得獎。當時獲獎者名單提前發布給了媒體,在她反復確認之后,終于趕得及在領獎之前趕到。因為沒時間準備,素顏、穿著高領燈籠袖睡袍的她被定格在了那一刻,幸好那樣也很美。
正如布朗溫·考斯格萊夫(Bronwyn Cosgrave)在書中所說“時尚和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天生一對”,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在1939年的造型做實了這一點。一件黑色紗裙裝飾著白羽毛般的絲領子,十分引人注目。后來,費雯麗的絲質罌粟花紋長裙和金格爾·羅杰斯(Ginger Rogers)突出蕾絲部分的灰紗裙都很好地突出了各自的形象。
1954年,奧黛麗·赫本穿著休伯特·德·紀梵希設計的印花束帶連衣裙獲得了最佳女主角獎,一字領是紀梵希喜歡的風格。相識于為《龍飛配》挑選戲服的契機,紀梵希發現了他的繆斯,得力于赫本,紀梵希從一家小型高級女裝店發展成為首批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奢侈品牌。自此之后的女演員都穿著戲服設計師的作品出席典禮。
世事總有例外,黛安·基頓(Diane Keaton)憑借和伍迪·艾倫共同出演的《安妮·霍爾》登上了奧斯卡領獎臺。當時她穿的那套男性風格的套裝并不是出自電影戲服設計師之手。因為艾倫堅持讓她保持自己的風格——馬甲、領結,胸前帶有紐扣的襯衣和卡其褲。事實上不僅是艾倫喜歡這樣的她,數不清的美國女性也愛上了如此中性風格的黛安。
1986年,雪兒被詬病的造型也是奧斯卡最難忘的一幕。鮑勃·麥克伊(Bob Mackie)設計的串珠狀的纏腰帶、山羊絨黑斗篷、公雞毛制成的莫霍克式頭飾,與2001年比約克的天鵝裝被列為紅毯殺手的典范。
2000年以前,像妮可·基德曼選擇迪奧“苦艾酒”風格禮服這樣大膽風格的嘗試還是常見的。然而,2000年以后女明星的選擇就越來越標準化了。哈利·貝瑞是第一個獲得最佳女主角的黑女郎,借助Elie Saab巧妙地點綴花朵與藤蔓,她也第一次成功推行了裸穿風格。大部分獲得最佳著裝評價的選擇都是貼身長裙,顏色要清淡柔和不要過于跳躍,除非要襯托女明星的膚色和發色。造型師的最終目的并不是進入“紅榜”,而是不要進入“黑榜”。
2005年,當時施華洛世奇國際公關部的弗朗索瓦發現了美國人的要求很特別,“大多數人只要手抓包,體積小,黑色、金色或銀色。她們似乎不愿意冒任何風險”。她對時尚作家黛安·托馬斯說:“在戛納電影節上,你能在紅毯上看到各種瘋狂的裝扮,但這里一切都很保守和傳統。太多評論家在審視你的穿著,奧斯卡的紅毯可容不下一點錯誤。”弗朗索瓦補充道:“你必須完美無瑕,符合大眾而不是你個人的期望。”
“你穿的是哪位設計師的作品?”
理論上來講,從1961年開始,紅毯環節就成了奧斯卡的一部分。但真正讓紅毯發展到如今這種關注程度的是1995年瓊·里弗斯(Joan Rivers)的一句話:“你穿的是哪位設計師的作品?”問這個問題本是紅毯環節主持人與名人間的一句寒暄話語,卻從此把時尚塞進了奧斯卡典禮的鏡頭里。當然,它的回答也不再是簡單地給一件禮服加個名字。
為了保證女性在電影中的地位,電影需要經受得起貝克德爾測驗(Bechdel Test),但這一局勢在紅毯環節,明顯是反轉的,男性根本不重要,他們必然是清一色的燕尾服,主角是女性。對于參加奧斯卡的女明星來說,她們想得到更多關注度可以通過兩種方式,要么是作品中的角色被提名并得獎,要么就穿對衣服,這方面的成功案例就是希拉里·斯萬克(Hillary Swank)。當然,如果你既有才能又很幸運,也可以像露皮塔·尼永奧(Lupita Nyongo)在2014年那樣雙贏。
誰決定了女明星在紅毯上穿什么?她們有些可以自己決定,而大多數的情況都比較復雜。《It Ended Badly: The 13 Worst Break-Ups in History》一書的作者珍妮弗·萊特(Jennifer Wright)就在本書中描述了奧斯卡紅毯的幕后。通常設計師會先和名媛們取得聯系,看看她們是否有意愿穿自己的作品走紅毯。這時,名媛們的造型師就會考慮是否接受提議,并對顏色和剪裁給出建議。他們要選擇的衣服不僅要適合明星的風格,更要讓觀眾能夠大飽眼福。
“因為網絡的原因,現在的壓力更大了。”造型師安妮塔曾對《Daily Beast》說。當時,她的客戶包括朱莉安·浩夫(Julianne Hough)、朱麗·德爾比(Julie Delpy)、艾瑪·沃特森(Emma Watson)和夏奈爾·伊曼(Chanel Iman)。“數以萬計自以為是造型師的人在批評你的工作,事實上挑一件裙子或鞋子穿在某人的身上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每一個造型師都有一個筆記本,里面貼滿了各種服飾的立拍得照片,從文胸到鞋子,旁邊還要加上注解,哪件衣服要在哪個場合穿,如果下雨,外出又要怎么辦等等。為了保證明星客戶的利益,要謹記紅毯上同一個奢侈品牌的服裝不能過度曝光。當天也要貼身服務,以防拉鏈爆開、扣子崩掉等意外。
而品牌要想贏得明星及造型師的好感就更要面面俱到了。1999年奧斯卡典禮的前一周,Jimmy Choo的創始人之一塔瑪拉·梅隆飛到了洛杉磯,隨行帶了60雙女鞋,7種不同風格,但全都是白色的,她還在塔林酒店(LErmitage Hotel)開了一個套間,迎接了大批女演員和造型師。塔瑪拉向她們保證,鞋子可以染成與其晚裝相配的顏色,并且預定期限最晚可以到典禮前夜。
為了爭取凱特·布蘭切特這個大客戶,塔瑪拉專門為她定制了一雙鑲滿鉆石的鞋。頒獎典禮還沒開始,關于這雙絳紫色的鞋的新聞已經鋪天蓋地,媒體們也在追蹤它的價格——11萬美元。然而,典禮的前一天,塔瑪拉接到來電,說幾星期前做好的鉆石鞋小了一號,不想穿了。這無疑是一場災難,當時塔瑪拉帶來的鞋已經全部送光了,就連洛杉磯店的貨架都空了,哪里還有備用鞋?數個確認電話之后,終于讓她在西好萊塢的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里找到一雙黑色的,可惜還是小了半碼。
在鞋匠杰克·扎迪凱恩的幫助下,問題終于解決了。他和他的伙計干了一個通宵,加長鞋底再重新接上鞋面,用白色的綢緞覆蓋整個表面,然后把它染成了絳紫色。第二天清晨,鑲上了珠寶裝飾。盡管所有人都翹首以盼,那雙鞋最終也沒能走上奧斯卡的紅毯。據說理由是,凱特覺得這雙鞋得到的關注比她本人還多。一切都功虧一簣嗎?當然不。塔瑪拉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數個版面的免費宣傳,其中還包括《Vogue》的封面。
同樣深諳此道的服裝品牌是阿瑪尼。《女裝日報》戲稱1990年的奧斯卡是“阿瑪尼獎”,最佳女主角杰西卡·坦迪、最佳女配角提名莉娜·歐琳、最佳男主角提名丹·艾克羅伊德和湯姆·克魯斯、最佳男配角得主丹澤爾·華盛頓,以及奧斯卡典禮主持人比利·克里斯托等都穿著阿瑪尼。《Vogue》主編安娜·溫圖爾評論道:“阿瑪尼以現代的方式重新包裝了電影明星。”結果可以預計,品牌的業績一飛沖天:從1990年至1993年,全球營業額翻了一倍,大部分銷售增長來自美國市場。
自此,名媛對品牌的影響越來明顯。麥當娜穿著古馳的寶藍色綢緞襯衫和黑色天鵝絨低腰緊身褲出席1995年MTV頒獎禮,之后古馳營業額暴漲。同年,戴安娜被拍到提著迪奧的手袋,這就是著名的“戴妃包”(Dior Lady)。當年售價1000美元的戴妃包就賣出了10萬個,僅是這個手袋的銷售情況就讓迪奧第二年的全球營業額增長了20%。
“明星在電視、電影、流行音樂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客廳里,讀者對他們有一種‘了解,這是模特所不具備的優勢。”《風尚》(In Style)雜志創刊主編馬莎·尼爾森曾說。于是,時尚雜志開始用明星取代模特做封面人物,雜志也好賣得多了。
回顧過去三年女明星們在五大曝光率最高的頒獎典禮——奧斯卡、格萊美、影視演員協會獎、金球獎、人民選擇獎——的紅毯上穿的品牌,出現最多的是阿瑪尼、華倫天奴、范思哲、Elie Saab、迪奧。他們有些在銷售上的表現并沒有達到預期。反而,像香奈兒、巴黎世家這樣人們期待卻鮮有出現的品牌,紅毯環節的缺失并未對其增長造成影響。畢竟,其品牌知名度已經不需要再借助其他手段來增強了。
在《華盛頓郵報》時尚評論人羅賓·吉芙瀚看來,這并不代表紅毯失去了它的魅力,正如小庫珀·古丁(Cuba Gooding Jr.)曾在接受她采訪時表示,他幻想著身穿阿瑪尼以提名者的身份參加奧斯卡。“無論是奧斯卡的紅毯還是大都會博物館的紅毯,你并不是在賣一條裙子,你賣的是一整套幻想的概念。”吉芙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