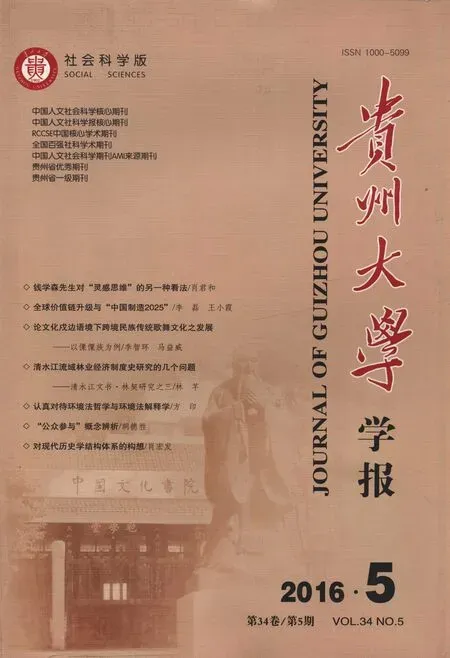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詁方法與特點(diǎn)探析
田黎星
(銅仁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貴州 銅仁 554300 )
?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詁方法與特點(diǎn)探析
田黎星
(銅仁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貴州 銅仁 554300 )
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在研究中主要運(yùn)用了聲訓(xùn),征引前人、時(shí)賢的訓(xùn)釋成果,歸納句法、用例進(jìn)行疏釋,根據(jù)上下文加以分析等幾種方法。在具體實(shí)踐中,馬瑞辰對(duì)這幾種方法常常是綜合運(yùn)用。這些方法的運(yùn)用,使其訓(xùn)詁實(shí)踐呈現(xiàn)出如下特點(diǎn):既注重旁征博引,又要擇善而從;既重視文義,但又能結(jié)合句法;更注重用聲訓(xùn)來破假借。
馬瑞辰;訓(xùn)詁;方法;特點(diǎn)
《毛詩傳箋通釋》一書成書于道光十五年,據(jù)馬瑞辰《自序》,著成此書耗時(shí)十六年而成[1],可謂是殫精竭慮之作。馬瑞辰此書與胡承珙的《毛詩后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皆作于嘉道年間,同為清代考據(jù)《詩》學(xué)的代表,成就令人矚目,且作者亦有交流往來,因此在詩經(jīng)學(xué)史上,常被相提并論。漆永祥在《乾嘉考據(jù)學(xué)》一書中稱“在十三經(jīng)清人新疏中,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和陳奐的《詩毛氏傳疏》承正統(tǒng)考據(jù)學(xué)派之學(xué),是對(duì)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成果繼承總結(jié)的代表之作”[2]246。統(tǒng)觀《毛詩傳箋通釋》全書,其顯著特點(diǎn)就是博采諸家,不辟門戶。而這個(gè)特點(diǎn)正上承乾嘉戴震一派“會(huì)諸經(jīng)而求其通”“雖出入漢儒門戶但不守藩籬,講求綜貫會(huì)通,不偏主一家”[2]130的學(xué)術(shù)特色。正是這種“求是”態(tài)度,使得其多有創(chuàng)獲,備受好評(píng)。比如,何海燕在其博士論文《清代〈詩經(jīng)〉學(xué)研究》的《緒論》部分,就說道:“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無門戶之見,秉承戴震一派實(shí)事求是之精神,將《毛詩序》、毛《傳》、鄭《箋》、孔《疏》等都納入檢查的范圍,所取得的成就最大。”[3]1
馬氏《毛詩傳箋通釋》的成就主要在考據(jù)訓(xùn)詁方面,因此,學(xué)界對(duì)《通釋》在訓(xùn)詁方面成就的研究也比較集中。有研究者從整體出發(fā),對(duì)《通釋》一書所用的訓(xùn)詁方法、訓(xùn)詁特色作整體探討,如王曉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釋方法》[4]313、程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詁特色》[5]62;也有研究者擇取馬瑞辰的某一研究方法或訓(xùn)詁對(duì)象進(jìn)行詳細(xì)分析,比如,從聲訓(xùn)方面探析的有夏春蓮的碩士畢業(yè)論文《〈毛詩傳箋通釋〉聲訓(xùn)研究》,從名物訓(xùn)詁方面進(jìn)行探析的有馬楠的碩士畢業(yè)論文《〈毛詩傳箋通釋〉名物訓(xùn)釋研究》;而從假借方面進(jìn)行研究的學(xué)者就更多了,有臺(tái)灣學(xué)者王安碩的碩士畢業(yè)論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通假字研究》,李書良的碩士畢業(yè)論文《〈毛詩傳箋通釋〉通假研究》,丁曉丹的碩士畢業(yè)論文《試析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對(duì)假借字的論說》等等。而現(xiàn)已出版的洪文婷的論文《〈毛詩傳箋通釋〉析論》也主要著眼于訓(xùn)詁方面對(duì)《通釋》一書進(jìn)行分析。今筆者綜合各家觀點(diǎn),間下己意,將馬瑞辰主要運(yùn)用訓(xùn)詁方法總結(jié)為以下幾點(diǎn):聲訓(xùn)(包括假借、右文等),征引前人、時(shí)賢的訓(xùn)釋成果,歸納句法、用例進(jìn)行疏釋,根據(jù)上下文加以分析。馬瑞辰在具體訓(xùn)詁實(shí)踐中,對(duì)這幾種方法常常是綜合運(yùn)用。因此,馬氏在具體訓(xùn)詁過程中對(duì)這幾種訓(xùn)詁方法的交叉使用也是筆者的主要關(guān)注點(diǎn)。本文擬對(duì)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詁方法與特點(diǎn)進(jìn)行探析,具體從以下幾個(gè)方面展開論述:
一、旁征博引與擇善而從
《毛詩傳箋通釋》的一個(gè)鮮明特征就是旁征博引,引證繁多。《通釋》的重點(diǎn)在于疏釋《詩經(jīng)》以及毛《傳》、鄭《箋》等的相關(guān)條目。在疏釋過程中,馬氏既要剖析《傳》《箋》《正義》對(duì)《詩經(jīng)》的解釋,又要對(duì)所征引歷朝諸儒解《詩》的舊說,歷代重要小學(xué)類著述以及其他經(jīng)傳注疏進(jìn)行辨析。然而,遍觀古籍,則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一詞多義、一物多名的情況屢見不鮮,因此,馬氏在利用前賢時(shí)修的訓(xùn)釋成果來在疏釋《詩經(jīng)》之時(shí),也需要對(duì)各家不同的釋義進(jìn)行判斷擇取。諸儒解《詩》之作以及其他典籍中所載相關(guān)解《詩》條目,可以為馬瑞辰疏釋提供最為直接的證據(jù)。因此,今首先探討的是馬瑞辰在面對(duì)各家解《詩》的說法不同時(shí),如何進(jìn)行決斷。
1.文義暢達(dá)與詞義擇取
正如趙振鐸所言,“古書注釋的任務(wù)在于解讀古書里面難懂的詞句”[6]37,疏釋具體典籍必須考慮釋義是否切合語境,馬瑞辰在進(jìn)行訓(xùn)釋時(shí),十分強(qiáng)調(diào)利用上下文來判讀詞義,在一詞有多種釋義的情況下,他常將文義文脈是否暢達(dá)作為判斷詞義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比如:
“率是農(nóng)夫”,《箋》:“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nóng)夫。”瑞辰按:《爾雅·釋言》:“畯,農(nóng)夫也。”孫叔然曰:“農(nóng)夫,田官也。”古者由官稱田畯,《七月》詩《傳》:“畯,田大夫也。”……《爾雅》言“畯,農(nóng)夫”者,畯之言俊,謂長也;夫當(dāng)讀如大夫之夫。王尚書曰:“率人曰夫。凡經(jīng)傳言準(zhǔn)夫、牧夫、嗇夫、馭夫、膳夫、宰夫,皆率人之義,故《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此詩言為天子所率,《正義》云:“若田農(nóng)之夫,非王所親率,故知農(nóng)夫是典田之吏。”蓋申鄭說則然,至毛《傳》不釋農(nóng)夫,據(jù)《甫田傳》“農(nóng)夫食陳”,則《傳》意農(nóng)夫及農(nóng)人,于下文“駿發(fā)爾私”文氣尤順。李黼平曰:“《國語》‘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即農(nóng)人,何言田農(nóng)之夫非王所率!”《正義》以《箋》義為《傳》義,失之。
——《周頌·噫嘻》[1]1069
上述引文中,馬瑞辰需要對(duì)“率是農(nóng)夫”中的“農(nóng)夫”一詞進(jìn)行疏釋。對(duì)于“農(nóng)夫”的釋義,文獻(xiàn)中主要有兩種觀點(diǎn):一種為田官,另一種則為農(nóng)人。《爾雅》有將之解為田官的相關(guān)記載,王引之將“夫”解為“率人”者,并引《禮記》為證,則“農(nóng)夫”確實(shí)可以解為田官。對(duì)于本詩的“農(nóng)夫”,鄭《箋》就解為“主田之吏”,即田官。而《正義》則申明鄭《箋》,以“田農(nóng)之夫,非王所親率”證“農(nóng)夫”為“典田之吏”。而毛公在本詩中,并未對(duì)“農(nóng)夫”加以注釋,但他在對(duì)《小雅·甫田》的“我取其陳,食我農(nóng)人”進(jìn)行注釋時(shí)說道:“尊者食新,農(nóng)夫食陳。”[7]832由此來看,毛《傳》以農(nóng)人為農(nóng)夫。馬瑞辰據(jù)此推斷本詩《傳》意以“農(nóng)夫”為農(nóng)人,并作出“于下文‘駿發(fā)爾私’文氣尤順”的論斷,而后他再征引李黼平的說法,駁斥《正義》認(rèn)為農(nóng)人非“王所親率”的觀點(diǎn)。由此,可見他更偏重將“農(nóng)夫”釋作農(nóng)人。今按:《噫嘻》“率時(shí)農(nóng)夫,播厥百谷”下云“駿發(fā)爾私,終三十里”。“駿發(fā)爾私”之“私”,義為“民田”[7]1319,至于“駿”,馬瑞辰贊同鄭《箋》訓(xùn)為“疾”,而“發(fā)”則為“發(fā)土”[1]1070。依馬瑞辰之義,此句應(yīng)指迅速開耕,而所耕作之田為民之私田。因此,上文將“農(nóng)夫”訓(xùn)為農(nóng)人,更切合文義,釋義明白曉暢。
2.借句式用例輔佐論斷
馬瑞辰對(duì)各家觀點(diǎn)進(jìn)行辨析時(shí)的依據(jù)并不只是詩歌上下文義,有時(shí),通過句式用例也能輔助論斷。根據(jù)上下文義可以輔助辨析詞義,而通過篇章結(jié)構(gòu)歸納出的句式、用例也能為辨析詩文中的詞義提供依據(jù)。例如:
“瞻彼淇奧”,《傳》:“奧,隈也。”瑞辰按:《正義》引陸璣《疏》云:“淇、奧,二水名。”《釋文》引《草木疏》曰:“奧亦水名。”劉昭《郡國志》注引《博物志》云:“有奧水流入淇水。”《水經(jīng)注》云:“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今按:奧本隈曲之名。水之內(nèi)為奧,與水相入為汭同義。古人或名泉水入淇處為淇奧,因有奧水之稱,猶夏汭、涇汭亦名汭水也。但《詩》言淇奧與汝墳、淮浦、淮濆,語句相類,不得分為二。仍從《爾雅》“澳,隈”之訓(xùn)為是。
——《衛(wèi)風(fēng)·淇奧》[1]189
根據(jù)引文可知,毛《傳》和《爾雅》都將“奧”釋為“隈”,即水的彎曲處;而《釋文》和《正義》引文則都將“奧”釋為“水名”,《博物志》也有關(guān)于“奧水”的記載。馬瑞辰根據(jù)“奧”的本義推究了“奧水”命名的緣由,以及把“淇奧”解為“泉水入淇處”這種情況。但就本詩“淇奧”的理解,馬瑞辰則根據(jù)“語句相類”原則,將之與“汝墳”“淮浦”等歸為一類,即認(rèn)為淇、奧為定中關(guān)系而非并列關(guān)系,此處“淇奧”應(yīng)隨毛《傳》解為淇水的曲隈處,而非具體地名。
上條引文可見馬瑞辰根據(jù)詞組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來選取恰當(dāng)?shù)尼屃x,反之,他也會(huì)因句法不類而對(duì)故訓(xùn)提出質(zhì)疑,進(jìn)行論辯。例如: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椹謂之虔。正斲于椹上。”瑞辰按:“方斲是虔”與“是斷是遷”對(duì)舉,正與《魯頌》“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文法相類。斲與虔二字平列,方猶是也。或言方,或言是,互文以見參錯(cuò)。猶《桑扈》篇“彼交匪敖”,《左傳》引作“匪交匪敖”,知彼亦為匪,而《毛詩》上彼下匪者,亦互文也。虔當(dāng)讀如虔劉之虔。方言:“虔,殺也。”《廣雅》虔、伐、刈并訓(xùn)殺,是虔猶伐也,刈也。《淮南·說林》:“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高注:“殺,猶削也。”是知?dú)⑷酥^之虔,削伐木亦謂之虔,“方斲是虔”猶云是斲是虔也。“是斷是遷”是斬伐木于在山之時(shí),“方斲是虔”是削伐木于作室之際。《傳》訓(xùn)虔為敬,固非詩義;若如《箋》訓(xùn)為椹質(zhì),必改經(jīng)文為“方斲于虔”而后明,又與“是斷是遷”句法不相類,胥失之矣。
——《商頌·殷武》[1]1189
此段引文,馬瑞辰對(duì)“方斲是虔”句進(jìn)行疏釋。毛《傳》、鄭《箋》對(duì)“虔”的釋義不同,《傳》釋之為“敬”,而《箋》則釋之為“椹”,即砧板。馬瑞辰在對(duì)“虔”的釋義進(jìn)行辨析時(shí),先對(duì)“方斲是虔”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進(jìn)行辨析:將“方斲是虔”與上一句“是斷是遷”相結(jié)合,并與《魯頌·閟宮》的“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句聯(lián)系起來,斷定這四句話的句法結(jié)構(gòu)相似。由此“方”與“是”同義,都為助詞。而“方斲是虔”上言“方”而下作“是”,則是《詩經(jīng)》中“互文以見參錯(cuò)”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而這種手法在《小雅·桑扈》也有體現(xiàn)。而根據(jù)《方言》《廣雅》記載,“虔”可訓(xùn)為“殺”,而《淮南子》高誘注又言“殺”可釋為“削”,因此,“虔”義可釋為“削”。而此解釋與上文“是斷是遷”正好相應(yīng),切合文義。因此,馬瑞辰將“虔”釋為“削”。而依據(jù)鄭《箋》的解釋,將“虔”釋為砧板,從而將這句詩解為“正斲于椹上”,也說得通。馬瑞辰根據(jù)“于”字釋義來源不明,以及這種解釋使“方斲是虔”與上句“是斷是遷”的“句法不相類”,因此不同意鄭《箋》的說法。
3.借音韻知識(shí)以助辨析
馬瑞辰在訓(xùn)詁過程中,多應(yīng)用到音韻知識(shí)。以音韻知識(shí)佐助辨析也是他對(duì)各家觀點(diǎn)進(jìn)行分辨時(shí)常常使用到的方法。他在對(duì)《周南·關(guān)雎》“窈窕淑女”條[1]30的疏釋之時(shí),就已用到這一方法。今就此條內(nèi)容稍加分析如下: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閑也。”瑞辰按:《廣雅》:“窈窕,好也。”窈窕二字疊韻。《方言》:“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窕。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又曰:“秦晉之間,美心為窈,美狀為窕。”蓋對(duì)言則異,散言則通爾。《說文》:“窈,深遠(yuǎn)也。”幽、深義近,幽與窈亦雙聲也。窕與姚通,姚冶一作窕冶。《說文》:“姚,美好也。”《方言》:“窕,好也。”窕又訓(xùn)閑。《爾雅》:“窕,閑也。”《方言》:“窕,言閑都也。”閑都亦好也。又窕與嬥聲近。《廣雅·釋詁》:“嬥,好也。”《釋訓(xùn)》又曰:“嬥嬥,好也。”合言之則曰窈窕。《傳》云“幽閑”者,蓋謂其儀容之好,幽閑窈窕然。《文選》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窈窕,貞專貌。”《楚辭》王逸注云:“窈窕,好貌。”《廣雅·釋詁》:“窈窕,好也。”義皆與毛《傳》同。《爾雅·釋言》:“冥,幼也。”幼,或謂即窈之假借。《說文》:“窈,深遠(yuǎn)也。”《釋言》又曰:“窕,肆也。”據(jù)《說文》:“窕,深肆極也。”極深為肆,是窈、窕皆有深義。窈窕通作窈窱,又作杳窱。《說文》:“杳,杳窱也。”《廣雅》:“窈窱,深也。”幽、深義相近。或以狀宮室之深邃,班固《西都賦》“又杳窱而不見陽”是也。至此詩窈窕,則不取深義。《箋》云:“幽閑處深宮貞專之善女”,亦謂幽閑貞專之善女處于深宮耳,未遂訓(xùn)窈窕為深宮也。孔《疏》謂窈窕為“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殊誤。
此處馬瑞辰用近四百字疏釋“窈窕”一詞,廣泛征引了《爾雅》《廣雅》《方言》《說文》以及《文選》李善注等文獻(xiàn)中的相關(guān)釋義,他喜旁征博引的特點(diǎn)在此已可見一斑。細(xì)讀文本可以發(fā)現(xiàn),他所征引的條目釋義并不一致,而他則是在對(duì)詩文“窈窕”的釋義的辨析擇取過程中,對(duì)毛《傳》、鄭《箋》的解釋加以申明,并對(duì)孔《疏》的理解進(jìn)行駁斥。此處他所征引的關(guān)于“窈窕”的解釋有“幽閑”“閑都”“貞專”“好”“美”“幽深”等等。毛《傳》將“窈窕淑女”釋為“幽閑貞專之善女”[7]22,窈窕即“幽閑貞專”之義,用以形容“淑女”(“善女”)。而馬瑞辰顯然是贊同毛《傳》的說法,他得出結(jié)論“《傳》云‘幽閑’者,蓋謂其儀容之好,幽閑窈窕然”之前,所引自《廣雅》《方言》等之釋義,基本上都可以總結(jié)為“好”(而他所引《說文》“窈,深遠(yuǎn)也”條則例外),而且在他看來,《文選》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訓(xùn)窈窕為“貞專貌”,王逸注《楚辭》釋窈窕為“好貌”以及《廣雅》釋窈窕為“好”,這些釋義“皆與毛《傳》同”。這即是把“幽閑”“閑都”“貞專”“好”“美”等義都?xì)w結(jié)為“好”,而這個(gè)“好”是為描述“淑女”。
而關(guān)于本詩的窈窕還有一種解釋,即“幽深”,用以描述“淑女”所處的地方。孔穎達(dá)即持這種觀點(diǎn),他將“窈窕”理解為“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馬瑞辰對(duì)這個(gè)觀點(diǎn)并不贊同,他直接說道“至此詩窈窕,則不取深義”。實(shí)際上,孔《疏》得出窈窕指深宮的結(jié)論,發(fā)端于鄭《箋》。鄭《箋》將“窈窕淑女”釋為“幽閑處深宮貞專之善女”,比之毛《傳》多了“處深宮”三字。由于“窈窕”可訓(xùn)為幽深,因此,就可能以《箋》義“窈窕”是為形容“深宮”。《正義》云:“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閑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閑,言其幽深而閑靜也。”[7]24據(jù)此可見,孔《疏》之誤,源于錯(cuò)解鄭《箋》,進(jìn)而誤讀毛《傳》。孔氏認(rèn)為窈窕是為形容“淑女”所居之宮,也是毛《傳》的觀點(diǎn)。對(duì)讀毛《傳》與《正義》就能發(fā)現(xiàn)二者大相徑庭,孔氏對(duì)毛《傳》的理解是錯(cuò)誤的。此時(shí)馬瑞辰是站在毛《傳》的立場(chǎng)上,批駁孔《疏》。至于他贊同毛《傳》的原因則沒有具體說明。今人關(guān)于本詩“窈窕”應(yīng)釋為幽深還是美好,也還有討論。劉毓慶通過形訓(xùn)考證窈窕指深宮,蔡英杰等則通過聲訓(xùn)考證窈窕為形容淑女的體態(tài)[8]156。今按:馬瑞辰于此提到“窈窕二字疊韻”,而他將窈與幽、窕與姚、窕與嬥等詞系連起來,主要也是通過它們的音韻關(guān)系。他在疏釋《陳風(fēng)·月出》“舒窈糾兮”條時(shí),又說道:“窈糾猶窈窕,皆疊韻,與下憂受、夭紹同為形容美好之詞。”[1]417聯(lián)系兩篇,可見,對(duì)“窈窕”“窈糾”,雖然馬瑞辰尚未把二者點(diǎn)明為連綿詞,闡明它們之間的同源關(guān)系,但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的聲音聯(lián)系,從而注意到它們的意義相關(guān)性。《月出》篇無疑沒有“深宮”的歧義,此篇將“窈糾”釋為美好,則《關(guān)雎》篇也與此釋義相類。這里馬瑞辰將窈窕解為“謂其儀容之好”,與他對(duì)音韻知識(shí)的熟諳可謂關(guān)系密切。
又如:
“依其在京”,《箋》:“文王但發(fā)其依居京地之眾。”瑞辰按:王氏《經(jīng)義述聞》曰:“依,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詞。依之言殷,殷盛也。言文王之兵盛,依然其在京地也。”今按:王說是也。依、殷二字雙聲,古通用。此詩“依其”正與《鄭風(fēng)》言“殷其”句法相同。
——《大雅·皇矣》[1]850
此段引文馬瑞辰所疏釋的對(duì)象是“依其在京”,而重點(diǎn)則是對(duì)“依”的解釋。以鄭《箋》之意,是將“依”釋為依憑,而清代學(xué)者王引之則將“依”讀為“殷”,釋為“盛貌”。馬瑞辰根據(jù)“依”“殷”之間的雙聲關(guān)系(“依”屬影母微部,“殷”屬影母文部,故為雙聲),判斷二者通用,因而贊同王引之的觀點(diǎn)。其后再提到“依其”與《鄭風(fēng)》“殷其”的“句法”相同,作輔助說明。今檢閱經(jīng)文,《鄭風(fēng)》無“殷其”結(jié)構(gòu),此結(jié)構(gòu)只見于《召南·殷其雷》篇。而馬瑞辰在訓(xùn)釋《鄭風(fēng)·羔裘》篇“羔裘晏兮”句時(shí),根據(jù)“晏”“殷”雙聲關(guān)系,將“晏”讀為“殷”訓(xùn)為“盛”[1]263,此處馬瑞辰引述有誤。從這段引文可見,馬瑞辰對(duì)所引各家訓(xùn)詁說法進(jìn)行辨析時(shí)并非只運(yùn)用某一方法,而是將不同方法結(jié)合在一起。
二、文義與句法
筆者在對(duì)馬瑞辰引證特點(diǎn)進(jìn)行概括時(shí)提到,他多采本證,而其采用本證在訓(xùn)詁方面,則表現(xiàn)為根據(jù)上下文義訓(xùn)釋詞句及經(jīng)文結(jié)構(gòu)用例訓(xùn)釋詞句兩種形式,即他所說的“以全經(jīng)明其義例”。對(duì)古書進(jìn)行注釋時(shí),必須考慮釋義是否切合語境。而《詩經(jīng)》多重章疊句,有的詩篇的章節(jié)與章節(jié)之間,不只在語義上相互聯(lián)系,在結(jié)構(gòu)上也具有相似性。此時(shí)利用上下文判讀詞義,不僅可以利用其章節(jié)間的語義聯(lián)系,也可以利用其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相似性。當(dāng)然,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相似性,并不限于單篇詩文之內(nèi),也可能橫貫多篇,甚至跳出《詩經(jīng)》的藩籬(此時(shí)則不屬于內(nèi)證的范疇)。在上文中,已對(duì)利用文義及結(jié)構(gòu)句例等判讀詞義作過討論,只是重點(diǎn)在于探討他如何利用文義、句法等對(duì)其所引注釋作辨析,著眼點(diǎn)在于他對(duì)前人對(duì)《詩經(jīng)》的疏釋的繼承方面。今主要著眼于他利用文義、結(jié)構(gòu)判讀詞義后所立新說,所得創(chuàng)獲。
1.以上下文義判讀詞義
利用上下文義對(duì)詞義進(jìn)行疏釋,是馬瑞辰進(jìn)行訓(xùn)詁時(shí)常常使用的方法,現(xiàn)就這一點(diǎn)略舉兩例:
“玁狁匪茹”,《箋》:“茹,度也。”瑞辰按:《廣雅》“茹,柔也。”“柔,弱也。”匪茹言非柔弱,即上章“玁狁孔熾”也。故下接言“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皆甚言其強(qiáng)恣。
——《小雅·六月》[1]543
此條引文中,馬氏疏釋“玁狁匪茹”句,其中“茹”字的釋義則是其主要關(guān)注點(diǎn)。鄭《箋》將“茹”釋為“度”,于文義頗為難解,孔穎達(dá)申明《箋》義云:“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dāng)度為也。”[7]636馬瑞辰據(jù)辭書《廣雅》對(duì)“茹”的釋義,將“茹”釋為“柔弱”,“玁狁匪茹”則指玁狁強(qiáng)恣。如此,這句詩既與上文言“玁狁孔熾”相應(yīng),又與下文中說玁狁“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相接,相較鄭《箋》之說,更為切合文義。
又如: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余卒為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dāng)?shù),單者,無羨卒也。”瑞辰按:三單非三重之謂,今(陳金生校云:今疑當(dāng)為《傳》)以為相襲,非也。《箋》以無羨卒為單,亦似未確。今按《逸周書·大明武》篇“隳城湮溪,老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即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為糧”承上“度其隰原”言,“豳居永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為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為三單耳。
——《大雅·公劉》[1]909
在上述引文中,馬瑞辰對(duì)“其軍三單”進(jìn)行疏釋。此條經(jīng)文頗為費(fèi)解,而對(duì)“三單”的訓(xùn)釋則是疏通這條經(jīng)文的核心。毛《傳》釋之為“相襲”,而鄭《箋》則以之為三軍無余卒。馬瑞辰認(rèn)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妥。據(jù)《逸周書》“隳城湮溪,老弱單處”之注,“單處”指“無保障”。根據(jù)詩文所述,此時(shí)在公劉初至豳地,尚未筑成城郭,未有保障。因此,用“單”描述“軍”。其后,他將“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句與其上句“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及下句“度其夕陽,豳居永荒”句進(jìn)行類比,因?yàn)椤岸绕溱粼瑥靥餅榧Z”“度其夕陽,豳居永荒”句的上句與下句之間都有前因后果的聯(lián)系,則“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內(nèi)部三小句之間也應(yīng)如此,“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之后才有“其軍三單”。因此,他將“其軍三單”釋為把軍隊(duì)分為三支,分別駐扎山陽、山陰及流泉之旁。這種解釋依據(jù)詩文的語義關(guān)系進(jìn)行論證,也可備一說。
2.以句法結(jié)構(gòu)判讀詞義
疏釋詩文不只可以根據(jù)上下文的語義關(guān)系,根據(jù)其句法結(jié)構(gòu)常常也能夠輔助訓(xùn)詁。今略舉幾例:
“美目揚(yáng)兮”,《傳》:“好目揚(yáng)眉。”瑞辰按:《方言》:“好目謂之順。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yáng)。”是揚(yáng)為好目貌。“美目揚(yáng)兮”與下章“美目清兮”《碩人》詩“美目盼兮”句法同,皆狀其目之美。邱光庭曰:“揚(yáng)者,目開之貌,《禮記》‘揚(yáng)其目而視之’是也。”《傳》以揚(yáng)為揚(yáng)眉,又云“目下為清”,并失之。
——《齊風(fēng)·猗嗟》[1]312
在這段引文中,馬瑞辰對(duì)“美目揚(yáng)兮”進(jìn)行解釋,而其辨析的重點(diǎn)是“揚(yáng)”字。毛《傳》認(rèn)為“揚(yáng)”指“揚(yáng)眉”,馬瑞辰并不贊同。《方言》中有“揚(yáng)”釋為好目之貌的記載。而且“美目揚(yáng)兮”與“美目清兮”“美目盼兮”句法結(jié)構(gòu)完全相同,此“揚(yáng)”應(yīng)當(dāng)與下章“美目清兮”之“清”及《碩人》詩“美目盼兮”之盼用法相同,釋義相近。《碩人》篇“美目盼兮”之“盼”,毛《傳》釋為“白黑分”[7]224,馬瑞辰已引《說文》對(duì)其加以申明,其意為眼睛黑白分明的樣子。因此,本詩“美目揚(yáng)”“美目清”中的“揚(yáng)”與“清”同樣是描寫眼睛的美貌,此“揚(yáng)”應(yīng)依《方言》的解釋。丘光庭將“揚(yáng)”解為“目開之貌”,正與馬瑞辰之說相近。而毛《傳》把“揚(yáng)”解為“揚(yáng)眉”,下章“美目清兮”之“清”又解為“目下”,則不妥當(dāng)。此段引文中,馬瑞辰根據(jù)句法結(jié)構(gòu),在對(duì)“揚(yáng)”進(jìn)行釋義的同時(shí),也對(duì)下章的“清”進(jìn)行了疏釋。
又如:
“穹窒熏鼠”,《傳》:“穹,窮。窒,塞也。”瑞辰按:詩以“穹窒”與“熏鼠”及下“塞向”、“墐戶”四者相對(duì)成文。穹,窮也;窮,治也,盡也。穹通作焪。《廣雅》焪與糞、寫并訓(xùn)為盡,又曰:“糞,寫除也。”是穹謂除治之盡也。《廣雅》:“窒、塞,滿也。”是知穹窒《傳》訓(xùn)窮塞者,謂除治其室之滿塞也。《周官·翦氏》“掌除蠧物,以莽草熏之”,正此詩熏鼠之事。《赤犮氏》“掌除墻屋,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肌蛷之屬。”即此詩穹窒之事。蓋貍蟲隱于墻隙,易于窒塞,故必除之務(wù)盡。《正義》乃謂“穹塞其室之孔穴”,失《傳》旨矣。穹窒與熏鼠為二事。
——《豳風(fēng)·七月》[1]461
這段引文中,馬瑞辰主要就“穹窒”進(jìn)行疏釋。毛《傳》關(guān)于“穹窒”頗為簡(jiǎn)奧難解。《正義》疏釋毛《傳》云:“以窒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1]503此即將“穹窒”視為狀中關(guān)系,認(rèn)為“穹”是描述“窒”的狀態(tài)。而馬瑞辰并不贊同這一觀點(diǎn),他對(duì)“穹窒熏鼠”與下文“塞向墐戶”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進(jìn)行判斷,認(rèn)為“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四者相對(duì)成文”,即這四個(gè)詞組都是一樣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熏鼠”之間無疑是動(dòng)賓關(guān)系,“穹窒”應(yīng)該也是動(dòng)賓結(jié)構(gòu)。因此,他將“穹”看作“焪”的假借字,解為“除治之盡”,而“塞”則為滿塞之物。其后他又在《周禮·赤犮氏》中找到文獻(xiàn)根據(jù),古有除去墻屋縫隙中的貍蟲之事。因此,他將“穹窒”釋為除盡墻隙中的貍蟲與“熏鼠”之事并列。
3.結(jié)合句法與文義判讀詞義
在詩篇之中,詩句的結(jié)構(gòu)與文義是并存的。因而,馬瑞辰把詞匯置于詩篇之中進(jìn)行訓(xùn)詁時(shí),常常將文義與句法結(jié)構(gòu)結(jié)合起來,對(duì)詞匯進(jìn)行訓(xùn)釋。今就此也略舉兩例:
“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文》云:“契闊,《韓詩》云:約束也。”瑞辰按:契闊二字雙聲。毛讀契如“契契寤嘆”之契,故訓(xùn)為勤苦;韓讀契如絜束之絜,讀闊如“德音來括”之括,故訓(xùn)為約束。但據(jù)下章“于嗟闊兮”正承上“契闊”而言,則契當(dāng)讀如契合之契,闊讀如疏闊之闊。《后漢書·臧洪傳》“隔闊相思”,闊亦闊別也。“契闊”與“死生”相對(duì)成文,猶云合離聚散耳。
——《邶風(fēng)·擊鼓》[1]121
這段引文中,馬瑞辰“死生契闊”的“契闊”進(jìn)行訓(xùn)釋,也是將上下文義與句法結(jié)構(gòu)結(jié)合起來進(jìn)行論說。馬氏首先對(duì)毛《傳》和《釋文》所引《韓詩》的意思進(jìn)行說明。其后,他將這句詩中的“契闊”與下一章“于嗟闊兮”的“闊”聯(lián)系起來,判斷毛、韓二家之解都不切合詩義,本章“闊”義與下章同,都含疏闊之義,相反,契則為契合。“契闊”正好與“死生”相對(duì)成文,結(jié)構(gòu)相似。因此,依《后漢書》將“闊”解為“闊別”,更為符合詩義。所謂“契闊”即指相聚分離。
又如: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瑞辰按:此章“防”與“邛”對(duì)言,猶下章“中唐”與“邛”對(duì)言。邛為丘名,則防宜讀如隄防之防,不得以為邑名。鵲巢宜于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應(yīng)有也。不應(yīng)有而以為有,所以為讒言也。詩之取興,與《采苓》同義。至《說文》:“邛,地名,在濟(jì)陰。”《后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此蓋后人因《詩》附會(huì),不足取以證詩。
——《陳風(fēng)·防有鵲巢》[1]414
這段引文中,馬瑞辰主要就“防有鵲巢”的“防”的含義進(jìn)行辨析。毛《傳》將“防”釋為“邑”。馬瑞辰根據(jù)章句結(jié)構(gòu)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以及詩義,對(duì)毛《傳》提出異議。本詩首章云“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次章云“中唐有甓,邛有旨鹝”。兩章的上下兩句之間,結(jié)構(gòu)相似。馬瑞辰根據(jù)“防”與“邛”、“中唐”與“邛”之間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認(rèn)為“防”與“邛”的釋義應(yīng)當(dāng)相對(duì)應(yīng)。毛《傳》既將“邛”釋為“丘”,則“防”釋為“邑”則不當(dāng),應(yīng)釋為“隄防”。“防有鵲巢”即指喜鵲筑巢于堤壩之上。而“鵲巢宜于林木,今言‘防有’”則是以其“不應(yīng)有而以為有”喻指讒言的興起。本詩之《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7]405馬瑞辰贊同詩《序》,將“防有鵲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鹝”結(jié)合起來對(duì)其進(jìn)行疏釋,認(rèn)為“鵲巢”“甓”“旨苕”“旨鹝”都處于其不當(dāng)處的位置,以此來證明“讒言之不可信”[1]414。因此,在疏釋“防有鵲巢”句時(shí),馬氏直接將此句與全詩意旨聯(lián)系起來,進(jìn)行解釋。
三、聲訓(xùn)之破假借
乾嘉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以聲音通訓(xùn)詁,在聲訓(xùn)方面成就卓然。馬瑞辰對(duì)其方法及成果皆有繼承,并應(yīng)用于訓(xùn)詁實(shí)踐之中,取得顯著成就,尤其體現(xiàn)在論說通假字方面。馬瑞辰在 《毛詩古文多假借字考》篇中論斷說:“毛《詩》為古文,其經(jīng)字類多假借。……說《詩》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經(jīng)義始明。”[1]23而他在《自序》中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時(shí),即“以雙聲疊韻別其通借”作為其中之一。由此即可看出他對(duì)《詩經(jīng)》假借字的關(guān)注。本節(jié)就馬氏破假借方面的方法與成就進(jìn)行論說。因?qū)W界對(duì)馬瑞辰《通釋》之假借進(jìn)行過研究的人甚多,因此,本節(jié)主要就破假借與其他訓(xùn)詁法的綜合使用方面進(jìn)行論述。對(duì)每種情況只舉一例,以資求證,不多贅言。
毛《詩》古文多假借,指其中有許多字本為古字,后書寫時(shí)直接以音同音近之字表示。因此,在對(duì)毛《詩》進(jìn)行疏釋時(shí),對(duì)這類字必須破讀為其本字,才可能得出正確的解釋。破假借最主要的依據(jù)就是聲音。以古音古韻考求毛《詩》傳注,則可見其中多有關(guān)于假借字的論說。馬瑞辰即以此法考證毛《傳》,將其對(duì)《毛詩》經(jīng)文假借字的訓(xùn)釋方法歸納為兩種:“毛《傳》釋《詩》,有知其為某字之假借,因以所借之正字釋之者;有不以正字釋之,而以所正字之義釋之者。”[1]23馬瑞辰在對(duì)毛《傳》的這類注釋進(jìn)行申明時(shí),即對(duì)《詩經(jīng)》中假借情況進(jìn)行了論說。例如:馬氏在對(duì)《周南·汝墳》“惄如調(diào)饑”條《傳》文“惄,饑也”進(jìn)行疏釋時(shí),即對(duì)“調(diào)”為假借進(jìn)行了詳細(xì)論說。而毛《傳》并未將經(jīng)文中所有的假借字都加以注釋,毛瑞辰在疏釋經(jīng)文時(shí)常常離開毛《傳》,自己對(duì)經(jīng)文用字進(jìn)行判讀,提出新解。而此時(shí),他就需要聯(lián)系其他訓(xùn)詁方法,尋找依據(jù),進(jìn)行說明。
遍尋經(jīng)傳典籍,尋找異文,通過對(duì)異文釋義的考證來判斷《毛詩》是否應(yīng)該破讀,這是馬氏判斷假借字的一個(gè)重要方法。上文中所引馬瑞辰對(duì)“執(zhí)訊獲丑”的疏釋中,就可見他利用《隸釋》中載有“執(zhí)訊獲首”之語,判斷“丑”為首之“丑”假借。
利用文義與結(jié)構(gòu)輔助判斷詩文是否應(yīng)當(dāng)破讀,也是馬瑞辰多有使用的方法。例如: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于君也。”瑞辰按:上言“不稱其服”,此言“不遂其媾”,媾與服對(duì),亦當(dāng)為服佩之稱。媾蓋韝字之假借。《內(nèi)則》“右佩玦捍”,是古者玦與捍并佩。《芄蘭》詩《傳》“能射御則佩韘”,韘者玦也。佩捍猶佩玦也。捍一名韝,一名遂。《說文》:“韝,臂衣也。”《鄉(xiāng)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韝也。以朱韋為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佩韝而不能射御,是謂“不遂其媾”,正與“不稱其服”同義。韝之借為媾,猶玦之借為決也。若訓(xùn)媾為厚,則與上章文義不相類矣。
——《曹風(fēng)·候人》[1]439
這段引文中,馬瑞辰將“不遂其媾”之“媾”判定為“韝”的假借,主要的根據(jù)就是詩句的上下文義。毛《傳》將“媾”釋為“厚”,鄭《箋》贊同毛《傳》觀點(diǎn),并對(duì)其加以申明,而馬瑞辰不贊同毛《傳》,認(rèn)為這種解釋“與上章文義不相類”。《曹風(fēng)·候人》第二章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第三章云:“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兩章結(jié)構(gòu)完全相同,釋義也應(yīng)當(dāng)相近。因此,馬氏認(rèn)為“服”與“媾”相對(duì)應(yīng),利用“服”之釋義推測(cè)“媾”也“當(dāng)為服佩之稱”,但“媾”并沒有相關(guān)義項(xiàng),因此,馬瑞辰認(rèn)為“媾”為“韝”之假借。《禮記·內(nèi)則》中有“右佩玦捍”之載,將“玦”“捍”并列。《芄蘭》詩“童子佩韘”之“韘”,毛《傳》解之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7]239因此,馬瑞辰據(jù)毛《傳》將本詩之“玦”解為《芄蘭》之“韘”。馬瑞辰在對(duì)“童子佩韘”進(jìn)行疏釋時(shí)引《說文》云:“韘,射決也,所以勾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1]218由此可見,“玦”為“韘”,即為射決。而馬氏又云:“韘為指沓,與韝捍為臂沓,其義正同”[1]218,正是將“韘”與“韝”并列而言,二者都是射御所憑藉之物。而“捍”又名“韝”,又名“遂”,三者同實(shí)異名。因此“玦捍”即為“韘韝”。《鄉(xiāng)射禮》所載“決遂”,亦即“韘韝”,因此,馬氏引之來闡釋“韝”的釋義,由此,“不遂其媾”即指其人與其所服佩不相稱,正與“不遂其服”意義相似。
馬氏在《芄蘭》篇中所引毛《傳》作“韘,決也”,所引《說文》作“射決”,因此他特意說明“決”為“玦”的假借字。據(jù)《正義》有云:“玦,本又作‘決’,音同。”[7]239因此,“決”“玦”音同而通用。據(jù)《說文》,“媾”,“從女,篝聲”[9]362;“韝”,“從韋,篝聲”[9]152。“媾”“韝”也音同,因此,“韝”可以借為“媾”。
馬瑞辰在對(duì)經(jīng)文用字進(jìn)行通假與否進(jìn)行判斷時(shí),也并非孤立使用某種方法,而是常常將幾種方法綜合起來使用,增加說服力。比如:
“實(shí)始翦商”,《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shí)而有王跡,故曰是始斷商。”瑞辰按:翦與踐古同音通用。《玉藻》:“凡有血?dú)庵悾ド碹`也。”鄭注:“踐讀曰翦。”是翦可借作踐矣。竊謂踐亦可借作翦。此詩“翦商”當(dāng)讀為踐履之踐。周自不窋竄居戎狄之間,及公劉遷豳,皆近戎狄。至大王遷岐,始內(nèi)踐商家之地,故曰“實(shí)始翦商”。翦商即踐商也。與《書序》“周公踐奄”文法相類,踐奄即《書》所云“周公居?xùn)|”。《史記》作“殘奄”,音近假借。鄭訓(xùn)翦滅,亦為未確。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高注:“踐,往也。”正與踐履同訓(xùn)。《豳詩譜》云:“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言入者,正對(duì)舊處戎狄在外言之。“實(shí)始翦商”正承上“居岐之陽”,故知其為踐商也。毛、鄭訓(xùn)為齊斷,既與大王所處之時(shí)事不合;惠氏棟訓(xùn)翦為勤,又與下文“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文義不貫。
——《魯頌·閟宮》[1]1139
這段引文中,馬瑞辰綜合利用古音、文義、句法結(jié)構(gòu)及歷史事實(shí)的考證來論證“實(shí)始翦商”之“翦”,應(yīng)被視為踐履之“踐”的假借字。馬瑞辰根據(jù)“翦”“踐”古同音(“翦”屬精母元部,“踐”屬從母元部;精母、從母皆為齒音,可互轉(zhuǎn)),并舉《禮記·玉藻》鄭注將“踐”讀為“翦”為證,由此,推論“翦”也可以讀為“踐”。其后據(jù)周代的歷史,論證大王之時(shí)才開始離開戎狄之地,向商朝境內(nèi)遷徙,因此本詩云“實(shí)始翦商”。其后他根據(jù)“翦商”與《尚書》所載“周公踐奄”之“踐奄”文法相似,利用諸家對(duì)“踐奄”的解釋來類比“翦商”。對(duì)于“踐奄”之“踐”,鄭玄仍訓(xùn)為翦滅,而至《呂氏春秋·古樂篇》高誘注把“踐”訓(xùn)為“往”,則與馬氏觀點(diǎn)相同,故馬氏以高誘注印證自己的釋義。其后根據(jù)《豳詩譜》并聯(lián)系上文“居岐之陽”,再次論證遷居岐陽,義為入處商地,即“踐商”。再根據(jù)大王之時(shí)周國尚弱的事實(shí),反駁《傳》《箋》將“翦”釋為“齊斷”的觀點(diǎn)。而后根據(jù)下文“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證上文“翦商”不應(yīng)釋為“勤商”(即輔助商朝),如此,則上文言輔助,下文言討伐,文義不相貫通。
四、結(jié)語
訓(xùn)詁是馬瑞辰《通釋》一書最為顯著的成就,其所使用的訓(xùn)詁方法也相當(dāng)多元。本文第一部分就馬瑞辰如何對(duì)諸儒解《詩》之作以及其他典籍中所載相關(guān)解《詩》條目中的不同觀點(diǎn)進(jìn)行討論,著眼點(diǎn)在于他對(duì)前人釋《詩》成果的繼承方面;第二部分對(duì)馬瑞辰利用文義及句法以訓(xùn)詁及第三部分對(duì)馬氏破假借以訓(xùn)詁的探討,主要關(guān)注點(diǎn)都是馬瑞辰在訓(xùn)詁過程中所得創(chuàng)獲。馬瑞辰上承乾嘉治學(xué)之風(fēng),論述十分強(qiáng)調(diào)證據(jù),不作鑿空之論。在《例言》部分就說道,他考證毛《詩》經(jīng)文所用假借字,對(duì)“可證之經(jīng)傳者,均各考其源流,不敢妄憑肊見”。這一原則,并非只針對(duì)假借字的論說,而被馬氏貫徹到全書的寫作過程中。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深入了解到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一書在訓(xùn)詁方面的成就。許多《詩經(jīng)》學(xué)史著作(例如,夏傳才的《詩經(jīng)研究史概要》,洪湛侯的《詩經(jīng)學(xué)史》等)都將“文字訓(xùn)詁”視為馬瑞辰最主要的成就。甚至有研究者認(rèn)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將《毛詩傳箋通釋》當(dāng)作《廣雅疏證》的補(bǔ)充,作為一部訓(xùn)詁專書使用。”[10]44筆者認(rèn)為,這些看法、評(píng)價(jià)是公允的。
[1]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diǎn)校.毛詩傳箋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 漆永祥.乾嘉考據(jù)學(xué)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9.
[3] 何海燕.清代〈詩經(jīng)〉學(xué)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2005.
[4] 王曉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釋方法[C]//中華書局編輯部.文史:第二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
[5] 程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訓(xùn)詁特色[J].樂山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22(1).
[6] 趙振鐸.訓(xùn)詁學(xué)綱要[M].成都:巴蜀書社,2003.
[7]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dá)疏.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8]劉毓慶.“窈窕”考[J].中國語文,2002(2).
[9] 〔漢〕許慎撰,班吉慶、王劍等校.說文解字校訂本[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0] 郭全芝.從經(jīng)學(xué)到近代語言學(xué)的過渡: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J].古籍研究,2015(2).
(責(zé)任編輯 鐘昭會(huì))
2016-05-29
田黎星(1966—),男,貴州石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學(xué)與文獻(xiàn)學(xué)。
H131
A
1000-5099(2016)05-0165-08
10.15958/j.cnki.gdxbshb.2016.05.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