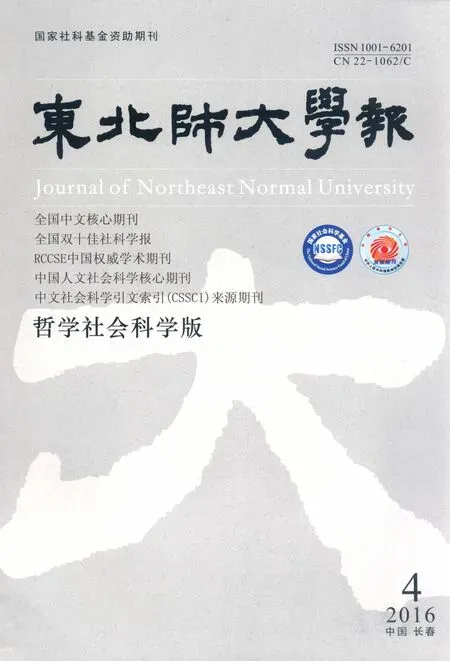破解全球投資增長困局
陸 婷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
破解全球投資增長困局
陸婷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投資在短期創造需求,在長期則在供給方形成生產能力。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投資,未來就有什么樣的增長前景。長久以來,投資也一直被視作是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核心環節。
一、危機后各國投資水平均出現下滑
金融危機后,全球各國的投資水平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發達國家下滑尤為顯著,這使得促進投資增長始終是危機后各國政府所重點關注的問題。它們希望通過推動中小型私人企業投資和戰略性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張,使本國經濟復蘇迅速步入正軌,避免陷入“弱需求-低產出”的惡性循環。
可惜的是,盡管危機后許多發達國家都施行了寬松貨幣政策,營造了歷史罕見的低利率環境,但就投資占GDP比重而言,不少國家都距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相差甚遠,尤其是歐洲和日本。2015年,歐元區和日本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較2008年分別下降了10.6和6.9%,占GDP比重僅在20%左右。經濟復蘇表現最好的美國,其投資雖基本恢復至危機前水平,卻依舊低于其長期均值。新興市場經濟體則大都在危機后的一段時間快速恢復了投資水平,不過,近幾年,受自身結構性問題和國際金融、經濟環境波動性增強的影響,這些國家的投資動能也在逐步減弱。
金融危機對全球跨國投資和公共投資也打擊沉重。全球直接投資(FDI)直至2015年才首次回升至危機前水平,達到1.7萬億美元。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聯合會的研究,2015年FDI增長主要由跨國并購導致,表明目前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旨在推進資產重組,而非擴張生產活動,這些資本流入僅改變了企業的資本結構和金融賬戶,并不帶來資源的實際流動,對全球經濟增長推動有限。
二、投資下滑的政策和金融因素
公共投資下滑主要是受各國財政整頓約束影響。OECD國家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在2010和2013年間下降0.6%,為財政整頓目標的實現貢獻了將近1/4。財政整頓問題越嚴重的國家,公共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越多,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平均每下降1個百分點,公共投資占GDP的比重就會被削減0.3%[1]。因此,危機后各國面臨的財政整頓約束也為投資增長帶來了一定障礙。
而在私人部門,未來經濟和政策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是導致企業,尤其是發達國家大型企業普遍投資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歐洲央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53%的歐洲企業認為,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是他們對歐元區外進行直接投資的主要障礙[2]。對于這些企業而言,不存在資金層面的約束,不少企業在削減投資規模的同時,還在主動選擇發放股息或回購股份以降低現金持有水平[3]。相應的,在美國,企業較為擔心監管、稅收和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用以衡量政策不確定性程度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EPUI)在2009、2010及2012年財政懸崖之前急劇飆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回落一段時間后重新在2014年和2015年走高。除此之外,一些長期不確定性,如在氣候變化和人口老齡化問題上的不確定,也使得企業對進行長期投資持保留態度。
對于小微型企業來說,融資約束仍然是它們無法擴張投資的一大制約。在金融危機之后,小微企業的資金約束程度較危機前有所上升。根據此前歐盟28國的一項調查,在使用過或考慮使用的融資工具中,只有16%的小微企業選擇了股權融資工具,4%選擇了債券融資,而銀行貸款(57%)、透支貸款或賒銷(53%)仍是小微企業最常用的融資工具。因此,在銀行大范圍地進行去杠桿以滿足監管要求時,這些小微企業愈發難以獲得資金進行投資[4]。
投資環境壁壘以及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足也是制約企業投資增長的重要因素。市場準入壁壘、跨境貿易和投資的稅收壁壘、良好商業行為準則體系的缺失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礙了資源流向最具有生產效率的企業,增加了企業投資生產的成本和負擔,進而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此外,當整體經濟需求的波動性顯著增強時,不靈活的勞動市場使得企業無法及時做出相應調整。出于對未來風險管控的考慮,企業將在面臨這種情況時選擇主動縮減投資規模,為投資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三、推動全球投資增長的政策方向
為打破全球投資增長乏力的僵局,促使經濟增長重新回到正軌,有效的需求面刺激政策依舊不可或缺。但需要謹記的是,此類政策還應伴隨著改善經濟長期增長前景、提升市場信心的結構性改革措施。不僅如此,需求面刺激政策自身也需要更加有的放矢,并充分考慮到政策的協同和溢出效應。
具體來說,各國推動投資增長的政策可重點著力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積極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在適度容忍政府債務擴張的前提下,有效調整和增加公共部門投資。如果使用得當,公共部門的投資不僅能在短期發揮提振需求的功效,還能夠拉升經濟體長期需求。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投資決策時應當對投資的種類和質量予以關注,一方面可將資源配置到投資乘數效應較高的領域,另一方面可加大投資于一些未來有益于私人部門投資的領域,這些領域包括公共研發、知識基礎設施(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氣候變化應對和環境保護等等。政府在公共投資中還可積極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在撬動公共部門資金的同時,提升投資效率。此外,政府可考慮施行部分稅收優惠政策,以減輕小微企業投資所面臨的融資約束。
二是降低政策相關的不確定性。在財政政策方面,各國需要明確在現有經濟增長率下如何實現財政可持續的戰略和路徑,這對歐元區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美國則需要避免預算法案上的不確定性,不再反復出現債務上限之爭。在貨幣政策方面,則需要清晰地量化寬松政策退出路徑。除此之外,要降低政策不確定性,各國還應當在一些國際性問題上加強政策協調和合作,包括跨國公司稅收處理、金融體系監管、以及氣候變化的應對等等。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的盡快落實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關國家的監管政策不確定性。
三是實施有助于長期投資增長的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是促使全球經濟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的核心所在,它能夠支持和鼓勵企業在資本和人力資源方面的長期投資,實現提升整體投資水平的目標。促進投資的結構性改革通常需要結合金融政策、市場監管政策、以及產業政策三者之力。
金融政策應著力于保證金融機構能夠為有發展前景的長期投資項目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金融危機之后,各國監管層吸取了危機教訓,意圖通過防止過度金融化來提升整個金融體系對沖擊的抵抗力。在這個過程中,監管當局增加了對養老金和保險公司等機構持有流動性較差資產的資本金要求,直接導致這類機構投資者投資于基礎設施項目或其他長期投資項目成本的上升。這是各國政府需要注意的,金融政策框架應該在維護金融穩定的同時,盡量鼓勵機構投資者為項目提供長期資金而非予以阻撓。
市場監管政策則應鼓勵市場公平競爭,減少市場準入管制,同時確保市場監管環境和融資安排能夠使得基礎設施項目獲得足夠的融資渠道。放松產品和勞動力市場管制,減輕降低監管要求對企業的負擔,能夠讓企業以更低的成本進行生產調整,從而提升企業在面臨較高不確定性時的投資意愿;確保發展前景良好的基礎設施項目能夠獲得暢通的融資渠道則有助于提升經濟體長期增長潛力。對于新興市場來說,擁有明確的市場監管政策框架尤為重要,因為市場監管政策的頻繁變動將導致企業投資趨于保守,不利于整體投資規模的擴張。
產業政策方面,政府需加強對研發、高新科技以及知識密集型行業的扶持。這類投資有利于推廣和傳播前沿理念和科技,從而能夠從根本上帶動生產效率的提高。研發相關的稅收激勵機制應進一步得到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也應該與時俱進,在保護知識產權,鼓勵企業創新的同時,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與鼓勵市場競爭的政策相協調,以使得各項政策能夠發揮最大效益。產業政策還需要對行業退出的相關條例予以關注,尤其是高新科技行業。由于技術更迭而導致的企業退出和破產,理論上不應該受到過于嚴厲的破產懲罰。保持高新科技行業進入和退出的活力,有助于資源的不斷配置向更有效、創新含量更高的地方,進而提升經濟長期增長潛力。
綜上,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基本都處于弱復蘇狀態,實體投資持續增長乏力逐漸成為各國所關注的一大結構性難題。經濟環境和政策的不確定性、政府財政整頓的壓力、商業環境壁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足等問題都令企業在擴張投資規模決策上裹足不前,導致全球經濟較難走出低速增長的泥沼。要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多方政策的配合與協調,積極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降低政策不確定性,同時推動大范圍的結構性改革,力求在拉動短期投資增長之余,增強和培養一國的長期投資潛能,促使經濟增長能夠重新步入健康、快速的發展軌道。
[1] ECB.Public investment in Europe[J].ECBEconomicBulletin,2016(2).
[2] ECB.What is behind the low investment in the euro area? Responses from a survey of large euro area firms[J].ECBEconomicBulletin,2015(8).
[3] OECD.Lifting investment for higher sustainable growth[J].complied inOECDEconomicOutlook2015(January),OECD Publishing,Paris,2015.
[4] OECD.Unlocking growth: the role of investment,innovation,skills and business climate[J].complied inOECDEconomicOutlook2015(June),OECD Publishing,Paris,2015.
2016-04-1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4ZDA081)。
陸婷(1983-),女,廣東廣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