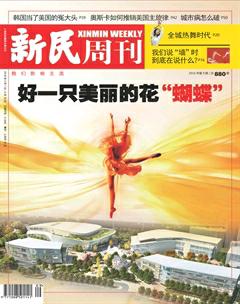一“街”之差,差在人氣
老沖
小區與街區,一街之差,差在開放的心態、規劃和人氣的融合,差在人對城市和居住環境更為深層次的理解,我們的城市和小區已經大成這個樣子,病得如此嚴重,不只是交通才是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于認識和行為方式的改變。
小區與街區,這一個字,差在哪兒了呢?咱們從頭捋捋。
你有我也有
街區聽起來很洋氣,有個英文名兒叫Block,除了街區的意思之外,還有障礙物的含義,美國紐約、西班牙巴塞羅那、德國柏林、捷克布拉格等都有很漂亮的標桿式的街區,風格不同,卻都整潔漂亮。
它是怎么來的呢?按照法國提倡開放街區的建筑師鮑贊巴克的分類,原因的表述我們都很“熟悉”——“歷史發展形成的”。
18下半葉工業革命之前,一直到古希臘、古羅馬,歐洲城市發展非常緩慢,城市住宅區處于“第一年齡段”,城市人口密度很低,規模很小,住宅區基本依附于街道自然形成,街道聚合交通、商業、社交等諸多功能,街區歷時數千年的首秀,其實很乏味。
中國這邊就嗨皮一點,究其原因,古希臘城市的形成,沿地中海的方便貿易為核心的經濟功能,更加核心一些。中國則不同,城市的首要功能在于軍事和政治,大城小城一個模子,四面高大厚實的城墻,保護城市中的統治者。

2016年1月30日,上海,武康庭。
中國城市的住宅區要保證秩序井然有序,統治者也很關心老百姓怎么老老實實地生活,從春秋戰國時代的閭里,到西漢至唐的里坊,城市的住宅區按照標準單位被方方正正地劃開小格子,居住和商業分開,做官的靠近宮城,方便為圣上服務;平民、農民靠近城門,工匠和商人靠近市場,方便謀生。
貌似很貼心,其實好管理。
通常認為設定的秩序都干不過人的基本需求,到了經濟和商業都異常發達的北宋,這套玩法就不管用了,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里畫的汴梁城,市場和住宅區之間的界限就被打破了,底層或者臨街鋪面經商,上層或者后院住人,所以才有了潘金蓮開個窗戶,不小心砸了西門慶,引發兩場血案的故事。
此時中國城市的街區味道也很明顯,只是我們不叫街區,叫個街坊,街道依然是住宅區的核心要素。
法國作家謝和耐寫了一本書叫《蒙元時期的中國日常生活》,事無巨細地描繪了當時世界第一大城市南宋臨安的生活方式,一百多萬人口,聚集在不到20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平民居住區的主體形式,依然是街坊(區)。
不管在西方還是中國,傳統城市里的街區,都是開放式的。
宋代以后的明、清,集權越來嚴厲,社會越來越封閉,街坊的居住方式,仍然有緩慢的發展。只是中國傳統社會歷來是重鄉村、輕城市,城市化率很低,所以城市住宅區還有一種更加基礎的淵源——庭院式。
四合院是代表形式,與街區的開放式不同,它是向內的、封閉的,比如北京的胡同,條塊很小,貌似街區,其實不是,而是由一個個小院落組成,通過院門進入街道,街道除了交通以外的功能,并不明顯。
一個院子一個家庭乃至家族,關起門來過日子,這個“小院”有點像小區的雛形。
美國式拆遷
西方工業革命干得熱火朝天,東方還在老婆孩子熱炕頭地歇著。
西邊兒這一忙活,就容易出問題,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城市人口密度陡然增加,容積率過高,商業雖然更加發達,生活更加便利,但是公共服務跟不上,衛生條件臟亂差,治安混亂,還出現了經濟洼地貧民區,讓城市管理者非常頭疼。
此時西方城市的發展,進入“第二年齡段”,到1950年代結束。這也是城市規劃成為一門學問的時期,最有名的一個叫埃比尼澤·霍華德,這個英國王室記者對城市規劃這個業余愛好,有著異常的興趣,他細心觀察了19世紀晚期倫敦窮人的生活方式,特別討厭城市里烏七八糟的東西,在他的眼里,倫敦簡直是邪惡之城,如此之多的人擁擠在一起,是對自然的褻瀆。
使命感一上來,這位外行就有點hold不住了,專門寫了一本書叫《明日: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花園城市”的理念,想把城市郊區已經衰落的鄉村,重新建設成新城鎮,把城市生活的便利和鄉村自然環境和諧結合起來,看上去是一個很美的解決方案。
霍華德一忽悠,美國人就信了,20世紀20年代開始,想把大城市去中心化,把企業和密度過高的居民驅散到郊區的衛星城鎮里,這個時期也是西方個人價值和權利高漲的年代,人們也傾向于需要一個相對封閉的居住空間,把自己“隔絕”起來。
這些美國規劃師們因為缺少權力,理念轉換為現實的能量并不夠強大,直到羅伯特·摩西的美國人1920年代進入紐約州政壇,這個近乎瘋狂的迷戀“城市公園”的人,利用巧妙的政治手段獲取權力,同時借助大蕭條時期,政府用大規模投資市政來拉動經濟的背景,摩西當上了“拆遷隊大隊長”,開著推土機就上街了,強推花園城市的玩法。
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他主導在紐約郊區興建大量城鎮式花園居住區,再修寬闊的大馬路和高速路,把中心區與衛星城連接起來。同時改造中心區里的傳統街區,修建千篇一律、向內封閉的居住區,他也承認這些建筑看上去越來越乏味,功能越來越單一,但他不在乎,因為他愛公園——街區變得乏味,他們去公園就好了。
這也是汽車成為城市主要交通工具的時代,摩西用大馬路展示他對小汽車和富人毫不掩飾的熱愛,以及各種小手段表現對貧民的厭惡,比如他特意把長島區的行路橋下高度設計為9英尺(約3米),而當時的公共汽車高度12英尺(約4米),為了不讓低收入者進入他設計的瓊斯海灘,他甚至運用法律鼓動人們否決了長島鐵路延伸到瓊斯海灘的動議。
摩西的玩法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為汽車服務,馬路越來越寬,很多傳統街區的“街道”只剩下了交通的用途。作為花園城市的小型替代品,封閉式的“超級街區”也出現在城市里,這種形式挺像中國人目前熟悉的“小區”,只是規模更小一些,不至于特別阻礙城市交通,但它有非常明顯的功能單一、自我封閉的特征,富裕的人們住在里面,仿佛過上了美好生活。
1920年代,面對同樣的“城市病”,還有另一個藥方,卻是美國一個社會學家開的,叫科拉倫斯·佩里,看來城市規劃這個行業,總是外行影響大。佩里覺得街區太小了,馬路一寬,交叉口一多,車禍經常發生,嚴重威脅老人和小孩。
這方面他就錯了,街區的大小,其實不是它的核心含義,別著急,往后看,會有人說明白這件事。
佩里覺得,城市居住區應該以“鄰里單元”的方式呈現,以小學在社區的服務范圍為界,規模要大一點,規劃要統一一點,這些人聯系要緊密一點,對外要相對封閉一點,促成鄰里關系的形成和熱絡。
佩里的方案,基本就是小區的思維。
于是小區出現了
西方工業革命傳遞到中國,演變成一場鴉片戰爭,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街區”卻意外地發展起來,近代開始的一些通商口岸,經濟和商業發達起來,城市化程度較高,采用的通常是街區的規劃類型,例如在上海市中心城區,一些較老的街坊尺寸約為100m*150m一個里弄的平均居住規模也僅為46戶。
中國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是被迫的,民國時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但是傳統街區的衰落和西方倒是保持同步,比美國稍晚一些,和英國差不多,原因和推動力卻不是工業化帶來的“城市病”,而是新中國的建立。
1953年,中國的建筑領域發起向蘇聯學習的運動,居住區規劃借鑒蘇聯的“街坊”形式,布局由四條道路包圍,住宅沿道路而不是街道來布置,圍合成中心庭院,中間設置幼兒園、小學、商店等日常服務設施,居民和工作單位連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聚集在一起,進行城中城式的體內循環,整體的封閉系統建立起來。
城市里各個獨立的工作單位圈一塊地,建一個集辦公生產、居住、后勤以及各項生活服務于一體的大院子,作為福利提供給職工,外人不能隨便進出。因為歷史延續性,現在單位大院仍然是國內許多城市的基本構成之一。這就是延續幾十年的“大院模式”,它既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結果,也暗合了中國傳統的庭院文化,有趣的是,也與佩里的“鄰里單元”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中國建立,百廢待興,人的思維也是傳統與前現代混合交織在一起,對于現代的理解,夾雜著快速工業化的欲望,形成兩個可以快速推進的城市規劃原則。
其一是政府可以以大生產的方式高效快速的劃定和提供大量住宅及配套設施,改良城市環境;其二是道路和住宅的供給完全分開,大廣場、大馬路、主干道利于人民游行、集會,大院利于人民工作和生活,城市支路被嚴重低估和忽略了。
特別是北京,軍營或者部屬大院,動不動就1公里見方甚至更大,數量還多,在城區星羅棋布,看上去不明覺厲,繞過去拐彎抹角。
這種玩法在經濟水平較低,人們出行和生活區域狹窄的時期,倒是起到了不錯的效果,既有傳統的思維慣性,又有現代性的外殼,方便管理和維護社會秩序。再加上幾十年的東西方敵對和割裂,整個國家都保持向內封閉的狀態,中國的經濟和城市持續低速運行和發展,私家車保有量基本等于零,倒也沒什么大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的住宅建設,經歷了兩個階段,以1998年住房分配貨幣化為界,之前興建的住宅規模和體量都比較小,2000年以后房地產市場風暴開始,以后十多年間,一直和宏觀調控拉鋸、博弈,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柱。
以2000年前北京興建的經濟適用房社區天通苑,和2001年廣東番禺開盤的星河灣為標志,前者如今形成的大天通苑地區居民已經超過60萬人,后者為代表的8個千畝以上規模社區,形成“華南大盤”模式,都是位于都市郊區的超大型小區。
它們起了個“花園城市”的頭,后面大干快上,10多年來興建的城市居住區不斷擴大城市外延,一個個大餅攤開來,成為中國快速城市化的一大景觀,至少在面積上,中國的城市化興高采烈地發展起來。從2000年到2013年,中國住宅竣工面積超過60億平方米,絕大多數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小區”。
華南大盤模式崛起時,有清醒的開發商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潘石屹當年在一次會上就提出來,說美國人好像沒玩這么大,住宅和馬路只隔一條寬寬的人行道,商鋪和咖啡館星羅棋布,人們生活更加方便。萬科的王石說話比較沖,說這種模式以后可能會成為城市發展的 “毒瘤”。
沒有人進行全局性的規劃和研究,也沒這個意識,也沒有人強制推行,小區在中國就遍地開花了,人們住 “大院”也習慣了,搬到封閉式小區里是很自然的事。鄰里和睦、生活保障,至于與外界的溝通,一個是沒必要,一個是沒勇氣,封閉式的思維方式是從內心開始的,它根植于貧困年代的集體記憶,和必須要秩序井然的潛意識。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沒有改變的外部條件,中國住宅開發起步的2000年前后,恰好是中國加入世貿前后,緊跟著就是的10多年的經濟高速運行,催生了出有中國特色的“中產階級”,這些年輕人有更自覺的自我權利意識和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小區作為貌似花園城市的玩法,很是讓大家滿意,覺得這就是屬于咱們自己的美好生活。
中國人一醒過味來,干什么都比別人快,經濟高速發展,城市不斷擴大,生產能力提高到移山填海跟玩似的,回頭一看,環境污染了,低端供給嚴重過剩了,城市馬路成了停車場,誰也走不動了,自己的城市病,也已經不輕了。
人們怨氣沖天,也沒啥好招兒,發泄是沒用的,總得想個辦法,反思來研究去,很多人都在找原因,吵來吵去也沒個定論,中央的“拆墻計劃”一出來,就更亂了,一種意見說得貌似在理:你說街區制好就好了?就算是好,那是人家基于私有財產,慢慢形成的結果,這一把拆了小區的院墻,就能一勞永逸了?
經過咱們這么一捋線索,西方街區基于財產私有形成的,中國的大院也未嘗不是,況且現在咱們自己也有《物權法》,想拆什么大家商量著來,何必這么緊張呢?一種消極環境的改變,基本動力不是辯論個中原因,而是對以往行為方式產生的作用和結果的評估,和改變行為方式的可能性。
究竟差哪兒了?
一個明白人終于華麗登場,這個人叫簡·雅各布斯,好玩的是,對于城市規劃,她也是外行,本來是做記者的,后來寫了一本書叫《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本書在美國出版的時間是1961年,對這之后的西方城市規劃理念,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可惜它被翻譯到中國,卻是2005年的事了,在一片歡騰的樓市里,沒人在乎它,沒病誰也想不起來吃藥,不過現在重視也好,特別適合咱們的現實情況。
美國人從大蕭條時期在城市建設上的大干快上,也持續了不少年,這本書就是對這個歷史階段的反思,這個美國老太太很有意思,像個居委會大媽一樣走街串巷,事無巨細地觀察和分析各種類型的居住區,發現了一個完全違背所謂規劃“科學”的現象。
那些為了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品質修建的公園,為中產階級重新改造的封閉式“超級街區”,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部分公園利用率很低、犯罪率卻在增高,人們在有保安和監控守護的“超級街區”里,也沒有獲取應有的安全感,人際關系越來越淡漠。
在一個超級街區里,她采訪到一位女士,這位女士搬進來時,將很大的精力用在和鄰居社交方面,和全部90多戶居民建立了聯系,有一天她不在家時,孩子被意外困在電梯里很久,卻無人主動施與援手,事后這位女士問起鄰居,鄰居居然驚訝地回應:原來那是你的孩子呀,早知道我肯定會幫忙的!
相反,雅各布斯在尚未被推土機入侵的所謂貧民區,卻觀察到了傳統街區在現代生活中展現的的活力,鄰里透過窗戶觀察街道上的情況、互相守望,主動提供幫助,孩子們可以得到陌生人的照料,人們在多樣的街邊商店、書店、咖啡館里購買生活用品和服務,還會把家里鑰匙交給店主保管。
這樣的街區,在中國也有相關的案例。房地產行業著名段子手馮侖,在20多年的住宅開發過程中,做過兩個開放式小區,一個在臺北,一個在北京,臺北的就不說了,北京的這個在國貿商圈,CBD核心區域,叫新城國際,可以容納2000戶居民,道路、綠地都屬于業主,卻是向外開放的,將近20年了,大家共享,溝通方便,也沒有任何人有異議,外部穿越小區的人,與小區內部業主,也沒有任何矛盾,房屋不斷升值,現在已經成了高端住宅。
馮侖很坦率,他做的封閉式小區更多,也不乏高端社區,保安、物業甚至監控系統都很嚴密,但并沒有徹底解決安全問題,甚至還出現過盜竊乃至于更加惡劣刑事案件,但這個新城國際,并沒有出現過此類案件。
好的建筑和美麗的環境,和良好的行為方式之間,并沒有簡單、必然的聯系。
另外一個案例是成都玉林社區,這是2000年房地產風暴來臨前形成的社區,近年來逐步開放,豐富的街巷路網承載了市井生活,除了城市平民,大量藝術家、音樂家乃至建筑師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圈子,社區生活非常有活力。
這是一個居民自下而上推動開放的社區,很好地解決了產權糾紛、社區安全性、城市交通干道干擾、停車位等諸多問題。
諸多的毛細血管道路并沒有吸引更多的汽車,反而諸多折線和遮蔽形成的曲徑通幽的效果,讓很多司機不敢貿然進入,公共建筑、廣場、綠地都小型化便捷化,靈活設置在社區的各個角落,避免大尺度的公共廣場或綠地,也避免了大量外來人員的涌入和共享。
為了提高安全性,1至4棟樓組成一個微社區,增設門禁系統,片區開放的同時,安全性并沒有受到嚴重影響,那些老居民幾乎認識所有住戶,對闖入者自然提高警惕,這既是雅各布斯推崇的“街道眼”,也有中國傳統庭院片區的影子。
小區和街區的根本差別,并不在于大小,美國的超級街區可以很小,中國的小區可以很大,但它們面臨的問題并沒有多大的不同;也不在于對安全的保護,可以用完善公共服務來實現,和規劃并無直接關聯,雅各布斯認為,城市公共區域的安寧,并不主要有警察來維持,而是由一個互相關聯的、非正式的網絡來維持,這是一個有著自覺的抑制手段和標準的網絡,由人們自行產生,也由其強制執行。成都玉林小區即是如此。
小區和社區的根本差別,在于街道和馬路,在于開放和封閉。街道是街區的血脈,兩者是同一個系統;馬路則是小區的邊界,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系統。街區是開放的,小區是封閉的,街區可以是一套可以自我循環的生態系統,小區則可能是溫暖、舒適、“安全”的“山洞”。
居住區首先基于人們的需要和頻繁的使用,這是最核心的要素,規劃必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一座現代城市之所以形成,是基于陌生人的自愿聚合,人們出于個體的需要聚居在一起,在相互獨立的狀態下互相提供產品和服務,高效溝通、互相幫助,個人權利與公共空間融合,有基本的公共責任感,才會有便利、舒適的生活方式。
從街區到小區,再從小區到街區,人們尋求的無非是更加舒適的城市空間,反映了人的溫暖需求和更加密切的鏈接,所謂由大變小、增加道路供給、提高商業多樣性,提高人們運行效率等等,只是其中的表象,遠有更為復雜的社會問題和人的需求值得關注。
小區與街區,一街之差,差在開放的心態、規劃和人氣的融合,差在人對城市和居住環境更為深層次的理解,我們的城市和小區已經大成這個樣子,病得如此嚴重,不只是交通才是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于認識和行為方式的改變。(參考書目:《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開放式街區的基礎是均衡的城市公共設施系統》、《“開放街區”規劃理念及其對中國城市住宅建設》、《鮑贊巴克的設計理念與作品研究》)
以1998年住房分配貨幣化為界,之前興建的住宅規模和體量都比較小,2000年以后房地產市場風暴開始,以后十多年間,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柱。
小區和社區的根本差別,在于街道和馬路,在于開放和封閉。街道是街區的血脈,兩者是同一個系統;馬路則是小區的邊界,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