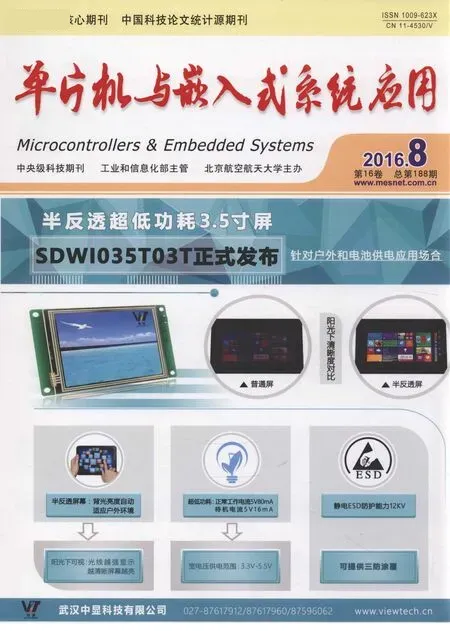從人工智能的源頭說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何立民
?
從人工智能的源頭說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何立民
2016年初春,谷歌的AlphaGo與圍棋高手李世石的人機大戰,引發了一股人工智能的熱潮。人們驚呼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了,熱議人工智能超越人類帶來的諸多思考。聯想到人形機器人在服務領域大肆擴展、工業機器人在生產線上替代工人工作,甚至在文化、藝術、媒體領域出現了計算機創作,在軍事領域涌現了無人化軍備競賽,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徹底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空前巨變時代是否已經到來?人類應怎樣應對?又該如何理性思考?人類究竟將向何處去?
1 什么是人工智能?
1.1什么是人類智能?
在厘清什么是人工智能之前,應先弄清什么是人類智能。AlphaGo與李世石的圍棋比賽,包括此前IBM深藍計算機與卡斯帕羅夫的國際象棋比賽,都被人們稱為人機大戰,嚴格來說,應稱為人機思維之戰。因為AlphaGo與深藍計算機既看不見棋盤,又不會走子,所說人機大戰只是人與機器思維的決戰。真正實現人機智能對決的,是日本東京大學石川渡邊實驗室研制的機器人“Janken 3.0”,它在與人類對手進行石頭、剪刀、布的猜拳游戲中沒有輸過一次。
之所以在厘清“智能”上如此較真不是無事生非。因為在論述人工智能時,必須弄情人類智能的真實含義,并了解不同智能表現上的差異性。IBM深藍計算機、AlphaGo體現的是人類思維(國際象棋、圍棋)的仿真能力,機器人“Janken 3.0”則實現了與人類(猜拳游戲)對決的智力行為。“思維”與“智力行為”都是人類的智能表現,但在人工智能領域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前者只有思考,沒有感知與控制,因此,其沒有行為能力,是一個實現人類智力仿真的“智力平臺”;后者不僅有思考,還有感知與控制,具有獨立的行為能力,實現了人類工具的“智力嵌入”。
“智力平臺”與“智力嵌入”都是知識基礎上的能力表現。前者是具有思考能力的各種形式的專家系統,后者是具有行為能力的各種形式的智能化工具。
人類智能有“思維”與“智力行為”兩種形式,在人工智能領域便有計算機思維仿真與智能化工具的智力替代兩種模式。
1.2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涵蓋眾多學科的一個大科技,不同學科對人工智能有不同的理解,每個學科都會從不同視角來詮釋人工智能。在本系列文章中,將從嵌入式系統視角來詮釋人工智能。
“科普中國”百科科學詞條中給出了一個較為冗長的人工智能定義:“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新的技術科學。人工智能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它企圖了解智能的實質,并生產出一種新的能以人類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應的智能機器,該領域的研究包括機器人、語言識別、圖象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專家系統等。”
人工智能學者對人工智能則有較為簡潔明了的定義。美國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爾遜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是關于知識的學科——怎樣表示知識以及怎樣獲得知識并使用知識的科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溫斯頓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用計算機去做過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這些說法反映了人工智能學科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內容。
尼爾遜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是關于知識的學科,點出了人工智能的基礎是知識。“思維”是知識基礎上的思考,“智力行為”是知識基礎上的行為能力。溫斯頓教授的觀點表明,實現人工智能的工具是計算機。這里指的計算機應該是“現代計算機”,即通用微處理(MPU)基礎上的通用計算機與嵌入式處理器(MCU)基礎上的嵌入式系統。前者主要是用于思維仿真的智力平臺(各類專家系統),后者主要是用于智力嵌入的智能化工具(機器人、智能設備等),從而形成了人工智能的兩大分支。
2 人工智能的科學源頭
人工智能的工具是現代計算機,現代計算機的源頭是圖靈機,圖靈機的靈魂是可計算原理與可計算模型。
古代人的計算從計數開始,后來普及到數值計算,人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除了數以外,有什么是可以計算的”。20世紀以前,數學界普遍認為,所有問題都應有相應的算法,其后,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仍然找不到解決一切問題的算法,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出現轉機。一批偉大的圖靈學者們,告訴人們“一切皆可計算”。從數值計算到邏輯計算,數學終于走上廣義的計算領域,開始人類智力計算的長征。
圖靈學者不僅奠定了人類智力計算的理論基礎,圖靈還設計出可實現智力計算的圖靈機。圖靈機是一種人工智能的模型機,用最簡潔方式模擬人類思維過程。該機器由一條無限長的紙帶、一個讀寫頭、一套控制規則表、一個狀態寄存器組成。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絕不是一個傳統的計算機器,而是一個在指令表控制下,紙帶步進狀態的字符狀態處理機,可以用“0”、“1”兩個最簡單的數字狀態來實現圖靈機的無限思維計算。
圖靈機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的基礎性與普遍適用性,即有最簡單的結構、最大的等價性、“0”和“1”狀態的數字符號集、軟硬件分離的智力計算方法等。圖靈機是一個全新概念的智力模型機,由此奠定了未來計算機軟、硬件的二元化獨立體系。此后,人們分別開始了圖靈計算機軟件與硬件的研究之路。
從20世紀30年代圖靈機模型誕生到圖靈機的實用化,經歷了漫長的道路。1950年,圖靈發表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為后來的人工智能科學提供了開創性的構思。直到1954年圖靈去世,基于圖靈機模型的理想計算機一直沒能創造出來。因為圖靈思想超越了現代科技力所能及的范圍,直到半導體集成電路誕生。
硬件方面,1946年,具有圖靈機思想的第一臺電子計算機開始了人工智能計算之路,但龐大的體積、有限的運算能力,無法成為人工智能的普適性工具。
1971年,全球第一個微處理器4004誕生;1979年,8088微處理器誕生;1981年,基于8088的第一臺個人計算機(PC)誕生。與此同時,在微處理器基礎上,一大批嵌入式處理器(MCU)誕生。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1976年的MCS-48微控制器系列與1980年的MCS-51微控制器系列,其后微控制器的發展呈現井噴之勢。
半導體微處理器以其微小體積、精巧結構、可無限擴展、極低價位等基本特征,成為了人工智能的一個理想的歸一化智力內核。它以通用微處理器基礎上的通用計算機智力仿真與嵌入式處理器基礎上嵌入式系統的智力嵌入方式,開始了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現代計算機知識革命、數字化革命、智力革命、信息革命與產業革命。不少專家將人工智能的起始年代劃定在20世紀70年代,原因即在于此。
3 智力革命與人工智能
智力革命迎來了人類的人工智能時代。智力革命的基礎是半導體微處理器,智力革命的工具有通用微處理器基礎上的通用計算機與嵌入式微處理器基礎上的嵌入式系統,它們都是微處理器基礎上的計算機,統稱為現代計算機。智力革命的表現方式有通用計算機基礎上的智力仿真與嵌入式微處理器基礎上的智力嵌入。
通用計算機與嵌入式系統的普適效應,使人工智能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因為微處理器的智力內核形式與量子化發展前景。微控制器微小體積、極低價位、內核形式,可以廣泛滲透到人們生活周圍,如智能家電、汽車電子、機器人、物聯網智能終端、穿戴式設備,甚至是嵌入人體內的生理檢測與醫療電子系統。此外,由于微處理器的體系結構與其構成的載體無關,具有無限的量子化發展前景。目前微處理器的載體是硅半導體,其集成度從微米級、亞微米級到納米級,在納米級時代逐漸到達極限時,人們有望迎來原子級石墨烯的微處理器技術,最終可以期待光量子級、電子級的微處理器與量子化計算機。
微處理器分化成通用微處理器與嵌入式微處理器后,形成了人工智能領域的兩大分支,即通用計算機基礎上的智力仿真與嵌入式系統基礎上的智能化工具。通用計算機基礎上的智力仿真以軟件為中心,沒有感知與控制能力,本質上是人類思維的仿真,典型的是形形色色的專家系統,如IBM深藍計算機的“國際象棋大師”、沃森計算機的“智力競賽”、谷歌的“阿爾法圍棋”,以及未來的“計算機頂級醫生”等,還有遍布人們周圍在計算機平臺上使用的獨立軟件。嵌入式系統基礎上的智能化工具具有感知與控制能力,早期用于傳統電子的智能化改造,隨后發展出諸多的新興智能化工具,如智能家電、智能家居、汽車電子、智能工控、工業機器人,以及與諸多前沿科技配套的智能化處理、分析、測試設備等。未來,智能化工具與計算機思維仿真會出現交叉融合,既能實現高級思維,又能展現知識力量的高級人工智能機。將“阿爾法圍棋”的應用程序嵌入到具有感知與控制的人形機器人中,便能實現真正的“阿爾法圍棋”人機大戰。
通用計算機基礎上的智力仿真與嵌入式微處理器的智力嵌入,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很多領域。軟件與硬件的分離,決定了人工智能有相對獨立又相互交叉融合的基礎技術與基礎產業。
4 人工智能推動科技超速發展
人工智能誕生之前,人類在共享公共知識基礎上發展現代科技;人工智能誕生以后,人類在人工智能的基礎上共享公共智力,以人工智能工具代替人類的腦力勞動,從而使現代科技呈現超高速發展態勢。
例如,只有數值計算知識,沒有計算工具的時候,人們用筆和紙進行手工計算。有了算盤和手搖計算機,人們借助簡單工具提高了計算效率。盡管效率提高,但數值計算的腦力勞動必須全部由人來完成。有了電子計算器以后,電子計算器中不僅有數值計算知識、計算規則,還有了數值計算能力的人工智能。使用電子計算器時,只要輸入數據及數值計算要求,計算器就能自動進行數值計算并給出結果,計算器完成了原來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仔細觀察我們周圍的世界,像電子計算器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在電子技術領域,有了半導體模/數轉換器芯片,工程師們在電子系統設計中不再需要設計模擬信號到數字信號轉換的腦力勞動;有了手機導航,自駕出行時,不再需要記憶地圖、辨識道路;有了收銀機,超市收銀員不再需要有貨品知識、計數知識,只需擺動手臂、手指就能完成結算過程。有了AlphaGo,人人都能向圍棋高手挑戰。
在科學技術領域,借助半導體芯片、計算機、科學計算軟件、統計軟件、分析軟件等智能化工具,科學家們可省去了許多的腦力勞動。科技成果應用不再是知識基礎上的傳統應用模式,而是智能化設備基礎上的“傻瓜化”應用模式。這種應用模式大大地加速了新興科技從成果到應用的轉化速度。2016年3月25日“大國重器”的張江發布會上,上海蛋白質中心專家指出:“以前一個科學家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認識一個蛋白質,但是在蛋白質中心,借助各式各樣的先進設備和儀器,最短僅需2分30秒就能認識一個蛋白質。”而且這只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在基因工程領域,2000年第一個人類基因組測定花費30億美元,2008年有了基因測序設備,做一個基因測序降至10萬元,如今在大量先進的基因分析設備基礎上,一個普通技師可在21小時內完成千人基因組的分析工作,而且費用可降至千元以下。
從民眾生活到科技創新領域,人們周圍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智能化工具,從半導體芯片、微控制器、計算機等基礎工具,到計算機軟件、智能硬件、智能電子、機器人、智能機具、自動生產線等。盡管形態不一,它們都具有知識基礎上的行為能力,可以代替人類個體的腦力勞動,稱之為知識力量平臺,簡稱“知識平臺”。
有了人工智能的知識平臺,人類將徹底告別以知識為基礎的傳統科技成果轉化模式,代之以知識創新與創新知識應用相分離的知識平臺模式,即知識創新者將創新知識成果轉化成相應的知識平臺,創新知識應用者在知識平臺上實現創新知識的“傻瓜化”應用。知識創新者不介入應用,有利于前沿科技的新領域探索;創新知識應用的“傻瓜化”,有利于將精力集中于應用領域的二次創新,從而大大加速人類新興科技發展的步伐。
[1] 百度百科.人工智能[EB/OL].[2016-06].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ghdhRBsYyjoDpp9 dWyNSiSxIzB 3xetX lpZx4E7wO5tGtN-tHgwj_srIlGfejIZUOncwBtqmg Nc17md UURqWes0Dh1GrZKsNP7yIr55j6qa.
[2] 何立民.知識學原理[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12.
[3] 何立民.工具簡史[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16.
(責任編輯:薛士然2016-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