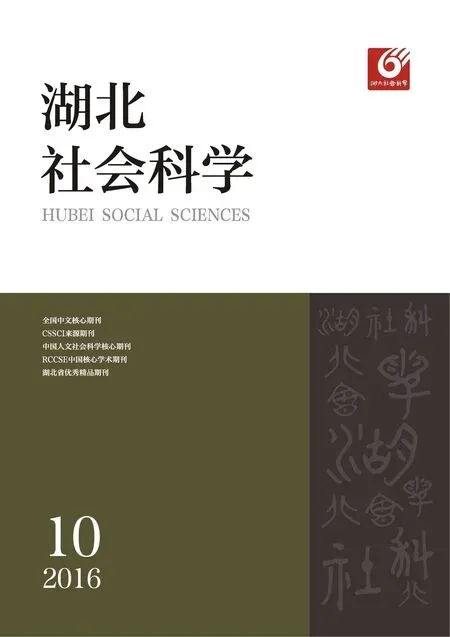毛奇齡試律詩理論及影響
梁梅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寧夏 銀川 750002)
毛奇齡試律詩理論及影響
梁梅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寧夏 銀川 750002)
毛奇齡是清初著名學者,他的試律詩理論主要體現在目前留存下來最早的唐試律詩選本《唐人試帖》中。毛氏關于試律詩源流的探討,創作方法的概括,審美原則的總結都在后世的理論著作中得到了響應,是試律詩研究珍貴的理論資源,由他掀起了試律詩理論研究和創作的高潮,為建立清代試律詩理論體系奠定基礎。
毛奇齡;《唐人試帖》;創作方法;理論原則;影響
乾隆二十二年起,清代鄉試、會試均增試律詩一首,各種唐試律詩選本紛至沓來。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康熙四十年刊刻,由毛奇齡論定的《唐人試貼》。毛奇齡,浙江蕭山人,世稱西河先生。康熙十八年薦舉赴博學鴻儒科,列上卷,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此后,“西河不負主知,其詩其文皆足上越唐宋而下掩后來。間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為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即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颣”(李天馥《西河合集領詞》)。毛奇齡集文人學者于一身,勤于寫作,于經、史、文皆有論述,《四庫全書》收錄其作品多達四百余卷,在清初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他的文學理論尤其是試律詩理論對于士人的啟發和指導作用顯然是不能忽視的。然而目前有關毛奇齡的研究極為有限,且大多仍拘于經學一隅。本文擬對毛奇齡的試律詩理論進行梳理,并簡要分析其對清代試律詩理論研究的影響。
一、試律詩理論框架
反思明代滅亡,有識之士順理成章地遷怒于明代的八股文,改革科舉的議案從清初便接連不斷。康熙博學鴻儒考試,以《璇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十二韻為題表明了當權者重建詩賦取士制度的決心。另外,從某種程度上,科舉考試左右士子的創作動力。清承明制,惟重八股,士子于作詩不免懈怠,詩歌發展難以為繼。乾隆文人蔣世銓提到“吾鄉自淵明以下,代多作者,數十年來老成凋謝,后生有才之士或專力八股文,棄詩不為或為之而不求其至……于是經生工詩者益希”[1](《詩法度針序》)。再者,唐代以詩取士,后世論及試律詩理論者代不乏人。然而,“宋人已有論及省試詩之文字,元明人對試律詩之批評、總結,顯然多于有宋,但都略顯凌亂、破碎,不足為論。”[2]清初士子對于試律詩非常陌生。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是試律詩中膾炙人口的名篇,它必定符合試律詩的創作規范,不能用一般古近體詩的標準去衡量。然而《唐人試貼》記載“(毛奇齡)住在揚州,與王于一論詩,王謂錢詩固佳,而起尚樸僿。相此題意,當有縹緲之致。霎然而起,不當纏繞題字。時余不置辨,但口誦陳季首句“神女泛瑤瑟”,莊若訥首句“帝子鳴金瑟”,謂此題多如是,王便默然。蓋詩法不傳久矣”。[3]圍繞題目進行破題、承題恰是試律詩創作的基本要求。王于一強不知以為知,他的“縹緲”之說若論古近體詩則可,若論及試律詩不免啼笑大方。清代以前,試律詩的科舉退場再加上理論探討的缺失,其體制特征和創作要求的確不為人所熟知,恰如毛奇齡說言:“古人制題之法,今人不曉矣”(評張子容《長安早春》)。所以,士子所面對的是朝廷有意詩賦取士與缺乏試律詩理論指導和訓練的窘境。這就是毛奇齡試律詩理論闡發的主要目的,如其評孟封《行不由徑》中言:“錄此以備詩體。”即明確試律詩文體特征,宣傳和普及試律詩的寫作規范和美學原則,以適應清初科舉取士的政治需求。
首先,必須明辨體制,通過試律詩之間或者試律詩與其他文體的比較,達到對其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的把握,即給試律詩準確定位。“夫詩有由始,今之詩非風雅頌也,非漢魏六朝所謂樂府與古詩也,律也。律則專為試而設。唐以前詩幾有所謂四韻、六韻、八韻者?而試始有之。唐以前詩又何曾限以三聲、四聲、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韻,而試始限之。是今之所為試律詩也,試詩也。乃人日為律,日限官韻,而試問以唐之試詩則茫然不曉。是詩且不知,何論聲律?”(《唐人詩帖序》)所謂“今之詩”特指試律詩。附會《詩經》或者樂府古詩已經成為提高文學品格的不二法門,尤其是一些非正統被鄙薄的文體,小說、戲曲無不如是。試律詩是科舉文學,具有士人所不齒的仕途經濟的世俗氣,若其源于《詩經》,則顯得出身高貴。然而毛奇齡并未人云亦云,他指出從《詩經》到樂府、古詩都沒有格式押韻的限制,更不用說規定官韻,因此它們不是試律詩的源頭。唐代科舉取士,試律詩應運而生,詩歌才由古詩變為律詩。清代試律詩就是唐代試律詩的延續,與《詩經》等無關。這種觀點其錯誤不言自明,律詩產生過程中,南北朝絕對是重要發展階段,但認為唐試律詩即試律詩的源頭則可見毛奇齡更具有現代學者突破傳統的理性精神。
既然由唐試律詩發展而來,就要肯定它的典范作用。毛奇齡在詩歌審美趣味上認同格調派,在試律詩理論中同樣倡導尊唐。“自無學者謂唐詩籠統,不知唐詩最刻畫。曾讀唐人試詩否?當光化戊午年長安省試,其題是《春草碧色》。時中式進士為殷文珪、王叡等皆用題‘春’字作韻。其詩有‘嫩葉舒煙際,輕陰接水濱。金堂明夕照,輦路惹芳塵’諸句。鄭子真見之,以為未盡其義,因別作一詩。中有‘窗紗橫映砌,袍袖半遮茵。天借新晴色,云饒落日春。風光垂處合,眉黛看時顰’,何刻畫也!”[4]評宋華《海上生明月》“制題當中尚存顥氣,初唐之殊于后來如此。”評潘炎《玉壺冰》“即此見唐人點題周到如是。”評濮陽瓘《京兆府試出籠鶻》“六朝《游獵篇》遜此勁爽,遂為三唐絕作。”在他看來,唐試律詩無論語言的表現力,雄壯博大的氣象,還是審題的能力都妙絕千古,必須維護唐試律詩的正統地位。
一般律詩與試律詩顯然是有區別的。毛奇齡為了說明試律詩的特點,在首先肯定二者創作具有相似點的前提下,提到:
七律作法與試律詩無異,憶丙午年避人在湖西,長至夜飲施愚山使君官舍。愚山偶論王維、岑參、杜甫和賈至《早朝》詩,惟杜甫無法。坐客怫然。予解曰:“徐之往有客亦主此說。”予責其或過,客曰:‘不然。律法極細。吾苐論其粗者。律,律也……杜既不然。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而燕雀賀,非朝時境也。五夜便日暖耶?舛也。且日暖非早時也。若夫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嘗朝者也。曰朝罷,亂也。詩成與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予時無以應,然則愚山之論,此豈過耶?
安史之亂后,中書舍人賈至下朝后寫詩贊嘆唐朝中興氣象,杜甫亦有合作即《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原詩為:“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這當然不屬于試律詩的范疇,但正如施潤章所說,假設肯定杜甫所作《早朝》屬于試律詩,那么它是不符合試律詩的寫作規范的。詩中所提到的并非朝堂之事,更非上朝之后;五夜即黎明時分,還談不上“日暖”,如此破題就不得法。另外,一共八句詩,只有四句點題,其他是對賈至的恭維,脫離題目,所以施潤章說杜甫“無法”。在律詩與試律詩的比較中強調后者的特點在于圍繞題面破題、承題,且不能隨心所欲地“出題”。
除此之外,還有應試與應制的比較。“唐有應試、應制二體。特應制無專本,且其體有七律、長律,但即事而不命題,與應試稍異,若其賦詩之法,則無不一輒。考應制與制科不同,無去取甲乙……持此雖與制科異,而甲乙去取,不異放榜,則雖謂之制科亦得耳。”通過應制與應試的比較,說明二者作法一致,都可以判定名次,區別是后者命題而作,并且有固定的形式要求。
毛奇齡最為重視的是試律詩與八比的聯系。在《唐人試貼序》中提到:
且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應之。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復其句、重其語、兩疊其話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頷比、頸比、腹比、后比,而然后以結收之。六韻之首尾即起結也,其中四韻即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今日為試文亦目為八比,而試問八比之所自始,則茫然不曉。是試文且不知,何論為詩?
在他看來,寫好試律詩的前提是必須擅長八比,因為八比是從唐試律詩演變而來。在詳細比較了八比和試律詩的結構特征后,指出試律詩六韻,中間四韻等同于八比之八股。另外兩韻即八比之破題、結尾。評張濯《迎春東郊》:“……皆以經書出題,前此試士并未有此,固知八比始試詩也。”毛氏舉出了從經書出題的試律詩,由此證明八比始于試律。雖然結論并不可靠,但是試律詩與八比皆是因題而作,都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規定格式的文章,做到起承轉合、由淺入深,達到一定的要求,確有可比性。另外,此時士子最精通者莫過于八比。八股文創作起承轉合的思維模式經過幾百年的不斷加強早就成為頭腦中固有的定式,用八比的結構特點來解說試律詩的布局方式,不失為一種化繁為簡的捷徑。紀昀也贊同此法:“然其(毛奇齡)謂試律詩之法同于八比,則確論不磨。夫起承轉合、虛實淺深,為八比者類知之;審題命意、因題布局,為八比者亦類知之。”[5]乾隆末年葉葆在《應試詩法淺說》當中提到“初學習文,其于破題、承題、前比、中比、后比、結題之法講之久矣。今仍以文法解詩,理自易明。”[6]以八比為詩對于普及試律詩寫作方法來說確實為明智之舉。
其次,是重法貴格。法,即律也,是試律詩創作必須遵循的法度;格,即規范、格式,從形式方面來要求。“及格”是合乎規范,反之則稱為“佚格”。遵守法度、合乎規范是試律詩創作的關鍵。除了有利于國家掄才,也有助于對試律詩的把握。毛奇齡為試律詩創作樹立法則,并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運用于詩歌評論中。評祖詠《終南積雪》“按本事,詠應試賦此題才得四句,即納于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據此,則試無二韻者,此詠自為之,非官限也。二韻已破例,不用題字,則更非例矣,不知當時何以有此。”一般試律詩為五言六韻十二句,極少八韻或四韻。此為二韻,律詩尚且不是,又何談試律詩。這首詩確為唐試律詩中的特例,卻足稱唐詩中上品。后人論述頗多,但大多從審美角度鑒賞。即便同是試律詩理論著作,也只是專注于它的藝術筆法。如康熙末年葉忱《唐詩應試備體》評為“上句先破終南,用‘陰嶺秀’以含下‘積雪’。下句承出積雪,用‘浮云端’,又抱上‘終南’。得不盡之意。”[7]紀昀在《唐人試律說》中評為“三句寫積雪之狀,四句寫積雪之神,各隱然含‘終南’二字。隨口讀之,是新雪;是高山積雪,非平原積雪。”[8]紀昀特重詩法,然而如此失法之處卻視而不見,怪哉!只有毛奇齡對這首詩存乎試律詩中表示質疑,其重法可見一斑。
毛奇齡對于創作法度的闡述散見于詩歌評點中,其中主要有審題法、句法、押韻法、調度法。
試律詩因題而作,這是它與古近體詩的重要區別。準確的審題是創作的起點,通常要求起句破題,頷比承題,四句完題。通過考察作品,毛奇齡歸納出審題五法包括:點注法,對應解釋題字。如評李虞中《府試初日照鳳樓》起句“旭景開宸極,朝陽燭帝居”為“此以對起作點注法”。“旭景”、“朝陽”點“日”,“宸極”、“帝居”點“鳳樓”。這種方法最為常見。直述法,直接重復題目。如評王泠然《館試古木臥平沙》“古木臥平沙,摧殘歲月賒”為“直述一句,亦一作法”。此法簡單易行,但缺乏文采。議論法,表達對題目的態度觀點。如評孟封《省試行不由徑》“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天衢皆利往,吾道本方行。”為“此以議論制題法”。作者借題發揮,表明君子應光明磊落、正道直行。此法最可突顯士子的邏輯思維能力。破意法,轉述題意。如評鄭谷《京兆府試殘月如新月》“榮落誰相似,初終卻一般”為“不用題一字,而‘新’、‘殘’、‘如’字俱見,此破意之法”。補題法,補充題目出處,或與題目有關其他內容。如評錢起《湘靈鼓瑟》“善鼓云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為“承點屈平一句,亦補題法”。此題出于屈原《楚辭·遠游》“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句,承題補充原文和作者。乾隆時期,為嚴格考察士子學術功底,詩中必點題目出處,此法就比較普遍了。此外還有特例。試律詩題目一般從經史子集中選取,最少兩字,長題極少。毛氏評崔立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壚煙》“四句雖完題,而無隔仗字,此長題次第也。”說明長題題字不必全部點出。除此之外,審題不當的情況分為三種。如評劉得仁《京兆府試目極千里》“苐以低眉起目字,反過巧耳。”以“眉”來點“目”屬于過分審題。評孔溫業《賦得鳥散余花落》起句“美景春堪賞,芳園白日斜”為“起太無著。”起句必須點題,而“美景”、“芳園”、“白日”都與題目無關,是為“無著”。評韓愈《精衛銜石填海》“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為“出題”。試律詩要圍繞題面敷衍開去,不可“精騖八極,心游萬仞”離題而作,否則即為出題。
句法包括起句法和結句法,而特重結句。如評童漢卿《省試昆明池織女石》“還如朝鏡里,形影自分明”為“關合祈請,渾化極矣。試詩必如此,方是完作。”結尾寫祈請,是最常見的寫作方式。此外,也可以頌圣或者稱揚主司。評令狐楚《青云干呂》尾聯“恭維漢武帝,余烈尚氛氳”為“直作頌語,體法一變。”評劉得仁《京城府試目極千里》尾聯“如何當霽日,無物翳平川”為“借言主司明也。”在句子構成上,毛奇齡指出唐試律中有用虛詞組句,以文為詩的現象。如評張籍《省試行不由徑》“從易眾所欲,安邪患亦生”為“是以文句入詩法,然終非俊語。”以文為詩雖然別出心裁,但對詩歌表現力并無助益。評劉得仁《京兆府試目極千里》“此心常極矣,縱目忽超然”為“以文句行詩,與題不合”。唐試律詩中以文為詩并不多見,毛氏遂認為不符合試律詩的寫作規范。事實上,隨著試律詩創作水平的提高,乾隆時期的以文為詩已經非常普遍,這是他無法預見的。
對于押韻之法,毛奇齡著眼于特例。評潘炎《玉壺冰》:“試帖限六韻,偶有八韻者。一是主司所限如《玄元皇帝應見貼》,舉子皆八韻,則官限者也。一是舉子自增,如此詩八韻,王季友詩仍六韻。《迎春東郊貼》,張濯八韻,王綽仍六韻。則舉子自增者也。”唐試律詩一般押六韻,偶有八韻、四韻。試律詩一般押平聲韻,也有押仄韻的。評張謂《賦得落日山照耀》:“題有無平字者,如《石鼓》、《玉燭》類,必用仄韻。故題字平仄俱見者,亦任其擇用,始知唐詩原有仄韻律。”唐試律詩處于詩賦取士的初始階段,法度尚未嚴明,創作相對自由。評李勛《泗濱得石磬》“省蘭按:試律詩雖始于唐,然其時尚余齊梁風格,時有拗調,今人正不得援以借口也。”律詩正是在齊梁詩歌基礎上形成的,以拗調界定顯然太過武斷。毛奇齡恰是提醒士子清試律詩和唐試律詩的區別,借以指明試律詩押韻嚴格,有創作不可逾越之繩尺。
試律詩要求在有限的時間內寫出多組對偶句,如何布局謀篇成為構思關鍵。以偶句拼湊成文,意脈混亂,次第不明可說是試律詩的大忌。另外,同樣一聯放在不同的位置產生的審美效果截然不同。評錢起《湘靈鼓瑟》:“此題所見凡五首,然多相襲句。如錢詩最警是“流水”、“曲終”四句,然莊若訥詩有“悲風絲上斷,流水曲中長”句,陳季、魏璀詩俱有“曲里暮山青”、“數曲暮山青”句。始知詩貴調度,此詩調度佳原不止以江上數峰見縹緲也,善觀者自曉耳。”對于士子而言,寫上一兩聯警句并非難事,關鍵是如何調配才能恰到好處,發揮點睛作用。“調度”要求作者從宏觀著眼,把握全篇結構,避免無次第拼湊成文。紀昀就是所謂“善觀者”,他認同毛奇齡的調度之法,評陳季《湘靈鼓瑟》:
“暮山青”語略同錢作,然錢置于篇末,故有遠神,此置于聯中,不過尋常好句。西河調度之說,誠至論也。此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悵一秋風時,余臨石頭瀨”作發端則超妙,試在篇中則凡語。“客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問我今何適,天臺訪石橋”。作頷聯則挺拔,設在結句則索然,此意當參。”[8]
紀昀更加詳細指明“調度說”的概念內涵,并將之延展到了試律詩創作的布局與構思方面,與毛奇齡隔空響應。
最后,試律詩承載著士人對世俗名利的全部想象,似乎與生俱來就是祿蠹的代名詞,因而品格低下。紀昀就曾提到“試律體卑,作者率不屑留意。”[8]文人一邊熱心科舉,一邊從心底輕視試律詩。毛奇齡同樣如此,如評焦郁《賦得白云向空盡》“六語刻畫殆盡,亦試帖有數之作。”與眾不同的是,毛氏并未就此止步,反而創造性的致力于提高試律詩的文學品格和審美價值。
第一,借鑒了古近體詩論中“妙”、“奇”、“神”、“俊”等美學概念,既守法度,又突破繩尺,著力提高試律詩的審美價值。試律詩首先要符合規范,可也是因為這一要求,容易程式化、教條化。但它又和八比不同,不用“替圣人代言”,具有相對自由度。所以,毛奇齡強調士子應該在準確把握題目的基礎上,運用豐富的思維想象能力,巧妙構思、精巧布局,突破形式局限達到神奇的“有法而無法”的藝術境界。“奇”指構思思路開闊、新穎獨特。如評《府試古鏡》“即以鏡合試事,大奇”。評郭求《日暖萬年枝》“上句實賦日暖,下句實賦萬年枝,奇絕”。“神”、“俊”則要求作者善于刻畫,有超乎尋常的語言表現力。如評鐘輅《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以無聲反見聞笙,且合‘夜’字,神來之句”。評濮陽瓘《京兆府試出籠鶻》:“二語寫出籠神筆。”都指作者筆力超群。“妙”則專指寫作技巧超妙。評鄭谷《京兆府試殘月如新月》“屈指期輪滿,何心謂影殘”為“屈指、何心對妙”,即針對修辭筆法而言。反之,語言寡淡、構思平俗,則斥之為“劣”或“拙”。如評周徹《尚書郎上直聞春漏》為“言上直也,但句劣矣。”符合法度,但語言缺乏文采,也非上乘之作。評孔溫業《賦得鳥散余花落》中“共看飛好鳥,復見落余花”為“截然分對,亦未的確”。對仗死板,缺乏靈動之氣,更談不上神妙了。
第二,毛奇齡首次在試律詩范疇內提出崇尚“自然”的審美標準。天工自然是古近體詩的最高境界,試律詩的文體規范似乎與之毫無關聯,創作環境的不“自然”,寫作目的功利性都決定一切只能刻意為之。文學本無定式,試律詩卻要違背這一法則,加上無數清規戒律,實在無法“自然”。然而,以自然之真美來補救試律詩人工雕琢的板滯之態,達到這一古典美學的藝術境界卻是提高文學品位的必由之路。評裴杞《風光草際浮》:“自然卷舒,全不見纂組之跡”。意脈流淌,隨物賦形,不見斧鑿之痕正是文學創作理想的審美效果。同樣希望提高試律詩品位的紀昀亦持此論,其評《賦得棲煙一點明》:“此題是神來之句,所以勝四靈者,彼是刻意雕鏤,此是自然高妙。當時終日苦吟,乃得此一句,形容難狀之景,終未成篇。今更形容此句,豈非剪彩之花持對春風紅紫乎?”[5]剪葉裁花,雖然五色俱備,卻終乏樹生之花迎風搖曳的活力神采。用古典美學自然的審美觀來向古近體詩靠攏,不失為提升試律詩的文學品位之一法。
第三,提高創作主體的精神品格。作家由于個性稟賦的差異,在試律詩中便會有不同的風格特征,即文“氣”不同。公乘億《郎官上應列宿》前兩聯“北極佇文昌,南宮早拜郎。紫泥乘帝澤,銀印佩天光。”作者自詡為文曲星,總有一日會得皇帝親筆題名,封侯拜相。祈請而不猥瑣,文辭間流動著“舍我其誰”的雄豪霸氣。毛奇齡對之頗為贊賞,評為“絕不似制題,但以青壯之氣行之。此三味法也。”與之相似的還有評宋華《海上生明月》“制題當中尚存顥氣,初唐之殊于后來如此。”此清朗博大之氣也異于后世之干謁之作。
士子為功令所驅,不得不低眉折腰,英雄氣短。他們在詩中祈請干謁,頌圣稱揚,壓縮自我甚至搖尾乞憐。這是最為毛奇齡所不滿的一點,他引中宗景龍年間上官昭容評沈佺期、宋之問二人詩作語:“二詩功力悉敵,但沈落句云:‘微臣凋朽質,羞睹豫章才’,詞氣已竭,不如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如果詞氣欠缺,即便符合格式法度,審美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反之,則無傷大雅。評喻鳧《監試夜雨滴空階》尾聯“病身惟輾轉,誰見此時懷”云:“結無丐態,甚佳。特詞稍未俊耳。”“氣”指作家的精神氣質和個性特征,以及二者在詩歌中的反映。毛奇齡所倡導的是正大陽剛的精神力量,清朗勁健藝術風格。初唐自信昂揚的社會心態下所產生的“顥氣”、“青壯之氣”正是試律詩所缺乏的。如果無法做到大氣磅礴,那也不能直接表露干請之意,要做到含而不露、婉轉陳情。評無名氏《廣州試越臺懷古》尾聯“不堪登覽處,花落與花開”云“結不露干請意,只自傷沉滯,亦是一法。”提高主體的精神品格,從而提高試律詩的文學品格,這種修養論也被紀昀所繼承,他提出“氣不煉,則雕鎪工麗僅為土偶之衣冠;神不煉,則意言并盡,興象不遠,雖不失尺寸,猶凡筆也”(《唐人試律說序》)。所不同的是,毛奇齡的“氣”僅意味作家的精神氣質,而紀昀的“氣”、“神”則擴展開去,包括精神、學力、識見等多方面,并在他的基礎上提出煉氣、煉神,論述更為深入,范圍更加廣泛。
二、試律詩理論影響
毛奇齡在學術史上的評價毀譽參半。貶之者有之,如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中提到:“則其中(《西河全集》)有造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為師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誤已經辨證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說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無稽者,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書以就已者。”對毛奇齡的學術品格進行全面打壓。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9]贊之者亦有之。阮元《毛西河檢討全集后序》:“至于古文詩詞,后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鄉先生(毛奇齡)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塞。人蓄一編以教子弟,所借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為尤捷。余囊喜觀是集,得力頗多。唯愿諸生其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10]高度評價了毛奇齡不求名利的品德和學貫古今的成就。如此天差地別的評價出現在一個人身上,本身就意味著毛奇齡的存在價值。
在紀昀的《唐人試律說》之前,毛奇齡的《唐人試帖》無疑是對士人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試律詩理論著作。
首先,以八比為詩的布局模式除了為士子指明了一個可操作的創作方法外,還形成了以八比為評的批評模式,為批評家提供了一個用起承轉合解說試律詩的思維套路。乾隆二十二年刊刻的徐曰璉《唐人五言長律清麗集》引用了汪東浦論五言六韻作法幾乎全篇都是在毛奇齡八比為詩的理論上敷衍而來,不過加上每一聯的句法功能和藝術手法。乾隆五十四年葉葆的《應試詩法淺說》中列舉了《詩法淺說十八則》其中包括“篇法淺說”、“破題法淺說”、“承題法”、“提比中比聯淺說”、“后比聯淺說”、“末韻收題法淺說”,也是通過八比為詩來解說詩法。毛氏此說原是針對士子不了解試律詩寫作程式而拼湊無次第,遺憾的是,到了清代末年這依然是試律詩寫作的通病,八比論詩的方法也依然應用于評點解詩中。如同治十二年刊刻的《棣萼山房試帖》引用汪少霞的點評就采取的這一傳統方法,評《明皇羯鼓催花》:“起態度安閑,毫不費力,承聯襯托雅切,三四五舒卷自如,方家舉止。六,一唱三嘆,其聲動心樂不可極,隱然于言外觀之。結有情致。”[11]可見,毛奇齡的試律詩理論為后世提供了作詩和解詩的途徑和方法,是試律詩研究中重要的理論資源。
其次,與之前批評家在對作品接受基礎上的鑒賞、印象式點評不同,毛奇齡的批評受清初疑古惑經的思潮影響,是建立在懷疑基礎上的。作為清初樸學的先驅,毛氏把樸學的考據方法、求實精神與詩學批評結合在一起,力求無征不信、實事求是。他沒有將理論批評等同于客觀闡釋,而是以學術論詩,視之為學術研究。比如在審題法的論述中,通過對具體作品點評繼而歸納總結,既有正面典范,也有反面例證,更有特例解析。評徐敞《圓靈水鏡》“水鏡,舊本誤作冰鏡,以致元人作《韻府》者,亦以‘冰’字收入韻腳,不知是題出自《月賦》,其下接以“周除冰凈”。安得先犯‘冰’字耶?。”有實證,《月賦》原句就是“水鏡”;有推理,原文一句之中不可能出現兩個“冰”字。這種解析方式與樸學之考據別無二致,大大加強了試律詩理論的專門性和學術性,與以往“以資閑談”的隨筆體悟迥乎不同。以學術論詩的方法在乾隆嘉慶樸學興盛時期頗為流行。如紀昀《我法集》中評《賦得野竹上青宵》曰:“野竹在地,何以能到青宵?再加上一‘上’字,意似運動之物,益不可解。蓋山麓土坡陂陀漸疊漸高,竹延緣滋長,趁勢行鞭,亦步步漸上,長到高處,故自園邊水際望之如在天半也,從此著想,‘上’字方不虛設,否則是賦得山頂竹矣。”[5]顯然,在毛奇齡的影響下,樸學考據求實的精神已經滲入到試律詩理論研究中,使之更具清代獨有的學者氣質。
最后,《唐人詩帖》是清代最早最有影響力的試律詩理論著作,毛奇齡所提出的審美原則和創作規范在后世理論著作中多有余緒。批評家或以之為典范,直接引述他的觀點,或認之為標靶,對其觀點做出延伸性探討。乾隆時朱琰《唐試律箋發凡》中提出:“西河《唐人試帖》四卷,詩一百五十九首,近人傳誦,其中紕漏甚多,已于詩下辯證一二。”但同時也承認他的著作是在《唐人試帖》的基礎上刪改修訂而來。“毛本多改字,所改往往未妥。有可從,亦必存之。注曰:毛作某。若較勝諸本。間取一二字,則曰從毛本改。蓋不欲忘所自也。”[12]康熙五十四年的《唐詩應試備體》顯然與《唐人試貼》具有理論上的繼承關系。甚至在措辭上都十分相似。如葉忱在《唐詩應試備體·凡例》中提到“唐人應試詩為八比之所由始”,“應試詩原限六韻……此一定之體格。至或有八韻,有四韻者皆主司所限,非試詩體格之正也。”[7]也不全是對毛氏理論隨聲附和的。如葉忱的侄子葉棟就在《唐詩應試備體序》中提出了和毛氏完全不同的觀點“此(八股)與詩學渺不相及者也,至于登高作賦,遇物能名,才人學士往往各出所見,抒寫性靈則又別為一體。”[7]在他看來,八股屬于科舉文學,和抒情表意的詩歌完全不同,對毛奇齡八比始于試律詩的觀點表示質疑。
在清代試律詩理論建構中,毛奇齡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個環節。清末吳蓉《守硯齋試帖初集序》曰:
國家自乾隆丁丑會試易表文以唐律,限五言八韻名曰試帖,爾后由州郡考迄廷試靡不系焉,而試差尤重。誠以是事也非含王李之韻,秋矩而春規;擷江鮑之腴,雕今而潤古。則重臺疊屋,既以鋪敘紊次而失謀篇,牛鬼蛇神;又以陶浣不精而傷雅道。是以西河毛氏、河間紀公,提倡元音,標舉程式,嗣是作者代有其人。[13]
從清初對試律詩的不甚了了到乾隆時期逐漸建立起試律詩理論體系,毛奇齡可謂厥功至偉。雖然他的理論顯得零散而缺乏系統性,甚至有些觀點仍值得商榷,但也足稱為最有影響力和開拓性的批評家,也由他掀起了試律詩理論研究和創作的高潮,為建立清代試律詩理論體系奠定基礎。
[1]蔣世銓.詩法度針序[A].徐文弼.詩法度針[M].清藻文堂刻本.
[2]彭國忠.《唐人試律說》:紀昀的試律詩學建構[J].文藝理論研究,2014,(5).
[3]毛奇齡.唐人試貼(卷四)[M].嘉慶六年聽彝堂本.下文引毛氏語,皆出自該書,不具注.
[4]毛奇齡.西河詩話(八卷)[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C].濟南:齊魯書社,1997.
[5]紀昀.我法集[M].嘉慶元年閱微草堂刻本.
[6]葉葆.應試詩法淺說[M].乾隆五十四年悔讀齋刻本.
[7]葉忱.唐詩應試備體[M].康熙五十四年最古園刻本.
[8]紀昀.唐人試律說[M].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9]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M].續修四庫全書本.
[10]阮元.研經室集(二集卷七)[M].續修四庫全書本.
[11]王葆修.棣萼山房試帖[M].同治十二年刻本.
[12]朱琰.唐試律詩箋[M].乾隆二十二年寫刻本.
[13]王心齋.守硯齋試貼初集[M].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責任編輯 鄧年
I206.5
A
1003-8477(2016)10-0126-07
梁梅(1978—),女,寧夏大學人文學院講師,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