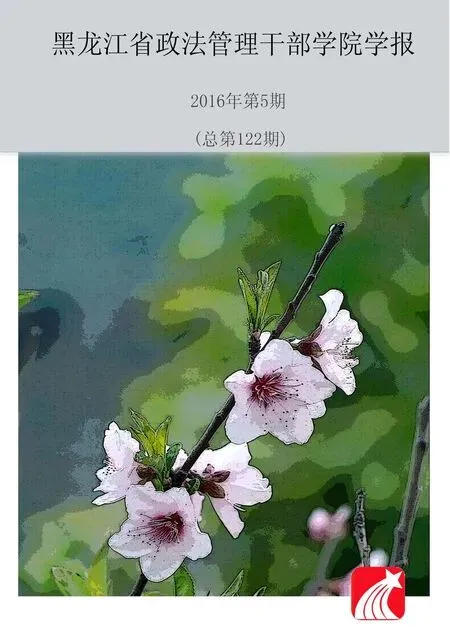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主觀方面探析
金經緯
(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學院,上海 200042)
?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主觀方面探析
金經緯
(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學院,上海 200042)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是我國《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由于本罪雖然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由于行為對象、立法背景等方面不同,兩罪在司法適用中又有很多區別,再者本罪主觀方面的司法解釋尚未出臺,因此本罪主觀方面的司法適用問題亟待明確。第一,本罪不屬于目的犯。第二,本罪中的“明知”包括“應知”,也包括可能性認識。第三,本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導致“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但只需認識到這種結果的可能性。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主觀方面;明知
隨著互聯網不斷的發展,信息爆炸的時代已經到來。面對紛繁復雜的信息,大眾往往不加篩選地予以接受,這使得網絡時代的信息甄別工作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網絡上出現大量的虛假信息,嚴重擾亂網絡秩序,侵害網民的合法權益。同時,為了打擊恐怖犯罪,我國在2003年通過出臺《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信息罪,將編造傳播恐怖信息的行為納入到了刑法打擊的范圍之內。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很多故意編造傳播虛假的災情、疫情、警情的行為,同樣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對于這類行為,我國通過頒布司法解釋的方式,將其納入到刑法規制范圍內。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恐怖信息擴大解釋為包括重大災情、重大疫情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的事件,與傳統的恐怖信息概念需要包含政治性的觀點相悖,這種擴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刑法解釋的原則,并不妥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國出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作為刑法第291條之一的第二款,處在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之后,將原來不宜歸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行為分離出來另立新罪,使刑法罪名體系更加完善。
由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是一個新的罪名,在《刑法修正案(九)》出臺之后,關于本罪的司法解釋之中僅有罪名方面的解釋,關于本罪的具體適用方面尚未出臺司法解釋。然而本罪的法律規定當中存在著諸多不明確之處,使得本罪在具體適用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問題。本罪所處的位置是291條之一的第二款,而與本罪同屬一條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無論是從罪名還是法條規定看,都與本罪有極高的相似性。因此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司法解釋能夠為本罪所借鑒。但由于本罪的出臺時間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相去甚遠,而且本罪規定的虛假信息類型又有一定的獨特性,這決定了本罪的司法適用又不能完全照搬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司法解釋的規定。在本罪的法律規定中,雖然對于主觀方面的規定僅有“明知”與“故意”兩點,但是具體適用中卻問題重重。
一、本罪是否為目的犯
犯罪目的表現為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希望態度[1]。因此目的犯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不能包括間接故意。對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是否為目的犯,理論界觀點并不統一。有些學者認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屬于目的犯,其中一部分學者認為,該罪的目的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2],另一部分學者認為該罪的目的是制造社會恐慌[3]。還有一些學者認為該罪的不屬于目的犯,主觀方面是希望或者放任[4]。
筆者認為本罪不屬于目的犯。首先,我們在研究本罪參照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理論成果之時,同時必須看到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兩罪的最本質區別就在于虛假信息內容不同。由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內容是恐怖信息,這就使得該罪歸入恐怖犯罪的范疇之中,符合恐怖犯罪的特性。我們注意到,學者們對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目的的研究中,大多都是從恐怖犯罪這個角度出發進行分析的。本罪涉及的虛假信息是險情、疫情、災情、警情。這種類型的虛假信息,其性質自然與恐怖信息有很大的區別。其次,典型的目的犯的條文規定往往會出現主觀目的的限定,例如《刑法》第303條賭博罪中規定的以營利為目的。或者行為模式只能是由具備一定目的的行為構成,例如盜竊罪當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雖然屬于理論解釋,但是基于盜竊行為本身只能是具備一定目的的行為。本罪并沒有關于主觀目的的規定,而且傳播行為本身完全可以在間接故意的支配下實施。最后,如果將本罪規定為目的犯,那本罪的處罰范圍將大大限縮。本罪出現的背景是網絡上出現大量的虛假信息,嚴重擾亂網絡秩序,侵害網民的合法權益,而傳統的行政處罰以及先前刑法中的罪名不能很好打擊網絡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網絡中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其主觀目的各不相同,有些為了商業的需要,有些為了吸引眼球,有些僅僅為了圖一時之快,如果將本罪規定為目的犯,限制了主觀目的的范圍,很容易使得本罪形同虛設,也違背了立法目的。因此筆者認為本罪不屬于目的犯。
二、對本罪“明知”的理解
“明知”是我國刑法當中出現頻率比較高的概念,從總則當中的直接故意,到分則當中各條文,都可以看到對“明知”的使用。但是“明知”這個概念存在嚴重的含義不統一的現象。雖然刑法條文允許并存在大量相同術語在不同條文中含義不同的情況,但是含義不統一無論對于法律體系的規范和完善還是對于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和實踐效果,都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對于“明知”的理解,主要是從兩個維度出發。一是從“明知”的含義角度出發是否包含“應知”,二是從“明知”的程度出發是否包含可能性認識。
(一)本罪中“明知”包含“應知”
從語義學的角度來分析“明知”,“明知”是指明確知道。應當知道主要指行為人負有知道的義務,但從實然的角度出發,義務人是否確實知道在所不論。因此包含應當知道的“明知”,其含義與語義學的解釋有相悖之處。但是刑法的解釋并不全然按照語義的角度出發,而是遵循其自有的解釋體系。對于“明知”是否包含“應當知道”,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明知”是以包含應當知道為慣例,以不包含應當知道為例外的[5]。兼具理論合理性和實踐的可操作觀點是劉憲權教授采用總則分則二元法進行劃分,劉教授認為總則中的“明知”是確知,而分則中的“明知”包括了確知和應當知道[6]。
筆者贊成劉憲權教授關于總則分則二元法,作為支撐本罪“明知”包括應知的理論依據。總則中的“明知”與分則中的“明知”所論述的并不是同一個概念。“明知”屬于主觀上認識因素的范疇,根據認識對象的不同,認識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行為人對犯罪對象的認識,另一類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行為性質和行為意義的認識。總則當中的“明知”正是對危害結果、行為性質和行為意義的認識,而分則當中的“明知”是對行為對象的認識。作為構成要件主觀方面的“明知”,在結果犯中主要是對危害結果的“明知”,在行為犯中是對行為性質和意義的“明知”,并非對行為對象的“明知”。對犯罪對象的“明知”,和對危害結果的“明知”兩者之間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后者包含前者。對于行為結果的“明知”,首先要求行為人對于行為對象存在認知。因為行為人是通過對犯罪對象實施危害行為,從而造成一定的危害結果的。如果行為人對于行為對象不是“明知”的,則不可能對危害結果存在認知。
犯罪對象的“明知”包括應知,實則是一種推定的結果,即以基礎事實的應知推出推定事實的“明知”。推定并不違背刑法的基本原理。推定是根據兩個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系”,當某一事實存在時,就可以認定另外一個事實的存在[7]。而本罪當中,對于明知是虛假信息和應知是虛假信息之間,由于設定應知的義務標準就是在這種情形下,“一般理性人”都會知道自己所要傳播的信息為虛假信息[8]。本罪正是存在這種“常態聯系”,才決定了這種推定的合理性。
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明知”也應包括應知。因為確知是一種純主觀方面的內容,證據都是客觀的事物,因此證明主觀方面的確知,只能夠從客觀方面的證據進行推斷,不僅非常復雜與煩瑣,而且在很多案件中也是不可行的。如果“明知”不能包括應知,容易使很多罪犯不能得到應有的制裁。刑法理論承認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只能采取推定這樣的替代方案,對于犯罪事實進行認定。因此從司法實踐角度出發,“明知”包括應知也是無奈之選。
(二)本罪“明知”是否包括可能性認識
對于“明知”程度,主要是在是否包括可能性認識展開的,即“明知”是否包括對象可能是虛假信息的情形。對于這個問題,學界分為三種觀點:確定性認識說、可能性認識說與確定+可能性認識說。由于本罪不存在確定性認識轉化為其他罪的情況,因此僅要求可能性認識而排斥確定性認識的可能性認識說并不能適用與本罪。因此,爭議焦點就在于 “明知”是否包括對象可能是虛假信息,應當從分則中的“明知”與總則中的“明知”的關系入手。
從理論的角度出發,首先本罪的犯罪故意可以包括可能性認識,而且還包括間接故意,前面已有論述。行為人在認識到自己傳播的可能是虛假信息,并希望或者放任傳播虛假信息,并造成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后果,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皆具,完全符合犯罪故意的成立條件。因此本罪犯罪對象的認識包括可能性認識在理論上完全具有可行性。
其次,有第一次之“明知”未必即有第二次之“明知”[9]。這句話精辟地概括了分則中的“明知”與總則中的“明知”實則是一種遞進的關系。從犯罪構成看,分則中的“明知”屬于構成要件要素,總則中的“明知”屬于有責性的要素。對于認識對象來說,并不存在可能發生與必然發生的問題,只有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10]。但是對于“存在”的認知來說,也可以分為必然存在和可能存在的認知。有責性是指就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對行為人的非難[11]。有責性主要是從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分析進行的道義譴責,衡量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在行為人僅僅認識到對象存在的可能性時,仍決意實施該行為,這種情況雖然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但并未完全消除。而且這種減輕只能在一個很小的范圍之內,并不能大幅度地減輕主觀惡性的程度。主觀惡性是以犯罪人的主觀心理狀態為基礎的,心理事實與規范評價的統一[12]。意志因素是指自覺確定目的并行動以達成預定目的的心理過程。意志在人的行為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與行為人的意識活動緊密相關。決定主觀惡性的因素更主要在于意志因素而非認識因素。因此,從行為人認知的角度出發,行為人僅認識到自己轉發的可能是虛假信息之時,完全符合“明知”的要求。
再次,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角度出發,僅僅認識到自己傳播的可能是虛假信息的情形,對于社會危害性來說沒有絲毫影響。因為本罪構成犯罪要求造成擾亂社會秩序的后果或者嚴重的后果,構成犯罪是已經造成犯罪結果的情形。因此,認為僅僅認識危害結果可能性會減少社會危害性的觀點也是行不通的。既然可能性認識并不會降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那么理應納入犯罪圈之中。既然可能性認識包括在“明知”之中,那么根據“舉輕以明重”的思路,確定性認識當然包括在“明知”之中。
從現實意義角度出發。首先,本罪涉及的犯罪對象是網絡中的虛假信息,在網絡這樣紛繁復雜的平臺,存在大量不確定的因素。這就要求行為人完全地確切地了解自己所涉及的信息,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其次,從本罪的立法目的角度出發,就是出現了大量網絡中不負責任的轉發虛假信息。先前的法律體系并不能有效防止這種行為,因此就設立了本罪,將網絡傳播虛假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的行為納入到刑法規制范圍中。再次,從行為人的角度出發,如果轉發虛假信息只能由確定性認識構成,那么在構成要件中必然包含行為人對于虛假信息進行審核,確認其為虛假信息之后再進行傳播。如果行為人沒有足夠的理由確信其轉發的是虛假信息,那么行為人的轉發行為無法歸入本罪的規制范疇,這顯然不合理。且這種“確信”是純主觀層面的范疇,很難通過客觀的證據進行證明。因此從現實意義的角度出發,對于虛假信息認識的程度也應包含可能性認識。
三、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的認識程度對于本罪認定的影響
《刑法修正案(九)》對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規定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行為人對這一結果是否需要認識,需要多大程度的認識存在爭議。對于本罪犯罪結果的主觀態度,存在以下幾種情況:第一,不要求行為人對該犯罪結果存在主觀認識;第二,行為人只需要認識到該犯罪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即可;第三,行為人需要認識到該犯罪結果確實會發生。
傳統刑法理論要求構成要件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因此對于犯罪結果需要存在主觀故意才能構成犯罪。但起源于德國的客觀的超過要素理論卻打破了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出現了僅客觀要素就能成立犯罪的構成要件要素。在客觀的超過要素理論中,客觀超過要素是指,客觀要件不需要存在與之相應的主觀內容[13]。張明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列舉的例子就是刑法第129條關于丟失槍支不報罪,其中的“造成嚴重后果”屬于客觀的超過要素,即無論行為人是否希望或者放任嚴重后果的發生,只要客觀上造成了嚴重后果,都應當構成丟失槍支不報罪。
同樣作為結果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中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是否與丟失槍支不報罪中的“造成嚴重后果”同屬客觀的超過要素呢?答案是否定的。筆者認為,無論從兩者的性質出發還是從實踐角度考慮,兩罪的犯罪結果在構成要件中的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語。丟失槍支不報罪中,刑法規制的重點在于行為人違背槍支管理條例,從而不報的行為。刑法假設這種丟失槍支而不報的行為會嚴重威脅到公民的人身安全,并通過刑法規定來對這種行為作出否定的評價,即刑法設定了丟失槍支不報的行為的抽象危險。這種抽象危險基于一種常態關系,即丟失槍支一般都會嚴重威脅到公民的人身安全。犯罪構成要件說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犯罪構成的總和說明了行為社會危害性的總和。從這個意義上說,僅僅存在丟失槍支不報的抽象危險不足以納入犯罪圈,還需輔之以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才能構成犯罪。在本罪中,傳播虛假信息并不必然產生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的結果。本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表現在產生的社會秩序的擾亂這么個結果之上。因此兩罪危害結果在表現社會危害性的作用可謂是差別甚遠。在構成要件中,客觀的超過要素僅僅作為例外而存在,在我國是否主張這一理論尚存爭議,因此將核心要件作為客觀的超過要素來對待是極不妥當的。因此筆者認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不能作為客觀的超過要素,必須以主觀認識為前提。
主觀認識分為確定性認識和可能性認識,本罪對于危害結果的認識不以確定性認識為限。包括確定性認識和可能性認識,因為本罪也可以由間接故意構成,詳細理由前文已有論述,此處不再贅述。綜上所述,本罪對于結果的主觀態度是認識到自己的轉發虛假信息的行為可能會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造成嚴重后果。
[1]劉憲權.刑法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61.
[2]童偉華.論恐怖主義犯罪的界定[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2,(4).
[3]魏東.刑法各論若干前沿問題要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312.
[4]賈學勝.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之實證解讀[J].暨南學報,2010,(6).
[5]王新.我國刑法中“明知”的含義和認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分析[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1).
[6]劉憲權.中國刑法學講演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54.
[7]勞東燕.認真對待刑事推定[J].法學研究,2007,(2).
[8]孫萬懷,劉寧.刑法中的“應知”引入的濫觴及標準限定[J].法學雜志,2015,(9).
[9]鄭健才.刑法總則[M].臺北:三民書局,1985:128-129.
[10]陳興良.刑法分則規定之明知:以表現犯為解釋進路[J].法學家,2013,(3).
[11]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22.
[12]陳興良.刑法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25.
[13]張明楷.“客觀的超過要素”概念之提倡[J].法學研究,1999,(3).
[責任編輯:范禹寧]
2016-06-01
金經緯(1990-),男,安徽金寨人,2014級刑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D924.36
A
1008-7966(2016)05-00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