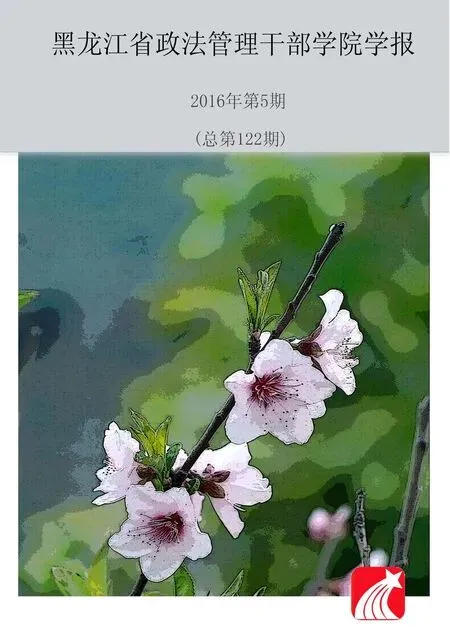論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搜集
張健一,高蘊嶙
(1.江蘇警官學院,南京 210031; 2.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檢察院,重慶 400060)
?
論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搜集
張健一1,高蘊嶙2
(1.江蘇警官學院,南京 210031; 2.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檢察院,重慶 400060)
毒品犯罪是典型的無被害人犯罪,犯罪現場有價值的線索有限,這都決定了毒品犯罪證據搜集活動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偵查的若干特點。為合理有效應對毒品犯罪證據搜集活動中的特殊矛盾,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工作應當堅持合法性、即時性和有效性的原則。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是發現客觀真實、實現程序正義的具體途徑,完成上述任務,偵查人員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辦案基本功,更需要有兢兢業業、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毒品犯罪;證據搜集;合法性;即時性;有效性
一、引言
我國《刑法》對毒品犯罪的綜合治理模式,集中體現了國家對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態度以及重拳治毒的決心。與之相對,毒品犯罪嚴厲的法定刑配置與犯罪風險的大幅度升高促使毒販們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逃避偵查、起訴、審判,諸如“體內藏毒”、“人貨分離”等新的犯罪模式應運而生也就不難理解了。于是,在偵查機關與毒販的“斗法”過程中,毒品犯罪證據就成為最大的看點:囿于無被害人、毒品交易現場證據有限、毒品因消耗而滅失等諸多客觀限制,較之于對普通刑事犯罪的偵查,偵查機關搜集毒品犯罪證據往往付出更大的努力;毒販們則盡其所能的撇清與毒品的關系,否認持有乃至販賣毒品的犯罪事實。鑒于毒品犯罪證據收集的特殊性、復雜性,本文對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收集問題展開分析。
二、毒品犯罪證據搜集的特殊性
毒品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諸多特點,正是毒品犯罪的特點催生了毒品犯罪證據收集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特殊性。
起因于其特殊的犯罪流程,毒品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特點:首先,“毒品案件沒有通常意義上的被害人,因而也沒有特定的報案人”[1]。傳統上的毒品犯罪表現為上下家之間一對一的交易,在物流運輸發達的當下,毒品買家與賣家之間甚至都可以不曾謀面而完成交易。犯罪的完成意味著買賣雙方各取所需,即便下家被上家所欺騙也不會、不敢或不能報案。毒品犯罪的線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受害人報案。毒品犯罪的線索很多可能是來源于涉毒人員(吸毒人員或者零包販毒人員)。其次,毒品犯罪分子的反偵查意識越來越強,一般很難勘查到犯罪現場[2]。在使用快遞、物流等方式實施的毒品交易中,毒品交易根本就不存在犯罪現場。即便是一對一交付毒品,犯罪分子也可以選擇人流、車流量比較大的鬧市區,交易過后雙方立即離開。犯罪現場一般不會留下有價值的證據。即便留有證據,也會因人來人往而致使證據滅失或致使證據難于提取。有些毒販在毒品犯罪的關鍵環節都佩戴手套,其指紋信息也很難被提取。再次,網絡的普及、物流的發展使得毒品犯罪開始出現了新的動向,呈現出隱蔽性高、移動性強、覆蓋范圍廣等特點,也給破獲毒品犯罪案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3]。毒販們借助網上虛擬店鋪、網絡聊天工具以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將毒品情況提供給不特定的主體,并借由郵件、物流等方式完成毒品運輸與交易。這種不曾謀面的犯罪方式極大的消解了作為偵查手段的“辨認”的作用。最后,毒品往往被迅速消費,物證難于提取。吸毒人員為避免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處罰,一般是零星購買毒品,這些毒品在短時間內會被消耗掉,使得作為關鍵物證的毒品不能被提取。
因應毒品犯罪的上述特點,毒品犯罪證據收集工作也體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第一,較之于傳統犯罪的偵查,毒品犯罪證據搜集更依賴現代科技手段。如果說控制下交付時的錄音錄像僅僅是較為普通科技手段的運用,如果說指紋對比與血清檢測等手段也因事實上或技術上的限制而在犯罪認定中作用有限,那么,根據毒品包裝上的微量證物來進行DNA鑒定的技術就不能不認為是高科技手段了。畢竟DNA鑒識甚至于可以個化至十億分之一,而全世界的人口不過如此,可以說,除了同卵雙胞胎之外,在人類族群中磨滅個人的DNA遺傳模式幾乎只屬于其個人所特有的[4]309。由于毒品犯罪分子反偵查意識越來越強,DNA鑒定較之于傳統的指紋鑒定的優勢也就愈發明顯。此外,網絡技術的運用成為治理網絡販毒的利器。
第二,抓獲經過在證明犯罪中的作用極為重要。傳統犯罪,如盜竊、搶劫,都有被害人與明確的犯罪現場,現場勘查筆錄、被害人陳述、搜查筆錄、扣押清單與抓獲說明之間可以相互印證,即便證據之間有些出入,其他證據也可以有效補強。然而,在毒品犯罪中,由于不存在傳統意義的犯罪現場與被害人,如果抓獲經過、情況說明和扣押清單等證據之間有出入,就會影響法官對相關證據證明對象的內心確信。抓獲經過在傳統犯罪中一般是作為次要證據出現的,其主要作用是輔助扣押清單、搜查筆錄,其在毒品犯罪中則是與后兩者相互印證,因此往往是主要證據。
第三,由于作為物證的毒品一旦流入吸毒者手中會在短時間內消費掉,因此,即便販毒行為具有重復、多次等特點,毒品犯罪證據收集也僅僅只能針對某一次特定的不法行為。至于之前的販毒行為,由于沒有作為關鍵證據的毒品,也就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體系。由此可見,搜集毒品販賣者之間的犯罪證據比毒品販賣者與吸食者之家的犯罪證據更易獲得較大“戰果”。
此外,許多販毒者反偵查能力及防范意識極強,在選擇毒品交易地點時相當謹慎,他們往往選擇河邊、廁所等可以隨時將毒品丟棄的地方進行交易,一旦發現非正常情況便將毒品丟棄[5]。這顯示出毒品犯罪物證搜集的即時性。第四,毒品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辯解極具迷惑性,如果無力反駁這種狡辯,毒品犯罪案件起訴時很可能是“零口供”。普通刑事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辯解往往可以通過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證據予以反駁;在毒品犯罪中,由于即便在控制下交付情況下也很難完全實現同步錄音錄像,加之毒販電話通信中也可能會有意識地避免使用“毒品”等字眼,犯罪分子對于在特定時間出現在特定地點所為何事的辯解往往無法當即予以反駁。某些看似無懈可擊的辯解往往是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線所在,如果能以無可辯駁的證據反駁其辯解,犯罪嫌疑人就很可能會不得不承認犯罪事實。
三、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的原則及其展開
如果說普通刑事案件證據搜集上的些許瑕疵還可以通過其他證據彌補,毒品犯罪中“零口供”情形的普遍存在則對證據搜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為避免因證據搜集瑕疵導致犯罪分子逃脫處罰,必須規范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搜集行為。本文認為,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工作必須始終堅持如下三項原則:
(一)即時性原則
首先,毒品犯罪的核心證據即毒品極易滅失,加之在販賣毒品案件中,沒有毒品交付就不容易認定行為人具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即便在毒品交付后第一時間抓捕犯罪嫌疑人,也面臨著毒品被犯罪分子拋離的可能性。因此,在控制下交付時,如果不能實現全程錄音錄像,必須保證即時(大致以避免毒販拋離毒品為標準)可以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雙手。倘若犯罪嫌疑人在發現被跟蹤即將被抓捕時將毒品拋離身體,偵查人員又沒能及時抓住其雙手,此時,犯罪嫌疑人如果足夠狡猾不予承認犯罪事實,并且在毒品包裝上沒有留下有價值的指紋或微量物質,偵查活動就很可能無法進行下去。
其次,在抓獲毒販的現場,要立即進行搜查,將搜查出的物品一一展示給犯罪嫌疑人,在現場見證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見證下將相關物品如手機、毒品封存,需要送檢的依法送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對當場查獲的毒品進行稱量、封存時,必須一一進行,實踐中出現過將幾包毒品可疑物一起稱量給偵查帶來阻礙的事例[6]。在兩人以上的販毒案件中,由于尚不能證明二人系共同犯罪,對于每個毒販身上搜出的毒品要分別封存、分別鑒定,不能混同。否則,極易發生毒販對販毒數量否認而阻礙案件辦理的問題。
再次,在控制下交付時,對于毒品賣家也應該在第一時間抓捕,及時提取必要的物證,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可能出現的意外。否則,如果讓毒品犯罪上家逃離了偵查視線,即便再次將其抓獲,一旦出現零口供,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通過其他證據間接證明其犯罪行為。
最后,在抓捕毒販的第一時間,應當展開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一定要抓住審訊的黃金時間,趁犯罪嫌疑人沒有時間思考并回顧自身紕漏的機會,對犯罪嫌疑人展開訊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線。尤其是在犯罪嫌疑人年紀較小,涉世未深,思慮不甚周全的情況下,其反偵查意識往往不是十分強烈。此時,在抓捕數犯罪嫌疑人后,應當抓住有利時機,對數個犯罪嫌疑人重點突破,及時形成主要的證據鏈條,縱然首要分子沒有交代,通過其他共犯人的口供也足以給接下來的偵查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合法性原則
首先,《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24條、225條規定:“執行查封、扣押的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本規定第223條規定的有關法律文書。查封、扣押的情況應當制作筆錄,由偵查人員、持有人和見證人簽名。對于無法確定持有人或者持有人拒絕簽名的,偵查人員應當在筆錄中注明。對查封、扣押的財物和文件,應當會同在場見證人和被查封、扣押財物、文件的持有人查點清楚,當場開列查封、扣押清單一式三份,寫明財物或者文件的名稱、編號、數量、特征及其來源等,由偵查人員、持有人和見證人簽名,一份交給持有人,一份交給公安機關保管人員,一份附卷備查。”因此,在抓捕毒品犯罪嫌疑人的現場,對犯罪嫌疑人隨身攜帶的物品如毒品、手機、手機卡、銀行卡依法扣押時,必須有見證人在場,見證人應當在相關文書上簽字。上述證據是證明犯罪嫌疑人資金往來、通訊往來的重要依據,一旦發生證據瑕疵則會給訴訟帶來根本性危害。在上述活動中,如果不依法納入見證人,犯罪嫌疑人可能會在庭審時突然發難,否認相關證據的合法性。此外,在搜查毒販身體時,為防止毒販反咬一口聲稱偵查人員栽贓陷害,也必須有見證人在場。
其次,毒品犯罪案件的證人證言很多源自于吸毒人員,犯罪嫌疑人供述則表現為毒販的陳述,然而,這些言詞證據穩定性差,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同案嫌疑人、吸毒人員翻供或改變證言的情況經常出現,導致偵查機關構建的整個證據鏈條中最重要的部分被打斷[7]。《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03條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記錄的同時,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前款規定的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是指應當適用的法定刑或者量刑檔次包含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是指致人重傷、死亡的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以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嚴重毒品犯罪等重大故意犯罪案件。”因此,為了穩定證據鏈條,有效反駁犯罪嫌疑人可能的翻供,應當依法對毒品犯罪案件的訊問過程尤其是第一次的訊問過程實施全程錄音錄像。一旦依法錄音錄像,即便犯罪嫌疑人翻供,也可以從被錄音錄像的供述中找到擊破其狡辯的線索。
再次,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認可了技偵措施所獲材料的證據能力,這對于有效打擊毒品犯罪意義重大,那么在毒品犯罪偵查過程中,為獲取隨時可能滅失的證據,是否可以先行使用技偵措施,事后再補辦相關手續。本文認為,既然《刑事訴訟法》第50條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加之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技偵措施需要履行嚴格的批準手續,未經許可實施的技偵措施就屬于上述被嚴令禁止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該證據不得作為定罪根據。德國法院對上述類似案件就做出了否定相關資料證據能力的裁決[4]297。
最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承認了隱匿身份實施偵查的合法性,同時規定,隱匿身份實施偵查時,“不得誘使他人犯罪”,換言之,機會提供型的誘惑偵查是可以被容許的。如果偵查人員實施犯意引誘型的誘惑偵查,獲取的證據即屬《刑事訴訟法》第50條所禁止的非法證據,不得作為定案依據。
(三)有效性原則
首先,鑒于毒品犯罪證據鏈條較為脆弱,在偵查終結撰寫起訴意見書時,應當重新系統地梳理既有的證據體系,及時發現證據體系內部可能出現的不一致現象,同時,也必須高度重視證據體系內部的某些高度一致現象,避免出現多人書寫的抓獲經過完全一致的現象。
其次,在多人實施的共同毒品犯罪案件中,如果數人之間是上下家關系,一般不會出現所有人都呈現“零口供”的現象。這時,結合共犯中的有罪供述與技偵措施所獲材料等其他證據,要讓該有罪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形成有效的證據鏈。
再次,正如上文所述,毒品犯罪的證據需要依靠現代科技手段。在“零口供”案件中,任何一項偵查工作都要保證其實效性。如果說對于法律限定了法定程序的偵查措施而言,嚴格依法執行就是保證實效性,那么對于諸如指紋鑒定等現代科技輔助性手段而言,仔細、認真、有責任心則是保證相關鑒定實效性的有力武器。在販毒案中,從毒品包裝的袋子上往往可以提取到很多人的指紋信息,在反復做鑒定后才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指紋信息,這就體現出嚴肅認真工作態度的重要性。試想,如果沒有該關鍵性證據,即便部分嫌疑人有所交代,證實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也可能費一番周折。
最后,販賣毒品犯罪“零口供”案件中,幾個下家對上家的指認非常重要,為有效證明上家不法行為的存在,必須及時固定好下家的供述。否則,高度依賴證人證言的“零口供”案件極易成為“夾生飯”。
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工作應當在堅持合法性原則的前提下,保證證據搜集的即時性和有效性。上述三個原則彼此之間關系密切,例如,堅持證據搜集合法性是保障證據有效性的重要手段,證據搜集的即時性不能以違背合法性原則為代價,證據搜集的有效性往往體現為證據搜集的即時性。
四、結語
毒品犯罪的特殊性決定了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的特殊性,而毒品犯罪案件證據搜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決定了毒品犯罪證據搜集的基本原則。毒品犯罪證據搜集活動既要保證案件實體真實被有效“投影”,也要確保案件辦理過程中的偵查措施符合法治要求,實現程序正義。合理有效地實現上述兩點,既需要偵查人員具備扎實的辦案基本功,更需要兢兢業業、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1]崔敏,王剛.毒品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及證據運用的特點[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03,(4).
[2]陳錫章,程生彥.毒品犯罪案件中證據認定問題研究[J].法學雜志,2010,(9).
[3]宋鵬.網絡背景下毒品犯罪新動向及其規制[J].河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報),2014,(1).
[4]林玨雄.刑事法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5]何祖倫.毒品犯罪證據收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從檢察機關公訴角度進行分析[J].法制與經濟,2010,(1).
[6]曾偉.毒品犯罪基本證據的審查[J].中國檢察官,2007,(11).
[7]樊學勇,陶楊.毒品犯罪偵查取證問題反思——以批捕、審查起訴和審判為視角[J].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5).
[責任編輯:王澤宇]
2016-04-24
2013年度江蘇警官學院科研項目“和諧警民關系視閾內婚內疑難不法行為的刑法回應”(13Q02);2014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重構犯罪論體系的微觀思考——以正當化情狀錯誤和不作為犯為視角”(2014SJB244);2015年度“江蘇警官學院警察法治科研創新團隊建設資助項目”(2015SJYTS01-02)的研究成果
張健一(1986-),男,山東濟寧人,法律系講師, 刑法學博士,主要從事刑法學研究;高蘊嶙(1984-),男,四川富順人,助理檢察員,刑法學碩士,主要從事刑法學研究。
D915.2
A
1008-7966(2016)05-0096-03